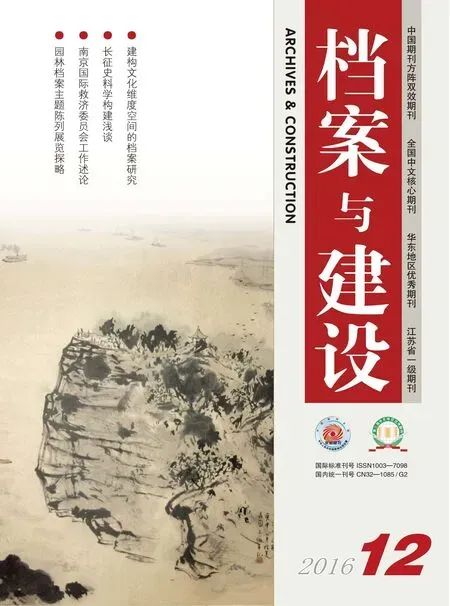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工作述論
袁志秀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江蘇南京,210017)
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工作述論
袁志秀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江蘇南京,210017)
南京大屠殺過后,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更名為“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安全區被迫解散。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延續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工作,通過糧食救濟、以工代賑、小額貸款、衛生服務與醫療救助等多種方式,為難民重返家園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南京大屠殺 難民 救濟 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 日軍
日軍攻占南京之前,留在南京的部分外國人參照上海南市難民區的成功經驗,提議在南京建立安全區,以便在最危急的時候給來不及撤離的難民提供一個避難的場所。1937年11月22日,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立,德國西門子洋行駐南京代表約翰·拉貝任主席。本著人道主義精神,委員會在南京城內發起設立一個旨在保護和救濟戰爭難民的中立區——安全區。安全區以美國駐華大使館所在地和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金陵神學院、金陵中學、鼓樓醫院等教會機構為中心,占地約3.86平方公里,界內分設交通部大廈、華僑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學等25處難民收容所。12月8日,委員會發布《告南京市民書》,安全區正式向難民開放。南京大屠殺期間,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開放難民收容所,記錄和抗議日軍暴行,施粥和救助南京難民,共保護了20多萬的難民免遭日軍殺戮。
1938年2月18日,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更名為“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安全區被迫解散。在遭日軍屠殺、強奸、劫掠、焚燒破壞后的南京城,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通過糧食救濟、以工代賑、小額貸款、衛生服務與醫療救助等多種方式,為難民重返家園提供了一定的保障。[1]
一、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更名為“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
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前身是成立于1937年11月22日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1938年1月初,由于日軍在南京的暴行引起世界輿論的譴責,東京方面給南京日軍當局發來嚴厲指示,命令南京的秩序要無條件地恢復,一切行政工作均應由“自治委員會”而非由國際委員會承擔。[2]南京日本大使館的參贊福田告知拉貝這一信息后,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在回復福田的信函中聲明:國際委員會將樂意看到地方自治委員會盡快承擔起地方民政機關應承擔的一切職責……您可以相信,國際委員會絕對不想繼續履行平時屬于地方主管部門的任何一種行政義務,也不想為自己要求這樣的義務。[3]與此同時,拉貝開始考慮為消除日軍誤解而更改委員會的名稱。1月12日,拉貝在日記中寫道:“為了同日本人友好相處,我想出了一個計劃。我想解散安全區委員會,成立一個國際救濟委員會,在這個委員會里也有日本代表。我是否會成功,還要等著看,這個建議首先必須同安全區委員會成員和3個大使館的官員們討論”。[4]這是拉貝在日軍的威脅下,為了南京難民的生活考慮而第一次產生關于更改委員會名稱的想法。
起初,這個想法并沒有得到委員會其他成員的贊同。委員們認為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事實上得到了日本人的承認,他們擔心一旦改名會自動解散原有的委員會,日本人可能會對委員會完全不予理睬。但是隨著形勢的變化,更名問題再次被提到了委員會的議事日程。2月5日,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舉行理事會會議,討論關于是否要將現用名改為“南京救濟委員會”。[5]2月17日《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關于形勢的內部報告》專門就更改名稱一事做了較為詳細的敘述,提到國際委員會早已考慮更改其名稱,為此選擇一個新的名稱,以更好地表達該委員會存在的理由。關于更名事宜,日本當局也表示了同意。[6]
2月18日,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召開理事會會議,拉貝、貝德士、米爾斯、特里默、馬吉、施佩林、斯邁思出席了會議,會議決定“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即日起以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名稱繼續工作”,并委托斯邁思博士將更名事宜通知給各國駐華大使館以及上海有關救援組織。米爾斯被選為救濟委員會的副主席,斯邁思被任命為財務副主任。[7]拉貝將更名事宜通知了美國大使館、德國大使館與英國大使館,說明“該名稱更符合委員會的工作性質,便于委員會繼續開展自己的工作”。[8]至此,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正式更名為“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2月19日,拉貝致信上海南京救濟委員會、自治委員會以及德國駐華大使館羅森博士,說明2月18日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決定即日起以“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名義運行。[9]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辦公地點起初在寧海路5號,后于1938年6月1日搬遷到天津路4號。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改名之后成為一個純粹的救濟委員會,但是其工作的內容和性質與更名之前沒有多少改變。對于國際救濟委員會的職能和工作任務,拉貝曾經說過:“我們是一個如同在其他許多國家常見的純民間組織,除了努力幫助本城受苦受難的貧苦居民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目的或目標”。“請你們注意‘純粹’二字,就是說什么也不多,但是什么也都不少”。[10]1938年2月23日,拉貝離開南京。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工作仍在繼續,一直持續到1941年。

職員(1938年6月至1939年4月)

成員(1938年6月至1939年4月)
二、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人員組成
從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立到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工作全部結束,有一些西方人士離開,也吸收新的委員加入,人員處于一個動態變化之中。
由于拉貝要離開南京,1938年2月18日的委員會會議選舉米爾斯為副主席,斯邁思博士繼續擔任秘書并增加了一個新的職務——財務副主任。1938年2月23日拉貝離開南京后,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主席先后由米爾斯和貝德士代理。米爾斯1939年5月離開南京回美國度假,貝德士則接替了他的工作直至1941年4月離開南京。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工作人員,論國籍有德、美、英、中、日、丹,論宗教則有耶穌教、天主教、回教、佛教,但是都能共同合作,在工作中沒有因國籍、種族與宗教之不同而發生障礙。[11]由于不時有人員離開,委員會職員和成員處于一個動態變化中,這從1938年6月至1939年4月的人員變化及任職時間中得到反映[12]。

三、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主要工作
南京大屠殺過后,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與南京萬國紅十字會、國際紅卍字會、南京中國紅十字會、鼓樓醫院、教會學校及教堂等合作,投入了繁忙的難民收容和救濟安置等工作中。對于救濟委員會中的秩序恢復委員會來說,1938年3月是一個忙碌的月份,救濟委員會總部及4個支部全面運轉。僅僅在2月7日至5月31日,秩序恢復委員會為17536戶家庭涉及84403人提供了幫助。[13]1939年5月后,由于經濟形勢的極度惡化,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救濟活動僅僅限于以發放谷物和面粉的形式提供事務方面的援助。到了1940年8月1日至1941年4月30日之間,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工作只能在繼續壓縮項目的憂慮中展開。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在艱難中開展的難民收容和救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為難民重返家園提供了保障,給南京難民在黑暗中帶來生的希望。
(一)記錄和揭露日軍暴行
難民區解散后,日軍的暴行并沒有減少,南京的秩序再次成為一個問題。因此記錄和揭露日軍暴行的工作并沒有停止,并成為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成員們的重要工作之一。
搶劫和強奸事件接連不斷,在委員會成員的眼皮底下就發生了多起。1938年2月19日下午,在一個隸屬的難民營里,一名年輕的女孩遭到了強奸。[14]3月11日,一個婦女在隔壁的一個小棚屋里遭到兩名士兵強奸。3月19日,在金陵大學語言學院難民營,一個日本士兵強奸了一個難民——一個19歲的姑娘。[15]魏特琳在1938年5月13日《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營報告》中提到:“如果此類事件在城市的許多地方正在發生,那么我們關閉難民營把數千名女性送回家會讓事態更惡劣?……我知道如果我有個年輕的女兒,我死也不讓她去城南或城東生活。”[16]
屠殺和搶劫并沒有停止。1938年3月1日,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在提交的目前形勢概述中記敘道:“2月28日上午,一個姓方的婦女(她一直住在軍校)和她的家人一起在珠江路。一個日本兵告訴她閃開,并用刺刀從她背部扎了進去。刺刀完全穿透背部并從前面露了出來。她在被送到醫院后大約5分鐘死去。”[17]1938年3月11日,門西五福路角落18號的蔡龐興本人遭受日兵射殺、妻子蔡李氏被刺、家庭財物被搶,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派調查員調查后向米爾斯反映,米爾斯說:“情況好多了。但是仍然比較混亂。……這個事件是我們兩個調查人員一天工作的一項內容。我按照他們的敘說,不加修飾地記下這起事件。這起事件中的哀婉與傷感直擊內心深處。”[18]
(二)南京地區戰爭損失調查
為了更好地開展賑濟工作,1938年2月中旬,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委托原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秘書、金陵大學美籍社會學教授斯邁思及其助手20余人,對南京市區、郊縣民眾在日軍暴行中人口傷亡與財產損失情況進行調查統計。調查工作從1938年3月上旬起至6月中旬止,歷時三月有余。斯邁思根據調查情況撰寫南京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城區、郊區人民在日軍暴行中損失情況的調查報告《南京地區戰爭災禍(1937年12月—1938年3月)》,該報告為后面的救濟工作提供了依據,更是關于南京地區戰爭損失狀況最早也是比較全面的一份調查報告。
(三)收容和救濟工作
1938年2月18日,安全區解散,但是難民收容所并沒有立即終結,而是采取了逐漸關閉的方式,直至1938年5月31日,難民收容所正式關閉。在這期間,當其中一家收容所關閉,就將其中的難民轉移至另外一個收容所,不至于使無家可歸的難民因為難民所的關閉而流落街頭,甚至招致日軍的屠殺等暴行傷害。截至1938年5月,25處難民收容所關閉了19處,還剩下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金陵神學院、金陵女子神學院、金陵中學和大方巷15號的六個收容所[19]。難民收容所難民人數從2月至收容所徹底關閉,處于動態變化之中,只能根據難民收容所接受救濟糧食的難民人數,估算出收容所的難民人數:二月份為36800人,三月份22處難民收容所的難民總數為26700人,四月份16處難民收容所難民總數為21750人,五月份7處難民收容所難民共計為12150人。[20]此外,除了難民區的難民外,還有數萬難民由國際救濟委員會協助居住在私人房屋里。
“無論是回到自己家里去的或是仍住在安全區內的那些人,人人都面臨著一個共同的困難,就是吃飯問題……”[21]因而,食物問題是委員會一直擔心的。1939年5月1日至1940年7月31日,委員會為16170個家庭發放了食品。1940年8月1日至1941年4月31日,委員會在資金許可的范圍內盡量救助那些有幾個年幼子女的家庭,救助名單壓縮到1.1萬個家庭。最后接受食品救濟的家庭總數為11724個,總計36763人。在這一階段,共發放了8188擔小麥、碾碎的小麥、玉米和不同等級的面粉,共為1965個家庭發放了2688件棉衣。[22]
除了糧食救濟之外,委員會還采取了現金救濟、小額貸款和以工代賑的方式對各種難民進行分類救濟。如1938年5月至1939年春,共發放救濟金10671元,平均每戶3.29元。小額貸款主要是資助扶持一些手工業小作坊。全部貸款中之3/4用在衣服與鞋之制作、紡織以及食物之制作業上,家具與器皿、印刷、金工、理發及竹草工作之救助占數較少。申請貸款的難民中,85%是重操舊業者。國際救濟委員會共放出個人貸款147宗,每宗平均42元,總額為7675元。[23]
以工代賑是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另一種救濟方式。如在1938年5月至1939年春天的工賑主要是在冬季被服的供給中,由難民參與棉花的彈制,衣服的裁剪、縫制及翻棉等。此外還有溝渠、道路填平,農場工作,修路,衛生工作,記錄繕寫等工作。各種工作共付工資15500元,相當于600人一個月的工作。[24]除此之外,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還在積極考慮為郊區提供春耕種子,以便盡快恢復農業生產。1938年4月13日,副主席米爾斯向日本大使館花輪義敬總領事寫信,指出水稻種子短缺最嚴重的地區是江寧和句容沿線,總共需要的且無法購買的水稻種子是23600石。提出如果軍隊能立即采取措施使種子和食物供應成為可能,會有很大援助作用,同時指出種子問題尤為緊迫。[25]
除上述救助之外,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還為離開南京的難民提供現金救濟。難民的通信、私人匯款,也多由救濟委員會中工作人員咨詢與協助。比較大的捐贈有兩次,一次是捐贈金陵女子文理學院1600元,使該院600名左右的女難民能繼續收容至夏季,另一次是有5名盲女孤立無助,遺留在收容所里,救濟委員會決定付款500元作為一部分資助,送其到盲人學校里等等。[26]
(四)難民的衛生服務和醫療救助
南京大屠殺期間,對于大多數平民來說,唯一可以提供醫療服務的是鼓樓醫院,在緊急時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除了緊急補充的160張床位及醫院的所有常規診所,在紅十字會的幫助下,醫院又成立了三個外出診所。南京大屠殺之后,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與鼓樓醫院約定,將貧病者移送該院,有時由委員會捐助現金,供醫藥服務之需要,或由委員會代為支付病人的醫藥費。
鼓樓醫院醫生布萊迪從返回南京的第一天開始,就為3萬難民接種天花疫苗,并安排難民營診所工作。[27]在1938年春收容所的防疫運動中,種痘者共為16256人,注射傷寒霍亂預防針者共在12000人以上。此外,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獲得了大宗魚肝油,以供鼓樓醫院之用,并煞費苦心將大量魚肝油分發給收容所兒童。自1938年3月起,國際救濟委員會還購買了奶粉,給醫院的難民嬰兒吃,并將其中若干分發給收容所中數十名嬰兒。委員會在醫療救助上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雖然難民中腳氣病、痧子、猩紅熱等患者較多,但是死亡者尚少,難民間沒有嚴重病癥的流行。
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在南京的工作,得到了國民政府的感謝和南京人民的銘記。1938年4月22日,國民政府外交部向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表示感謝,感謝委員會的全體成員發揚了正義的精神,盡最大努力保護了南京難民。[28]并給貝德士、斯邁思、里格斯等人授勛,但由于當時特殊的戰爭環境,授勛并沒有公開。1939年1月23日美國駐華大使館函告貝德士:“1938年6月30日中國國民政府秘密訓令,授予您襟綬景星勛章。此項勛章現已送至使館,希盡早來館出席授勛招待會。您當可同意,此事不宜為外界廣泛知曉”。[29]1941年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致信給貝德士,以表彰其在救濟和安置難民上所做的重要工作:“您的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同事熱切地向您致以誠摯的謝意,感謝您……積極參加本委員會的后期工作。在擔任本委員會主席的兩年時間里,您更是不遺余力地工作。我們懷念您的諄諄教誨,傾慕您的卓越能力。您將激勵我們向前。我們代表本委員會由衷地向您贈與‘名揚南京’的美譽。你是南京人民過去4年里最忠誠的朋友,您給予了他們最真實最無私的服務和幫助。”[30]
[1]袁志秀:《南京大屠殺之后的難民安置與救濟工作》,《日本侵華史研究》2015年第4期。
[2][3][4][5][6][7][8][9][10][21][德]約翰·拉貝:《拉貝日記》,江蘇人民出版社、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第369、370、397、587、677、678、674、674、684、580頁。
[11][12][19][20][23][24][26][28]張生等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12:英美文書·安全區文書·自治委員會文書》,江蘇人民出版社、鳳凰出版社,2006年1月,416、422-425、397、395、404、402、406-407、138頁。
[13][14][15][16][17][18][22][25][27][30]張生等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70:耶魯文獻(下)》,江蘇人民出版社、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10年12月,第577、545、548、570、529、543、618、568、517、236頁。
[29]章開沅:《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第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