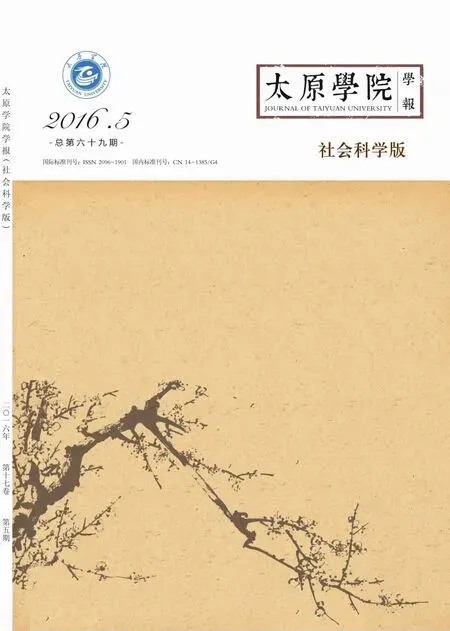“互聯網+”時代故宮的信息傳播研究
鄭 丹
(三亞學院 傳媒與文化產業學院,海南 三亞 572022)
?
“互聯網+”時代故宮的信息傳播研究
鄭 丹
(三亞學院 傳媒與文化產業學院,海南 三亞 572022)
“互聯網+”時代,博物館肩負著向社會大眾宣傳博物館的歷史和文化,保護、弘揚歷史文明的社會使命。面對信息傳播環境的變化,故宮博物院借助互聯網媒介和各類新興數字技術手段,面向社會大眾開展了全新的博物館教育,讓傳統嚴肅的博物館文化變得更為親民。微信、微博、APP甚至VR虛擬現實技術都成為了故宮博物館傳遞信息的輔助手段和延伸表達,在此基礎上,故宮博物院靈活運用互聯網思維開展故宮電子商務和文創產品設計,為重新認識博物館信息傳播方式提供了新的參考與啟示。
“互聯網+”;故宮;信息傳播;新媒體
自“互聯網+”在十二屆人大三次會議首次提出后,數字技術不斷深入到社會生活的衣食住行等方面,信息傳播逐漸變為以碎片化閱讀、可視化閱讀和快速閱讀為主的方式,博物館的信息傳播在互聯網信息爆炸的干擾下逐漸變得尷尬。博物館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宣傳傳統文化成就的重要窗口。“互聯網+”時代,博物館肩負著向社會大眾宣傳博物館的歷史和文化,保護、弘揚歷史文明的社會使命。面對傳播環境的變化,博物館需要在傳統文化的傳承發揚與網絡時代的互聯網傳播特點中尋找平衡,找到適合博物館信息傳播的創新方式。以往博物館在文化傳播方面是以單向傳播為主要方式,被動接受公眾的參觀需求進而提供信息,缺乏與受眾之間的互動交流,公眾的個人喜好也難以更好滿足。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和數字技術的發展,博物館在數字化傳播的道路上也可以變得不再嚴肅“高冷”,具有了趣味性和互動性。“互聯網+”時代,作為國內目前最大規模的古代文化藝術博物館,故宮博物院除了文物的收藏、整理、記錄、研究之外,借助互聯網媒介和數字技術的手段,面向社會大眾進行教育、傳播,增加了信息傳播的維度。微信、微博、APP甚至VR虛擬現實技術都成為了故宮博物館展覽的輔助手段和延伸表達。
一、故宮博物院定義為“媒介”的思考
我們生活在一個訊息空前繁榮的時代,自媒體、網絡等新興事物發展迅猛,傳統的電視、報紙媒介仍然活躍。故宮博物院有著與大眾媒介完全不同的面孔,但卻在傳播方式上與大眾傳播有著相似之處。大眾傳播可以用三項特征來確定:
1.它針對較大數量的、異質的和匿名的受眾。
2.消息是公開傳播的,在時間安排上通常可以同時到達大多數受眾,在特征上是稍縱即逝的。
3.傳播者一般是某個復合組織,或者在某個復雜的組織之下運作,這通常需要龐大的開支。[1]4
故宮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是目前中國最大的古代文化藝術博物館,主要收藏明清兩個朝代的文物。故宮博物院的觀眾近年來一直在持續增長。2002年故宮觀眾第一次突破了700萬,成為當時世界上觀眾人數第二多的博物館,僅次于盧浮宮。但是僅僅過了十年,到2012年,故宮的觀眾突破了1500萬,達到1534萬,相當于天津市總人口數量。
故宮博物院目前一共有180萬件套藏品,其中珍貴文物占93.2%、一般文物占6.4%、資料只占0.4%[2]。故宮博物院的藏品不僅是對歷史文化遺產的繼承,還借助故宮博物院研究院對藏品進行研究和開發,對這些具有科學、歷史和藝術價值的藏品和展品進行信息的發掘,并向廣大參觀者開放,承擔教育、宣揚館藏文化的意義。故宮博物院對于文物的展覽和介紹不僅涉及到相關的歷史背景、發掘過程,還有專家的解釋。無論是常態化的參觀或者是特定主題的展覽,都需要經過漫長、復雜的準備工作才能向公眾開放,需要專業化的團隊在背后運作。
以此來看,故宮博物院同樣具備大眾傳播的功能屬性。與其他大眾傳播媒介不同的地方在于,故宮博物院承擔社會公益的色彩更為濃厚,信息價值的界定也有比較明顯的區別。另一方面,電視、網絡等大眾傳播媒介傳遞的訊息多注重時效性,信息傳播的時間有限,往往過了時間就失去了傳播價值。而故宮博物院所傳遞的訊息卻與之相反,隨著對館藏文物的研究深入和挖掘,這些信息并不會因為時間流逝而失去意義,館藏的文化信息經過時間的沉淀反而歷久彌新,更能凸顯信息的價值。
二、故宮博物院作為媒介的信息傳播特征
1949年香農和韋弗(Shannon and Weaver)在《傳播的數學理論》中提出了信號傳輸的模式圖,這一數學模式將傳播過程描述為一種直線型的單項過程。在這個模式中,信息由信源發出,以信號方式從發射器傳遞到接收器,進而還原成訊息抵達信宿。信源從一組消息中挑選一條進行傳播。這條消息可以由口語、文字、音樂、圖像等組成。發射器將消息轉變為信號以適合傳播渠道使用。渠道是將信號從發射器傳送到接收器的中介。接收器所做的是與發射器相反的工作,將信號重新恢復成信息。信宿是消息想要傳達到的人或物。
故宮博物館作為信息傳遞的起點——信源,從所有可能傳遞的訊息中選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內容,借助照片、文字、音樂、圖像、光線等各種形式,向前來參觀的人們傳遞文物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價值。在展覽過程中,從信源出發的信號通過感官的接觸得到傳送,到達受眾。受眾的理解程度取決于自身的文化積累和興趣,對信息內容的接收和理解也存在差異。正像香農和韋弗描述的那樣,傳播模式中的噪音增加了傳播過程的不確定性。對專業術語的不解、導游的解說、參觀時間的長短以及周圍環境的聲音都可以成為來自渠道以外的干擾因素。參觀過程的單向傳播缺乏受眾與故宮博物館之間的互動性,對傳播效果產生不利影響。
在現今社會,受眾的需求已經從以往的被動性選擇接收變為主動性選擇獲取,在信息獲取過程中更注重個性化和生活化,講究信息理解的快捷新穎。信息的傳播從以往的媒介為中心轉變為基于社交群體的傳播,借助社交媒體的轉發、關注和評論,信息傳播以幾何式增長。故宮博物院作為傳統文化的傳播者,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改善信息傳播模式的缺陷,增強信息傳播效果,在國內眾多博物館中率先邁出了觸電“互聯網+”的步伐,將以往單向的大眾傳播模式與人類傳播模式相結合,在信息到達信宿(觀眾)之后形成二次傳播渠道,并增加了信源(故宮博物院)與信宿之間的互動,減少傳播過程的噪音。
新媒體技術的發展擴展了故宮博物院的傳播方式和手段,也改變了故宮博物院以往的信息傳播模式。故宮博物院目前開設了微博、微信公眾號、電子商務、APP等各類傳播平臺,在展覽過程中也借助數字技術不斷創新故宮的展現方式。故宮博物院的信息傳播突破了參觀地點的地域空間因素,在文字、圖片和聲音之外增加了體驗元素,與參觀受眾的互動也擴展了時間上的有效性。
三、故宮博物院的信息傳播方式創新
(一)傳播渠道上融合數字技術開發
出于對建筑物和收藏品的保護和管理,故宮在展示方面不得不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保護故宮的文化資產,同時還需提高故宮文物和古建筑面向大眾展示的水平,數字技術的出現有效解決了珍貴藏品的展示和保護相矛盾的問題。早在2003年通過VR技術展示清朝宮廷內景時,中日合作的故宮文化資產數字化應用研究所正式成立,并建立了網上故宮文物的三維數據庫。當時故宮展出了《紫禁城·天子的宮殿》,通過高清晰VR(虛擬現實)技術展示了1889年光緒大婚的情景,還有近期推出的“故宮三希堂VR”360度虛擬漫游,都增加了游客的體驗感。
不僅如此,故宮博物館突破了展覽的地域限制,通過數字藝術增加了藝術展覽的體驗方式。故宮于2016年6月文化遺產日在廈門鼓浪嶼推出了“《韓熙載夜宴圖》數字藝術展”,結合非物質文化遺產“南音”樂舞演繹、故宮專家講座與數字交互體驗等展示方式,讓故宮經典書畫“走出紫禁城”,既解決了珍貴文物的保護問題,又以新穎別致的面孔與受眾近距離接觸,增加了信息傳播的渠道和受眾體驗方式。
不僅如此,故宮博物院也是目前國內博物館對于APP開發最為熱衷的機構。從2013年起至今,故宮先后推出六項免費APP供大眾下載使用,借助新媒體技術展現了不一樣的人文風景(如表1)。
與其他博物館不同,《胤禛美人圖》是故宮博物院首次嘗試開發制作的App應用,而不是推出一個“大而全”的導覽功能App。在APP內容選取上,選擇以近年來影視作品中較多出現的清朝雍正帝為主要對象,雖然影視劇作品中虛構成分較多,但因為《甄嬛傳》、《步步驚心》、《宮鎖心玉》等電視劇的熱播,雍正的妃嬪在觀眾中均有一定的知名度。《胤禛美人圖》APP以雍正帝的“十二美人”繪畫藏品為為基礎,串聯起清宮廷家具、陶瓷、宮廷生活、書畫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對繪畫本身的構圖、技法進行分析,將清朝美人以類似GIF圖的形式放諸眼前,拆解成12幅表現皇家生活的主題畫,如“消夏賞蝶”、“觀書沉吟”等。
不僅如此,美人身處的環境暗藏玄機,指尖輕觸,諸多家具、擺設、掛畫、文玩等,都能被逐一點開,讓人一探究竟。不僅在內容上能夠吸引受眾的好奇心和觀賞興趣,在形式上也具有靈動新穎的特點。

表1 故宮APP內容概述
故宮博物院的APP應用在后期開發上改善了前期只能應用于蘋果IPAD系統的不足,覆蓋面更為廣泛。在內容題材的挖掘上,注重受眾心理的好奇因素,對某一領域知識內容結合游戲方式進行展現,同時具備娛樂性和實用性。
(二)互動形式全方位展開,粉絲用戶粘度高
故宮目前在新浪微博和微信公眾號平臺上同樣都開設了兩個賬戶,分別是故宮博物院和故宮淘寶。故宮博物院新浪微博是其官方微博,粉絲數量目前已達到207萬,主要負責發布故宮近期展覽、藏品、文章和故宮圖片等訊息,內容上偏向正統嚴肅。截至2016年6月,官博內轉發量最高的文章為故宮在國際博物館日發布的《牡丹亭——游園驚夢》短視頻,展現昆曲在紫禁城內的畫面,共有五千多位網友轉發,一萬多網友點贊,七百多條評論。
故宮淘寶屬于北京故宮文化服務中心,目前新浪微博粉絲數量達57萬。故宮淘寶主要是為故宮文創用品的電子商務服務,相比于官博龐大的粉絲數量,故宮淘寶優勢在于與粉絲的互動較多。僅故宮淘寶一篇介紹自己的九宮格圖片微博就有三萬粉絲轉發,七千多網友進行評論。故宮淘寶2015年11月發布了一條“愛是一道光!”的微博,用清朝道光帝畫像作為底稿,將圖片中道光皇帝的手指指尖上加上了一道白光,在黑色的背景色上尤為明顯,該微博獲得了二萬多的轉發量,共有接近五千多位網友評論,一萬多網友點贊。
不僅與自家粉絲擅長互動,故宮淘寶還擅長多向互動,在社交媒體話題制造上也別出心裁。2015年12月,故宮淘寶官微與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官微積極互動,兩家互相攀比,炫耀各自館藏“萌文物”。11月27日,三星堆博物館官微曬出呆萌的“東漢陶狗”,被故宮調侃不如自家的陶狗可愛。緊接著,三星堆博物館曬出“南宋龍泉窯青瓷長頸瓶”,稱“應該是燒制的時候出了問題,這個長頸瓶彎了一點,莫名有一絲淘氣的感覺。”故宮的回應是“歡迎大家來我宮看瓷器!我宮瓷器不彎,都是直的。”兩家博物館的“攀比”和調侃引發了網友的圍觀,在話題關注上贏得了更多的討論和關注。
故宮博物院與故宮淘寶針對不同的網絡用戶群體開展互動,無論是正統的博物館信息發布還是輕松幽默的互動形式,都能彌補一方的不足,從而形成聯動效應,更好地推動故宮與受眾之間的互動交流。
(三)社交媒體軟文推廣新穎,不失教育性
在故宮的軟文推廣上,故宮淘寶做得較為出色。正如上文提到,無論是微博還是微信,故宮淘寶發布的文章和圖片總能獲得較高的關注度和點擊率。2015年3月,故宮淘寶微博發布了一篇文章《朕有個好爸爸》,獲得了二十多萬的閱讀量和八千多的轉發量。長微博頁面置頂圖片為不茍言笑的雍正爺雙手捧著腮幫微笑。文章以四爺胤禛的口吻講述了康熙帝如何教育子女的故事。文章的撰寫沒有正面說教的嚴肅,反而加入了網絡上流行的表情包圖片,和故宮館藏書畫相配合,講述康熙帝如何教育子女的故事。在講述康熙帝對皇子的文化教育時,文章以一張胤禛讀書畫像和三張康熙帝讀書寫字畫像來論證皇家文化教育的重要性。為了論證康熙帝的教育對子女的影響,文章從康熙與胤禛的相關書法、繪畫作品以及文獻中節選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內容來印證胤禛在很多方面都有意識地效仿康熙帝的做法,無論是書法、執政理念還是著書,胤禛的相關作品中都有類似的模仿。例如康熙帝注重農耕,康熙年間曾編了一本《耕織圖》,胤禛以此為藍本同樣繪制了一套圖,但是把原畫中的農夫和農婦替換成了自己和福晉的形象,讓清朝的珍藏繪畫也具有了現代的圖片修飾技術,趣味性躍然紙上。文章最后才點明寫作主旨,竟是為了推廣故宮的文創產品胤禛耕織圖記事本和十二美人圖記事本。整篇文章講述過程中,網絡流行的搞笑表情包始終穿插其中,減淡了文章的嚴肅性。同時,在故宮館藏圖畫和文獻的基礎上抽絲剝繭,挖掘了歷史中的小故事,讓觀眾在看圖過程中不知不覺增加了對于書畫創作歷史背景和畫面內容的理解,增強了故宮館藏文化的趣味性。
繼《朕有個好爸爸》試水大獲好評后,10月故宮淘寶微信公眾號發布文章《夠了!朕想靜靜》,以極具幽默調侃的語氣介紹了“一個悲傷逆流成河的運氣不太好的皇帝的故事”,即明朝崇禎皇帝朱由檢的生平。在為崇禎帝作自我介紹時,故宮淘寶別出心裁地為崇禎帝制作了一張頗具現代感的身份證,上面標注了崇禎帝的姓名、名族、出生日期以及公民身份號碼。有趣的是,在身份證住址一欄中,圖片上顯示的內容是“北京紫禁城想住哪就住哪”。文章仍然使用了大量的微博表情包,從歷史文獻中挑選有價值的信息,以趣味的圖片和文字講述崇禎帝從登基到自縊的人生故事。從崇禎帝不同尋常的人生經歷出發講述了這個亡國皇帝背后的辛酸,用調侃的語氣點評崇禎帝在位期間的執政經歷,最后給出結論是崇禎帝的運氣不太好,借此推銷故宮淘寶的文創產品故宮福筒。
故宮在軟文推廣上注重歷史真實性與趣味性相結合,借助社交媒體平臺上常見元素表情包和調侃方式,輕輕松松將一個真實的歷史故事講得通俗易懂,同時還推廣了相關文獻藏品的信息,讓受眾在接收信息過程中能更好理解枯燥的歷史,形式新穎有趣。
(四)特色文化創意產品兼具文化價值和趣味性
文化創意產品同樣是故宮信息傳播的外化表現。文化創意產品最根本的特征是產品的文化價值和審美價值,除卻功能上的實用性之外,文化象征的意義更為濃厚。消費者之所以購買故宮文化創意產品,主要是對于故宮文創產品蘊含的文化象征意義和產品的藝術設計感興趣,同時也看中了故宮文創產品的趣味性。故宮目前已有七千多種文創產品,僅2015年上半年文創產品銷售額就已突破7億元。故宮文創產品具有極強的歷史價值和實用價值,同時還具有趣味性和話題性。比如雍正御批系列折扇上面的文字均取材于雍正御批奏折資料。扇面一面為有特色的雍正御筆批語,包括:朕亦甚想你、朕心寒之極、朕即福人矣、朕生平不負人四種。另一面為臣子年羹堯上奏折縮寫。折扇的扇面文字取材自真實的人物筆跡,具有歷史紀念意義,行文上又有網絡用語輕松幽默的內容,產品具有較強的實用價值。
再比如說功能上極具現代感的皇帝親親之寶手機座,同樣源自故宮博物院藏品“皇帝親親之寶”寶璽。乾隆皇帝將御寶總數定位二十五方,并詳細規定了各自的使用范圍,其中皇帝親親之寶一方為白玉質,交龍紐。據《交泰殿寶譜》記載,該寶璽作“以展宗盟”之用,為皇帝親密親王之印,向親王頒旨時用。如此莊重的寶璽卻被設計成了手機座,用戶使用過程中也能體驗別樣的感受。目前手機座設計上采用了皇帝、格格和御前侍衛三種人物版本,曾經還推出過皇子面壁版本。還有故宮創意行李牌,可以作為公交卡套使用,靈感源自古代官吏系在腰間的腰牌,借用腰牌出入門禁、過關的寓意,故宮創意行李牌設計了“如朕親臨”“奉旨旅行”“錦衣衛”“六百里加急”“肅靜”“回避”“微服私訪”等多種款式,在外觀上“微服私訪”與古代腰牌外形最為接近,但在故宮淘寶銷售上“如朕親臨”“奉旨旅行”兩款更受歡迎。
不僅如此,故宮淘寶文創產品在開發新功能的同時也契合了受眾的使用心理。近年來清朝宮廷劇成為電視劇主要題材,以此而為人們所熟知的影視形象也成為了故宮文創產品的創意來源。比如容嬤嬤針線盒,就是基于熱播劇《還珠格格》中容嬤嬤給紫薇扎針的電視畫面創作,將原本苦情的畫面變成現實生活中具有使用價值的針線盒。其他小商品還包括皇帝大婚膠帶、龍鳳香囊鑰匙扣、皇帝狩獵盆栽、康熙賜福筆筒等等,每一款商品都有著濃濃的故宮特色,價格也很親民,能滿足與眾不同的心理訴求。
四、對“互聯網+”時代博物館信息傳播的啟示
故宮博物院一方面對收藏的明清珍貴文物保護、修繕,圍繞這些文物展開的文獻研究中蘊含著歷史學、考古學、文學等多方面因素。另一方面,故宮博物院公共文化傳播的使命促使故宮有責任向社會大眾普及館藏文化,傳承歷史文明,而由此傳遞的訊息卻由于館藏書畫、文獻、文物深奧的文化內核讓普通大眾望而卻步,部分珍貴文物出于保護的考慮也難以向社會大眾展示。在訊息傳遞渠道上,故宮博物院通過VR技術、APP應用和數字技術實現了博物館傳播渠道的擴展,增加了受眾接收訊息的方式,全方位的感官體驗也比單一的參觀體驗有所增強。故宮博物院館藏文化的信息本身具有古文著書的嚴肅性,文字的撰寫無一不是字斟句酌,但這樣的古典文字對于現在習慣了快速閱讀、碎片化閱讀和可視化閱讀的普通大眾來說,存在信息傳播的溝通障礙。故宮淘寶結合網絡文化對歷史資料重新梳理,提煉出有趣實用的故事元素進行重新組合,能讓受眾接收訊息時更容易理解,同時也為受眾進一步了解館藏文物提供了切入點。
另外,針對博物館受眾參觀興趣的調查表明,大多數人參觀博物館事先都沒有明確的參觀目的,說明用戶參觀前并不了解要參觀的展品, 針對性不強[4]。故宮博物院館藏文物之多,展館面積之廣非一般博物館所及,受眾在參觀之前難以找到適合自己的參觀路線,借助故宮已有的數字傳播渠道,用戶在對故宮博物院有了基本了解后再去有意識地參觀,用戶需求可以得到更好的實現,從而為用戶提供個性化的信息服務。
目前許多國內外博物館也開始探索和研制移動終端上的應用項目,網上博物館和數字博物館都在應觀眾需求而不斷發展變化,“智慧博物館”和“新媒體”等概念成為了近年來博物館發展的焦點。“互聯網+”時代,博物館對于新媒體技術應該不僅僅只是在信息導覽和簡介上,應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故宮博物院的傳播方式可以視為一面鏡子,為其他博物館應用數字技術提供發展方向和思考。
[1]Werner J.Severin, James.W.Tankard, Jr.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M].郭鎮之,等,譯. 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
[2]廖翊.故宮將向社會公布所有藏品 93.2%系珍貴文物[EB/OL](2012-07-07)http://news.qq.com/a/20120707/000238.htm
[3]胡濱.我國公共文化空間用戶信息行為及文化服務需求實證研究—以10所科技博物館用戶為調查對象[J].圖書與情報,2015(2):128-132.
[責任編輯:王麗平]
On Information Spreading of Imperial Palace in “Internet+” Times
ZHENG Dan
(School of Media and Cultural Industry, Sanya College, Sanya 572022, China)
In the “Internet+” times, Museums carry the social mission of propagating the museum history and culture to the masses, protec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historical civilization. Facing the change of information spreading environment, the Imperial Museum uses all kinds of means of the internet media and various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carry out the brand-new information spreading methods so to make the traditional and serious museum culture more populous. All the micro blogging, web chat, APP, and even the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have become the auxiliary means for museums to spread information. Based on all this, the Imperial Museum uses Internet thinking to carry out E-commerce and cultural products of the Imperial Palace so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re-understanding museum information spread methods.
“Internet+”; Imperial Palace; information spread; new media
2016-06-12
鄭丹(1983-),女,湖北咸寧人,三亞學院傳媒與文化產業學院廣告學專業講師,研究方向:新聞與傳播學研究。
2096-1901(2016)05-0088-05
G26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