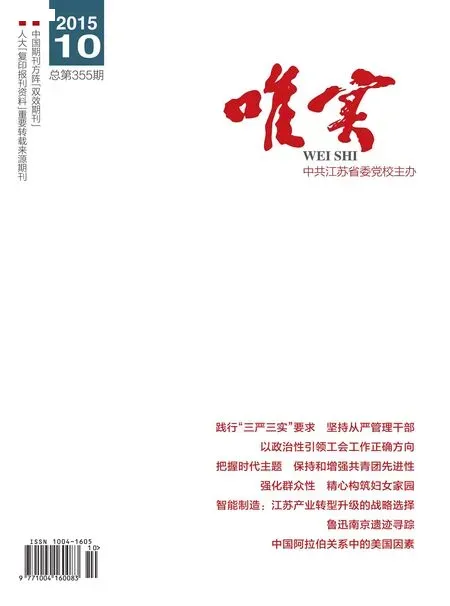孔僖的自辯
宋志堅
我寫孔僖,并非因為他是孔子的第19代孫,而是因為他對于“鄰房生”梁郁告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的自辯,辯得通情達理,辯得從容不迫,辯得義正詞嚴。即使今人讀去,也會為他的思辨與氣節所折服并自愧不如。
其實,所謂“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之言論,并非出于某個正兒八經的場合,諸如什么講壇或媒體之類,而是他與他的朋友崔骃之間私下閑談時的議論,論的“先帝”,乃是西漢武帝,所謂“始為天子,崇信圣道,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后恣己,忘其前善”云云,無非是說漢武善始而不善終,于是就被人密告了。說的“當世”,即為東漢章帝。所謂“刺譏當世”,則是密告之人自己的想象與發揮,此公的政治嗅覺很靈,政治敏感性也很強,認定這便是借古諷今,就像當年“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孔僖與崔姻的“誹謗先帝”與“刺譏當世”之間,似乎也就有了必然的聯系。
此類密告還真有效,一告就靈,一告就準,立馬就有人接招。“事下有司,詣吏受訊”,用今天的話說,叫作立案審查。孔僖之“自訟”即我所說的自辯,就在這個大禍即將臨頭之時,可見他之從容。
孔僖首先辯的是“誹謗先帝”。他為“誹謗”二字正名,“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因此,據實而言之者,不可稱之為“誹謗”。說漢武“及后恣己,忘其前善”,并非過甚其詞。窮奢極欲也好,窮兵黷武也罷,執政56年,看似轟轟烈烈,其實乏善可陳,連他自己在臨終之前,也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所以,孔僖說漢武“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在他看來,當皇帝的,為善為惡,天下莫不知曉,誰也掩蓋不了。僅是據實而論,何言“誹謗先帝”?
孔僖接著辯的是“刺譏當世”。他肯定章帝“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如果將“刺譏”視為“作案”,那么,“作案”的動機先就不能成立。當然,這只是孔僖的一種假設,即使真的“刺譏”,他也并不認為可以視同“作案”。假使“所非”即“刺譏”的屬實,“則固應悛改”;假如“所非”即所“刺譏”的有所“不當”,包括真借評說漢武來“刺譏當世”,也無非要“當世”以漢武為鑒,善始善終,此中包含著多少憂心與期待,無疑“亦宜含容”,又何罪之有?這與我們今天說的“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庶幾一致。生活在近兩千年前的孔僖,能有這般見識,已令人刮目相看。
對這兩條作了辯說之后,孔僖意猶未盡,筆鋒一轉,就直接批評“當世”了。他說“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謀國策,卻注重“私忌以快其意”。這樣做的結果,“臣等受戮,死即位耳”,就怕當今的天下人會以這件事來窺測陛下之心,“茍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當今陛下“欲為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難道也要你的子孫到時再去為你今日之所為作百般掩飾?孔僖如此臨危不懼,直言不諱,更是令人肅然起敬。
孔僖作“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之辯,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略去了《后漢書》中的若干細節。例如,“鄰房生”梁郁之所以“上書”告發自有其因。先是孔僖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廢書嘆曰:“若是,所謂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上述關于漢武帝的那番話,原是崔骃接著這個話頭說的,孔僖只應了一句:“書傳若此多矣!”倒是這位“鄰房生”附和:“如此,武帝亦是狗邪?”要說“誹謗”,此類“辱罵”倒是有點接近。然“僖、骃默然不對”,未予理睬,致使梁郁懷恨于心,這遂上綱上線,秘密告發。
章帝還是明智的:“書奏,帝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既沒使直言者因此遭罪,也沒讓密告者因此得逞。
(作者單位:福建人民出版社)
責任編輯:張功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