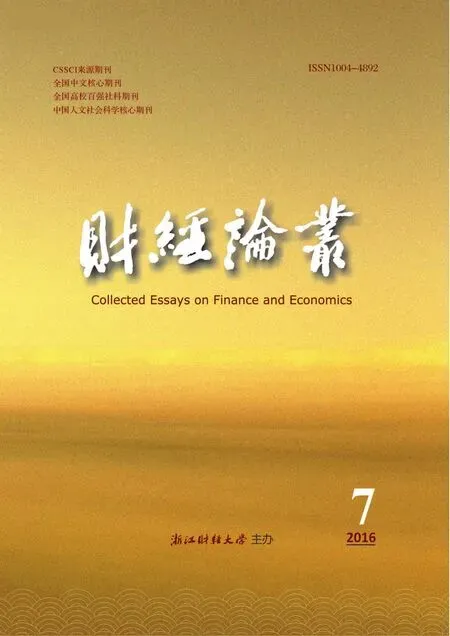出租車數(shù)量管制、經(jīng)營模式與專車規(guī)制
商 晨
(浙江財經(jīng)大學經(jīng)濟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出租車數(shù)量管制、經(jīng)營模式與專車規(guī)制
商 晨
(浙江財經(jīng)大學經(jīng)濟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專車受到非議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出租車需要接受政府監(jiān)管而專車不用。本文從出租車數(shù)量管制入手,通過構(gòu)建包含管制數(shù)量、監(jiān)管成本、代理層級的委托代理模型對出租車行業(yè)改革和專車發(fā)展進行分析,認為監(jiān)管技術(shù)、監(jiān)管成本、出租車數(shù)量都會影響出租車經(jīng)營模式,政府對專車行業(yè)應當從提高專車司機投機成本和提高行業(yè)進入門檻兩方面來進行規(guī)制。
數(shù)量管制;經(jīng)營模式;專車規(guī)制
一、引 言
最早的專車公司Uber 2010 年誕生于美國舊金山,2014年年初進入中國市場,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專車公司獲得了飛速的發(fā)展,攪動了沉寂已久的出租車市場,使出租車市場改革重新受到關注。但專車的處境一直比較尷尬,包括人民日報在內(nèi)的官方媒體和大多數(shù)專家民眾都認為,專車使乘客擁有便捷優(yōu)質(zhì)的出行選擇,打破了出租車市場的壟斷,不應急于否定[1];但地方的行業(yè)管理部門和出租車公司都認為專車是黑車,應當堅決取締,媒體上也經(jīng)常出現(xiàn)專車車輛被查扣甚至公司被查封的消息。不同群體對專車的態(tài)度反差如此大的原因在于,作為一種新事物,人們對專車的屬性還缺乏清晰的認識。此外,要想對目前“野蠻生長”的專車制定必要的行業(yè)規(guī)范,既要尊重市場的客觀需求,也要避免不合理的制度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前提是要對專車的客觀屬性有一個深入的研究。專車與出租車是“近親”,對出租車行業(yè)的分析將有助于我們對專車的深入了解。本文將從解釋出租車行業(yè)數(shù)量管制的原因入手,建立一個多層級委托-代理模型,通過比較靜態(tài)方法分析最優(yōu)的出租車管制數(shù)量的決定因素,對出租車行業(yè)經(jīng)營模式的變化規(guī)律進行探究,并且討論政府對專車規(guī)制所應該著眼的方面。
二、出租車數(shù)量管制和經(jīng)營模式的理論分析
出租車雖然比公交車、地鐵等典型的公共交通方式具有更強的競爭性,但由于信息不對稱性強、負外部性、交易成本結(jié)構(gòu)特殊等市場失靈問題,完全依賴市場調(diào)節(jié)會帶來社會福利和市場效率的損失,所以必需由政府對出租車行業(yè)進行管制[2][3]。在世界大多數(shù)城市,出租車運營都要經(jīng)過政府的授權(quán),受到嚴格的管制。
政府對出租車管制的手段主要有三種:數(shù)量管制、價格管制和質(zhì)量管制。各地由于社會制度、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社會文化習俗的不同,在三種手段的選擇和組合上存在較大差別。在質(zhì)量管制方面,由于出租車司機和乘客間存在較強的信息不對稱,理論和實踐都表明,政府對出租車的服務進行質(zhì)量管制是必需的,世界范圍內(nèi)還沒有哪個地方政府不對出租車的運營質(zhì)量進行必要的控制;對于價格管制,在理論和實踐中都存在一定分歧:有一部分研究認為可以放開出租車價格管制[4][5]。實踐中也有一些城市嘗試放開價格管制,但效果并不理想。近幾年出現(xiàn)的打車軟件加價叫車其實也是一種價格管制的變相放開,但這也給一些不熟悉移動互聯(lián)終端的群體帶來更大的不便。總體來看,價格管制仍然是大多數(shù)地方政府所選擇的政策。
出租車管制中爭議最大的是數(shù)量管制。數(shù)量管制減少了行業(yè)供給,增加了打車難度,特別是在高峰時段,很多大城市的打車難問題非常嚴重,公眾對此意見很大,要求政府放開出租車數(shù)量管制的呼聲一直很強烈。但在理論研究中對出租車數(shù)量管制的態(tài)度卻存在較大分歧:大多數(shù)意見認為數(shù)量管制造成了壟斷,降低了社會福利,所以應當取消數(shù)量管制[6][7][8][4][9][10]。但Schroeter(1983)、Gaunt(1996)、Yang et al.(2005)等一些研究認為放松數(shù)量管制不會使福利增加,甚至弊大于利,出租車數(shù)量管制是合理的[11][12][13]。Moore和Balaker(2006)[14]通過對之前的28篇研究出租車市場管制的文獻進行整理,發(fā)現(xiàn)其中有19篇支持放開管制,2篇認為結(jié)果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弊,還有7篇認為放開管制弊大于利。從實踐看,愛爾蘭、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一些城市曾經(jīng)放開出租車數(shù)量管制,但隨后均出現(xiàn)了比較多的問題,如司機工作時間增加,收入減少,司機為此私自漲價、挑客、繞道等問題日益嚴重,所以這些城市又重新開始實行出租車數(shù)量管制[15][2][16]。來自理論和實踐的證據(jù)都表明,單純強調(diào)數(shù)量管制弊端的認識存在片面性,應當對出租車數(shù)量管制背后的原因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1.對出租車數(shù)量管制的解釋
(1)政府俘獲理論
政府俘獲理論首先由1971年被斯蒂格勒提出,后由匹茲曼等人發(fā)展完善。該理論認為政府管制部門是經(jīng)濟人,政府管制的權(quán)力可以產(chǎn)生租金,特定利益集團可以對管制部門進行尋租,使管制者成為被管制者的俘虜,雙方共同分享管制帶來的壟斷利潤。Barrett(2003)基于政府俘獲理論,解釋了愛爾蘭政府在1978-2000年間凍結(jié)出租車牌照發(fā)放,但2001年利益集團的努力沒有奏效,政府取消了出租車牌照的凍結(jié)[17]*愛爾蘭于2009年又重新恢復了對出租車的數(shù)量管制。。張樹全(2009)同樣基于政府俘獲理論,認為國內(nèi)地方政府的一些部門機構(gòu)龐大,需要依靠收費來養(yǎng)人。政府對出租車行業(yè)管理的成本低而收益高,所以地方政府傾向于加強對出租車行業(yè)的管制[18]。盧正剛 等(2007)進一步認為,在西方健全的法律體制下政府俘獲的現(xiàn)象比較少,但在法制有待健全的轉(zhuǎn)軌國家,政府被利益集團俘獲的可能性則比較大,合肥市的政府管理部門和出租車公司間存在明顯的利益鏈條,管理部門具有明顯的管制俘獲的特征[19]。
政府俘獲理論的確可以對管制部門執(zhí)著于數(shù)量管制進行部分解釋,但也存在明顯的問題。首先,這種觀點難以對管制解除后又重新恢復的現(xiàn)象進行合理解釋。愛爾蘭2000年取消數(shù)量管制,2002年出租車數(shù)量增長到2000年的3倍,牌照價格由8萬愛爾蘭磅下降到5千愛爾蘭磅[17]。出租車行業(yè)沒有高額利潤,不會形成強大的利益集團,政府就不會被利益集團俘獲來進行管制,但愛爾蘭政府卻在2009年重新凍結(jié)了出租車牌照的發(fā)放,類似的情況在美國和加拿大的一些城市也出現(xiàn)過。其次,很多實施數(shù)量管制的地方政府事實上沒有從管制中分享壟斷利潤。2004年以前國內(nèi)很多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的出租車牌照投放方式為審批制,只要申請人的相關經(jīng)濟能力比如車輛數(shù)量、運營資金、辦公場地等通過審查,既可無償獲得經(jīng)營權(quán)[20]。并且2004年國務院辦公廳發(fā)布《關于進一步規(guī)范出租汽車行業(yè)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規(guī)定“所有城市一律不得新出臺出租汽車經(jīng)營權(quán)有償出讓政策”。
(2)出租車經(jīng)營具有外部性
出租車經(jīng)營具有交通擁堵、環(huán)境污染等負外部性,造成的社會邊際成本超過運價。按照經(jīng)濟學理論,社會邊際成本等于價格才能實現(xiàn)社會凈福利最大,所以政府需要對出租車的數(shù)量進行限制,來確保市場出現(xiàn)有效率的結(jié)果[7][10][13]。
政府對出租車進行數(shù)量管制可能有緩解交通擁堵和控制污染的考慮,但應當不是主要原因。以上海為例,1996年上海率先在國內(nèi)嚴格控制出租車數(shù)量,但上海決定是否投放新的出租車牌照的依據(jù)并非交通擁堵指標,而是出租車滿載率。當滿載率持續(xù)高于70%時,政府才增加出租車的數(shù)量[21]。出租車滿載率與交通擁堵、環(huán)境污染沒有直接關系,所以政府的主要目的并非是緩解交通和環(huán)境的壓力。
(3)數(shù)量管制可以簡化政府對司機的監(jiān)督
Cairns 和Liston-Heyes(1996)認為,在高度分散的出租車市場上,政府在監(jiān)管司機提供服務的安全性、舒適性及設備的良好維護方面的行為時,存在很強的信息不對稱,司機在提供服務時很容易出現(xiàn)“縮水”(shrink)的投機行為,在大城市中這個問題尤其嚴重。如果出租車市場是自由進入的,出租車服務的價格僅僅和司機的機會成本相等,司機就有比較強的投機動機。但是如果服務的價格能超過機會成本,司機有投機行為時,暫停他運營的權(quán)利可以使他承擔損失,政府對出租車進行數(shù)量管制可以使出租車運價超過機會成本,從而可以起到對司機的約束作用,簡化政府監(jiān)督[15]。
這種觀點既可以從理論上解釋政府堅持數(shù)量管制的原因,在邏輯上與政府將滿載率作為數(shù)量調(diào)整的依據(jù)也是一致的,但認為數(shù)量管制會使價格超過機會成本是不正確的。政府對出租車進行數(shù)量管制后,出租車服務價格會提高,但相應地出租車牌照的價格也會提高。尋租的結(jié)果最終會使租金完全耗散,即運營價格等于機會成本,牌照擁有者的利潤等于零。
基于Klein和Leffler(1981)提出了可自我執(zhí)行契約的理論[22]。本文認為,政府通過對出租車數(shù)量的管制可以使擁有牌照的企業(yè)或個人獲得更高的經(jīng)營收入,發(fā)生投機行為后政府如果收回特許經(jīng)營權(quán)或者限制對其投放新的經(jīng)營權(quán),較高的運營收入就成為司機投機的機會成本。出租車數(shù)量控制越嚴格,運營的收入越高,投機行為的機會成本就越高。數(shù)量管制就成為政府對出租車行業(yè)進行有效管理,保障公共利益目標的手段之一。
在國內(nèi)一些城市的出租車管理政策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邏輯。2006年4月頒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強出租汽車行業(yè)管理的意見》規(guī)定,出租車公司競標出租車特許經(jīng)營權(quán)需要以規(guī)范經(jīng)營、安全運營、服務質(zhì)量為主要競標條件,公司和政府要簽訂特許經(jīng)營協(xié)議,如果不能達到服務承諾,有可能被收回特許經(jīng)營指標。上海的出租車公司的服務質(zhì)量和誠信的數(shù)據(jù),直接決定出租車公司的發(fā)展。上海的出租車牌照不招標,每一輪更新都是以公司服務質(zhì)量投訴量來決定本輪更新比例[23],成都的政策和上海相似[24]。由此思路出發(fā),我們還可以解釋其他的出租車管制措施,比如倫敦的出租車沒有數(shù)量管制,但服務秩序在全世界名列前茅。Cairns 和Liston-Heyes(1996)[15]的觀點對此難以進行解釋,但從司機投機成本的角度就不難理解。在倫敦要取得出租車運營資格需要參加非常嚴格的執(zhí)照考試,考試的準備時間至少要一年[6]。出租車司機如果欺騙乘客,一旦被發(fā)現(xiàn)就會被吊銷執(zhí)照[21]。司機之前為考試花費的大量時間就會成為沉沒成本,司機自然會約束自己的投機動機。所以倫敦雖然沒有對出租車進行數(shù)量管制,但這種手段和數(shù)量管制本質(zhì)上一樣,區(qū)別僅在于倫敦司機投機的機會成本是前期投入的大量時間,而數(shù)量管制下司機投機的機會成本是未來可以獲得的高額收入。
2.出租車經(jīng)營模式中的委托代理關系
除事后處罰機制以外,管理機構(gòu)對出租車進行一定的事前監(jiān)管也是必要的,這是通過不同的出租車經(jīng)營模式來實現(xiàn)的。下文將從委托代理理論出發(fā)對幾種出租車經(jīng)營模式進行歸納,由于資料所限,討論僅限于國內(nèi)的經(jīng)營模式。
Jensen和Meckling(1976)認為,在一種契約關系下,一個人或更多人聘用另一人代表他們履行某些服務,他們間就存在委托代理關系[25]。出租車的運營效率和服務質(zhì)量關系到公共利益,進而影響到政府的效用函數(shù),所以政府與出租車司機間存在委托代理關系。作為代理人的司機,行動目標是自身收益最大化,而非委托人(政府)的收益最大化,而且出租車行業(yè)具有比較強的個體勞動屬性,司機具有很強的信息優(yōu)勢,這也是政府應當對出租車行業(yè)進行監(jiān)管的原因。
在具體的委托代理形式上,政府可以選擇單層的代理關系或者多層的代理關系。如果出租車數(shù)量比較少,政府將出租車運營權(quán)交給司機,直接對出租車的運營進行監(jiān)管,就屬于單層的委托代理關系。但一些大城市出租車數(shù)量比較多,政府直接監(jiān)管存在很大困難,往往把部分監(jiān)管責任委托給出租車公司,形成政府與公司和公司與司機間的雙重委托代理關系。這時,政府作為最終的委托人并非不承擔對司機的監(jiān)管責任,而是與公司分攤監(jiān)管責任。一個例證是,無論國內(nèi)那種出租車經(jīng)營模式中,乘客如果對出租車服務不滿意,可以撥打出租車公司的投訴電話,也可以直接向政府的運管部門進行投訴。
不同經(jīng)營模式的區(qū)別在于,政府和公司間監(jiān)管責任的分攤比例是不同的。國內(nèi)出租車經(jīng)營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種:個體經(jīng)營制(溫州模式)、掛靠經(jīng)營制(天津模式)、承包經(jīng)營制(北京模式)、企業(yè)經(jīng)營制(上海模式)。我國85%以上的城市出租車經(jīng)營模式與北京模式基本相同[26]。個體經(jīng)營制中,政府和司機間是單層的委托代理關系,政府將出租車運營權(quán)交給個人,并且直接對司機進行監(jiān)管,所以政府的監(jiān)管責任比例是1。其余三種經(jīng)營模式中,政府都將部分監(jiān)管責任委托給出租車公司。
掛靠制中出租車公司基本無償從政府獲得特許經(jīng)營權(quán),然后將車輛加價轉(zhuǎn)賣給個人,特許經(jīng)營權(quán)也隨之轉(zhuǎn)給個人,但司機的運營需要掛靠公司,由公司負責代繳稅費、培訓、年檢等,個人向公司繳納一定數(shù)額的管理費。掛靠制比個體經(jīng)營在組織方式上前進了一步,有專人傳遞信息、組織學習、代辦日常事務、督促安全生產(chǎn)[27]。但總體來看掛靠制中公司承擔的監(jiān)管責任非常有限,主要的監(jiān)管責任還是由政府承擔。
在承包制中,出租車經(jīng)營權(quán)和車輛由出租車公司所有*北京承包經(jīng)營的出租車原為個人出資購買,但1996年以后政府要求公司回購車輛,現(xiàn)承包經(jīng)營出租車的所有者為公司。,個人與公司間是承包關系,個人通過份子錢的形式向公司付費使用出租車經(jīng)營權(quán)。公司雖然可能無償獲得經(jīng)營牌照,但要向政府承諾監(jiān)管義務,如果公司達不到規(guī)范、安全和服務質(zhì)量等承諾,將被取消特許經(jīng)營權(quán)。所以相對于掛靠制,公司對司機的監(jiān)管更加嚴格。
在企業(yè)制中,出租車經(jīng)營牌照和車輛也為公司所有。但與承包制不同的是,司機與公司簽訂勞動用工合同,雙方是勞動雇傭關系,駕駛員按照企業(yè)的管理制度進行營運,收入按任務定額和服務質(zhì)量等各項指標考核后確定。出租車的維修、保養(yǎng)、投訴處理等都由公司統(tǒng)一辦理,司機只需按照公司規(guī)章制度提供服務,公司對違反公司有關管理制度的駕駛員照章處罰直至解聘。相比其他經(jīng)營模式,公司制對司機的約束更多,獎勵和處罰制度更健全[27][23]。
三、模型設定與比較靜態(tài)分析
作為理性人,政府通過出租車的數(shù)量控制和經(jīng)營模式選擇的目標,是實現(xiàn)凈收益的最大化:
max(U-C)
(1)


(2)
上文已分析,政府對出租車司機實施監(jiān)管需要通過委托代理的方式,由此會產(chǎn)生代理成本C。具體來說代理成本包括以下三個部分:首先,盡管政府可能將部分監(jiān)管責任委托給出租車公司,但仍然需要對出租車司機的運營承擔一定的監(jiān)管職責,會給政府帶來監(jiān)管成本C1;其次,由于出租車運營中的信息不對稱,為了約束可能的投機,政府需要通過出租車數(shù)量管制來提高投機的機會成本,但數(shù)量控制會造成出租車市場出現(xiàn)短缺,民眾在高峰期打車等候時間增加,會對政府的出租車管理政策產(chǎn)生不滿,由此給政府帶來成本C2;再次,由于出租車運營有比較強的個體勞動性質(zhì),委托人和代理人間存在較強的信息不對稱,司機仍然可能出現(xiàn)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甚至出租車公司也可能出現(xiàn)道德風險,和司機合謀損害政府的利益,由此給政府帶來成本C3,則有:
C=C1+C2+C3
(3)
1.政府所承擔的出租車監(jiān)管成本與監(jiān)管的出租車規(guī)模成正比,而同樣的出租車規(guī)模,多層代理中政府監(jiān)管成本就比單層代理中要少,而且同樣的代理層級下政府所承擔的監(jiān)管責任比例越小,監(jiān)管成本也越小。此外技術(shù)創(chuàng)新可以帶來有效監(jiān)管的單位成本的變化,政府的監(jiān)管成本還和對每輛出租車進行有效監(jiān)管所需的單位成本有關,考慮以上幾方面因素,則有:
(4)
其中,k為政府選擇的代理層級,k為大于等于1的整數(shù)*在現(xiàn)有的出租車經(jīng)營模式中,k等于1或者2,但在第四部分會討論k進一步增加的情況。。n1為政府進行數(shù)量控制的出租車數(shù)量,n1≥0。α為多層委托代理關系中,政府在每一級代理中,所承擔的監(jiān)管責任比例,α∈(0,1]。t為對每輛出租車進行有效監(jiān)管所需要的單位成本,t∈(0,+∞)。假設隨著委托代理關系層級的增加,政府監(jiān)管成本C1呈指數(shù)下降。
監(jiān)管成本隨政府責任比例增加而增加,隨代理層級增加而減小,但始終為正,隨出租車數(shù)量增加而增加,并且邊際成本也上升,對單位出租車進行有效監(jiān)管所需的成本增加,政府監(jiān)管成本也會增加,并且單位監(jiān)管成本越高,政府越傾向于通過提高出租車違約成本的方式約束司機,政府直接監(jiān)管成本上升的速度要慢于單位監(jiān)管成本上升的速度,函數(shù)具有以下特征:
2.假設出租車市場出清時,公眾打車比較容易,對出租車行業(yè)滿意度較高,政府效用能達到所期望水平。數(shù)量管制所帶來的成本與出租車短缺程度正相關,則有:
(5)

3.政府與司機的委托代理關系中, 代理成本主要由司機運營中的道德風險行為所導致,道德風險行為與雙方信息不對稱程度正相關。出租車數(shù)量越多,雙方信息越不對稱,且司機投機行為的機會成本越小,司機越有可能選擇投機;政府與司機間代理層級越多,信息之傳遞過程中“失真”的可能性越大,政府與出租車司機間信息越不對稱,代理成本越高。此外,需要對司機進行有效監(jiān)管的成本越高,司機道德風險行為被發(fā)現(xiàn)越困難,道德風險行為會越多,代理成本越高,并且上升速度會快于單位監(jiān)管成本上升的速度。則有:
(6)
將(2)-(6)式代入(1)式,所得政府凈收益函數(shù)對n1求一階偏導數(shù),并使結(jié)果等于0,可得最優(yōu)的出租車管制數(shù)量為
(7)



同理,將政府凈收益函數(shù)對k求偏導,并使結(jié)果等于0,可得最優(yōu)的k*滿足以下關系:
(8)
(8)式中k*對t求一階導數(shù),可得
(9)
(9)式分母大于0,所以(9)式符號由分子部分的符號決定。由α的取值可知(-lgα)>0,所以分子部分可能為正也可能為負,將(9)式分子等于0的α值記作α′,則有
(10)


由以上分析可得:


四、模型結(jié)論的分析與討論
專車提供的服務與出租車基本相同,專車行業(yè)的運營效率也會影響到政府的效用函數(shù),所以政府和專車行業(yè)間事實上也存在委托-代理關系,前文的模型也可以用于分析專車。
1.監(jiān)管技術(shù)創(chuàng)新導致規(guī)模擴張
由命題(Ⅰ)可知,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如果對出租車進行監(jiān)管的單位成本下降,城市出租車的最優(yōu)數(shù)量規(guī)模應該增加。
以上海出租車發(fā)展為例,在1996年以前上海沒有對出租車市場實施嚴格的數(shù)量管制,1992-1995年出租車數(shù)量由1.2萬輛增加到3.8萬輛(2013年數(shù)量也不過4.9萬輛)。但監(jiān)管技術(shù)卻沒有跟上規(guī)模擴張的步伐,由于國產(chǎn)的計價器質(zhì)量比較差,司機普遍不愿意用計價器而是和乘客議價,亂收費、拒載等問題非常普遍。時任市長朱镕基親自命令從國外進口幾千臺計價器,還統(tǒng)一從國營上海儀電廠生產(chǎn)計價器,強制要求出租車使用,否則“抓住兩次就吊銷營運證”,計價器的使用使亂收費、拒載等問題逐漸被壓制住[21]。顯然,監(jiān)管技術(shù)創(chuàng)新使監(jiān)管成本降低,這為出租車規(guī)模擴張創(chuàng)造了條件。
技術(shù)創(chuàng)新導致監(jiān)管成本降低同樣是專車獲得迅猛發(fā)展的根本原因。專車進入中國只有一年多的時間,但發(fā)展的速度非常驚人,上海規(guī)模最大的出租車公司大眾出租車公司成立于1988年,目前擁有9000余輛出租車*數(shù)據(jù)來自上海大眾出租車公司官網(wǎng)。,而2014年7月才出現(xiàn)的“一號專車”,在各大城市提供的車輛就已經(jīng)超過1萬輛*數(shù)據(jù)來自快智集團1號專車官網(wǎng)。。專車規(guī)模的快速擴張并沒有導致企業(yè)對運營質(zhì)量失控,相反,專車司機的運營要接受嚴格的監(jiān)督。以滴滴專車為例,企業(yè)要求司機統(tǒng)一著裝、全程標準化商務禮儀服務,上下車主動開關車門、提行李,車內(nèi)備有免費充電器、飲品、干濕紙巾、雨傘、兒童老人專屬靠墊等出行必備用品。公司對司機會進行定期的安全培訓,還規(guī)定了多條違規(guī)項目,如果司機遲到、沒有使用標準話語、沒有配備飲用水、因任何原因要求乘客取消訂單等,都會受到相應處罰,輕則被警告,重則解除合作。專車平臺能夠?qū)?shù)量龐大的專車司機進行嚴格監(jiān)管的基礎就是已經(jīng)比較普及的GPS技術(shù)和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
2.出租車數(shù)量增長與出租車經(jīng)營模式變革
由命題(Ⅱ)可知,出租車最優(yōu)數(shù)量與政府在監(jiān)管責任中的比例成反比,如果政府在委托代理關系中將更多的責任委托給出租車公司,那么最優(yōu)的出租車數(shù)量就能夠增加。
設個體制、掛靠制、承包制、企業(yè)制中政府的監(jiān)管責任分別為α1、α2、α3、α4,由2.2分析可知α1=1,αi<1(i=2,3,4),且α1>α2>α3>α4。
隨著城市規(guī)模的迅速擴張和出租車數(shù)量的增長,出租車的數(shù)量也需要增加,此時,政府監(jiān)管責任比例較高的個體經(jīng)營和掛靠經(jīng)營的弊端會越來越明顯,政府應當選擇監(jiān)管責任比例更低的經(jīng)營模式來適應這種變化。溫州是個體經(jīng)營的典型,溫州市區(qū)3770輛出租車中,個體經(jīng)營的占88%。在2010年浙江省的出租車服務質(zhì)量評比中,溫州名列倒數(shù)第二,有消費者因為出租車服務質(zhì)量向溫州運管部門投訴時,得到的回復是10天后才處理。2013年12月由溫州市政府會議審議通過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出租車行業(yè)管理的意見》中明確提出,溫州出租車即將由個體經(jīng)營模式主導,逐步轉(zhuǎn)變?yōu)橛晒局鲗У慕?jīng)營模式,鼓勵出租車企業(yè)回購個人出租汽車。其原因用運管局出租車管理處處長的話說,就是“政府部門要管理這么多出租車確實有困難……溫州模式這樣一路走來,純粹的個體經(jīng)營很散很亂”[28][29][30]。類似的問題在實行掛靠經(jīng)營為主的天津也有,“此種(天津)經(jīng)營模式體現(xiàn)的管理難點是,盡管出租車輛掛靠在不同公司,但由于實行的是個體經(jīng)營,管理部門直接面對的是眾多經(jīng)營個體,管理模式較松散,管理困難大,難以到位”[31]。
以承包制的代表城市北京和企業(yè)制的代表城市上海作比較,兩地常住人口都在2000萬以上,北京出租車數(shù)量為6.6萬輛比上海4.9萬輛更多,但上海的出租車口碑相對要好很多,車輛干凈整潔,拒載與繞路等問題不常發(fā)生,而且在上海打車并不那么困難[21]。
3.監(jiān)管成本、責任比例與代理層級
隨著技術(shù)、制度和乘客維權(quán)意識的提高,對每輛出租車進行必要監(jiān)管的單位成本會逐漸降低。舉例來說,在傳統(tǒng)出租車服務中,乘客通過將司機所選擇的路線與手機導航軟件推薦的路線進行對比,即使對城市道路不熟悉,也可以容易地判斷出司機是否繞路;運管部門要求出租車運營時必須放置司機服務監(jiān)督卡并且使用計價器,服務監(jiān)督卡和計價器打印的發(fā)票上都有司機和車輛的信息以及投訴的方式,這給乘客維權(quán)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總體來看,對出租車進行監(jiān)管的單位成本在逐漸降低。
由命題(Ⅲ)可知,在單層委托代理關系中,最優(yōu)代理層級應當與出租車單位監(jiān)管成本反方向變化,隨著監(jiān)管成本的下降,最優(yōu)的代理層級應該增加。
溫州的個體經(jīng)營模式就是單層的委托代理關系,溫州已經(jīng)確定經(jīng)營模式的改革方向是企業(yè)制,實際就是在政府和司機之間增加出租車公司這一級代理關系。這個結(jié)論與3.2的結(jié)論是一致的。
同樣由命題(Ⅲ)可知,雙層委托代理中政府的責任比例較高時,最優(yōu)代理層級也應與出租車單位監(jiān)管成本反方向變化。掛靠制中政府承擔了絕大部分的監(jiān)管責任,但我們并沒有觀察到在掛靠制中發(fā)展出新的代理層級。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對政府來說,代理層級增加和政府責任比例降低本質(zhì)上相同,都是將更多監(jiān)管任務讓別的機構(gòu)承擔。但增加代理層級顯然要比在現(xiàn)有的委托代理關系中調(diào)整責任比例更復雜,所以現(xiàn)實中的經(jīng)營模式改革都選擇降低政府責任比例而不是增加代理層級。
由命題(Ⅳ)可知,當政府監(jiān)管責任比例較低時,代理層級與監(jiān)管成本應當同方向變化,隨著監(jiān)管成本的下降,代理的層級應當減少,如果監(jiān)管成本上升,代理的層級應當增加。
目前國內(nèi)出租車經(jīng)營模式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以上海為代表的企業(yè)經(jīng)營制,這種模式相對于其他幾種模式,有比較明顯的優(yōu)勢,目前還沒有觀察到企業(yè)經(jīng)營制發(fā)生進一步改革的情況。但我們不妨假設,如果為了應對來自于專車的日益嚴峻的挑戰(zhàn),傳統(tǒng)的出租車也開始采用基于“互聯(lián)網(wǎng)+”的監(jiān)管技術(shù),監(jiān)管者仿照專車平臺進行運作。此時單位監(jiān)管成本出現(xiàn)大幅降低,保留出租車公司這一代理層級將不再有明顯的必要,政府完全可以成立一個規(guī)模不大的監(jiān)管機構(gòu),直接對出租車運營進行監(jiān)管。單純從技術(shù)的角度看,既然輕資產(chǎn)的專車平臺可以做到對大量的專車進行有效的監(jiān)管,政府部門做同樣的事情也不會遇到太大困難。所以命題(Ⅳ)在邏輯上是可以成立的。
五、政策建議
政府對出租車的監(jiān)管也可以采用各種比較成熟的新技術(shù)來降低監(jiān)管成本,將能夠使有效監(jiān)管的出租車數(shù)量大幅增加,政府就可放松對出租車的數(shù)量管制,使市民能享受到更便捷的出租車服務。
專車是市場自發(fā)產(chǎn)生的事物,專車到目前的發(fā)展是游離于政府監(jiān)管以外的,但專車與政府間存在委托代理關系,應當接受必要的監(jiān)管。套用我們的模型來分析,目前專車運營中,政府的責任比例α基本為0,但這個比例應該適當提高。由命題(Ⅱ)可知,α提高時,最優(yōu)的行業(yè)規(guī)模數(shù)量應該降低。目前專車行業(yè)的擴張似乎沒有邊界,只要有一輛車一臺智能手機,接入了專車平臺就可以上路接單。這樣無序的狀況應該有所改變,未來專車在政府的規(guī)制下,行業(yè)的規(guī)模應該得到控制,車輛和司機只有滿足一定條件才可以參與運營。
目前政府給專車的運營劃出一條紅線:嚴格禁止私家車接入專車平臺運營,專車車輛必須來自租車公司,司機必須由勞務公司派遣。必須由勞務公司派遣司機其實就是增加一個代理層級,由政府與專車平臺、專車平臺與司機兩個代理層級變?yōu)檎c專車平臺、專車平臺與勞務公司、勞務公司與司機三層代理關系。目前專車的委托代理關系中α值接近于0,如果出現(xiàn)單位監(jiān)管成本上升的情況,代理的層級應當增加。但這種情況現(xiàn)實中恐怕不會出現(xiàn),目前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已經(jīng)普及,在沒有新的革命性的監(jiān)管技術(shù)出現(xiàn)之前,監(jiān)管成本會大體保持穩(wěn)定,并且隨著技術(shù)和制度的邊際創(chuàng)新而逐漸降低,不會出現(xiàn)單位監(jiān)管成本上升的情況。所以在專車的委托代理關系中增加勞務公司這一新的代理層級是不合理的。而且從新產(chǎn)權(quán)理論出發(fā),這種制度安排還會帶來一定的問題:司機駕駛租車公司的車輛,司機有車輛使用權(quán),但車輛使用的殘值不歸他,他沒有足夠激勵以合理的方式使用車輛,車況反而會比較差。
從專車服務在國內(nèi)一年多來的發(fā)展情況看,政府沒有進行必要的監(jiān)管,但專車公司對司機的管理提高了乘客的體驗,專車服務在大眾中享有比較好的口碑。但這恐怕不會是長期均衡的結(jié)果,專車作為新事物需要提高知名度、拓展市場,所以會盡心盡力提供高質(zhì)量的服務,同時給乘客發(fā)各種補貼、紅包,但是沒有理由相信當企業(yè)已經(jīng)打開市場,有穩(wěn)定的盈利時,也能主動保證比較高的服務質(zhì)量,并且進行大幅度的讓利。所以政府對專車運營的質(zhì)量和價格進行必要的規(guī)范,從長遠看是必須的。
按照本文的觀點,政府對專車的監(jiān)管應該從兩方面入手,首先,通過制度安排提高司機投機的機會成本,使司機作為經(jīng)濟人主動克制自己投機的動機,而對司機是否隸屬于公司不必進行規(guī)定。倫敦有超過一半的的出租車是個體司機,但并不妨礙倫敦出租車的服務質(zhì)量在世界上享有盛名,高昂的投機成本在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其次,對司機的駕駛技術(shù)和車輛的車況應當設置比較嚴格的條件,可以對專車司機一年當中的違章次數(shù)和需要承擔責任的事故次數(shù)做出規(guī)定,如果超出就取消專車運營的資格。在專車進行車輛檢驗時也可以設置更高的標準,并且提高車檢的頻率,這些措施就可以保證車輛有比較理想的車況。
[1]王偉健. 網(wǎng)招“專車”前路如何[N]. 人民日報,2015-1-08,015.
[2]王智斌. 國內(nèi)外出租車經(jīng)營管理模式研究——以數(shù)量管制和經(jīng)營者準入資格為核心[J]. 金陵法律評論,2014,(1):217-229.
[3]袁長偉,吳群琪. 國際出租車管制模式與改革啟示[J]. 經(jīng)濟體制改革,2013,(6):151-155.
[4]Williams,DJ.Theeconomicreasonforpriceandentryregulationoftaxicab:AComment[J].JournalofTransportEconomicsandPolicy,1980,(14):105-112.
[5]Seibert.Taxideregulationandtransactioncosts[J].EconomicAffairs,2006,(6):71-73 .
[6]Beesley,M.E.Regulationoftaxis[J].TheEconomicJournal,1973,(83):150-172.
[7]Shreiber,C.Theeconomicreasonsforpriceandentryregulationoftaxicab[J].JournalofTransportEconomicsandPolicy,1975,(9):268-279.
[8]Coffman,R.B.Theeconomicreasonsforpriceandentryregulationoftaxicab[J].JournalofTransportEconomicsandPolicy,1977,(11): 288-304.
[9]Toner,J.P.ThewelfareeffectsoftaxicabregulationinEnglishtowns[J].EconomicAnalysis&Policy,2010,(40):299-312.
[10]Cetin,T.,Eryigit,K.Y.EstimationtheeffectsofentryregulationintheIstanbultaxicabmarket[J].TransportResearchPartA,2011,(45):476-484.
[11]Schroeter,JohnR.Amodeloftaxiserviceunderfarestructureandfleetsizeregulation[J].BellJournalofEconomics,1983,(14): 81-96.
[12]Gaunt,C.Theimpactoftaxideregulationonsmallurbanareas:SomeNewZealandavidence[J].TransportPolicy,1996,(2):257-262.
[13]Yang,H.,Ye,M.,Tang,W.H.,Wong,S.C.Regulatingtaxiservicesinthepresenceofcongestionexternality[J].TransportationResearch,2005,(39): 17-40.
[14]Moore,A.T.,Balaker,T.Doeconomicsreachaconclusionontaxicabderegulation?[J]EconJournalWatch,2006,(3):109-131.
[15]Cairns,R.D.,Liston-Heyes,C.Competitionandregulationinthetaxiindustry[J].JournalofPublicEconomics,1996,(59): 1-15.
[16]徐康明,蘇奎. 出租車改革當借鑒國際經(jīng)驗[N]. 南方日報,2015-05-14,GC02.
[17]Barrett,S.D.Regulatorycapture,propertyrightsandtaxideregulation,acasestudy[J].EconomicAffairs,2003,23(4):34-40 .
[18]張樹全. 政府管制動機對出租車經(jīng)營模式的影響[J]. 云南財經(jīng)大學學報,2009,(6):146-150.
[19]盧正鋼,趙定濤,楊敏. 合肥市出租車市場管制效應及其成因解析[J]. 公共管理學報,2007,(3):57-62,124.
[20]黃鳳鳴. 出租車行業(yè)特許經(jīng)營權(quán)研究[D].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21]陳中小路,陳伯英. 上海出租車的管制邏輯 “最不壞的市場”是如何形成的[N]. 南方周末,2013-06-06.
[22]Klein.,B.,leffler,K.B.Theroleofmarketforceinassuringcontractualperformance[J].TheJournalofPliticalEconomy,1981,(89): 615-641.
[23]李陽陽. 四張藥方,治好上海五萬的士[N]. 錢江晚報,2013-1-30,A8.
[24]徐雁行. 成都市員工制出租車企業(yè)駕駛員管理研究——基于心理契約視角[D]. 四川:四川師范大學,2012.
[25]Jensen,M.C.,Meckling,M.H.Theoryoffirm:Managerialbehavior,agencycostsandownershipstructure[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976,(4):305-360.
[26]柴寶亭. 我國出租車經(jīng)營模式分析[J]. 汽車與安全,2013,(8):48-53.
[27]凌顯峰. 城市出租車經(jīng)營模式分析及其適應性評價[D]. 吉林: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28]甘凌峰. 溫州出租車官司集中爆發(fā)[N]. 都市快報, 2011-5-17,A21.
[29]劉星.溫州改革出租車個體經(jīng)營模式[N]. 中國青年報,2014-1-03,07.
[30]歐陽瀟、陳越、葉卉. 探秘溫州出租車亂象 撥打投訴熱線稱10天后才處理[N]. 溫州晚報,2014-8-29.
[31]蘇曉梅. 拒載不拒載 誰說了算?[N]. 天津日報,2013-8-14,009.
(責任編輯:風 云)
Quantity Control and Business Model of Taxicab ,Regulation of Tailored Taxi
SHANG Chen
(School of Economics ,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The censure of tailored taxi results from the fact that taxi is under government control while tailored taxi is no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form of taxi and development of tailored tax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quantity control of taxi. Through the analysis with a principal-agent model which includes quantity control, supervision cost and supervision levels, we find that the supervision technology, the supervision cost and the quantity of the taxi a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taxi business model.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drivers’ speculative behavior and raise threshold to supervise tailored taxi.
quantity control;business model;regulation of tailored taxi
2015-10-14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10BJL001)
商晨(1977-),男,山西太原人,浙江財經(jīng)大學經(jīng)濟學院副教授。
F294.3
A
1004-4892(2016)07-01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