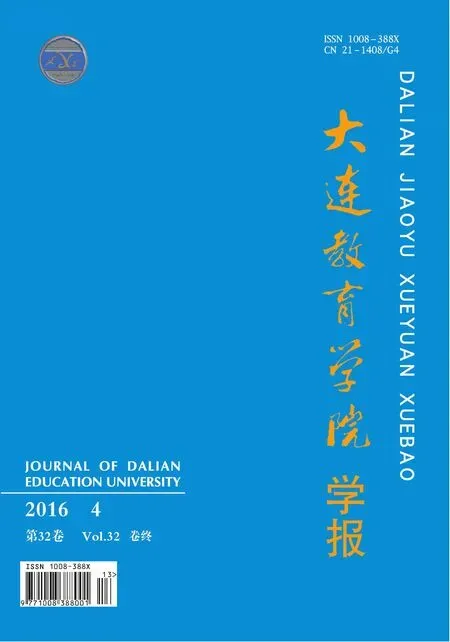河與岸之間的放逐與追尋
——蘇童小說《河岸》的闡釋
高小弘
(大連理工大學 人文學院, 遼寧 大連 116023)
?
河與岸之間的放逐與追尋
——蘇童小說《河岸》的闡釋
高小弘*
(大連理工大學 人文學院, 遼寧 大連 116023)
在蘇童的小說《河岸》中,河流與河岸是具有參照意味的對立空間,河岸是一個被政治徹底主宰的現實世界,而河流是一個被政治無情邊緣和放逐的世界。因此,《河岸》是一個有關現實與歷史、放逐與尋找的故事,也是一個成長的故事。
對立空間;放逐;追尋;成長
蘇童在訪談中,多次談到他的河流情結,他早期的隨筆《河流的秘密》,曾是他最喜歡的隨筆文章。他的長篇小說《河岸》,又是一個有關河流的故事。在他看來,這兩篇作品雖然體制不同,但卻因展露了共同的河流情結,它們之間有內在聯系,屬于一個精神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隨筆《河流的秘密》應當成為解讀《河岸》的一把鑰匙。在這篇隨筆中,蘇童深情地談到了他童年居所后窗所對的一條瘦小的河流,河流那憂郁壓抑、牢騷滿腹、自暴自棄的表情讓童年的他癡迷于河流的秘密。然而任憑孩子怎樣諦聽河流那類似囈語的喃喃之聲,河流內心的秘密始終不與人言說。河流的心靈要比任何人所能描述的豐富得多,深沉得多,無論編織出什么樣的網,也注定無法打撈河流的心靈。歷史的神秘與現實的荒誕就像那沉默寡言的河水一樣不可言說。在這篇隨筆中,“河流”的意象充滿了神秘、壓抑。
在小說《河岸》中,河流不僅作為故事發生的敘事空間背景,也一躍成為敘事的目標之一。首先,河流與河岸成為相互具有對立意味的參照空間,河岸,以“油坊鎮”為中心的現實社會,是一個被政治徹底主宰的現實世界,具有深刻的文革時代烙印。岸上的政治世界基本上就是一個荒誕的世界,對于一個人至關重要的政治身份憑靠的是胎記和猜測。河流,從現實層面來講,是以“向陽船隊”為中心的世界,是一個被政治無情邊緣和放逐的世界。向陽船隊上所有人都由于不同程度的“有罪”而被放逐。由于政治面貌曖昧模糊,政治身份缺失,向陽船隊遭到河岸社會的歧視與抵制。其次,河岸以堅固穩定的陸地承載著堅硬殘酷的政治律令和世態炎涼的人情法則,是一個政治等級森嚴的冰冷的世界;河流因其深沉、神秘和寬厚的氣質容納著歷史的神秘和人性晦澀朦朧的欲望,是一個不帶偏見的為放逐者提供家園的溫情世界。《河岸》里的主人公們受命運的驅使奔突于這兩個空間,輾轉于歷史與命運對于人性的擠壓中。例如,庫東軒在岸上的世界被剝奪了政治身份,無法生存,不得已來到河流上定居,這種被放逐的命運徹底圍困住他,他拒絕上岸,但是他一次又一次把渴求的目光伸向岸上,他希望求助岸上的力量來幫助他恢復“烈屬身份”。他那被歷史塵霧徹底籠罩的神秘的出身,就像河流一樣成為永遠無法獲得真相的秘密。他原屬于岸上,但荒謬的時代和荒謬的政治徹底把他放逐到河流之上。小說的開頭,以兒子的視角洞穿父親在河與岸之間的命運沉淪。“我父親從岸上消失很久了,他以一種草率而固執的姿態,一步一步地逃離岸上的世界。他的逃逸相當成功,河流隱匿了父親,也改變了父親,十三年以后,我從父親未老先衰的身體上發現了魚類的某些特征”。魚的意象成為解讀庫文軒命運的一把鑰匙。在鄧少香烈士裝著嬰兒的籮筐里,嬰兒身下就有一條大鯉魚,“我父親就是那個懷抱水草坐在鯉魚背上的嬰孩”。父親馱碑投河之后,庫東亮潛入水底,找到了那塊碑,卻發現“石碑下的人影子已經不見了,我把手探到碑下,感覺到一個冰涼的寬闊的縫隙,里面似有生命,我的手背被輕柔地啄了一下,一條魚從碑下游出來,我看不清那是一條鯉魚還是草魚,它的游姿輕盈而歡快,嗖地一下,就從我眼前游走了。我去追那條魚,很快就失去了方向。我不是一條魚,怎么追得上一條魚呢?就這樣,我眼睜睜地看著它游走了,我覺得那是我的父親,那一定就是父親,父親消失在河水深處了”。那么魚與河流是怎樣的關系?在蘇童那篇《河流秘密》的隨筆里,“一個熱愛河流的人常常說他羨慕一條魚,魚屬于河流,因此它能夠來到河水深處,探訪河流的心靈”“這是河流的立場之一,它偏愛魚類的眼睛,卻憎恨人的眼睛”。庫文軒最后由人幻化成魚的過程,正是一個逐漸被陸地遺棄而被河流接納的過程。主人公庫東亮也是在河與岸中奔走,他的溫暖的童年記憶在岸上,但隨著父親失勢,父母婚變,他隨著父親奔向船與河流。這是一次永遠的放逐。在船上航行的日子里,面對寬闊的河床中流淌的河水,他依稀感到自己生命不過像一灘水漬,脆弱而渺小。但當他回到岸上,他又覺得自己不如一條狗,因為狗還有個窩。他意識到只能回到河里。河上的生活使他連走路都變成了外八字。而岸上卻有他的母親,他心中的愛人,岸上構成一種永遠的誘惑,他一次次不顧父親勸阻回到岸上,可每次遭遇的都是誤解、歧視、羞辱、暴力,甚至是死亡。開始是人民理發店在告示中對他的徹底驅逐,“即日起禁止向陽船隊庫東亮進入本店”,當他錯失了搭上開往“幸福”之地的汽車后,他便永遠失去了擺脫河流重返岸上的機會。結尾的象征意義是非常明顯的,傻子扁金寫的驅逐告示,“即日起禁止向陽船隊船民庫東亮上岸活動!!!”這份由傻子書寫、但格式規范、措詞嚴肅強烈的告示徹底將庫東亮驅逐到河流里。傻子扁金也成為當時那個荒謬時代的象喻。庫文軒父子二人最后的命運竟然殊途同歸,雖然二人走向河流的過程與路途完全不同,其間糾纏著父子沖突,但河流卻成為二人永遠的棲身與救贖之地。慧仙也是一個在河與岸之間奔走的人物,她有著同樣神秘的出身,她出生于岸上,卻因母親失蹤而被河上的向陽船隊收留,在河上長大,一個偶然的機會,使她重回岸上,但由于她無法適應岸上的人情世故,而被掃入社會底層,雖然她最終留在岸上,但那種與岸上現實生活的格格不入卻標識了她的整個人生。
《河岸》還是一個有關現實與歷史、放逐與尋找的故事。整個故事的緣起就是庫文軒的現實政治身份的被剝奪。這個光榮的“烈屬”身份被罩于重重的歷史迷霧中,僅憑屁股上一個魚形胎記來認定。在文革那個荒謬的年代里,一個虛幻的政治身份卻成為個體命運的主宰。庫文軒因獲得這個身份從孤兒成長為“油坊鎮”的最高領導,卻也因喪失這個身份而成為被迫隱匿在河流上的賤民。從庫文軒戲劇性的命運遭際中,我們看到歷史的魅影對于現實的主宰。然而歷史的真相也如同河流的真相一樣,任憑編織什么樣的網都無從打撈。庫文軒屁股上的胎記、傻子扁金屁股上的胎記和油坊鎮居民屁股上各種以假亂真的胎記都暗示了歷史的各種可能性。正因為歷史真相的缺席,才使得歷史成為一個巨大的真空,可以被形形色色擁有話語權力的人進行填充。文革工作組的人可以憑借道聽途說、猜測想象就輕易剝奪庫文軒的政治身份,而庫文軒在失去這個歷史身份的庇護之后,竟然落魄到只能像“魚”一樣茍且偷生。重新挽回這個歷史身份就成為庫文軒活著的唯一信念,他除了不斷四處寫信請求平反,還在河流上通過憑吊烈士的圣潔儀式來獲得假想的身份。他的結局充滿深意,他在走投無路之際,馱著歷史紀念碑投入水中。烈士紀念碑正是歷史的物化形式,庫文軒最后的死亡姿勢暗含著他對虛幻政治身份的執著和悲劇性的追尋。與庫文軒偏執追尋政治身份相對應的是庫東亮對于歷史的恍惚與神秘充滿了迷惘。小說中多次描寫了庫東亮的幻覺,歷史的鬼魂鄧少香多次從河里爬到船上,雖然每次形態各異,有時甚至溫情脈脈,甚至留下“水跡”和“紅蓮花”象喻歷史的蛛絲馬跡,但始終沉默不語拒絕透露歷史的任何秘密。對于歷史,她雖洞察一切,卻既不寬恕也不批評,三緘其口。具有吊詭意味的是,這個歷史的鬼魂唯一透露的是卻是人物的悲劇性的現實命運,那就是化身為魚,真正與河流融為一體。非常值得一提的一個細節是,庫文軒身體的“魚形”胎記到了后來居然“魚的頭部和身體已經褪色,幾乎辨認不出了,只剩下一個魚尾巴,還頑強地留在松弛蒼白的皮膚上”。如果聯想到“胎記”政治學,對于庫文軒那種“不停戰栗,老淚縱橫”的過激反應就不會驚訝了。正如庫文軒所言,這是 “在銷毀證據”,割斷與烈士“奶奶”的聯系,割斷了確認現實身份的歷史印記。從這個意義上講,現實身體胎記的褪色已經跨越了身體本身,上升為一種政治倫理學,直接指向歷史幽秘的存在。
《河岸》還是一個成長的故事。小說以主人公庫東亮的視角敘述了青春成長的經歷。與蘇童筆下的其他“成長”故事一樣,這是一段充滿陰郁色彩的殘酷的青春記憶。庫東亮由于父親政治牽連,得到一個奇怪的綽號“空屁”,正如七癩子的姐姐所言,“庫文軒是階級敵人,他現在算個屁,你是屁的兒子,連屁都不如,你就是一個空屁”。在一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里,階級敵人身份的認定就相當于排除出“人民”的范圍,甚至是“人”的范圍,身份就是一個無,相當于一個“屁”。而連“屁”都不如的“空屁”更是一個無所依恃沒有價值的虛無,“它有空的意思,也有屁的意思,兩個意思疊加起來,其實比空更虛無,比屁更臭”。把一個存在的個體等同于虛無,本身就是對于人的絕大的侮辱。然而失去了社會與父母護佑的庫東亮卻愿意承認自己就是空屁。在他成長的那段青春歲月里,“空屁”不僅成為別人和他對于自己的稱謂,更是成為少年心中不敢面對現實從而放縱自己、逃避自己借口。當他面臨感情和責任的難題,深感無能為力時,他總在自怨自艾:“我什么也做不了,我什么用也沒有,我什么也不是,我是空屁,空屁。”這種四處受挫、飽受非難的成長經歷甚至使他開始質疑幸福的可能,“都是空屁,是空屁,哪一種生活都不好!”“空屁”像影子一般如影隨形地附著在庫東亮的精神世界中,“空屁”所象喻的價值虛無成為少年庫東亮真正的成長悲劇。在這個成長故事里,被壓抑的身體欲望也成為蘇童小說著力描寫的部分,正處于青春期的庫東亮對于慧仙的喜歡,使他的身體不斷處于情欲不能滿足的煎熬中。由于文革時代普遍的禁欲氛圍,再加上父親庫文軒對于兒子身體發育變化的過度監視,庫東亮對于自己的身體充滿了“不潔”和“罪惡”的感覺。更有意味的是,庫東亮親眼目睹了父親自我懲罰、棄絕欲望的自我閹割,這種被閹割的恐懼成為他始終揮之不去的青春夢魘。為了平息這種情欲的沖動,他多次上岸,多次忍受眾人歧視和羞辱,然而最終換來的卻是暴力、傷害、父子失和。故事的結尾也是深有寓意的,庫東亮深愛的慧仙雖然沒有接受他的感情,卻把自己最為珍視的“紅燈”留給了他,這只燈是安慰,是溫暖,也是照亮,這也許是成長少年未實現的愛情夢想的最后一個光明的尾巴。在有關“成長”的敘述里,“奔跑”同樣是個值得注意的意象,在庫東亮成長的路途上,處處都留下他疲于奔命奔跑的身影。他被別人驅逐、被別人呵斥、被別人威脅時,他在奔跑,他被父親責罵、被母親遺棄、被慧仙誤解時,他也在奔跑。特別是各種矛盾紛紛激化的那一天,他的腳步就沒有停止過,“我驚魂未定,身體各個部位都疼痛難忍,但我一直堅持在跑。恍惚中我覺得自己這樣奔跑了很多年了。我從不練習跑步,可是我從小到大一直在經歷各種各樣的險情,必須拼命地奔跑,不跑不行”。奔跑已經定格成他為成長的一個悲愴的姿勢,岸上沒有家,河上的家又不能回去,兒時的家早已在政治的風雨中另易其主,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他停下腳步,安頓他的苦難,沒有一處幸福之地可以讓他奔赴。正是無處棲息的“奔跑”意象,把庫東亮塑造成一個 “局外人”的形象,“他不太關心肉體與靈魂,人類與自然的區別;這些思想會產生邏輯思維和哲學,他對于兩者都排斥。對他來說,惟一重要的區別是存在與虛無。”[1]
綜上所述,《河岸》的真正意義在于,它通過建構一個豐富飽滿的意義空間,探討荒謬處境下靈魂的放逐與追尋,在曲折幽微的人性表達中復顯那段未曾真正遠去的歷史。
[1] 科林·威爾遜.局外生存[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20.
[責任編輯:惠人]
Exile and Pursuit between River and Banks——Interpretation of Novel “River Banks” by Su Tong
GAO Xiao-hong
(SchoolofHumanities,Dal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Dalian, 116023,China)
In the novel “River Banks” by Su Tong, the river and the banks are opposite spaces with referential meaning. The world of banks is a real world ruled by politics, while the river is a world marginalized and exiled by politics. “River Banks” is a story about reality and history, exile and pursuit, and it is also a growth story.
opposite spaces; exile; pursuit; growth
2016-09-15
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地域文化視角下的當代遼寧女性文學創作”(L11DZW014);大連理工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性別視角下二十世紀文學底層敘事中的民生情懷”(DUT14RW205)
高小弘(1976- ),女,內蒙古烏海人,副教授,博士。
G632.3
A
1008-388X(2016)04-006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