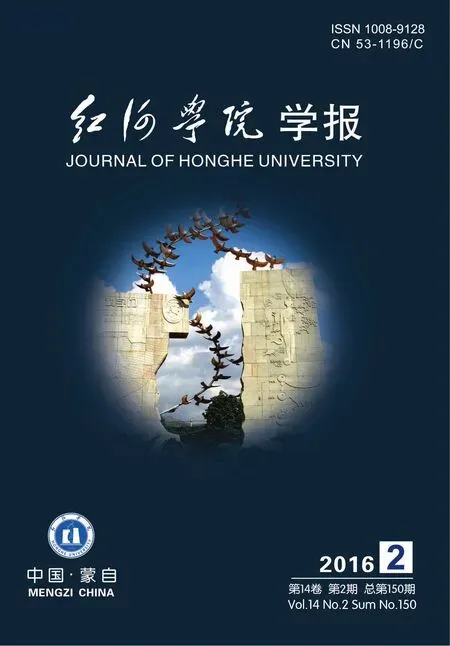華員心態與民族主義:以滇越鐵路警察為視角
陳 力
(云南大學,昆明 650500)
?
華員心態與民族主義:以滇越鐵路警察為視角
陳力
(云南大學,昆明 650500)
摘 要:在外國勢力把持的機構中,華人屬員由于民族主義與生活現實的并存,普遍帶有既對抗又妥協的情緒,即華員心態。滇越鐵路系中法之爭的產物,因而滇越路警這個群體,從誕生之日起,便不可避免地帶有這種華員心態。出于維護主權的需要,滇緬路警具有民族主義的天然屬性,但在法國勢力把持的滇越公路中,民族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對抗,呈現出曲折的局面。華員化心態的消漲,最終決定了滇越路警的興衰。
關鍵詞:滇越鐵路;鐵路警察;中法之爭;華員心態;民族主義
一 華員心態:現實中的民族主義
晚清以降,外國勢力對中國的控制,往往通過間接的方式來實現,其表征為:通過把持中國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事業、機構,借管理和營運為名,為其殖民政策的實行提供方便。自此,中國的內政與外交出現合流的局面。長期為袁世凱幕僚,歷仕大清、北洋的張一麟因而感嘆:“清之亡,實亡于庚子而非亡于辛亥,八國聯軍之后,一切內政無不牽及外交”。[1]事實上,在清朝風雨飄搖的最后數年內,早有人注意到這個情況,批評當局“不知六十年內,內政之失,所以啟戎心,而招外侮者”。[2]
這種情況,并未因為清朝的滅亡而有所改變,相反,軍閥割據,南北混戰的局面,使中國的國家機器更加零落,外國勢力對中國各國家機構的滲透,可謂變本加厲。國人此時已認識到,內政把持在外人之手,將導致國家在外交上處處被動,“外交建筑于內政之基礎之上,隨內政之變化,以為轉移,內政腐敗,外交固將破壞,內政不良,外交亦將失其效用”,因此,外交上要爭國權,必先整頓內政,“就我國而言,國民政府北伐成功之先后,一時整飭綱紀,革新內政,……因之當時之外交,亦頗能打破從來不良之因襲,獲得相當之進步,如收回九江租界地,提議修改不平等條約等”。[3]
正如羅志田的觀察,在近百余年的紛亂局面中,始終存在一條潛流生生不息,“雖不十分明顯,卻不絕如縷貫穿其間,這條亂世中的潛流便是民族主義”。[4]民族主義在整個近代中國社會中有著深厚的根基。在時人看來,國權之不爭,主要在于內政不修。內政之不修,又主要因為外人的掣肘:“凡獨立自主的國家為保全他的尊嚴與主權,絕對不許外國過問他的內政。……健全的國家及健全的國民沒有不承認這個道理,外國干涉內政是‘國恥’,勾結外國干涉內政是‘賣國’”。[5]
在此大環境下,外資鐵路、海關等操之在外人之手的半殖民機構,無疑處于輿論的風口浪尖。在九一八事變前,就有國人質疑日本經營滿鐵的真正目的,非為發展商業,而是“循輻射形四向發展,實行其蠶食鯨吞之預定步驟!”[6]1924年,孫中山強行收回粵海關,結果引致列強干涉,軍艦開進廣州示威,并派兵登岸占領海關大樓。此舉令民情大嘩,民國以來“全國高等專門以上之學校,不下數十百所,人才濟濟常浮于事,固無庸外人代吾任行政細事”,[7]力主逐步革除海關管理層中的外人。這種限制外人的看法,在當時附和者眾,有人痛心于海關“主客易位,而洋員之跋扈愈不可制矣”的局面,要求將海關稅務司中洋人的數量限定為只占三分之一,且“其待遇與華員一律平等”。[8]
值得留意的是,在這些由外人控制的機構中,除了少數管理和技術人員外,基層員工絕大多數為華人(時人一般稱其為華員)。以身份而言,他們作為機構內的一員,對上級有服從的義務,以感情而言,他們作為民族的一份子,對外人有對抗的天性。他們處于現實生活與民族感情的夾縫之中,成為半殖民機構與中國民族情緒交鋒的最突出的矛盾體。
在這些機構中,管理層為外人壟斷,華員升遷機會極其渺茫,多半從事的是外人不愿為、不屑為的厭惡性工種,待遇也與洋員有天壤之別,處處受其欺辱,華員在這些機構中,具有天然的反抗性,如1928年,海關華員聯合會就公開要求收回關稅自主權,其中一個原因便是“既憤列強之攘奪稅源,外商之壟斷稅款,客卿之把持稅收。復慨在同一機關服務,待遇不公,備受痛苦,貽中華國民人格之羞”。[9]
每每在國難深重的關頭,華員的對抗性便為民族情緒所激發,往往采取罷工、辭職等方式抵制所服務的機構。在淞滬會戰前后,在上海的日商洋行、銀行的華員“多自動辭職”,“即一部因生活關系,暫時工作者,亦已準備脫離”。[10]遠在千里外的香港,日商的洋行也出現同樣的情況。[11]
民族情緒的高漲,也在迅速改變著大眾對華員的觀感,華員大有形同賣國賊、漢奸之勢。安徽蕪湖的學生,曾要求“通告各日商洋行里工作的華人,即日起自行退出洋行。否則,一經查出,以賣國論罪”。[12]上海市各界抗敵后援會的宣傳大綱中,也明確要求:“全國同胞,一致拒絕為日人服役,已服役者即日脫離”。[13]
然而,在中外合辦的機構中,民族情緒的釋放便要謹慎許多,在九一八事件后,據供職于本溪煤鐵公司的華員張大焱稱:“是時,我國職員皆以公司既為中日合辦,不忍放棄國應有之權利,故凡未經日方提出停止出勤者,大多數均忍辱照常供職以待政府之交涉”。[14]
在外人勢力較大的地區,忍辱生活反而是常態。國聯調查團在東北調查期間,就發現面臨“頗多困難”,“一般證人望風卻走,諸多華人,甚至有不敢與調查團團員一面者,以故與各界交談,殊匪容易,非秘密約會不可”。[15]有東北華商私下向國民政府控訴,“我商民被迫而屈服于惡政之下,……陷入畏懼忍辱狀態”。[16]
因而,有華員表示,留守在外資機構其實也不失為一種曲線救國之道:“洋行華員主要握著中國輸出入貿易的命脈的地位,我國與友邦之間的物資需給關系,敵國對于我國的物資依賴關系,都是最明白不過的人們。在這時候,我們應該與友邦作如何的戰時貿易的調整,對仇貨應該怎樣杜絕,對于以糧食和原料資敵的現象怎樣消除,洋行華員實在都有無限重大的任務”。[17]
這種言論,是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的。外資機構的華員出于義憤,選擇退職之后,這帶來另一個現實問題,他們的生活如何處置?洋行華員聯誼會對此作過粗略的統計,在日資機構的華員不少是“工程師、翻譯、機器工人、會計員、調查員等,他們除了各人有特殊技能以外,一般的他們大半能說日語”。而當時的國民政府,對退職華員并無針對性安排,僅有“精神上獎嘉和鼓勵”,這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因此,洋行華員聯誼會提出,當局“應當趕緊量才使用,替他們找工作,并且要保證他們的生活權利”,否則,“如果他們看見已退職的華員,社會對他們很冷淡,生活絲毫沒有保障,那么他們覺得只有一條路——違著良心替敵人干下去!”[18]
現實生活的壓力,始終是制約半殖民機構里的民族情緒的最大因素,抗戰期間,經濟破敗,物價升騰,生存壓力非前代可比。施廷鏞便因為生活困難,無奈之下,往投“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盡管其意識到“圖解決個人糧食問題而去準備銀行工作,失去了民族氣節,豈不是幫了敵人的忙”,[19]然而,現實卻迫使他作出如此選擇。
國人這種矛盾心理,早為外人洞察,日本特務稱:中國民眾“他若國事民生一概不顧,雖一小部分尚能顧全大體而謀向上,均屬居近下層,無米對炊以致英雄無用武之地”。[20]可見,中下層人民尚有民族氣節,但礙于現實條件,不得不忍辱生存。
上海淪陷之后,日本全面接管市內設施,中國第一大都會的數百萬人口,在某個程度上,俱成為了“華員”性質的群體。此時的民族情緒,逐漸趨于理性。《立報》指出,守備上海的偽軍“大部分是為生活所迫,為權威所脅,他們并沒有失去靈魂,只要經過相當的說服工作,可以使他們撥亂反正的”。[21]有人注意到很多底層市民,“這些人跟高級漢奸不同,他們往往由于生活所迫而毀滅自己的良心,出賣民族[22]”,如果加以救濟改善其生活,就能避免其誤入歧途。1943年被戴笠發展為軍統一員潛伏至汪偽政府的周佛海,戰后為廣大被打成“漢奸”的基層職員鳴不平:“至于中下級職員,或為生活所迫,或為敵威所逼,……出而任事均系不得已或有所為,其情可憐,其心亦可憫”。[23]
徘徊在服從與對抗,周旋于外人與民族之間,正是華員心態的明顯特征。
二 民族主義的溫床:中法之爭與滇越路警之設
滇越鐵路警察的設立,主因在于中法滇越鐵路之爭。甲午一役后,日本勒索甚巨,清廷乃求助于列強。在德、法、俄三國干涉下,日本最終放棄割讓遼東的要求。不料,前門驅狼,后門引虎,德國、俄國以還遼有功為由,先后強租膠澳、旅大。1898年,法國乘機向清廷提要求“允準法國國家或所指法國公司自越南邊界至云南省城修造鐵路一道。……中國國家所應備者,惟有該路所經之地與路旁應用地段而已”。[24]在威逼之下,清廷同意此請求。法國便迫不及待派人沿途勘探調查,準備開路。時逢義和團大熾,神州掀起排外仇洋浪潮,勘察遂告中止,路事暫時停頓。
運動平息后,法人卷土重來。中法雙方商議鐵路章程,按照原議,法方出資出工,中方為地主,利益應當均沾。但實際上,法人毫不顧及中方利益,1901年7月5日,法國政府與東方匯理等數家銀行簽訂合約,決定成立法國滇越鐵路公司,負責修造、經營滇越鐵路,資金均由法越殖民政府提供,合約中還明確規定:“此公司應照法國律例辦理。其督理之人,均須法國人氏”。[25]獨占之意甚為明顯。
在中法雙方交涉鐵路章程時,滇撫魏光燾發現“滇中借地助工,而(章程)于中國應有權利一未之及”,遂向法駐滇領事方蘇雅(Auguste Francois)對質,方蘇雅言辭閃爍,似有推諉意。外務部指示魏光燾,需要法方保證中國在滇越鐵路上有以下利益:“運送水陸各軍及軍械糧餉賑濟等事,車價應減半,遇有戰事,不守局外之例”;“此路應訂明若干年限,即歸中國管業,或先期若干年,照原修值買回”;“每年納路稅若干”等項。[26]
法方對中方的要求,大部分表示同意,惟于“限期收回”和“分利”的要求,則一口拒絕。雙方相持數月,法方終于作出讓步,同意經過一段時間后,“可由中國議收”,同時允諾借200萬法郎予中方作向地方買地之用,不取利息。中方經過考慮,決定不接受法方借款的提議,改為“公司股票,中國亦可任便購買”,清廷此舉,可謂思慮周延,一旦股票可自由賣予中方,“如將來購股票較多,籍可收回權利”。[27]
雙方于1903年10月29日簽訂《滇越鐵路章程》。
可見,中法雙方圍繞滇越鐵路路權的斗爭,從一開始就存在。法方表面上以企業的模式營運,但實際卻是以政府為后盾,企圖長期獨占該路。中方則著眼于長遠,想方設法為收回鐵路作好鋪墊。
中方最關心的,除了滇越鐵路的歸屬權之外,便是其用途。1899年6月26日,云貴總督崧蕃上奏清廷,痛陳滇越鐵路的弊害,言辭懇切:“滇省西南邊界,雖與滇越接壤,然重巒疊嶂,洋人來此頗不容易,所以不惜重資,急于興路者,蓋以鐵路修成,必設保路之兵,以后征軍運糧,均惟其所欲,恐滇省鐵路一成,川黔湘廣各省必定接續開辦,此時若不阻擋,將來更無阻擋之時,竊恐鐵路所至,即彼族兵力所至,更恐兵力所至,即彼族侵占之所至。興言及此,涕淚交零”。[28]
針對這種憂慮,在《鐵路章程》第15條作出規定:“該公司亦可會商駐蒙大員,自行出資招募本地土民充當巡丁,以保護各廠平安。并可延請中國人或外國人充當巡捕長、管帶,擇要駐扎,以資彈壓。如遇事故本地巡丁不能彈壓,一經該公司人員稟請,滇省大吏即當遣派官兵,前往彈壓保護。該公司所招募本地巡丁,責任但為巡查各廠,彈壓工匠、人夫。一俟路成后,此起兵丁自可以隨時修補道路,其費亦由公司發給。倘有民情不平之事,保護鐵路工程乃系地方官專責。無論出有何事,該公司總不得請派西國兵丁”。[29]
從條文來看,中方嚴格限制法方利用該路作軍事用途的可能。法方組織的巡丁,只有處置鐵路工人的權力,活動范圍也僅限于工廠,巡丁的組成,也僅限于招募本土華人。但百密一疏,此條文還是留下一個隱患,即將鐵路的執法權,交由鐵路公司負責。鐵路公司自聘巡捕(此時中國尚無警察制度,巡捕即行警察權),巡捕又可以在鐵路要地駐扎,只要不涉及與地方民眾的糾紛,鐵路的治安大權基本上落在公司之手。
《鐵路章程》頒布后,滇越鐵路正式動工。大權獨攬的法國滇越鐵路公司,實際上把該路變成了獨立王國,1904年,有人向清廷奏陳種種弊端,清廷派時任云貴總督丁振鐸負責調查,一向畏懼法人的丁振鐸竟向清廷報告:“沿路并無法兵。公司設洋巡捕十名,系專為約束洋人起見”。[30]
然而,丁振鐸的復奏,與民情卻有很大的差別,當時滇境流行一句諺語:“越路短,滇禍緩;越路長,滇速亡”,此語“滇中三尺童子知之”。[31]可見此路威脅之大。
有理由相信,丁振鐸隱瞞了實情。1907年,滇籍留日學生楊振鴻受同鄉所托,沿鐵路線考察,發現“彼沿路二百余工所、白藥所,儲蓄槍彈,無慮數千”,甚至有的工所中竟由法國陸軍上尉駐守,已變質為“駐防之先聲”的兵站。楊振鴻在蒙自城外,“見一法國憲兵駐屯所,內房約十余間,門外站立憲兵四系法人,四系越人,均著軍服,……其內有多數兵士”。滇越鐵路沿線的中國領土“已形同占領”。[32]
楊氏的觀察,也為他人證實:“自河口至云南省城,法人沿所勘定之鐵路線,或三里,或五里,遇有阨塞之處,必建一碉樓,……其碉樓之高闊,可望十數里,布置周密,已成連營千里之勢。……且彼所用鐵路工頭,皆帶兵武官,一旦時勢可乘,……只化工為兵,已足直搗省城”。[33]
法人的記述也在某個程度上印證了這個事實,公司為員工興建的所謂住處,有的“格式全是新樣,并且堅固。墻壁多用沃土及石灰為之。墻之外加以鐵柵欄,稍為堂皇,而且舒展”。[34]顯然超出了當時一般住房的標準,頗惹嫌疑。
丁振鐸偏袒洋人的行徑,激發了滇人的抗爭,留日學生在其中出力尤多。1906年7月,留日學生公推李根源、吳琨、由宗龍為代表,“赴京告訴總督丁振鐸誤滇罪”,“至天津見直隸總督袁世凱”,[35]面見清政府高層。1907年初,貴州提學使陳榮昌亦參劾丁振鐸,種種情況,令清廷對丁振鐸起了疑心,密令湘撫岑春煊暗中調查,岑春煊遂派沈祖燕前往云南密查。
沈祖燕在滇越兩地作實地調查,證實了法人確有借路引軍的企圖:“路工未竣,法人已屢有中國保護不力,須自派兵來華之說,……其心本不測,……反謂我之不能護路,而逞其朝發夕至之兵,以直入省城,可以惟所欲為”。[36]最終,清廷決定以錫良代丁振鐸接掌云貴。
錫良上任后,向清廷奏稱:“滇越鐵路公司不宜設巡丁,以礙主權”。[37]可見,此時中方已經認識到,《鐵路章程》中關于鐵路執法權的讓渡,實際上留下了國防上的隱患。
時人認為,若要挽救局面,最徹底的辦法,便是收回滇越鐵路。
1908年6月,滇籍京官吳炯上奏督察院,稱“近日法人舉動,則無一不為軍事上之經營”,建議清廷,“所有由滇省邊境至省城鐵路,歸中國收回自辦”。[38]
滇人亦紛起,要求政府贖回滇越鐵路:“不趁早贖回,將來的下場,還不如東三省呢,……如今我們大家不爭氣踴躍集股,求政府將此路贖了回來,將來一亡,便要先做安南人的奴隸,才到法人的牛馬呢!”[39]
《鐵路章程》第34條規定,只有在80年期限屆滿后,中方才能提出收回的要求,且應償清法方造費、人員工資及股息。雖然附件中有中方購買該鐵路股票“均準任便購買”的規定,從鐵路的造價高達5370萬兩白銀的情況來看,要在市場上大量收購其股票,顯然需要一筆巨資。因而,有人清楚地認識到:“鐵路能否贖回,又視吾云南之資力為斷”。[40]
就當時而言,滇省的財政面臨巨額赤字,各項新政相繼舉辦,又增不少開銷,可謂舉步維艱。1909年接任云貴總督的李經羲,向清廷報稱:“綜計滇省歲出各款,需銀四百余萬兩,省庫歲入各款,近則僅有二百余萬。出入相懸,所虧至鉅。……從來官中籌款,無非取自商民,……兵荒以后,元氣頗傷,禁煙之初,生計尤蹙。……閭閻形敝不堪,……民力既竭,商困莫蘇”。[41]
以滇省官、商、民的財力觀之,贖路一策并無可行性。駐法公使劉式訓在回復留日滇籍學生的函中,表示:“善治國者,非強鄰逼處之為患,而無備之為患。善用兵者,毋恃敵之不來,恃我有以待之。吾誠內政修明,武備整飭,才能奮與鄰交輯”。[42]從中可以看出官方的態度:鑒于其時國力有限,清廷不愿倉促收回鐵路,激化與法國的矛盾。
1910年1月,滇越鐵路修成。原按《鐵路章程》,巡丁之設,在于巡查工所,彈壓工匠,路既修成,工人紛紛遣散,巡丁亦應隨之撤銷,原本清廷派3營巡防隊負責守備鐵路沿線,“但每年所費不資”。于是,滇巡警道楊福璋、臨安開廣(蒙自)道龔心湛聯合提出,“仿照膠濟鐵路設立警察章程,于滇越鐵路各段安設鐵路警察,以期稍省經費”。
然而,此舉“本為定章所無”,滇方設立鐵路警察,無疑將法方原有自聘巡捕之權剝奪。因此當滇方派人與法領事商討時,“彼堅執原章不肯附設,辯駁再三,仍前執拗,籍故刁難,幾不成議”。李經羲親往力勸,“法領始允轉圜,并知設警保路為中國應有主權”。
法方最終同意,滇方可“設警于車站地內”,“車站之內每于車到時,須多派警察,至入站查緝,只派巡官率警察二名,其余警察均在站外守候,有匪鳴笛,即可入內幫同拿辦”。[43]
隨后,雙方會訂《滇越鐵路巡警章程》,滇越鐵路警察(簡稱路警)正式成立。縱觀路警的創設過程,始終伴隨著中法之間的明爭暗斗。法方通過《鐵路章程》攫取了滇越鐵路的警察權,通過暗度陳倉的手法,大量布置軍事力量于該路。中方在贖路不成的情況下,通過設立路警來維護主權。
正因為中法矛盾始終貫穿其中,這使得滇越路警在成立之初,便成為妥協性與對抗性交織的產物。
三 對抗與妥協:華員心態下的滇越路警
從《巡警章程》的條文中,明顯反映出滇越路警的折衷性質。
首先是其民族性:路警收回了滇越鐵路上的警察權,“滇越鐵路公司及中國人均應一體遵守”,“凡在車內搭客,暨車站工役人等,無論內外國人,均得隨時稽查”,“中國人在火車及車場或鐵路上有違犯規則及不正之行為,而警官未及覺察者,應由站員、車長告知警官,或送交查辦,該公司人等不能私行毆罰”。由于該路嚴禁運送軍火,路警還有權檢查貨物是否夾帶違禁品。路警分局局長有權“隨時附車調查一切事件,不論何時何站,利便登車,不論何等車位,均聽往來,該公司不得阻止”。
不過,其妥協性也是明顯的:1.路警對公司各洋員有“保護”的責任。2.路警平時不得在站內值守,只有在車進站時,方得進站執勤。3.路警的執法權有限制,如果犯人是“法國人或法國保護人或未與本國立約通商之外國人”,“其情節輕者即由警官知會車站主管之員分別處理”。情節重者,則報告巡警道查核,“并報交涉司或關道照會領事,按約辦理”。4.車站職員犯事,“應由警官就近告知公司車站主管之人分別懲戒”,情節重者,則報巡警道和涉司、關道照會領事處理。[44]
因此,官方和民間,對滇越路警的評價,頗趨于兩極。
在官方看來,設警于路,收回了鐵路的警察權,遏制了法人陰謀,維護了國家主權,為未來收回路權奠定了基礎,為中國的一大勝利。“滇越路警,原系用以保我土地主權而設,非為保衛彼外人之特別權利者。路警同人在此線上服務,因明了本身之責任,無不以收回路權為愿望,即教育警生,亦莫不亦此為目的”。[45]
鑒于該路“有關內政外交及國防軍事之重要”,進入民國后,路警機構雖然名稱有所變化,但就建制言,滇方一直使路警直隸于省府之下。皆因路警在中外合辦的鐵路中,不僅有維持治安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路警乃見漢家旌旗,是亦國權之收回者也”。[46]
在民間看來,路警的角色就不那么光鮮了。路警的所有開支,均由滇方承擔,按《巡警章程》,只有路警正局長才享有免費上車待遇,其他警察押車,費用“也要按人、按次、按月、按年計算,統由云南省政府負責”。[47]加上裝備、月餉等各種經費,每年開支高達20余萬元,可謂一筆不小的負擔。
因此,外交部特派員張維翰大力抨擊:“滇省政府對該公司所負之義務,已可謂至巨且重,而該公司對滇省政府及人民,直無義務可言。……警察負保護鐵路之責,而無行使職權之力。”[48]有人甚至稱,滇越鐵路的諸多護路人員,不過是替法人當“守門狗”而已。[49]連法國人也認為,滇省設警于鐵路,不過是“負保護這條路線的責任”,龍云借護路為名,而行“親法”之實。[50]
外界截然不同的觀感,實際上反映出滇越路警的尷尬立場:滇越鐵路為法方獨資籌建,耗資不菲,對法方而言,為重大利益所在,倘若護路不力,徒增法方干涉的借口。因此,保護法方的利益,是路警的首要任務,“設辦理不善,不惟不能達到行政目的,抑恐予外人以口實”。[51]
維護主權的理想,與受制于法人的現實,兩相沖突之下,便在路警中形成一種忍辱負重的心態:“既受法人種種無理之要挾,恒以個人精神痛苦之事小,國家主權維護之事大,上下一心,咸隱忍持重,以待時機之來臨,而將鐵路收復”。[52]
在實際執行任務的過程中,路警的這種心態更加表現無遺:
滇越鐵路公司所聘用的查票員,多以駐越的法兵充任,對待乘客異常兇蠻,“甚或商務小販,偶觸彼怒,竟將人與貨掀翻下車,當車疾駛如飛的時候!……此種現象,幾乎每月不免!自通車以來,屢因此而引起中法交涉”。[53]
1930年10月5日,由昆明開往阿迷的列車行至可保村時,有1名約莫7、8歲的中國女童在未買票的情況下登上四等車廂,被法人查票員葛阿德發現,葛阿德抓住該童后施以虐打。押車路警聞訊立即上前制止,“向該查票法人說明,如普通乘客,抗不買票者,可交查車隊,送交路警處罰,……不必如此野蠻”。
然而,葛阿德不聽勸阻,仍舊蹂躪女童,女童驚懼之下,往后面車廂跑去,葛阿德緊追不舍,其時列車正好駛入隧道中,漆黑之中,惟聽到女童慘叫救命,“聲音十分緊急,如臨死然”。駛出隧道后,“只見該查票法人喘氣并不見有該幼女”,眾人詢問葛阿德,其起初支吾不肯答,眾人一再逼問之下,葛阿德遂辯稱女童躲藏在某處。路警及乘客便在車上展開地毯式搜索,“暨車頂上車腳下,及火車頭內均已尋過”,卻一無所獲。
到達宜良后,押車路警急忙拍電至可保村路警分局,請其派人往隧道搜尋,亦無下落。眾人推斷,女童必然系被葛阿德推跌下車,為車輪所碾扎,一路摩擦掉落,以致無影無蹤。葛阿德這種獸行,實在天理難容,登時激起車上乘客憤怒,“欲將該法人捆綁由群眾處死”。此舉為押車路警所勸阻,路警提出“靜待政府提出抗議”。[54]一場慘劇竟以此種結局收尾,實在令人不勝唏噓。
路警遵照《巡警章程》向葛阿德曉之以理,希望制止其暴行,葛阿德卻置若罔聞,最終導致了慘劇的發生。最后當民眾提出要嚴懲葛阿德時,路警出面制止。這起事件中,折射出路警在執法上的困境,尤其當犯人系法方職員時。所謂的《巡警章程》,在法人眼中,根本毫無約束力,不過是一紙空文而已。難怪有人提出,“此種章程,實有取消重訂之必要”。[55]
滇越路警的存在,僅是在形式上體現了中國的主權,在實際上,路警在外人與國人沖突之時,往往采取妥協的態度,并未維護國人的利益。法方職員在鐵路上的胡作非為,并未因為路警的存在而稍有收斂,“時有橫加侮辱,推墮車客的事件發生,但乘車者,多系無權無勢的平民,雖身受痛苦,亦告訴無門,含憤忍受,敢怒而不敢言”。[56]
路警的忍辱無為,導致了民眾的忍辱受屈。民眾并不寄望于擁有執法權的路警能夠伸張正義,只能靠其他組織來表達訴求,如1931年5月24日,阿迷住民李青云之孕妻被法籍稽查員羅赫毆打致死。憤怒的民眾只能通過國民黨的黨務組織以表抗議。[57]
1937年11月1日,滇越鐵路全線的華、越籍員工舉行大罷工,原因是該年9月,公司以虧本為由,先后兩次減薪,津貼減少45%,薪金減少20%,員工曾呈文請求管理層收回成命,不獲理會,最終決定以罷工相逼。
員工與資方的矛盾,屬于公司內部事務,路警往往并不直接插手。如1933年8月,滇越鐵路準備裁減工人資薪,芷村鐵路工人密謀舉行罷工抗議。時任路警總局局長郭建臣下令,“派探嚴密偵查,并監視該工人等行動”[58],以“秘密調查”為主,目的在于查清“有無越南黨人及其他不良分子從中主動”,并非偏袒資方,而是避免事件政治化。
而1937年的大罷工,參加者眾多,且獲得輿論的同情,“此次滇越鐵路職工之突然罷工,固屬憾事,然其目的,純為要求維護原有待遇,……為貫徹主張起見,不得而已而出此,亦久無可以原諒和同情之處”。[59]
罷工造成極其嚴重的后果,鐵路運行幾乎全線癱瘓。
鑒于茲事體大,公司總管巴杜迅速與郭建臣相討對策。之前,公司對待工人訴求的態度可謂倨傲。而此次罷工,公司與路警總局會商后,態度趨向軟化,承諾“此事擬在一星期內解決,予各職工以圓滿之答復”。與此同時,各路警分局長“召集機械股、營業股職員及基路工人,說明此次解決辦法及情形,一方面并向公司交涉恢復原有所得工資”。[60]
由此可見,滇越路警在這起罷工風潮中,立場頗為明顯,是站在華、越員工一邊的,但亦不贊成員工采取罷工的手法,鐵路公司此前對員工態度頗為強硬,路警則從中起調解的作用,使對立的局面向理性的協商轉變。
僅1日之后,“在路警局出面調解后”,所有罷工工人于11月2日復工。從協商的結果來看,大部分員工可謂取得勝利,高級職員減薪10%,低級職員資薪則不變。[61]
路警在這次大罷工中,并未以保護法方利益為根本考量,而是站在民族立場出發,幫助罷工工人實現其合理訴求。體現出一定的對抗性和民族性,多少表現出滇方所謂的“維護主權”的形象。
四 華員心態的消漲:滇越路警角色的轉變
實際上,滇省政府對滇越路警設置的考慮,并非全以外爭國權為考慮。《巡警章程》規定,路警不能常駐車站,只有列車進站時,方能派巡官和警員進入稽查,而除始發站外,經停時間一般僅為10分鐘,最多也不過20分鐘。[62]如此一來,在路警的日常勤務中,稽查列車只占很小部分。
更多時候,滇省政府更重視路警對內的鎮壓作用,因為鐵道兩側15華里內均屬路警轄區,而滇越鐵路長達900余華里,所以路警“事實上乃滇省南防經常維系治安之中心機構,……對于附近各縣發生之匪患,十有八九多賴路警撲滅之。……沿線各縣之治安,恒賴路警之武力而震懾之”。[63]
路警兼顧地方治安,這便帶來另一個問題:如何協調與地方治安機構的關系。
車廂相對封閉的環境決定了犯人在得手后,往往不會久留于車上,而是離開火車逃諸地方。路警在緝匪時,如果限于轄區范圍,畏手畏腳,便不能收到效果。因而便需要路警和地方治安機構的“聯防”。[64]1934年8月,國民政府公布《地方警與鐵路警服務規則》,以協調路警和地方的關系,避免“執行職務時,每每發生事權爭執,影響公務”的情況。但該規則只規定地方警察在必要時,有權在路警轄區內執法,路警“應予以協助”[65],但并無界定路警在地方執法時,地方有否協助的義務。
因此,路警與地方治安機構沖突的風險,并未得到根除。
1937年,波普渡路警分局長商文正奉令調查鐵道路件失竊一事,前往文山縣擺衣寨搜查,閭長張興漢提出無理要求,雙方發生爭執,商文正率警毆打張興漢,并將其手槍搜走。不料此舉激起民憤,張興漢煽動民團圍攻路警分局,毆傷路警,并將分局內槍械等物搶掠一空,“行同盜匪,實屬野蠻”。[66]
此事件雖然肇于路警的野蠻執法,但地方民團的反應明顯過激。由此可以看出:第一,路警力量之羸弱,竟讓鄉團圍攻繳械。第二,路警雖直屬省府,為特種警察,但地位并不高,地方治安機構對其并不買賬。
滇越路警自1910年設立之初,便兼負內政外交責任,維持治安以絕法人口實,因此“槍械敷用,內容充實,是以沿路一帶,盜賊斂跡,外人稱許”。1921年后,滇省政局動蕩,“槍支損失罄盡”,后來稍有起色,但又適逢“金融紊亂”,“長警每月所得,幾至不能自存”。雖然滇省政府有心力圖振作,“終屬整頓乏術”。
1932年,滇省政府主席龍云便已注意路警的頹勢,稱其“沿途查車,均不盡職,形容亦極腐敗”,要求其迅速整頓,“以免貽外人非笑”。[67]
兩年后,情況并未改觀。1934年,滇省調查員王德明奉命視察各地路警。王氏指出,路警的員額不足,武器亦不敷分配,“試問以少數赤手空拳之警察,安能負茲重大任務?”裝備亦頗不足,諸如臥具、雨衣、外套等物,“均付厥如”。分局各房舍,均系清末所蓋,大多“已倒塌不堪住坐”,部分路警只能“結茅為屋,以避風雨”。在王氏看來,路警原代表國家形象,使法人不敢小視,“國家體面攸關”,[68]仍要求滇省大力整頓。
但路警的面貌始終未得徹底的改觀,1937年11 月22日,路警總局上報省政府,“所屬路警請改著軍服”。龍云斷然拒絕此要求,認為:“該局員警執行職務,只要認真辦理,與服裝無涉”。[69]對照同年被鄉團圍攻一事,配合龍云的答復,便不難理解,路警之所以要改換軍服,乃由于其權威已蕩然無存,執行職務起來,受到諸多掣肘,才想出此下策,以圖振作。路警之衰頹,從此亦可見一斑。
事實上,滇省對路警的待遇不可謂不隆,由于其直屬省府,除比照省會警察的資薪外,還另有煙瘴津貼,抗戰后,物價騰升,省政府還將路警的生活補貼照省級公務員待遇發給。王德明在視察中,也稱路警“生活比較安定,……月除伙食外,各警尚能稍有剩余”。滇越路警的種種待遇,相比起同時期的各縣警察而言,實在優越不少。[70]
可以合理推斷,路警的不振,物質待遇應非其主要原因。
筆者認為,導致此問題的根本原因,便是華員心態的應激作用:
在滇越路警成立之初,當時法人借路滅滇之言論大熾,因而,路警有維護主權的鮮明反抗性,是以士氣高昂,氣象一新。當滇越鐵路順利運營后,滇人普遍意識到,法國對云南的圖謀,主要以經濟利益為主,[71]法人經營滇越鐵路的目的,并非著眼于軍事用途,而是“謀擴張本國商品的銷路”,以及壟斷云南進出口的商路。[72]對法人軍事上的擔憂,便有所減退。
隨著歐洲戰云密布,法方不得不在亞洲進行戰略收縮,1936年2月,中法雙方對《鐵路章程》和《巡警章程》作出修訂:法方在管理層中增加中國顧問1名;鐵路公司每年撥出專款作為中國職工教育經費;法方物資除路用物品外,其他一律完稅;路警經費一部分由公司承擔。這次修訂,以法方讓步為主,顯示出其支配滇越鐵路的能力急速下降。
法人的主動步步退讓,使一直以保護為名,卻暗行對抗之實的滇越路警喪失了持續與之對抗的外力,其核心價值觀便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作為紀律部隊,其核心價值觀一旦發生變化,則往往意味著質變。1940年,日本進占越南后,滇省將該路河口至芷村路段路軌拆毀,遂撤銷了12個路警分局。此后,路警角色的轉型趨勢越加明顯,各地路警除了負責鐵路沿線的治安外,還有“聯合各鄉、鎮、保、甲清查戶口,防止奸宄混跡及盜匪潛滋之責”。[73]儼然已成為一般的地方警察。
從對外到對內,這種角色的轉變,促使滇越路警從一支旨在“維護主權”的特種警察,退化為一般的警察力量,已無力承擔“維護國權”的重任。1943年8月1日,國民政府宣布與維希政府(Régime de Vichy)斷交,同時宣布接收滇越鐵路。負責接收的交通部路政司長楊承訓抵達昆明后,首要便要求第五軍軍長長杜聿明派憲兵約百人,“開赴滇越鐵路各主要站點,俾于接收該路時監視法越籍人員行動,守護鐵路材料”。[74]國民政府舍近求遠,以憲兵替代路警以行護路之責,更足證路警已失去了象征國家主權的色彩,演變為一般的警察了。
縱觀滇越路警的興衰,其過程與“華員化”現象是始終貫徹一致的。
創設之時,乃是出于折衷應變的無奈之舉,為了抗衡法人,又忌于過于激進,惟有以警察之名,行主權之實。路警與法人雖有妥協,亦有對抗,形成了頗為矛盾的華員心態。然而,法人勢力衰微,路警的華員心態亦隨之消解,由特種警察向一般警察轉型,最終在不斷式微的過程中,完成了其“維護主權”的歷史使命。
參考文獻:
[1]張一麟.古紅梅閣筆記[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56.
[2]論內政外交之相關[J].外交報,1907(168):2.
[3]王之相.外交與內政[J].外交月報,1933,3(4):59-60.
[4]羅志田.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
[5]內亂與外患[J].現代評論,1925,3(55):1.
[6]田玉珍.抵制滿鐵與開發東省[J].三民半月刊,1930,4(3):2.
[7]衛深甫.海關用人行政權收回之步驟[J].現代評論: 關稅會議特別增刊,1925:21.
[8]張家棟.收回海關管理權之我見[J].太平洋導報,1926,1(24):31,34.
[9]海關華員聯合會請愿收回稅權[J].銀行周報,1928,12(5):6.
[10]八月份國內勞工消息[J].國際勞工通訊,1937,4(9):110.
[11]十月份國內勞工消息[J].國際勞工通訊,1937,4(11):97.
[12]張學恕.安徽青年運動史話[J].安徽青運史研究,1986(2-3):40.
[13]上海市檔案館.上海抗敵后援會[M].北京:檔案出版社,1990:374.
[14]本溪湖華員被日本壓迫離職[J].河南中原煤礦公司匯刊,1932(5):4.
[15]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節要[J].中央周報,1932(227):28.
[16]關東廳警務局長致拓務次官報告(1931年5月2日)[M]//滿鐵檔案資料匯編:第十三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345.
[17]楚辛.緊守自己的崗位[J].救亡周刊,1937(1):11.
[18]華光.救濟敵人企業機關的退職華員[J].救亡周刊,1937(2):19.[19]施銳.奮斗一生——紀念施廷鏞先生[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87.
[20]行政院秘書處為日本駐平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上關東軍秘密報告的箋函(1936年10月3日)[M]//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外交1.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250.
[21]李時新.上海立報史研究1935-1937[M].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2:218.
[22]趙康.爭取民族抗日戰爭的勝利[M].重慶:黎明書局,1938:94.
[23]周佛海.周佛海獄中日記[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80.
[24]法使致總署請準修滇越鐵路租借廣州灣并襄辦郵政照會(光緒24年3月19日)[M]//清季外交史料:第二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2183.
[25]海防云南府鐵路合同[M]//宓汝成.近代中國鐵路史資料:中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7:655.
[26]外部奏遵議魏光燾勘辦滇省鐵路請由該撫與法員妥議折(光緒28年3月15日)[M]//清季外交史料:第三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2498.
[27]外部奏議訂中法滇越鐵路章程折(光緒29年9月10日)[M]//清季外交史料:第三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2798.
[28]滇督崧蕃奏英法各員同時查勘鐵路縷陳窒礙情形請飭設法補救折(光緒25年5月19日)[M]//清季外交史料:第三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2294.
[29]滇越鐵路章程[M]//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第2冊.北京:三聯書店,1959:205-206.
[30]德宗實錄:卷528[M]//清實錄:第59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32.
[31]特參司道大員奸邪柔媚貽誤疆臣折[M]//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9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1:777.
[32]志復.滇越邊務及鐵道之實況[M]//云南雜志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518-522.
[33]蟄生.游滇述略[M]//云南雜志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382.
[34]蘇曾貽.滇越鐵路紀要[M].1919年12月刊本:44-45.
[35]李根源.雪生年錄[M].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23.
[36]沈祖燕.奏派云南查辦事件稟稿(光緒33年6月)[M]//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9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1:793.
[37]德宗實錄:卷576[M]//清實錄:第59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625.
[38]云南京官吳炯等呈督察院文(光緒34年5月)[M]//宓汝成.近代中國鐵路史資料:中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7:672.
[39]對鏡狂呼客.為滇越鐵路敬告吾滇父老兄弟[J].滇話報,1908(1):17.
[40]無己.滇越鐵路贖回之時機及其計劃[M]//云南雜志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481.
[41]滇餉奇絀懇飭籌撥的款折[M]//滇事危言初集.北京:毓華印書局,1911:85-86.
[42]劉式訓.復留日滇學生書[M]//滇事危言初集.北京:毓華印書局,1911:56.
[43]滇督李經羲咨外部滇越鐵路設警事法領業已認可擬訂試辦章程文(宣統元年10月22日)[M]//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10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1:518.
[44]滇越鐵路警察章程[M]//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10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1:518-520.
[45]續云南通志長編:中冊[M].云南省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86:49.
[46]王丕承.路警之性質[J].路警周刊,1926(2):2.
[47]朱家修.我了解到的一些滇省外事[J].大理州文史資料,1989(6):220.
[48]張維翰.擬呈另訂中法商約及改善中法關系意見書[M]//續云南通志長篇:下冊.云南省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86:102.
[49]盛襄子.法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的滇越鐵路[J].新亞細亞,1932,3(6):52.
[50]馬宗融.法人口中的云南[J].人民周報,1932(37):14.
[51]王德明.視察滇越鐵路警察報告書[J].云南民政月刊,1934(8):15.
[52]續云南通志長編:中冊[M].云南省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86:49.
[53]滇越鐵路紀聞[J].津浦路月刊,1931(7):13.
[54]滇越鐵路查票法人戕害華人[J].津浦路月刊,1930(1):21-22.
[55]蔣用莊.關于修改滇越鐵路章程的幾個建議[J].正論,1935(45):12.
[56]老侃.滇越鐵路[J].華年,1934,3(30):593.
[57]阿迷黨部為法人在滇越路槍傷工人毆打孕婦之通電[J].云南半月刊,1931(8):29.
[58]滇越鐵道警察總局訓令第564、573號[M]//云南工人運動史資料匯編1886-1949.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335-336.
[59]社論:滇越鐵路職工罷工[M]//云南工人運動史資料匯編1886-1949.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338.
[60]云南工人運動史資料匯編1886-1949[G].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337-338.
[61]云南工人運動史資料匯編1886-1949[G].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336.
[62]滇越鐵路客車時刻表[J].旅行便覽,1943(2):1.
[63]續云南通志長編:中冊[M].云南省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86:49.
[64]王丕承.路警防務與地方警察防務之聯絡[J].路警周刊,1928(68):2.
[65]地方警與鐵路警察服務規則[J].內政消息,1934(2):111.
[66]訓令文山縣長、滇越鐵道警察局長據楊視察員呈擬查明文山亦樹柯鄉團與路警沖突案解決辦法核飭遵照[J].云南民政月刊,1937(37):30.
[67]民廳指令滇越鐵道警察總局呈復路段軍警情形[J].云南省政府公報,1932(576):2.
[68]王德明.視察滇越鐵路警察報告書[J].云南民政月刊,1934(8):15-18.
[69]云南省政府指令:秘一民字第一一四三號[J].云南省政府公報,1937(101):28.
[70]李迪俊.縣公安局及其局長[J].時事月報,1929,1(1):17.
[71]云南在法國經濟獨占中[J].滇聲,1935(2):44.
[72]原勝.法國向華侵略與云南的經濟危機[J].太平洋月刊,1935,2(3):38.
[73]續云南通志長編:中冊[M].云南省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86:49.
[74]曾養甫抄送楊承訓接收滇越鐵路經過詳請報告呈(1943 年9月2日)[M]//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財政經濟10.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325.
[責任編輯 自正發]
The Chinese Servants Mentality and Nationalism:A Study Based on Yunnan-Vietnam Railway Police
CHEN Li
(Yun 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China)
Abstract:In the institutions that dominated by the foreign force,the Chinese servants were contradicted because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colonialism.Since the Yunnan-Vietnam Railway was the result of the gaming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the railway police was set up as a power stand for the sovereignty of China.But in pratice,the railway police had to obey the order of the Franch company.This complicated situation is worth of further study.
Key words:Yunnan-Vietnam railway;Railway Police;The confilct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Nationalism
作者簡介:陳力(1987-),男,廣東廣州人,碩士生,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
收稿日期:2015-08-06
DOI:10.13963/j.cnki.hhuxb.2016.02.004
中圖分類號:D8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9128(2016)02-00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