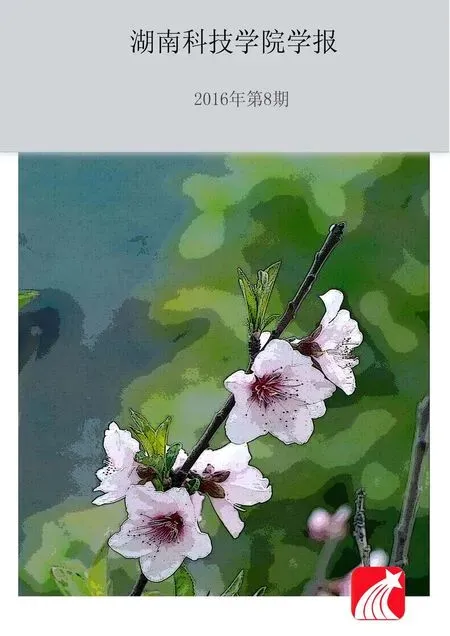歷史與現實的對接:“中”以治國與依“法”治國的內在聯系
陳仲庚(湖南科技學院,湖南 永州 425199)
?
歷史與現實的對接:“中”以治國與依“法”治國的內在聯系
陳仲庚
(湖南科技學院,湖南 永州 425199)
摘 要:“法”與“中”,在字義的原始本義上本就有著內在的一致性;作為一種治國理念,中以治國與依法治國都特別強調公平公正,也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在其目的性上,中以治國追求“三大平衡”,依法治國也要“平衡社會利益”,更是有著內在的一致性。而“中”與“庸”結合,作為“天下之定理”的實踐方法論,可以直接借用于依法治國之“平衡社會利益”的過程中。因此,中以治國之理念和方法,不僅具有歷史意義,也具有現代意義。這一意義,是通過歷史與現實的對接來實現的。
關鍵詞:中以治國;依法治國;內在聯系;借鑒意義
在舜文化傳統中,關于怎樣治國的理念曾設計為一個系統工程并有著遞進的邏輯關系,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在這一進程中或曰邏輯節點上,又對應著一個特定的概念:“誠”以修身、“孝”以齊家、“中”以治國、“仁”平天下。這四個特定概念的內涵,主要是屬于道德范疇,因而中國傳統的治國理念主要是強調以德治國。但四個概念當中的“中”,則又不僅僅是一個道德概念,而是有著更為豐富的內涵,特別是與依法治國之“法”,在其原始的本義上,有著內在的一致性。
一 “法者”,天下萬事之“準則”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是“十八大”以來的新提法。這種新提法,與此前提倡的“以德治國”相比較,顯然有著更強的現實針對性。《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顯而易見,“依法治國”不僅是現在的“必然要求”,還事關將來的“長治久安”。從近幾年所發現和查辦的貪腐案件來看,更多、更重要的是目無法紀的問題,其次才是道德問題,因而有必要特別強調“依法治國”的重要性;同時,還必須強調“全面推進”的重要性,即“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尊重憲法法律權威,都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都必須依照憲法法律行使權力或權利、履行職責或義務,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必須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切實保證憲法法律有效實施,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從中國的文化傳統來看,幾千年的專制體制所造成的“官本位”和特權思想,導致“刑不上大夫”在司法執法領域幾乎成為普遍現象,給依法治國的推行造成了嚴重的障礙。因此,無論是從歷史還是從現實來看,在中國要想真正實現依法治國,“全面推進”——“任何組織和個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才是最為關鍵的。
中國古代主要是強調以德治國,但并不廢棄“法治”。舜帝治國,素以“睿哲文明,溫恭允塞”、“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的德治為先,同時也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的法治舉措,還不乏“流共工于幽州,放歡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尚書·舜典》)等嚴厲法治判案。孟子云:“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為政”(《孟子·離婁上》)。司馬遷說:“德防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更有“德主刑輔”、“陽儒陰法”的說法。從總體上看,這些說法都是指以德為主、以法為輔。當然,“陽儒陰法”則還暗含了統治者在國家治理上的另外一種策略:口頭提倡的是儒家的仁政,實際所做的則不乏法家的手段。自“罷黜百家”之后,儒家在中國思想界確實取得了一家獨尊的地位,但在治國理念和手段上,法家的思想則一直是相伴始終的。
儒家的地位超過法家,可以說是后來居上。在先秦思想史上,法家的出現早于儒家,其地位也超過儒家。最早明確提出依法治國并身體力行的應該是齊國的管仲,他早于孔子近兩百年,作為齊國的國相,其地位顯然也高于孔子;特別是秦國運用法家的理念和手段統一了六國,與儒家四處游說、四處碰壁相比,其地位更是天壤之別。《管子·明法解》云:“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這里的“程式”、“儀表”都是準則、規范的意思,意指“法”是衡量天下萬事是非曲直的客觀準則,是天下人都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這里其實已經暗含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思,后來的韓非子則說得更明白:“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當然,這是有所保留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為韓非子只說到“大臣”,沒有提“君上”。
作為天下萬事的準則和規范,為什么要用“法”來表述?這是與“法”的原始本義相關的。“法”字古體寫作“灋”,《說文解字》云:“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會意”。之所以偏旁為“水”,是因為法律如水那樣公平;而之所以有“廌”,因為“廌”是古代傳說中的一種獨角獸,生性正直,古代用它進行“神明裁判”,見到不公平的人,會用角去頂,于是就有了“去”。因此,從“法”的原始本義來看,至少包含有三重意思:一是懲惡,這就是“刑”,是“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法”直接訓為“刑”,是因為中國古代的法律基本上就是刑法,“懲惡”是其主導傾向和主要作用;二是公平,“平之若水,從水”,才有了“法”字,雖然經過了幾千年的演變,但“平之若水”的偏旁至今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要求“法”必須是公平的;三是正直,“廌”用獨角“觸不直者”并要“去之”,要保護下來的就是“直者”。《說文解字》云:“直,正視也。”“直”字古訓有正、中等意思,這就使“法”與“中”有了內在的聯系。尤為重要的是,“依法治國”強調公平公正,“中以治國”同樣強調公平公正,從治國理念來說,這才是本質上的內在聯系。
二 “允執厥中”之治國“心傳”
“中”作為一種治國理念或治國方略由來已久,從現有的文獻資料看,似乎是從堯帝時代就確定下來了。堯禪位給舜時,傳授了“四字方略”:“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堯曰》)堯帝所強調的治國方略是“允執其中”,重點要解決的問題是“四海窮困”的物質需求。當舜禪位給禹時,則擴大為“十六字心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尚書·大禹謨》)這里所傳授的“允執厥中”方略,與堯帝完全一致;但舜帝所關注的重點卻有了轉移:從解決“四海窮困”的物質問題轉向了“人心惟危”的精神問題。這一轉移,可以說是國家治理理論的一大提升,因為不僅是“四海困窮”的物質問題值得重視,“人心惟危”的精神問題更值得重視,更需要花大力氣解決,特別是在當時生產力低下的情況下,控制人的欲望恐怕比增加物質財富來得更容易、更有效。舜帝在位時極力推行“道德教化”,就是希望從官員到百姓,都應該“以德節欲”,以實現物質與精神的平衡。這與我們今天所強調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有著內在的一致性。由此而論,舜帝所總結的“十六字心傳”,是人類社會的共同經驗、共有財富,是人類高度智慧的結晶,是古今中外可以通用的。
舜帝所總結和確立的大政方略,在秦漢以前就得到了普遍的認同。《中庸》云:“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近年發現的清華簡《保訓》篇記載周文王給周武王的遺言云:“昔舜舊作小人,親耕于歷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違于庶萬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遠邇,迺易位邇稽,測陰陽之物,咸順不擾。”通過對這兩段話的分析可以看出,舜帝“用其中于民”主要是做到了“兩順”:一是理順了民眾之“多欲”的關系;二是順應了“陰陽之物”的生長規律。其成效也就是舜帝在《南風歌》中所唱的:“解吾民之慍”,“阜吾民之財”。
國家管理者需要“用其中于民”,對民眾來說則應該“設中于心”。《尚書·盤庚》載:“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奸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這是盤庚決定遷都時的一段訓詞,他要求民眾“各設中于乃心”,也就是從內心真心誠意地堅守中道。這說明,舜帝所探求、運用的“允執厥中”,到了殷商時代,不僅已經成為一種很流行、很普及的處事原則或道德原則,同時也是國家治理的基本法則。正是從上到下一致奉行的“中”道,成為了國家治理由“亂世”到“治世”的基本保障。
三 “中者”,國家治理之“正道”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中”或“中道”的理念幾乎涵蓋一切事物。將“中”提升到哲理化高度,并使之成為運用于一切事物的理論,孔子的首創之功不可忽視。《論語》對“中”的最好闡發,就是將它與“庸”結合了起來。關于“中”與“庸”的關系,朱熹《中庸章句》云:“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李樹青進一步發揮說:“‘庸’字從庚從用,‘庚’并通‘更’、‘徑’,有經歷久遠與經久耐用的意義,故訓功訓常”;“中是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庸是經久可用的道理,正如農業里面,各種農事均有適當的節氣,不能早也不宜遲;而每年中的二十四節令,又是依次循環,永恒不變。”[1]46從字義上看,“庸”有“用”、“常”、“久”三層含義;而這三層含義,又恰好形成了中庸之道理論上的三大特點。
1.“用”與中道的實踐性。《說文》:“庸,用也。從庚,庚,更事也。”《尚書·大禹謨》:“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弗庸。”“用”是“庸”之基本義,中庸就是“用中”,既包括個人在處理人際關系時的“用中”,也包括統治者在處理國家政務時的“用中”,還包括人類在處理與自然的關系時的“用中”。總之,“中道”滲透在萬事萬物的方方面面,“用中”可貫通于人類的一切實踐活動。從這一意義說,“中道”類似于馬克思所說的客觀規律,“用中”則類似于對客觀規律的把握和運用。
2.“常”與中道的普及性。《論語》:“中庸之為德也……”何晏注:“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可常行”,也就有通常流行的意思。《中庸》反復強調中庸之德、中和之美在于日常運用,在于自身的自覺,在于內在的超越,“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道既來源于“夫婦”等日常生活之中,也來源于“天地”等自然現象之中,就其理論來源說,已經具有普遍性。根據理論來源于實踐并反作用于實踐的定律,當中道運用于實踐指導時,自然就具有了普及性。所以《中庸》又說:“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圣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圣人亦有所不能焉。”中道對普通人的作用已不待言,即便是對愚笨或不肖之人也可以有“啟智”或“指導”的作用,而且可以使他們在某些方面甚或超過圣人,這也就是經由“中庸”的途徑抵達“高明”境界的效果。
3.“久”與中道的恒常性。中道是常道,是經久不變之道。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庸,從庚;庚,猶續也。事可施行,謂之用;行而有繼,謂之庸。”“庸”固然是“用”,然而是用其所當用,不是亂用。也就是說,中道不是主觀設定的,而是本之于“常”,“常”是“恒常”,是不變、恒定;中道是確定不變的“天下正道”,必須把它當作普遍存在的定律來遵循和運用,決不允許進行隨意的更改和變異。因此,奉行“中道”是絕對的,不是可有可無的,這是“中者,天下之正道”的第一層要求。第二層的要求是奉行“中道”的持續性、恒久性,它不是一時通行的權宜之計,而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永恒真理,所以需要一代代人“行而有繼”地永久堅持。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中者,天下之正道”,它作用于上下四方,應用于往古來今,是國家治理的“正道”、“常道”和“長久”之道。
四 “庸者”,治國實踐之“定理”
“中”與“庸”的結合,實際上就是理論之本與實踐之用的結合,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統領萬物的方法論。“中庸”從實踐方法論上進行總結就是“用中”,它可歸納為三大定理。
1.執兩用中。孔子總結的“凡事叩其兩端而用其中”的方法論,后來被簡化為“執兩用中”一詞。《論語·子罕》:“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對此進行解釋云:“此‘兩端’,即《中庸》舜‘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之‘兩端’也。鄙夫來問,必有所疑,唯有兩端,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端,謂先還問其所疑,而后即其所疑之兩端而窮盡其意,使知所向焉。”按照孔子自己的說法,他其實也沒有什么先見之明,即使是山野村夫來求他解答疑問,也不可能有現成的答案,唯一能做的就是先叩問疑問的兩端,再從“中”找到一個適宜的答案。因此,“中”就是“宜”,“宜”也是“中”。而要找到“中”之所“宜”之處,關鍵的做法是“叩其兩端”,“叩”也是“權”,即權衡利弊。其實質就是將矛盾對立的調和原則與行為原則結合起來,然后運用于各種事物的處理。如《尚書·呂刑》談執法:“惟良折獄,罔非在中”;談判案:“民之亂(治)也,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執法在“中”,判案也在“中”,都是要求公平公正、不徇私情;后者還要求能夠調和兩家對立的申訴,公正地判案。因此,“執兩用中”是在總結長期的社會實踐和政治實踐的基礎上所提煉出來的方法論,它具有普遍的應用價值
2.比中而行。“執兩用中”是叩問同一事物的兩端,權衡利弊之后選其適宜者而行之;“比中而行”則是在眾多事物中進行比較,選其最適宜者而行之。《荀子·儒效》云:“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謂中?曰:禮義是也……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無益于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于理者,為之;無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奸事,知說失中謂之奸道。”“先王之道,仁之隆也”,這是荀子經過眾多的比較之后得出的結論,由此推廣開來,“凡事”、“凡知說”都應該經過比較之后再做出選擇或得出結論。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無論是“執兩用中”或“比中而行”,都不是“二者必居其一”或“多者必選其一”,更不是“折中調和”,它是經過權衡優劣利弊之后所做出的選擇,既可以多元選一,也可以多元并存,一切以“適宜”為原則,決不能“舉一而廢百”。因此,這種多元并舉、多向選擇的思維模式,與二元對立、二元取一的思維模式是截然不同的。
3.中和以成。“執兩用中”或“比中而行”主要是具體的實踐方法,“中和以成”則是更高層次的方法論。《廣韻》:“庸,和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中、庸、和三者的涵義均是相通的。從哲學的意義說,三者的偏重在于:“中”是本體論,“庸”是方法論,“和”是目的論。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中道,通過執兩用中、比中而行的方法和途徑,運用于一切事務的管理或操作過程,最終達到心和、政和、天人之和的目的,這就是“中和以成”的最終效果。
關于“中和以成”的問題,劉師培曾有過精辟的分析:“問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何也?曰:天地之道,一陰一陽而已。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位者,陰陽之中;育者,生成之謂。故以陰陽生成萬物,明春秋化育之功,亦以見仲尼上律天時,與天同極也。”[2]“春生秋成”,這是自然的“中和”之功,“上律天時,與天同極”,則是人力的“中和”之功。因此,“中道”作為創生萬物的本體,也是“天道”與“人道”之“中和”的結果。“真可謂:中和之用大矣哉!”[3]7“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之謂也。
總結“中庸”的治國實踐目標,主要是解決三個問題:其一是解決“人心惟危”的問題,其關鍵點就是做到利益適度平衡,化解人們心頭的不平之氣,求得個人心境的平衡;其二是解決“四海困窮”的問題,其關鍵點是在促成“物阜民豐”的基礎上去滿足民眾的需求,化解供需矛盾,求得社會需求的平衡;其三是遵循自然規律的問題,其關鍵點是順從客觀事物陰陽變化的規律,適度地選取人類的所需而不是無限制地索取,化解人與自然對立的矛盾,求得自然生態的平衡。解決三大問題,實現三大平衡,這就是“庸者,天下之定理”的精髓所在。
實現三大平衡,不僅是古代國家治理所想要達到的愿望,更是今天現代國家所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同樣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所要實現的價值指向。《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要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維護和運用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更好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在這里,核心中的核心是“平衡社會利益”,不僅包括國內各方的“社會利益”,也包括國際各方的“社會利益”;而在這一“平衡”的過程中,借助于“中庸”的理念和方法,應該是“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最好借鑒。從這一意義說,中以治國與依法治國不僅在理念上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在其目的性上更有著內在的一致性,而在方法手段上更是可以直接通用的。因此,“庸者,天下之定理”,亦即“中庸”之實踐定理,不僅具有歷史意義,也具有現代意義,還具有世界意義,而且是永久之意義。當然,這種意義,是通過歷史與現實的對接來實現的。
參考文獻:
[1]李樹青.儒家思想的社會背景[A].中國文化的危機與展望——當代研究與趨向[C].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884.
[2]劉師培.中庸問答[A].劉申叔遺書[C].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3]龐樸.中庸平議[A].龐樸學術文化隨筆[C].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
(責任編校:張京華)
中圖分類號:K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219(2016)08-0003-03
收稿日期:2016-06-10
作者簡介:陳仲庚(1959-),男,湖南祁陽人,湖南科技學院副院級督導員,中文系教授,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首席專家,研究方向為舜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與文藝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