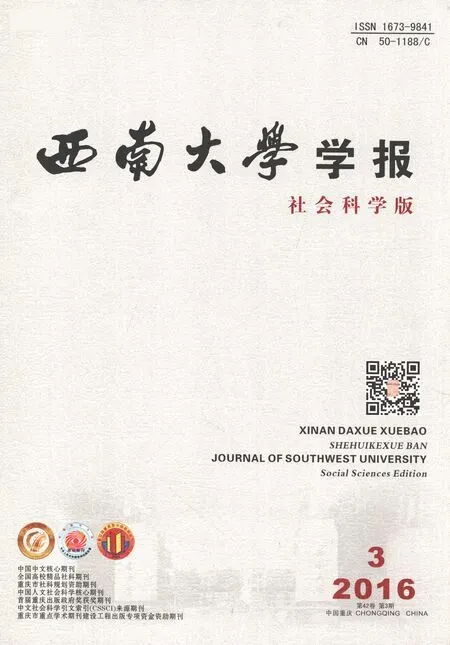明代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及其構成①
——兼論明代人的生活質量
陳 寶 良
(西南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重慶市 400715)
明代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及其構成①
——兼論明代人的生活質量
陳 寶 良
(西南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重慶市 400715)
摘要:在生活質量以物質財富為基本衡量標準的時代,收入的高低,事實上已經決定了生活質量的好壞。明代社會各階層的收入構成,大抵可以分為基本收入與額外或業余收入兩大類,且呈現出極強的社會等級性。基本收入是明代一個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是維系家庭生計的基本物質保障;業余收入主要是指基本收入之外的額外收入。在基本收入大體穩定的情況下,生活質量的改觀,無疑有待于業余收入的增加。
關鍵詞:明代;社會階層;收入;生活質量;等級性
一、問題的提出
在生活質量以物質財富為基本衡量標準的時代,收入的高低,事實上已經決定了生活質量的好壞。明代社會各階層的收入構成,盡管相當復雜,然若細究之,大抵可以分為基本收入與額外或業余收入兩大類。
在通常情況下,基本收入是明代一個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且是維系家庭生計的基本物質保障。基本收入的構成,大抵包括官員的官俸與家庭經營性收入;士人的廩糧與補貼性的膏火銀,以及處館收入;農民、佃戶、各類雇工、商人、工匠等庶民階層,因為職業的差異,其基本收入高低不同,或來自耕地的產出,或來自勞動力付出的報酬,或來自資本經營的收入;而武官、軍兵,他們的基本收入則主要來自官俸與餉銀。至于業余收入,則主要是指基本收入之外的額外收入,諸如:官員違法的貪污、受賄收入,以及并不違法的隱性灰色收入,乃至正常的如“潤筆”一類的業余收入;士人包攬錢糧、硬幫中保的收入,以及包攬詞訟、囑托公事的收入;小農家庭的副業收入等。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深入考察明朝人的生活質量,顯然繞不開收入這一問題。下面選取官宦、士人、庶民、軍人和賤民這五個代表性的社會階層,就他們的收入構成乃至基本狀況稍加厘定。
二、社會各階層的基本收入
明代社會各階層的收入構成呈現出社會等級性的差異,從而決定了在考察收入構成時,很難從總體上把握,而是必須將其置諸不同的社會等級層面加以分類考察。
(一)官宦
明代官宦的基本收入,大致由官俸與家庭經營性收入兩項構成。
早在洪武十三年(1380),就已確定了文武官員祿米俸鈔之數。至二十五年,又重新更定官祿,并成為一代定制。其中規定:正一品月俸米87石,從一品至正三品依此遞減13石,從三品26石,正四品24石,從四品21石,正五品16石,從五品14石,正六品10石,從六品8石,正七品至從九品遞減5斗,至從九品月俸5石止[1]卷32,明官俸之薄。
由此不難發現,明代官俸之薄,堪稱歷代之最。唐時,百官都有“職田”,包括“職分田”與“永業田”兩種。在宋代,官員也有“公田”。到了明代,朝官只是仰仗俸薪,別無給賜。而從俸薪來看,明代與唐及五代相比,也是低了許多。據明人于慎行的考察,明代宰相(即內閣大學士)的月俸,還不能達到五代北漢時的一半,而比起唐代來相差就更多了[2]卷9,月俸。內閣大學士的官俸尚且如此之薄,至于那些下層官員,其俸薪就更低了。以儒學教官為例,府學教授從九品官,月俸米才5石,而府學訓導為未入流,月俸米3石。巡檢司的巡檢,從九品官,月俸米5石[3]。明代后期,官員俸祿改為折銀,然據謝肇淛的記載,明代在外官員,七品以上,月俸每年可得100兩銀子,四品以上又可加倍。可見,明代官員俸祿除糊口之外,還是有一些贏余的。至于那些大臣,俸祿會更優厚一些[4]。
不過,明代官俸所實行的折鈔之制,則更使一些下層官員感到生計不足。大體說來,在洪武年間,京官除了能支全俸之外,尚多歲時賞賜,如正旦、元夕、冬至,照例賜予京官酒米錢。至永樂以后,遷都北京,定下京官俸祿折色之例,春夏折鈔,秋冬折蘇木、胡椒。其中五品以上官員,折色為十分之七,五品以下官員,折色為十分之六,而只有十分之三、四為本色之米。當時鈔重物輕,尚屬公私兩便[5]。然折鈔之制,其結果還是導致官員俸祿的降低。如文武官員的俸祿,原本每石可以折鈔25貫。宣德九年(1434)春,掌管戶部之事的禮部尚書胡濙上奏,主張將每石改為折鈔10貫,盡管遭致蹇義等人的反對,但最后還是降為每石折鈔15貫[6]卷10,京官折俸。成化七年(1471),戶部鈔少,又改用布估,給布一匹,當鈔200貫。當時鈔一貫僅值錢二、三文,而米1石折鈔10貫,于是1石米僅值二、三十錢。布一匹也僅值二、三百錢,而折米20石,于是1石米也就只值十四、五錢。可見,先是以鈔折米,繼而以布折鈔,最后又有折銀之例,正是因為官俸由本色改為折色,才使明代官俸與歷代相比,最顯低薄。此外,明代南北兩京官員的俸祿,同樣存在著一些差異,體現出北高南低的基本特點。如南京各部的主事,每月支米3石,而北京各部主事則可月支4.5石,且折俸亦不同[7]34。
當然,上面所謂的俸祿,僅僅是官員的常俸而已,因其過分低薄,難免使官員有捉襟見肘之嘆。于是,明朝廷為了讓官員維持還算體面的生活,只好在常俸之外,給官員增加柴薪銀與馬丁銀,有時甚至還有“廩給銀”。如李樂任福建按察司僉事,照例每天有廩給銀3錢,每月合計9兩[8]。此銀原為支付外巡官員每天的飲食費用,不過官員外巡之時,地方官照例會為外巡官員提供飲食。可見,外巡官員其實可以多支每月9兩銀子的“廩給銀”。在明代初年,衙門官員下面設有皂隸,作為隨從與服役人員。至宣德年間,宣宗因楊士奇上言京官俸祿低薄,允許皂隸納銀免役,收取銀兩,此即所謂的“柴薪銀”。至天順年間,根據官品的隆卑,定下官員應有皂隸的名數,每年按名收取“柴薪銀”。可見,明朝京官索取皂隸銀,進而轉為“柴薪銀”,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可以彌補官俸不足[9]。
明代官員的常俸,僅僅是官員基本收入的一小部分,其更多的基本收入,理應來源于家庭許多經營性的收入。在這些經營性的收入中,田地、房產出租當屬大宗。此外,有些官員家庭甚至還開設紡織機房,藉此增加收入,甚至獲利頗為豐厚。
限于目下史料匱乏,若欲將明代官員所占田產的平均數作一估計,顯然存在著不小的困難,且南北方官員家庭的田產數,其實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不過,從明代史料記載來看,松江府上海縣的“縉紳富室”,其占有的田產,最多可以達到“數千畝”[10]卷1,田產,顯然已經數目可觀。以公安派袁中道的家產為例,其經營性收入主要包括三大塊:一是田產收租,每年可得租440余石,以其中一半供應居住在城中的妻孥之用,一半供自己在鄉下生活及“舟中資糧”,亦即出游費用;二是“銀租”,每年的收入大約有100兩銀子,以其中的1/5付與城中妻孥,以“作蔬具”,以大半作為自己的“游玩度支”;三是房產收入,袁中道在沙市有一處多余的房產,若將其變賣,所得之值又可置田數百畝[11]。此外,在明代的江南,大多“以織作為業”,即使是士大夫家庭,亦“多以紡績求利,其俗勤嗇好殖,以故富庶”。像徐階這樣在位的內閣大學士,也是“多蓄織婦,歲計所積,與市為賈”[2]卷4,相鑒。諸如此類的資料,已經足證士大夫家庭的經營性收入相當可觀。
(二)士人
所謂士人,大抵是指那些尚未出仕做官的知識人。就其科名而言,士人群體又可分為已經獲得生員身份與尚未具有生員身份兩類。這些知識人的生計來源,主要是他們的處館教書收入,也就是所謂的束脩。
在已有生員科名的士人中,尤其是廩膳生員與增廣生員,其基本收入包括兩部分:一是統一的廩糧,二是帶有補貼性的膏火。根據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知,明代廩膳生員的廩銀,其最為優厚者,每年可得18兩銀子,一般是在12兩左右[12]。
明代的士人群體,其主要職業還是以處館維持生計為主。至于士人處館,則又可分為蒙師與經師兩類,進而決定其收入稍有差異。在明代那些尚未具有生員科名的塾師,其整年所獲束脩之低,實在令人咋舌。如據陳確記,其父陳穎伯在外處館,一年的脩金僅僅4兩銀子[13]卷11,父覺庵公;又據魏禧記載,明末在江西寧都,若是無秀才身份,出任童子之師,“歲所獲脯脩資不過數金”[14]。當然,上述收入較低的塾師,大抵屬于童蒙師一類,若是那些經師的束脩,大概一年在30~50兩之間,多者亦有超過50兩,甚至還有超過100兩的特例[12]307-309。
(三)庶民
明代的庶民階層,大致包括農民、佃戶、各類雇工、商人、工匠等。因為職業的差異,他們的基本收入高低不同。即使是在同一社會階層中,也會因為區域、田地多少乃至資本厚薄而收入迥異。
1.農民
在明代的農民階層中,首先需要考察的是自耕農的基本收入。下面以江南自耕農為例,稍加考察。按照明代的史料記載,江南自耕農所占田地數,少者為3~5畝,中者為5~10畝,多者不超過40畝*相關的記載,可分別參見〔日〕清水泰次.明代福建的農家經濟,載《史學雜志》第63編,第7號;葉夢珠.閱世編·卷1,《田產》1,第23頁;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8,《答徐敬可十》,中華書局2002年版,上冊,第227頁.。至于江南田地的畝產量,可選取蘇州府常熟縣與嘉興府海寧縣為例加以說明。常熟縣的畝產量,按照單位面積產量的高低,分為“上農”、“中農”與“下農”三等,其中上等田地的畝產量為2石,中等田地的畝產量為1石余,下等田地的畝產量僅為1石[15]。這一記載理應僅僅是指單季稻米的產量,并未包括別季麥、豆等的產量。如處于相同地域的浙江嘉興府海寧縣,其中等田地每年可產米、麥、豆3石以上;至于上等的腴田則更是高達4~5石[13]卷15,投當事貼。這一記載大抵符合江南田地每年的單位面積產量。這同樣可以從廣東水稻的畝產量得到部分印證。史載廣州之稻,分為一熟、早晚兩熟與三熟三種。其中一熟豐產者,每畝可得4石。晚稻的產量,每畝少于早稻三分之一[16]。照此記載,若是按兩季概算,廣東水稻每年每畝的產量大致可以達到將近7石,僅僅略高于浙江海寧。
若以折中的海寧畝產量為標準,那么就可以對明代江南自耕農每年的基本收入作一大致的匡算:以占田5畝的下等自耕農為例,若是中等產量每畝3石,那么每年的收成為15石;若是上等產量每畝5石,那么每年的收成為25石。陳確所云,一畝田地收入,大體上可以維持“一夫之食”,即供給一人一年的口糧[13]卷15,投當事貼,大致是可以相信的。當然,這僅僅是以種植糧食作物而論。若是海寧的田地,改種桑麻瓜果,那么每畝每年可以產出10~20兩銀子,可以供給每年“數口之糧”[13]卷15,投當事貼。
2.佃戶
就其總體而言,在明代農民中,有田的自耕農僅僅占據1/10,而9/10則為替人佃作的佃戶。那么,明代佃戶的基本收入如何?則可以南方與北方為例,分別加以探討。
以明代的南方為例,如南京一帶的寄莊戶,將田一畝出租給佃戶,并為佃戶提供牛與車等生產工具,甚至還提供房子給佃戶居住。在南京當地,一畝田每年的最高產量為收稻谷2石,而佃戶必須將一半交給田主作為田租,自己僅得一半[17]。蘇州府的佃農,其收入較南京佃農低。按照蘇州的慣例,計算畝數“甚窄”,凡是溝渠道路,均計算入收租的田畝數之中。每年收成僅秋禾一熟,一畝的收成不到3石,少者不過1石有余。至于田主收取的私租,重者達1.2~1.3石,少亦需交0.8~0.9石。佃戶竭盡一歲之力,糞壅工作,一畝之費達一緡,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斗,致使有些佃戶,“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18]。至于浙江桐鄉縣,佃戶終歲勤勞,祁寒暑雨,也必須將收成的一半交給田主[19]。
以明代的北方為例,如在河南,凡是家中田產達到百畝,往往就不親自力作,而是雇傭佃戶耕作。盡管佃戶有“主家之手足”的說法,且主家諸凡“夜警”、“興修”、“雜忙”之類,無不仰賴于佃戶,但佃戶還是缺衣少食。一等佃戶向主家稱貸,輕則加三,重則加五。“谷花始收,當場扣取,勤動一年,依然凍餒”[20]。
綜上所述,就佃戶耕種的土地數來看,明代佃戶的基本收入,大抵只有自耕農的一半,史料所謂的“今士庶之家,以田佃人,歲入其半”,大抵符合明代的史實。然田主通常不僅僅滿足于收取一半,而是通過“腳米”、“斛面”之類的名色,“以求取盈”[21],使佃戶收入明顯低于自耕農的一半。
3.各類雇工
明代無田的農民,替人傭耕,分為“長工”、“忙工”兩種。兩者同屬雇工,其差別僅僅在于,長工是“以歲計”,而忙工則“以月計”。
明代長工收入,根據從事勞作的不同而稍有差異。若是從事的是農田耕作,那么田主每年支付給每名長工的工費支出,大抵包括以下幾項:工銀5兩;田主供給的飲食米5.5石,折成平價,值銀5.5兩;盤纏銀1兩;農具銀0.3兩;柴、酒銀1.2兩。諸項合計,長工每年的收入為13兩銀子[22]。若是從事經濟作物的種植,如桑地種植與管理,那么此類長工來自田主的每年收入大抵為:每人每年工銀2.2兩;每人每天從田主那里獲得飯米2升,每月計0.6石,一年共計7.2石,折成平價銀7.2兩。兩項合計,此類長工的每年收入則為9.4兩[23]。顯見,其收入稍低于從事農田耕作的長工。不過綜合明代的史料記載來看,由于務農者日漸減少,必然導致“農夫日貴”,其工值甚至“增四之一”,上漲25%[24]。
至于忙工或短工的收入,可以從一些資料所言的傭工收入中得以窺知。按照明代的史料記載可知,明代替人傭工的收入為每天得錢30文,一年得錢14 000文[25]。
4.工商業者
在一個賦稅、徭役不重的時代,自耕農基本能維持比較富裕的生活,而且可以旦暮不失父母妻子的團聚,所以很少有人去逐末經商。原因很簡單,外出經商,且不說失去天倫之樂,即使一般的小商小販,其獲利也是甚微。在明初宣德年間,京畿地區的業賈之人,終日勤勞,外出經商,不出二、三百里,遠的一月,近的十日即可返回。但他們的獲利情況也并不理想,其厚者十之二、三,薄者不過十分之一,更有盡喪其利者[6]卷10,172。
明代商人收入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豐厚,而是呈現出兩極分化之勢:普通的販夫,或者游走于城鄉之間的貨郎,他們的收入其實僅可滿足全家的糊口而已;至于那些資本雄厚且貨殖有方的大商人,尤其是來自徽州的鹽商、典商,其收入乃至財富積累之多,則讓人難以想象。當然,即使是那些富賈,很多最初也是通過自己的奮斗才最終獲得成功。不妨舉一較為典型的例子,以考察明代成功商人的基本收入。如濮陽人劉滋,少為庠生,后因家貧,不得已只好賣掉僅有的不足20畝田,“逐十一之利,十余年至數萬金”[26]。稍加平均,則每年收入有數千兩銀子。
至于一般的手工作坊的業主,通過自己的經營,其資產的積累有時亦相當可觀。這可以張瀚祖上的發家史為例加以剖析。張瀚自己回憶在先祖毅庵時,家道開始中落,只能靠酤酒為業。但酤酒生意并不好做,而后就改為置辦織機,開始從事紡織業。因為所織“諸色纻幣,備極精工”,所以產品一出,“人爭鬻之,計獲利當五之一”。僅僅過了兩旬,又增添一張織機,到后來織機數更是增達20多張。張家靠紡織起家,最后是“家業大饒”。即使分為四支,同樣從事紡織之業,亦各“富至數萬金”[27]。
5.工匠
明代工匠分為官匠、民匠兩類。自明代中期以后,官匠制度衰落,即使官方匠作之事,同樣需要調遣地方民匠*即以南京龍江船廠為例,其廠中工匠,即有從官匠向民匠轉變的趨勢。史載其事云:“凡造船之料物司之也。計料有科,人匠有科,屬吏各承行也。人匠皆洪武、永樂年間取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邊江府、縣熟于造船者,挈家于提舉司隸籍。今知藝者,百無一二,召外匠也。”參見李昭祥.龍江船廠志·卷6,《孚革志·律己之弊有五》,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126.。總體上說,明代工匠的生活相當艱辛。關于此,明代史料已經一語道破:
夫工匠執役于官,晨出暮歸,豈真有奉公之義哉,為糊口計也。興工之初,工食未領,先稱貸以自給,工完支糧,計其出息,十已損二矣!而府吏胥徒,蠶食于公門者,又方聚喙而睜目焉,故匠工之所得者,僅十之六七耳[28]。
可見,官匠執役于官,僅僅是為了糊口。然在用工制度不全且人身依附關系頗為緊密的明代,官匠不但人身不得自由,甚至糊口亦成問題。
服務于朝廷或官府的工匠,其每月的收入高下不一。如服務于蘇州織造局的各色人匠,每名每月給食糧4斗,每年計得食糧4.8石,折成平價銀4.8兩。蘇州衛軍匠在織造局服務者則工食稍高,每名每月給食糧8斗,每年計得食糧9.6石,折成平價銀9.6兩[29]。若是調入民匠,替官府服役,則收入相對較低。如在遵化鐵廠服役的民匠,每名每月支口糧3斗,每年計得口糧3.6石,折成平價銀僅3.6兩;而同在鐵廠服役的軍匠,收入相對較高,每名歲支行糧10.8石,折成平價銀為10.8兩。此外,尚可補助冬衣布2匹,棉花2.8斤[30]。還有明末崇禎年間在歷局中當差的廚夫,他們的收入為每月得銀6錢,每年計得7.2兩[31]。至于那些為皇家服務的工匠,其收入顯然就高出許多,一般為月糧1石,并有直米3斗5升。兩者相加,每月可得1.35石,每年計得16.2石,折成平價銀為16.2兩[32]。更高者則屬南明弘光朝宮中銀作局的工匠,“人日給工食銀一錢二分”,每月計3.6兩,每年計得銀43.2兩[33]。
至于民間手工業作坊工匠的收入,應該說也是相當微薄,僅僅可以維持一家生計而已。譬如紡織業中,按照明代的慣例,已是“機戶出資經營,機匠計工受值”,每個季度除工資之外,僅給“機匠酒資一錢,二月朔日給付四分,三月朔日給付三分,清明給付三分,三次分給,共是一錢之數”[34]。這種低下的待遇,從明末到清康熙、雍正年間仍是如此,所以激起了工匠“叫歇”,即罷工運動。
當然,在明代的城市中,有些工匠因為一時僥幸,其工值相對較高。如明末南京有一位櫛工,專門從事替人梳頭之事,曾被南京戶部主事王承曾所雇,替王氏寵信的“美少年”門子梳掠,每天的工值高達3分銀子[35]。更有很大一批著名的手工藝人,他們憑借自己的技藝,甚至可以與士大夫平起平坐。而他們所制的產品,銷售價格甚高。如龔春、時大彬所制宜興砂罐,以及王元吉、歸懋德所制錫注,其價格均高達四、五兩銀子一件[36]。顯然,這些著名工匠的收入相對較高,生活也比較富足。
(四)軍人
在此,軍人僅僅是一個通稱,在具體收入的考察中,當分為武官與軍兵兩類。
1.武官
明代的武官,分為衛所軍官與標營軍官兩類,其收入各有不同。以衛所武官為例,大同鎮的大小武官,其收入構成就分“有廩給”、“無廩給”兩種。據楊嗣昌的考察,兩者的差別在于,有廩給者無養廉地,無廩給者有養廉地[37]卷8,西閱大同情形第七事疏。明代衛所武官的廩給,大抵如下:指揮僉事,每月得米4.8石,每年計得米57.6石,折成平價銀57.6兩;正千戶,每月得米3.2石,每年計得米38.4石,折成平價銀38.4兩;副千戶,每月得米2.8石,每年計得米33.6石,折成平價銀33.6兩;百戶,每月得米3石,每年計得米36石,折成平價銀36兩;鎮撫,每月得米2.4石,每年計得米28.8石,折成平價銀28.8兩[7]10。
至于標營軍官的收入,相比衛所武官較為豐厚。如節制中營中的統領參將,每月支廩銀18兩,每年計得銀216兩;中軍,每月支廩銀8兩,每年計得96兩;千總,每月支廩銀6兩,每年計得銀72兩;把總,每月支廩銀5兩,每年計得銀60兩;沖鋒、塘馬、遠哨、通丁、火器材官、占候、醫生,每月支廩銀3兩,每年計得銀36兩;馬兵百總,每月支廩銀2.4兩,每年計得銀28.8兩;步兵管隊,每月支廩銀1.8兩,每年計得銀21.6兩[37]卷7,請定標營疏。
2.軍兵
明代的軍兵有衛所的軍、營兵與募集的兵以及地方弓兵之別,且收入高低不一。
就衛所的軍來看,亦可分為在京衛所、沿邊衛所、沿海衛所與漕運衛所,其收入差別較大。在這些衛所的軍中,其收入以月糧為主,尤以在京衛所之軍最為優厚。如在京各衛之軍,其有家小者,月糧明顯比邊衛多。即使是無家小者,所支月糧數相同,但因無折鈔之例,算起來也比邊衛旗軍為優。成化六年(1470),根據刑部衙門的上奏,制定了在京各衛所旗軍的月糧定例,其中規定:軍人所支月糧,若有家小,每月例支1石,每年計得12石,折成平價銀12兩;若無妻小,每月例支6斗,每年計得7.2石,折成平價銀7.2兩;若是妻子亡故,但尚有父母、弟娣、子侄同居共爨,亦按有家小之例關支[38]。沿邊衛所之軍,若以大同鎮為例,其間月糧稍有變化。宣德十年(1435)下令:山西衛所旗軍,有家小者,每月支月糧8斗,每年計得9.6石,折成平價銀9.6兩;無家小者,每月支月糧6斗,每年計得7.2石,折成平價銀7.2兩。至于調來操備的旗軍,無家小者,每月支月糧5斗,每年計得6石,折成平價銀6兩;有家小者,每月支月糧8斗,每年計得9.6石,折成平價銀9.6兩。正統九年(1442)又下令:大同、宣府衛所旗軍的月糧,有家小者,月支月糧8斗,每年計得9.6石,折成平價銀9.6兩,然月糧中,每月有1斗折成鈔;無家小者,月支月糧6斗,每年計得7.2石,折成平價銀7.2兩,月糧中每月有4斗折成鈔。正統十四年,下令大同選操屯軍,按照守城軍士一樣支月糧。若是有家小,則每月支月糧8斗,每年計得9.6石,折成平價銀9.6兩;若無家小,每月支月糧6斗,每年計得7.2石,折成平價銀7.2兩。至天順元年(1457),又下令沿邊各衛所軍人,不分馬兵、步兵,均改為月支米1石,每年計得12石,折成平價銀12兩。此例一直延續至明末[37]卷8,西閱大同情形第七疏。沿海衛所如福建福州衛所之軍,則分為征操軍、屯旗軍、屯種軍三種。其中的征操軍,若按季踐更,是月得米8斗,每年計得9.6石;若是給銀,則月給銀4錢,每年計得銀4.8兩;若是出外海或守煙墩,則月給米1石,每年計得12石;若是給銀,則月給銀5錢,每年計得6兩。其中選練備戰的余丁,月給米8斗,每年計得9.6石。屯旗軍主要用于屯種,其收入是受田輸糧,不從官方領取行糧或餉銀。但屯軍一旦被調防守,也可得月米8斗,每年計得9.6石[39]。在衛所軍士的收入中,當數運軍收入較低。按照明代的制度規定,漕運軍士,每月支米8斗,每年計得9.6石,折成平價銀9.6兩。至于漕運中的操備及諸雜差,有妻者,每月支米6斗,每年計得7.2石,折成平價銀7.2兩;無妻子者,月支米4斗5升,每年計得5.4石,折成平價銀5.4兩;若是羸老殘疾的軍士,則月支3斗,每年計得3.6石,折成平價銀3.6兩[7]10。
按照一般的慣例,遼東邊兵,在營月食為銀4錢,每年計得4.8兩。但正是因為正常的邊軍僅僅是充數而已,缺乏戰斗力。于是,在邊地各級將軍之下,均有自己的隨任家丁,原無定額,多者有百余人,少者五六十名,或三四十名。這些家丁,一般被軍中用為前鋒,每次遇到征戰,家丁當先,弱兵隨之。正因為他們善戰,所以在待遇上相對就比一般軍士顯得優厚,除了部分仍支單糧之外,大多可以支雙糧,亦即每月可得餉銀8錢,每年計得銀9.6兩[40]。
在募兵制興起以前,京城各營勇士,每月的收入為月糧1石,每年計得12石,折成平價銀12兩。此外,還可支馬料豆9斗,外加谷草30束[32]。嘉靖末年以后,譚綸在浙江練兵,在他的奏疏中就說到,3萬兵歲需餉54萬兩,可見,當時所募之兵,每名歲需餉銀16兩[1]卷34,將帥家丁。盡管這16兩餉銀并不一定能完全到兵士手中,但募兵收入顯較衛所軍士優厚。又如松江沿海募集的兵士,每名月給銀8錢,每年計得銀9.6兩[41]卷14,《史》10,p122。即使吏胥、隊長不免蠶食其中,兵丁并非能如數拿到月銀,但相對還是比較優厚的。至于標營兵士,其收入亦相對優厚,如馬番、漢丁,每月支銀1.6兩,每年計得19.2兩;馬軍,每月支銀1.5兩,每年計得18兩;步兵,每月支銀1.4兩,每年計得16.8兩[37]卷7,請定標營疏。至于那些標下之教師、內丁,在待遇上比起一般的營兵更為優厚。按照慣例,教師為眾兵師范,勞苦倍常,就可以在軍兵食糧之外,每名每月加銀3錢,亦即每人每月支銀9錢,每年計銀10.8兩,外加每月得米6斗,每年計7.2石,折成平價銀7.2兩。兩項相加,每年的收入可達18兩銀子。而內丁,則是每名每月加銀2錢,亦即每人每月支銀8錢,每年計得銀9.6兩,外加每月得米6斗,每年計得7.2石,折成平價銀7.2兩。兩項相加,每年的收入可達16.8兩[42]。
至于地方巡檢司的弓兵,其收入為每年餉銀7.2兩[43]。
(五)賤民
在明代,倡優、奴仆屬于賤民,從身份上說處于社會的最底層。這一社會群體的收入,同樣可以根據部分的史料記載加以體現。就戲子與藝人而言,在明代中期,戲子通常在衙門中侍候承應,這大抵類似于唱堂會。若是如此,則每名戲子每天可得工食銀0.5兩[36]卷1,寄祝二陶兄弟書。相較于城市普通的販夫走卒乃至于農村的農民來說,這一天的收入顯然不薄。然戲班與戲子不可能每天都有戲可演,一年中且多有歇息的時間,即使能夠獲得演出的機會,亦并非一概均如赴唱堂會那樣能有豐厚的酬勞。在藝人群體中,若是較為著名者,那么其收入就較一般藝人更為豐厚。如明末著名的說書藝人柳麻子,一天說書一回,可得銀1兩[41]卷13,《史》9,p109,就是典型的例子。
至于奴仆的收入,在明代盡管因時代及區域差異而有所波動,但大致可以通過明末的史料而加以揭示。根據史料記載,在明末的江南,主人給家中仆人的報酬,大體是維持在每天支付米1升。這1升米,若是按照固定不變的平價銀計算,大致值銀子1分,然在明末僅僅值銀子8厘。按照這一收入,將仆人一月的收入折成銀子,大概每月為0.24兩銀子,每年為2.88兩銀子[13]卷5,柳敬亭說書。
三、社會各階層的額外及業余收入
在明代的各個社會階層中,盡管并非所有社會階層均有額外收入,但確實有很多社會階層,在基本收入之外,尚有額外以及一些業余收入,且在某些社會階層中,這類額外及業余收入,有時會遠超其基本收入。
(一)官宦
明代官員的收入來源,其實并非依靠低薄的俸薪,其大宗恰恰來自各色額外收入。通觀明代官員的額外收入,大致包括以下三項:一是違法的貪污、受賄收入,以及并不一定違法的隱性灰色收入,如說事過錢之類,亦即替人說人情;二是接受非法的投獻與詭寄;三是正常的業余收入,如“潤筆”。
明代官場腐敗,這是人所共知的史實。清代廣泛流傳的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一類的民間諺語,其實并非空穴來風,早在明代已是既成的事實。明代官員在俸薪之外,通常可以貪污、受賄獲取額外收入,甚至還有各種規例。以地方官員為例,每一縣有佐貳官二、三員,各有職掌分工,司捕者就以捕盜為“外府”,收糧者以糧為“外府”,清軍者以軍為“外府”。外府之說,頗有些“靠山吃山”的味道,無非就是依仗自己的職權,從中謀取俸薪之外的好處。佐貳官之上就是知縣,也有很多額外的好處,如“罰谷”、“羨余”之類。從知縣往上,就是一省的方面官。他們的好處就更多了,“歲節則有獻,生辰則有賀,不謀而集,相向而來。尋常之套數不足以獻芹,方外之珍奇始足以下黠”[44]。又根據明代史料的揭示,當時的地方官員,從省級的布政使,一直到知縣,貪者居半。其多者一年可得一、二萬兩銀子,少者一年也可得二、三千兩銀子[45]。
除了貪污、受賄及各色規例之外,明代官員在田地經營一類的基本收入中,通常又會借助朝廷賦予他們的優免特權,從中額外獲得優厚的回報。按照明代的制度規定,凡是兩榜鄉紳,無論官階高低及田之多寡,決無簽役之事。乙榜舉人,視其官位之崇卑,多者可免二、三千畝,少者亦達千畝。至于貢生出仕的官員,則根據其官位,多者可免千畝,少者不過三、五百畝[10]卷6,徭役。
在明代官員士大夫的額外收入中,有時“潤筆”也算得上是一筆較為重要的收入。文字潤筆,自晉、宋以來即已出現,至唐始盛[46]。在明代的官員群體中,尤其是那些翰林院的官員,可以替人寫應酬文獲取“潤筆”。在正統以前,一般是寫一篇應酬文,可得二、三錢銀子。正統以后,價格有所上漲,一篇可賣5錢或1兩銀子。有時替人寫一篇合葬的挽辭,還可以得到一件古董作為報酬[47]。在萬歷年間,李日華以善書及精于書畫鑒賞著稱,向其求書者絡繹不絕。為此,他專門定下了書寫扇面及卷冊收取潤筆費的規矩:書寫一柄扇子,若是有號者,收取磨墨錢5文,不寫號,則收3文;若是書寫細楷,收筆墨銀1錢,磨墨錢亦止3文;若書寫卷冊且又字多,收磨墨錢20文;書寫扁書,一具收30文;書寫草書單條,每幅收5文[48]。相比之下,潤筆收錢顯得較為俗氣,所以有時潤筆又以收取古董為清雅。如賀伯闇請李日華替自己的父親寫一傳記,就專門贈送“二縑、書畫、爐、硯”作為潤筆[49]。
(二)士人
在明代的士人群體中,尤其那些已經具有生員科名的士人,處館獲得脩金當然是其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但亦不乏通過一些額外收入而藉此補貼家用。明代生員的獲利途經很多,明代史料有如下揭示:
至于請托行私,起滅罔利;包攬錢糧,隱蔽差役;請祀名宦、鄉賢,管分齋膳、廩糧;鄉飲邀速賓介,祭祀營求監宰;進學先為保引,行禮圖充導贊;扳親人族,上書獻詩;奪授生徒,勒索束脩;霸佃學田,占種拋荒;放債收租,過取利息;科舉起貢,爭論盤纏;身具衣巾,雜乞人而待賑;手提秤斗,作牙儈而不辭。傍驛遞,撥馬差夫;予里甲,掛牌銷卯;當行坐鋪,賭博贏錢。彼方得意,何有愧顏?[50]
上述種種,生員決非會白白忙碌,其目的還是為了“罔利”。可見,明代生員的額外收入來源甚廣。考明代士人的額外收入,大抵來自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包攬錢糧、硬幫中保,藉此獲得“二三錢轎馬”[51]。其中的包攬錢糧,是指生員通過優免權而獲得普通百姓的投獻;而中保一類,則是憑借個人身份的信譽而獲取好處。二是包攬詞訟,囑托公事,從中獲利,亦即到府、縣衙門里去說人情。尤其是到了冬盡,一些原在鄉村訓蒙糊口的生員,都歇館在家過年,一等有事,就終日纏官擾民,今日上手本,明日上呈子,興訟、息訟,一由他們任意所為。事前,可先得酒肉吃喝,索取轎錢。事妥,又有謝銀、白米[52]。至于通過說人情而獲利,則可以下面史料加以說明。史載周心鑒任嚴州府推官時,其中就有一位出自他門下的生員,通過獻大部古書的方式,向周氏行賄,“為人居間”[53]。當然,這種居間說人情之事,生員決非白白忙碌,最終還是為了獲取好處費。
(三)庶民
在明代的庶民階層中,尤其是以自耕農與半自耕農為主體的農民家庭,家庭收入的構成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即家庭生計的維持,不再僅僅依靠男性勞動力所從事的農業勞動乃至由此而來的田地收入,而家庭婦女的副業收入亦不再是補貼家庭生計的輔助收入,有時家庭副業收入甚至可以與主業收入并駕齊驅,進而印證了婦女能頂“半邊天”之說[54]決非空穴來風。
農民家庭副業收入的增長,在明代可謂一種大勢,無論是北方,還是南方,無不如此,當然還是以江南最具典型性。以北方為例,如山東東昌府臨清州,“闔境桑麻,男女紡績,以給朝夕。三家之市,人挾一布一縑,易擔石之粟”[55]第2冊,p712。再將目光集聚到廣東。明代廣東農民家庭的副業,尤以養蠶為主。從史料記載不難發現,當時按照一個家庭農婦的勞動力來計算,通過養蠶,一年可得絲40斤。這40斤絲,就“可充八口之食矣”,也就是可以維持一家八口的吃食。當然,其前提是必須有10畝之地,以供種桑[16]卷24,八蠶。
至于明代的江南,家庭生計的來源,更是依賴家庭婦女的紡織副業收入。如松江府,無論是“城中”,還是“鄉落”,紡織業均相當興盛。史稱“里嫗晨抱綿紗入市,易木棉花以歸,機杼軋軋,有通宵不寐者”。松江府農民田地收獲,除了輸官、償債之外,未到年終,就已陷入“室廬已空”的窘境,全家衣食,全都依賴婦女的紡織補貼。若是棉花、大米踴價,“匹婦洗手而坐,則男子亦窘矣”[55]《南直隸·松江府》,第1冊,p310,確乎道出了當時的實情。又如常州府所轄五縣,只有無錫縣不種草棉,然棉布之利,卻以無錫為盛。關于婦女紡織在無錫農民家庭生計中所占的地位,下面的史料記載已是一語道破:“鄉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及還租已畢,則以所余米舂白,而置于囷;歸典庫以易質衣。春月則闔戶紡織,以布易米而食,家無余粒也。及五月田事迫,則又取冬衣,易所質米歸,俗謂種田飯米。及秋,稍有雨澤,則機杼聲,又遍村落,抱布貿米以食矣。”[56]由于家庭紡織副業在家庭生計中越來越占據重要的位置,所以無錫縣的農民,即使遇到兇年,只要其他地方棉花成熟,那么鄉民亦不致大困。
在浙江桐鄉縣,“女工”在家庭生計中的重要性大抵也是如此。史稱桐鄉西鄉女工,大致以紡織“綿綢素絹”為主,或者織“苧麻黃草以成布匹”;而東鄉女工,“或雜農桑,或治紡績”。至于其他鄉里,亦有以“紡織木棉與養蠶作綿為主”。可見,就桐鄉縣農家生計而言,顯已“隨其鄉土,各有資息,以佐其夫”[19]。雖說男耕女織,自古以來就是農家的本務,然尤以明代江南農家的表現最為突出。在江南農家幾乎家家織衽的大勢下,一些經營性的地主乃至自耕農家庭,不得不對家庭副業格外重視,百般算計。根據張履祥的記載,當時江南家庭婦女紡織生產力乃至由此而帶來的家庭副業收入,已經不可小覷。若是家庭婦女紡織技藝出眾,且夙夜趕趁,其產生的勞動價值相當可觀。即使按照當時的常規,婦女2名,每年可以織絹120疋。每匹1兩,值平價銀1錢,計得價銀120兩。在這120兩的收入中,其主要的成本開支有:經絲700兩,價銀50兩;緯絲500兩,價銀27兩;籰絲錢、家伙、線蠟,價銀5兩;2名婦女全年的口食,需銀10兩。這幾項成本開銷相加,共計費銀92兩,那么其實際的收入則為28兩銀子。若是自己養蠶,外加自己繅絲,則成本開支將更為減少,全年收入利潤則更為豐厚[21]。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的諺語。可見,賢妻是家庭生計的重要輔佐。換言之,女工勤者,其家必興;女工游惰,其家必落。婦女紡織收入,對于家道興衰,尤為關鍵[19]。
在明代庶民階層的額外收入中,商人、手工工匠因限于史料匱乏,姑且置之不論。即以屬于賤民的戲子來說,除了工食錢之外,有時戲子在士大夫家唱堂會,還可以得到賞錢。賞錢少者,一個多達六七十人的戲班子,僅得賞銀5錢;賞錢多者,每名樂工各獲賞銀二、三兩[41]卷15,史。兩者差別甚大。
(四)軍人
明代軍人的額外收入,可從武官與軍兵兩者論之。就武官來說,其額外收入主要來自克扣軍兵的軍餉。即以明代邊軍的糧餉為例,根據當時地方官員建議的撙節之例,軍兵每上繳糧1石,理應折銀1.2兩,然在實際收受之時,只是折8錢銀子,余下4錢銀子就流入官吏的腰包。到了發放軍餉之時,每糧1石,僅給軍兵4錢銀子,存留4錢,稱為“撙節”。所以,以糧餉的實際價值而言,每名軍士一月實際所得,只有3斗2升而已[57]。這是典型的克扣軍餉,而克扣下來的軍餉,則分別被地方官員與軍隊武官落入私囊。
明代軍兵軍餉頗低,再加之武官的克扣,其生活更是苦不堪言。當然,明代軍兵除了軍餉之外,有時也有一些額外的犒賞銀,藉此貼補生活。如在萬歷四十七年(1619),徐光啟受命負責訓練山西、陜西、河南三營民兵,光宗皇帝就曾下發內帑,犒賞兵士每名1兩銀子。泰昌元年(1620),光宗登極,又犒賞兵士每名2兩銀子。天啟元年(1621),熹宗登極,頒發皇賞每名2兩銀子。這些犒賞銀,對于那些一直生活艱辛的軍兵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所以,“每一奉旨,輒歡欣鼓舞,如獲新生”,無不愿意捐軀報效[42]卷4,謝皇賞疏。
四、余論:從收入構成看明代人的生活質量
綜上所述,明朝人的收入構成,雖分基本收入與額外或業余收入兩大項,卻呈現出極強的社會等級性。換言之,在基本收入大體穩定的情況下,生活質量的改觀,無疑有待于業余收入的增加。
進而言之,在業余收入構成中,卻又體現出等級性的特點。官宦、士人,憑借他們身份特權,拓展業余收入的渠道甚多,既有合法的灰色收入,又可輕易取得諸多不合法的收入。在官俸甚薄且廩膳無法維持生計的現實狀況下,諸如此類的業余收入,大抵構成了士大夫階層收入的主體,并使他們得以維系較為體面的閑適生活。至于像農民、佃戶、工匠一類的庶民階層,基本收入還是他們維系生活的主要來源。當然,庶民階層中的一部分人,因為耕織并重的生產方式,或者借助于多種經營,從而走上了發家致富之路,使家庭生計在維持基本生存的前提下得以改觀。
最為關鍵的是,通過對明代社會各階層的收入構成基本狀況的考察,大抵可以證明,作為衡量物質財富主要標志的收入,事實上決定了生活質量的高低。
參考文獻:
[1]趙翼著,王樹民校證.明官俸之薄[M]//廿二史札記:卷32.北京:中華書局,2001:750.
[2]于慎行.月俸[M]//谷山筆麈:卷9.北京:中華書局,1997:106-107.
[3]重修毘陵志:卷10:職官[M]//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4]謝肇淛.事部[M]//五雜俎:卷1.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310.
[5]黃瑜.京官折俸[M]//雙槐歲鈔:卷9,北京:中華書局,1999:184.
[6]余繼登.典故紀聞:卷10[M].北京:中華書局,1981:183.
[7]逸典·兩京官俸[M]//談遷.棗林雜俎:智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
[8]李樂.見聞雜記:卷3[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45.
[9]陸容.菽園雜記:卷5[M].北京:中華書局,1997:61-62.
[10]葉夢珠.閱世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1]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后汎鳧記[M]//珂雪齋集:卷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2]陳寶良.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414-416.
[13]陳確.陳確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9.
[14]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7:劉參傳[M].北京:中華書局,2003:797.
[15]常熟縣志:卷4:食貨志[M].明嘉靖十八年刻本.
[16]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4:谷[M].北京:中華書局,1985:376.
[17]顧起元.客座贅語:卷5:三宜恤[M].北京:中華書局,1997:162-163.
[18]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10:蘇松二府田賦之重[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241.
[19]張履祥.補農書:下:總論[M]//載氏著.楊園先生全集:卷50,下冊.
[20]呂坤.實政錄:卷2:民務·小民生計[M]//載氏著,王國軒,王秀梅整理.呂坤全集: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947-948.
[21]張履祥.言行見聞錄二[M]// 楊園先生全集:中冊:卷32:.
[22]張履祥.補農書:上:運田地法[M]//楊園先生全集:下冊:卷49.
[23]莊元臣.曼衍齋文集[M].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3.
[24]朱國禎著、王根林校點.農蠶[M]//涌幢小品: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8.
[25]江盈科.聞紀·紀警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07.
[26]謝肇淛.劉滋傳· 小草齋文集:卷11[M]//《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天啟刻本:集部第176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27]張瀚.異聞紀[M]//松窗夢語:卷6.北京:中華書局,1985:119.
[28]李昭祥.孚革志·律己之弊有五[M]//龍江船廠志:卷6..
[29]文徵明.重修織染局記[M]//孫佩.蘇州織造局志:卷3.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30]韓六章.遵化廠夫料奏[M]//陳子龍等編.明經世文編·補遺:第6冊:卷2.北京:中華書局,1997.
[31]徐光啟.奉旨修改歷法開列事宜乞裁疏[M]//徐光啟集: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41.
[32]劉體乾.財用詘乏懇乞圣明節省疏[M]//孫旬輯.皇明疏鈔:卷39.明萬歷十二年刻本.
[33]李清.弘光[M]//三垣筆記:下,北京:中華書局,1982:108.
[34]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集[M]//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北京:中華書局,1982:58.
[35]吳應箕.時事[M]//留都見聞錄:下卷.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39.
[36]張岱.濮仲謙[M]//陶庵夢憶: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7]楊嗣昌著,梁頌成輯校.楊嗣昌集[M].岳麓書社,2005:172.
[38]戴金編次.旗軍人等有家小關米一石無家小關米六斗例[M]//皇明條法事類纂:卷16.日本古典研究會,1966:408.
[39]福州府志:卷20·兵戎志2·武備[M]//福建文史叢書,方志出版社,2007.
[40]李化龍.摘陳遼左緊要事宜疏[M]//陳子龍等編.明經世文編:卷422,北京:中華書局,1997.
[41]何良俊.四友齋叢說[M].北京:中華書局,1983.
[42]徐光啟.簡兵事竣疏[M]//徐光啟集:卷4..
[43]民事志[M]//鹽城縣志:卷3.明萬歷刻本.
[44]沈國元.兩朝從信錄:卷3[M].明刻本.
[45]伍袁萃.林居漫錄別集:卷3[M].清鈔本.
[46]趙吉士輯撰,周曉光,劉道勝點校.獺祭寄[M]//寄園寄所寄:卷7.合肥:黃山書社,2008:518.
[47]葉盛.翰林文字潤筆[M]//水東日記:卷1.北京:中華書局,1997.
[48]李日華撰,郁震宏,李保陽點校.六研齋三筆:卷4[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242-243.
[49]李日華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軒日記校注:卷1[M]//萬歷三十七年己酉十一月五日條,上海:遠東出版社,2011:59.
[50]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134·陜西學政[M]//《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歷三十九年刻本:集部第153冊.
[51]華陽散人.第1回[M]//鴛鴦針:第3卷.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116.
[52]金木散人.第32回[M]//鼓掌絕塵.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355.
[53]丁元薦.西山日記:卷上·器識[M]//涵芬樓秘籍:第7集,影印舊抄本.
[54]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269-314.
[55]顧炎武著,譚其驤,王文楚,朱惠榮等點校.山東·東昌府·物產[M]//肇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6]黃卬.錫金識小錄:卷1[M].清光緒二十二年王念祖活字本.
[57]霍韜.第三札[M]//明經世文編:卷185.北京:中華書局,1997.
責任編輯張穎超
網址:http://xbbjb.swu.edu.cn
DOI:10.13718/j.cnki.xdsk.2016.03.020
收稿日期:①2016-02-29
作者簡介:陳寶良,哲學博士,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明代社會變遷時期生活質量研究”(15AZS006),項目負責人:陳寶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明清商人傳記資料整理與研究”(14ZDB035),項目負責人:張明富。
中圖分類號:K2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841(2016)03-0158-11
[明清史研究]主持人:陳寶良
主持人語:隨著各種新式理論模式的引入,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日趨多樣化。不論如何變化,“國計民生”的課題,仍將屬于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核心課題,且有進一步深化乃至細化的必要。就“國計”的層面而言,明清國家財政的變遷乃至時代轉型,已經成為史學界關注的重點;就“民生”的層面而言,明清時期民眾的生計,尤其是當時人們的生活水平甚至生活質量,同樣值得引起研究者的重視。
本期所收兩篇論文,陳寶良所撰之文從基本收入與業余收入兩個層面,系統考察了明代各社會階層的收入構成,進而探討明朝人的生活質量;郭燕紅所撰之文,以晚清江南常熟、昭文二縣為個案,對均賦到民變的歷程進行了系統的梳理,進而對晚清江南的社會危機加以透視。透過這兩篇論文,不難發現這樣一個事實:一個時代的民生即百姓的生活質量,取決于收入、負擔、物價、消費諸要素。民生的好壞,又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民心的向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