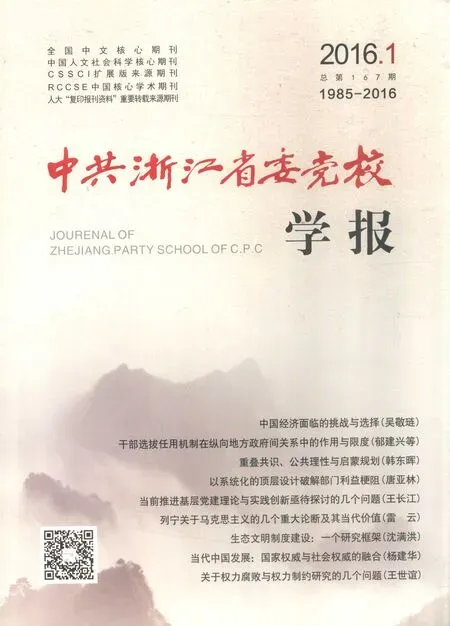重疊共識、公共理性與啟蒙規劃
重疊共識、公共理性與啟蒙規劃
□韓東暉
摘要:對于當前若干重要的政治哲學問題而言,羅爾斯論述重疊共識和公共理性的思路和方法頗具啟發意義。他認為社會穩定是社會正義的必要條件,而在理性多元論條件下,重疊共識又是穩定的必要條件。本文首先勾勒了從正義理論到重疊共識的焦點轉換,然后指出重疊共識概念對于我們理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理論特征具有借鑒意義,核心價值觀為構建當代中國重疊共識提供了一種現實范例。進而,重疊共識為公共理性提供指南,本文梳理了公共理性概念的涵義,力圖說明理性的公開使用的自由是從比附型啟蒙到內生型啟蒙轉換的哲學前提,而公共理性是這一轉換的一種可選擇的政治觀念。
關鍵詞:重疊共識;核心價值觀;公共理性;內生型啟蒙
一、從正義理論到重疊共識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德性。”這是羅爾斯《正義論》開宗明義的觀點。這部“正義論”(theory)正是以“正義”概念(concept)為中心、以“公平正義觀”(conception)為理念而展開的。它要探究的是,如果完全正義的社會是可能的,那么所需要的正義原則及其可辯護的制度安排是怎樣的。這種解讀帶有一種先驗論證的特點。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近代以來的“正義論”多持同情的批判態度。例如,持批判的態度是因為或者這些正義論沒有認識到所謂的永恒正義不過是在資產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的正義,或者誤以為只要真正的正義理論一旦被發現,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誤以為絕對真理是不依賴于時間、空間和人類的歷史發展的;卻沒有認識到正義根本上是與具體生產方式相一致的正義,不正義則首先是生產關系上的不正義,正義理論只是上層建筑,而不是支配著世界的“努斯”(nous)。持同情的態度則是因為啟蒙思想家“也同他們的一切先驅者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使他們受到的限制”。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536-537頁。
沒有一種理論能夠完全超出自己賴以產生的時代的限制,具體的時代才能賦予一種理論真實的共性和豐富的個性。沒有任何預設也就不會產生任何內容,明確有力的前提是有生命力的內容的先決條件。羅爾斯的正義論也是如此,自由、民主、法治的現代社會是其理論得以理解和辯護的語境,得以展開和前瞻的參照系,盡管這些語境和參照系的某些部分看上去似乎是理論推演的結果,而不像是前提。*這一情況與康德批判哲學的先驗論證有相似的地方:康德可以為牛頓力學乃至普遍性的先天綜合判斷的可能性做出先驗的辯護,卻不可能從其先驗理論中推出牛頓力學,推出各種先天綜合判斷。這種先驗論證可以理解為一種特殊類型的溯因推理(abductive reasoning),即從作為結果的給定事實開始反推其作為原因的原則(規則),這些原則是理解復雜實在的解釋模式。
也正因為如此,作為道德哲學的羅爾斯正義論,遇到了社會-政治哲學的難題。*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Expanded ed.(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p.xv-xviii.下文簡稱PL,隨文標注頁碼。參見John Rawls and Samuel Freeman,Collected Pap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414 n.33.《正義論》中在道德哲學上能夠得到理性辯護的公平正義觀,在進入良序社會,成為公共正義原則的時候,是作為某種總括性學說(comprehensive doctrine)或道德倫理的核心部分出現的。而可持續發展的自由、民主、開放的社會,必須奉行理性多元論(reasonable pluralism)原則,理性多元論尊重多種總括性學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然而,由于判斷責任的存在,出自理性的理論建構和思想探索會產生各種社會政治、哲學宗教學說,這些總括性學說或者彼此異質,其基本原則有可能相互沖突,或者不能一致接受包含某種正義觀的道德理論,例如羅爾斯的正義即公平的正義論。
如果良序社會缺乏共同接受的正義原則和正義理論,就會造成了類似于硬幣兩面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理論問題是包含某種政治正義觀的道德理論能否得到合理辯護;現實問題是如何既尊重理性多元論,又保障自由民主政體的穩定,保證開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是政治自由主義面臨的核心問題,也是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考察的基本主題。羅爾斯對這一問題的概括,就現實性而言,是“一個由自由平等的公民組成的、穩定而正義的社會,因為若干理性的卻不相容的宗教、哲學和道德學說而產生深刻分歧,這樣的社會如何可能長期存在?”就辯護性問題而言,是“理性的卻深入對立的各種總括性學說,如何可能共同生存,并一致支持憲政政體的政治觀?一種能夠獲得這種重疊共識支持的政治觀的結構和內容是什么?”(PLxviii)于是,“重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概念就是首要的解決思路:“在理想的重疊共識中,每一個公民都既支持一種總括性學說,也支持作為共識的政治觀,兩者多少相互聯系。”(PLxix)
重疊共識不是權宜之計、臨時妥協(modus vivendi),不是具體政策、應對策略,也不是罷黜百家、獨尊一術,相反,羅爾斯的重疊共識概念力圖在各種理性的總括性學說之間,以憲法共識為前提,在基本權利、統治原則、制度要素上,達成基于道德根據的理性辯護的政治觀。這種“觀點”(conception)只是“學說”(doctrine)的組成部分,涉及根本性的政治正義原則。唯有這種重疊共識才能提供一系列獨特的公共的理由(reasons),讓各種理性的總括性學說的支持者基于自身的理由,贊同公平正義觀,維系出于正當理由的社會統一和社會穩定。(PL 134)這是單純的憲法共識和獨立的理論辯護無法實現的。
羅爾斯的重疊共識也就是他提出的政治正義觀,包含了特定的基本理念、基本原理、制度安排和兩個實現階段。重疊共識的重點是“求同”,尋求共同支持的正義觀;同時也強調“存異”,即承認理性分歧的事實,尊重對何謂善惡的不同觀點,參與開放而真誠的協商,寬容不同的結論。*Jon Garthoff,"The Idea of an Overlapping Consensus Revisited," 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46,no.2 (2012).p.183.
二、作為重疊共識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重疊共識概念在政治正義觀的重大問題上,通過細致明晰的理論考量為求同存異的理念樹立了范例,值得我們借鑒其思路,凝聚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共識。在筆者看來,當代中國的社會發展之所以需要構建重疊共識,并不是因為缺乏共識,而是需要在理論和現實上更深入、更豐富地解決共識問題,以回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現代化進程和全球化語境中遇到的各種新情況、新問題,同時與古代傳統中對“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文化期許相呼應,再造漢唐氣象。
在這個意義上,即便在理想形態的理論考察中,構建中國社會的重疊共識也面臨遠比羅爾斯的重疊共識理論更為復雜的背景和情境。也就是說當代中國的復雜性不僅僅是若干總括性學說之間的差異,不同意識形態紛爭的壁壘,根本上是不同文化類型和不同歷史進程的共存與共生、抵牾與混搭。
從文化類型而言,自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基本走向是圍繞選擇何種現代化路徑展開的。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從言技、言政、言教的三階段劃分,到中西文化與價值的體用之爭,莫不逐漸顯現出中國文化和現代化追求的思想背景和時空構架,這就是“古-今”歷史性向度與“中-西”文化地域性向度。這就是說,不存在單向的古今之爭和中西之爭,也不存在單一層面的現代化追求和進程。重大的文化問題既在復古與求新、舊邦新命與開天辟地的雙重張力下展開,也在中體西用與西體中用、兼收并蓄與綜合創新之間變奏。無論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持續進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構建,都體現出古今-中西兩個向度之間的張力與交匯。也許沒有哪一種文化像中國文化這樣,在20世紀及其前后幾十年間,經受著如此紛繁復雜的理論學說、文化態度和價值教化的拷問;也許沒有哪一個時代,像百余年來這樣,匯聚了如此豐富而深厚的思想資源,使中國文化能夠在這個時期積累起多層次的思想寶藏,為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提供條件,為構建基于文化的重疊共識積累可選擇項。
從歷史進程而言,在“古今-中西”十字路口上各種思想形態、社會建制和倫理價值的交匯處,在現代化進程中和全球化背景下,我們能夠看到形形色色的前現代階段的、現代化的和后現代狀態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形態交織碰撞在一起。這無疑是因為上述“古今-中西”的架構發生在后發國家“主動仿效型”現代化追求和文明古國“積極參與式”全球化進程的歷史背景中,因此當今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型現代化努力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導方向。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的融入、傳統文化精華的繼承、面向現實和未來的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構成了我們回應時代挑戰的主要思想資源。因此,這種“古今-中西”架構下的現代化追求決定了尋求重疊共識的可能性。
要探尋作為具有文化和歷史維度的政治正義觀的重疊共識,可以有三種路徑。第一種是探尋現實的、實然的實質性共識的具體內容,這種路徑可以試圖在當代不同類型的主流思潮中,尋找能夠作為共識的共通因素;第二種是為理想中的、應然的實質性共識來辯護,如同羅爾斯所考慮的那樣,僅在各種理性的總括性理論中達成特定的政治正義觀,證明其應有的合理性;第三種是基于歷史性的創造性轉化路徑,這種路徑的名稱借自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理論,*參見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三聯書店1996年版。也類似于前兩種路徑的綜合,其著力點既非尋求最大公約數,也不是單純的理論構造,而是立足于復雜的文化背景、多重的歷史階段,基于憲法共識,參照當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實際情況,根據中國改革與發展的經驗與理論總結,通過公共的理性活動,創造性地構建重疊共識。
筆者認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堪稱構建當代中國價值領域重疊共識的現實范例,并且明確體現出基于歷史性的創造性轉化路徑,可以作為這一規范性探究的典范。
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包括三個層面的十二個德目的核心價值: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
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而言,這十二德目也許還可以進一步補充或修正,如同羅爾斯認為基本善的五條目必要時可以補充一樣;但這十二個核心德目的選擇精當,達到了歷史與現實、繼承與創造、共通與特色、社會與個人的高度結合,堪稱是價值觀領域重疊共識的現實范例。
例如,就歷史與現實而言,以富強為理想,以民主為途徑,建立一個富強的民主國家,是中國近代以來百年共和與革命的首要目標,小康社會的建立便是這一目標的初步實現;自由是啟蒙運動和德國古典哲學的核心理念,經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揚棄和發展,使“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成為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在當代中國將這一哲學自由理念與公民基本權利的政治自由理念結合在一起。
就繼承與創新而言,和諧、誠信是中國傳統中的核心價值,《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即可見一斑。而和諧社會是21世紀第一個十年建設的目標,誠信則是當前社會和個人最需要的基本品格。
就共通與特色而言,圍繞保障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而建立的社會治理方式,在維護社會穩定和秩序上已經被證明為行之有效的,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也成為當代社會的價值共識;與此同時,這四個理念在中國語境中又獨具特色,需要隨著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系、民主政治體制、法治體系的逐步完善而逐步彰顯。
就社會與個人而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與社會層面的追求價值目標,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則是個體的價值目標,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則是兼社會與個體于一體的價值目標,在實現國家與社會和個體與群體的價值目標中居于樞紐地位,堪稱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由此觀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十二個德目,既不同于《大學》中以修身為本的君子進學致仕以至于“哲學王”的次第,也不同于如法國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單一層次口號,而能夠最大限度地包容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人類文明的崇高理念和當代中國的國家治理與個人品格訴求,體現出基于歷史性的創造性轉化特征,能夠發揮當代中國社會的重疊共識的作用。
與羅爾斯的重疊共識概念相似,核心價值觀不是單一的總括性學說,而是多種文化傳統、多個歷史進程、多樣哲學觀念的共同價值理念,同時又體現出代表先進文化、倡導科學發展和深化改革開放的進取導向,一種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氣象。同樣,核心價值觀將嚴格意義上的重疊共識(政治正義觀)與寬松意義上的重疊共識結合在一起,即“除了獨立的政治正義觀所表述的政治價值外,還包括一大類非政治價值”(PL 145),表達了多樣性的觀點。正如羅爾斯在《作為公平的正義》所概括的那樣,“重疊共識觀念的引入,使良序社會的觀念更具現實性,使之適合于民主社會的歷史和社會條件,包括理性多元論這一事實”*John Rawls and Erin Kelly,Justice as Fairness : A Restatement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32.,作為重疊共識的核心價值觀也能夠成為保障政治穩定、社會正義的指南。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闡發和踐行既保障了公共理性的價值,同時也有待更深層次的理性辯護。理性辯護和公共理性的運用從來不是一蹴而就、萬事大吉的活動,因為理性多元論、理論多樣性始終是公共文化的持久特征,因為在重疊共識當中對政治正義觀的接受,不是持不同觀點者的暫時妥協,而是依賴于被每一個公民贊同的總括性學說中的特定理由的總體。(PL 170-171)因此,重疊共識的構建與公共理性的運用密不可分,而公共理性的運用與啟蒙規劃的重啟一體兩面。
三、理性與公共理性
羅爾斯延續了“理性的”(reasonable)與“合理的”(rational)這兩個概念的區分。事實上,這兩個詞(乃至涉及reason和rationality的各種詞匯)在日常用語中的區分并不清晰,時常混用,甚至與哲學、倫理學上的慣用法相左,原因在于二者都是合理性(rationality)的不同表現。
羅爾斯的這一區分源于康德,借自西比利(W.M.Sibley)。在康德那里,“理性的”與“合理的”的區分,是絕對律令與假言命令的區分,因而體現了純粹的實踐理性和經驗的實踐理性的區分。在西比利那里,合理的行為源于其行為是明智的,而不是行為的目的;理性的行為則是由共同遵守的原則轄制的、以他人的福祉來解釋其后果的行為。*W.M.Sibley,“The Rational Versus the Reasonable”,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62,no.4 (1953).p.60.甚至可以說,前者是合理利益驅動的,后者是由理性法則驅動的。由于涉及政治正義觀,羅爾斯對“理性的”的使用更為嚴格,使之與兩種意愿相關聯:一種是提出并尊重公平的合作條款,另一種是承認判斷責任(burden of judgement)并接受其后果,以便運用公共理性,引導在憲法政體內合法使用政治權力。(PL 49、54)
這樣,“理性的”便是道德感的一種形式,體現出個體的道德人格,具有公平合作、對等互惠(reciprocity)和公共性的特征;這些特征使“理性的”能夠為正義原則辯護,而“合理的”不具備這些特征,因此它是從屬性的,正義原則不能僅用原初狀態中各方的“合理”選擇來辯護。同樣,自由民主社會中總括性學說的多元論、多樣性也不能根據其“合理的”方面來辯護,這最終會陷入利益之爭,價值分裂。只有基于理性的學說才能得到有理性、有道德人格的公民個體的贊同。“合理的”集體主義如果缺乏“理性的”特征,也無法具備公共精神。同樣,由于認識論和道德哲學上存在著判斷責任,導致了出自理性的分歧,也造成了理性多元論下的總括性學說之間的競爭甚至沖突。這一點使羅爾斯強調理性,但不落入理性主義;尊重公民的有限經驗,但不陷入經驗主義;承認判斷責任,但不陷入懷疑主義;進而以“公共理性”概念取代啟蒙運動中被逐漸形而上學化的“純粹理性”、“絕對精神”,用代表公共理性的最高法庭取代純粹理性的最高法庭。
闡明公共理性概念與闡明理性概念一樣,是非常復雜而艱苦的理論工作。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1993)和后來發表的“公共理性觀念再探”(1997)中,將這一自盧梭、康德以來的重要觀念與當代問題(如馬丁·路德·金的公民不服從理論)相聯系,大大推進了公共理性觀念,例如關于公共理性的觀念與理想的區分、排他性觀點和包容性觀點的區分、宗教與公共理性的關系等等。不過,筆者認為,公共理性觀念應與康德式的啟蒙觀相結合,才能夠克服啟蒙精神自身的弱點,形成當代中國所需要的啟蒙精神。
英文中的reason作為哲學概念,大致有兩種主要涵義,一是推理能力和活動(a faculty of reasoning,discursive reason),通常被譯為“理性”,包括理論(或思辨)理性和實踐理性,二是一個或多個理由、原因、動機、根據。*參見Michael Proudfoot and A.R.Lacey,The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4th ed.(Milton Park,Abingdon ; New York,NY: Routledge,2010).p.341.這兩個意思當然密切相關,但仍然有明顯區別。在英文中出現時可能只是單復數的差別,在中文中卻是“理性”和“理由”兩個概念的分別。例如在《牛津大詞典》中,譯自意大利語“ragione di stato”和法語的“raison d'état”的英文概念“reason of state”,被理解為“統治者或政府行為的純粹政治根據(ground)”,因此是“理由”而不是“理性”;“public reason”在17世紀則是“reason of state”的同義詞。*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Reason,N.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盡管有人不滿足于“國家理由”而希望建立“國家理性”的理論,但至少在近代早期語境中,這種“reason”是理由和根據,而不是思辨或實踐的理性。不過,原因和理由是推理的前提或依據,是理性活動鏈條中的必不可少的部分;理性的活動也離不開理由空間(space of reason),因此,理性、推理和理由,這三者的共同作用便可形成“道理”、“常識”,這也是公共理性觀念的語義基礎。公共理性實際上形成了一套概念框架,也許稱之為“公共理據”更貼切一些;不過公共理性已成通譯,如無必要勿增實體可也。
因此,我們在羅爾斯的著作中,既看到單數的“public reason”,也看到復數的“public reasons”,既看到作為“政治社會的行為方式”的理由,也看到不同的意義上的作為“實施這種行為的能力”的理性——“一種根植于人類社會成員諸潛質中的理智能力和道德能力”。(PL 212-213)在這個意義上,羅爾斯的“公共理性”觀念實際上綜合了“國家理由”(純粹政治根據)、盧梭的“公意”、康德的“理性的公開運用”等多種內涵,并進一步做了多重限制,聚焦于根本性的政治關系。
在羅爾斯看來,公共理性的觀念(idea)屬于良序的憲政民主社會觀(conception),公共理性的內容和形式是民主觀念本身的一部分,即公民理解公共理性的方式和公共理性詮釋公民的政治關系的方式。(PL 440-441)因此,公共理性的觀念在最深層次上明確了那些基本的道德和政治價值,這些價值決定了憲政民主政府與其公民的關系以及公民與公民之間的關系,也就是政治關系本身。我們看到,無論是公共理性觀念的五個層面、其內容所包含的政治概念的三種特征,還是其公共性的三種表現方式,以及公共政治論壇的三個部分,這些要素以及公共理性的推理方式,均是在政治正義觀中進行的,而這種政治正義觀就是各種總括性學說所達成的重疊共識,因此重疊共識是公共理性的指南。
于是,我們看到,羅爾斯設想的是在一個良序的多元民主社會中,自由平等的理性公民,在社會的背景文化或公民社會的文化中的理性運用之外,在公共政治論壇當中履行其公民之為公民的責任(duty of civility),運用公共理性這種共享的理性活動形式,決定憲法基本要素和基本正義問題,為政治的合法性做出了彼此可以接受的辯護,以實現社會公平合作的理想。這種公共理性的觀念是協商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之一。*另外兩個要素是憲政民主制度框架和公民普遍遵循公共理性并在其政治行為中實現公共理性之理想的知識和愿望。(PL 448)
羅爾斯認為,公共理性與政治自由主義與當代世界飽受爭議的問題是高度相關的。(PL 438)他的公共理性理論的確富于啟發意義,但在這里,筆者不打算進一步評論,而是要根據構建重疊共識的基于歷史性的創造性轉化觀,擴展公共理性概念,使之與康德的理性的公開使用的觀念相結合,調整和重啟啟蒙的規劃,概言之,公共理性是理性的公開使用的自由在政治領域的實現,理性的公開使用的自由是從比附型啟蒙到內生型啟蒙轉換的哲學前提。
四、從公共理性到啟蒙模式的轉換
通常認為,啟蒙是歐洲歷史中的事件,而“什么是啟蒙”的爭論則是獨一無二的德國風。法國啟蒙哲學家和英國的道德學家都不像他們的德國同行那樣關心什么是啟蒙的問題。在中國,自近代以來,“如何啟蒙大眾”的問題就遠比“什么是啟蒙”重要,因為睜眼看世界、尋求富強的“先知先覺”們逐漸認識到,西方文明就是啟蒙的典范。20世紀的自由主義者如胡適將中國的啟蒙規劃視為帶有啟蒙精神色彩的文藝復興。左翼知識分子如魯迅則將中國的啟蒙規劃視為啟蒙主義的精神改造和反抗壓迫的文化覺醒。激進左翼和革命知識分子則利用啟蒙運動的革命色彩、歷史進步意味,將其作為政治革命規劃中在文化上的工具(“新啟蒙運動”)。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把近代中國的啟蒙運動觀稱為比附式的啟蒙運動觀。這種比附的(forced analogy)、乃至工具性的啟蒙運動,與內生的(endogenous)啟蒙運動存在著明顯差異,如同中國近現代的現代化進程實際上也是效法西方、或被認為是遵從歷史規律的效仿性現代化(imitative modernization)。
在這樣一個啟蒙的規劃幾乎成為思想史的過氣的研究對象、知識分子幾乎淪落為犬儒主義者的時候,為什么還要談論所謂“內生”的啟蒙?誰有資格來啟蒙?拿什么來啟蒙?一個回答是,啟蒙之所以必要,是因為我們還尚不具有啟蒙精神,還需要現代性的寶貴財富,避免陷入后現代主義的新懷疑論和新智者運動的狂歡。這種內生的啟蒙把我們帶回康德。
康德關于啟蒙的論述集中體現在1784年的短文《回答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當中,也散見于1786年的文章《什么叫做在思維中確定方向》、1790出版的《判斷力批判》、1794年出版的《純然理性限度內的宗教》等論著,甚至隱含地體現在《純粹理性批判》之中。當然,這一切都是因為自由是純粹理性體系的整個大廈的拱頂石,而理性是真理的最終試金石。
康德在“回答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這篇影響深遠的文章中給出了“啟蒙”的經典定義:“啟蒙就是人從他咎由自取的受監護狀態走出。受監護狀態就是沒有他人的指導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如果這種受監護狀態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缺乏無需他人指導而使用自己的理智的決心和勇氣,則它就是咎由自取的。因此,Sapereaude[要敢于認識] !要有勇氣使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的格言。”*《康德著作全集》第八卷,李秋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0頁。
“受監護狀態”也就是“不成熟狀態”、“未成年狀態”,不是身體的,而是心智的,不是缺乏心智,而是能否運用心智,其關鍵在于是否有勇氣和決心使用自己的理智,確定“自己思維”的知性準則,*在耶舍編輯的康德《邏輯學》中,表述如下:“總而言之,避免錯誤的普遍規則和條件是:1.自己思維;2.在一個他者的位置上思維;3.任何時候都與自己一致地思維。人們可以把自己思維的準則稱為啟蒙了的思維方式,把在思維中置身于他人觀點之中的準則稱為擴展了的思維方式,把任何時候都與自己一致地思維的準則稱為一以貫之的或者連貫的思維方式。”(《康德著作全集》第九卷,李秋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55-56頁。)也就是“公眾給自己啟蒙”。這之所以成為問題,因為懶惰怯懦,貪圖舒適是人之本性。
在康德看來,被動的理性、理性的他律、靠別人來引導便是成見和迷信的來源,從中解放出來是啟蒙,而自己思維的準則、理性自律更是啟蒙的唯一途徑。啟蒙最需要的是決心和勇氣,“要有勇氣使用你自己的理智”。這也就是最無害的自由,即“在一切事物中公開地運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這種自由落腳在“某人作為學者在讀者世界的全體公眾面前所做的那種運用”。*《康德著作全集》第八卷,李秋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0-41頁。
這種自主的、內生的啟蒙觀包含三個關鍵因素:(1)強調啟蒙在主題、議題、對象和結果上的普遍性:每一個有勇氣使用自身理性的人,針對一切事物,面向全體公眾,得到普遍啟蒙;(2)理性運用上的條件:每個人必須作為學者運用理性,這樣就排除了基于教派、階層、私利和意見的立場,反過來,作為學者的人恰恰享有了“充分的自由、甚至天職”,“通過著作對真正的公眾亦即世界說話”,*《康德著作全集》第八卷,李秋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頁。而不受自身職位的限制;(3)理性運用的公開性:公開運用雖然是與私人運用相對而言的,但其意義卻是最為重要的,因為唯有公開運用,才能“敞開自由地朝此努力的領域”,生活在雖然還不是“已啟蒙的時代”,卻是一個“啟蒙的時代”。
理性的公開運用的合法性來自理性批判的自由,理性自身的公開性、公共性是理性自身的要求。因此,康德將純粹理性的批判視為純粹理性一切爭辯的真正法庭:“屬于這種自由的,還有公開地展示自己的思想和自己不能解決的懷疑以供評判、而不會因此被人罵成不安分守己的危險公民的自由。這已經包含在人類理性的原始權利之中,除了本身又是每一個人都在其中有發言權的普遍人類理性之外,人類理性不承認任何別的法官;而既然我們的狀態能夠獲得的一切改進都必須來自這種普遍的人類理性,所以這樣一種權利就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康德著作全集》第三卷,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78-485頁。
因此,就理性的運用而言,啟蒙喚起理性的勇氣和理性的自身批判意識是結合在一起的,而且能夠時時警惕將理性自身絕對化的傾向。康德在《判斷力批判》的一個腳注中,似乎將這種批判稱之為“真正的啟蒙”:“因為以自己的理性不是被動地、而是任何時候都自己為自己立法,這對于只想適合于自己的根本目的而不要求知道超出自己知性的東西的人來說,雖然是某種十分容易的事情;但既然追求后者的努力幾乎是不可防止的,而且這在其他那些以諸多信心許諾能夠滿足這種求知欲的人那里是永遠也不缺少的:所以,要在思維方式中(尤其是在公共的思維方式中)保持或者確立這種純然否定的東西(它構成真正的啟蒙),必定是很困難的。”*《康德著作全集》第五卷,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06-307頁。
筆者認為,康德式的啟蒙觀是當代中國最需要也最可能的啟蒙觀。它不是用成見來培育成見,用成見來遏制成見,而是針對著當代中國最需要的精神,去培養啟蒙的精神:運用自身理性的勇氣、公開運用理性的自由和以學者身份和專業性敢于面對真相倡導公論的精神。當代中國已經具備了哲學啟蒙的和平環境、物質條件和思想資源。憑借敢于運用理性的勇氣、開放平和的胸懷和自我反思的批判能力,當代中國的啟蒙能夠從比附型向內生型轉換。
在這個過程當中,理性的公開運用作為啟蒙精神,能夠在社會各個領域培育人格,凝聚共識,能夠倡導平等對話,理性反思,使社會的心智不至于遲滯偏枯,使理智的視域不至于狹隘封閉,從而能夠為公共理性的觀念開辟道路。公共理性能夠培育公共的政治場域,保障理性啟蒙的進程,推進協商民主政治的步伐,在重疊共識的引導下,促進社會正義,創制當代中國的正義論。□
(責任編輯:徐東濤)
中圖分類號:B7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9092(2016)01-0022-007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規范性的本質與結構研究”(編號:15BZX076)。
作者簡介:韓東暉,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常務副院長、教授、博導,主要研究領域為近代早期哲學、分析哲學和中西哲學比較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