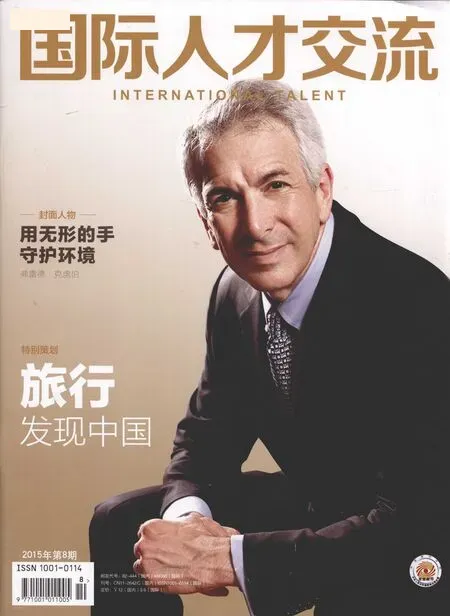畫情畫景畫鄉(xiāng)愁
—— 專訪2014年中國(guó)政府“友誼獎(jiǎng)”獲得者、畫家司徒立
文/吳星鐸 阮帆
畫情畫景畫鄉(xiāng)愁
—— 專訪2014年中國(guó)政府“友誼獎(jiǎng)”獲得者、畫家司徒立
文/吳星鐸 阮帆

布列松作品《畫室中的司徒立》
觀司徒立的畫,自然會(huì)感動(dòng)于其筆下天地。
就像中國(guó)美術(shù)學(xué)院院長(zhǎng)許江在《南山肖像》中所說,司徒立“帶著幽深的鄉(xiāng)愁,生活在巴黎”,他畫瓷瓶,“將瓷瓶放置在這片空間之中,以純粹直觀的方式,用炭條靜靜地與之對(duì)話。”他畫蘭花,“并沒有去塑造一般意義上的幽蘭的形象,而是讓這些蘭花真實(shí)地生長(zhǎng),如眼所見,如眼親見,在生長(zhǎng)之中遭遇某種生的、活的機(jī)緣。”
司徒立的畫不在求取西方或東方的風(fēng)格,也不著意描寫景物的美貌。他的畫面,除了美貌,兼具深情。
這位法國(guó)“藝術(shù)與文學(xué)騎士”勛章獲得者,2014年中國(guó)政府“友誼獎(jiǎng)”獲得者在外國(guó)專家大廈接受了我們的專訪。談笑風(fēng)生之間,為我們素描他的繪畫觀點(diǎn),勾勒他的思鄉(xiāng)情感,工筆他的教學(xué)點(diǎn)滴,寫意他的人生畫卷。
“我從小就喜歡畫畫,這一輩子什么事都沒做過,就是畫畫。一直畫到現(xiàn)在,除了畫畫,我可能什么都不懂。”畫家司徒立這樣說。
鄉(xiāng)愁里的“神經(jīng)佬”與“火鳳凰”
司徒立1949年生于廣州,很小的時(shí)候就因?yàn)楹苡欣L畫才能,而被市里集中起來接受訓(xùn)練。
那一批孩童當(dāng)中,真正一直在繪畫這條路上走下去的人不多,而司徒立就是一個(gè)。說起童年在他創(chuàng)作上留下的最直接的痕跡,竟然是放學(xué)回家路上總可以遇見的一個(gè)“神經(jīng)佬”。
這個(gè)神經(jīng)佬據(jù)說是一個(gè)很聰明的大學(xué)生,因?yàn)檎剳賽郾婚_除了。神經(jīng)佬總在他們家住的街頭擺棋局,“許多人就前去挑戰(zhàn),但始終沒有人贏過”。因而,盡管神經(jīng)佬總用他那“臟得不能再臟的腳站著下棋”,小孩子們對(duì)神經(jīng)佬還是敬畏三分的。
但真正令熱愛畫畫的司徒立感到激動(dòng)的,是有一天神經(jīng)佬僅憑一根釘子和一塊石頭,就在灰色的水泥地上叮叮叮地敲出了一只鳳凰來。正看得出奇,神經(jīng)佬又用紅磚磨了些粉末撒進(jìn)去,然后就開始圍那只火紅的鳳凰跳舞。
神經(jīng)佬邊跳還邊叨唱著那只有兩句詞的歌:“花開花不開,花不開花又開。”
司徒立說:“當(dāng)時(shí)雖然不懂,卻覺得非常的深?yuàn)W,有些禪意,于是這簡(jiǎn)單的歌便這么印在了我腦子里。”
1975年,司徒立只身一人從香港輾轉(zhuǎn)去巴黎求學(xué)。剛在公寓住下不久,他就發(fā)現(xiàn)寓所前面的空地上恰巧也有這么一塊灰色的水泥地。仿佛那只火紅的鳳凰從來就未遠(yuǎn)離,又好似花開花不開的童年仍然在繼續(xù)。
不用說,對(duì)于一個(gè)在異鄉(xiāng)漂泊的人來說,那種似曾相識(shí)的感覺令他又驚又喜,竟溫暖得有點(diǎn)攝人心魄。感慨之余,他決定,要以這個(gè)石板為題材,畫一幅畫。
憑著記憶里的曲線和力度,司徒立用鉛筆描了幾天幾夜,復(fù)活出了一只“高清”的火紅鳳凰。
這幅畫后來被法國(guó)東方藝術(shù)博物館的館長(zhǎng),一個(gè)漢學(xué)家相中。他懇請(qǐng)司徒立一定要把畫賣給他,并給出了2000法郎的高價(jià)。
在那個(gè)時(shí)候,2000法郎是什么概念呢?“我記得當(dāng)時(shí)在大學(xué)飯?zhí)贸砸活D飯是2塊9毛錢。”司徒立說。
就這樣,他的畫被2000法郎買走。不過,他的鄉(xiāng)愁卻留了下來。司徒立說:“其實(shí)是想起了我的故鄉(xiāng),想起了我的童年,就是一種思念。”

司徒立作品《家居物事·明凈》紙本木炭
四十多年前的風(fēng)華少年
司徒立說自己的命運(yùn)“很有點(diǎn)古靈精怪,算是很幸運(yùn)的那種,一路走來,結(jié)交了許多的大師”。
早年在香港的時(shí)候,他就接觸了幾個(gè)“民國(guó)時(shí)期就已經(jīng)很著名的老先生”,比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復(fù)觀。他們是中國(guó)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國(guó)儒學(xué)界里最受西方關(guān)注的幾位大師。司徒立說,跟著他們上課的時(shí)候,發(fā)現(xiàn)他們的書都是一大摞一大摞的,可見學(xué)問之深。而更難得的,是他們不依附權(quán)貴也不向任何政治勢(shì)力臣服的獨(dú)立精神。
“對(duì)于學(xué)者,這個(gè)獨(dú)立精神是很重要的,他們就保持在那里,做學(xué)問。雖然他們的日子過得非常艱苦,比香港的普通公民都要艱苦,但也就是因?yàn)樗麄儯拍軌虬阎袊?guó)的一個(gè)門脈保存到今天。”司徒立說。
徐復(fù)觀對(duì)司徒立影響頗深,他坦言,自己帶的40多個(gè)博士生中,有三分之一是學(xué)中國(guó)的美學(xué),而他指導(dǎo)學(xué)生的思想主要就是從《中國(guó)藝術(shù)精神》這本書里來的。《中國(guó)藝術(shù)精神》采取了一種融匯諸家、吸其所長(zhǎng)的態(tài)度,站在精神的高臺(tái)上,將魏晉至唐宋以來的文人畫論進(jìn)行了梳理和解讀,將繪畫史的山山水水盡收眼底。對(duì)于中國(guó)文化的不同思想傳統(tǒng),書里也沒有表現(xiàn)出什么門戶之見,更不搞什么黨同伐異。透過文字,人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徐復(fù)觀的藝術(shù)魅力,和一種做人為文的境界。
這一點(diǎn),司徒立也有所傳承。他向往絕對(duì)的獨(dú)立和自由,享受不帶功利色彩的創(chuàng)作,提倡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還保有那么點(diǎn)文人的清高,以至于他現(xiàn)在還會(huì)懷念六七十年代的巴黎。
“那個(gè)時(shí)候是絕對(duì)的自由的空氣,我們享受著人性的完全釋放。”他直言不諱,“這種絕對(duì)的自由我不知道好不好,但是對(duì)我們藝術(shù)家來說就是最重要的,因?yàn)闆]有自由就沒有創(chuàng)造。”
司徒立說,“那個(gè)時(shí)候經(jīng)濟(jì)太好,大家都不講錢”,他是真正感受到了“人的精神解放的時(shí)候是如何的一種狀態(tài)”。
“我們也真的不怎么談到事業(yè)啊,成功啊,職業(yè)啊什么的。那時(shí)候我們完全沒有想過一個(gè)專業(yè)畫家要通過畫畫賺錢。當(dāng)時(shí)我們想的就是畫畫,就要把畫畫好。”那不容置疑的語(yǔ)氣,讓你以為眼前坐著的是40年前那個(gè)在法國(guó)留學(xué)的風(fēng)華正茂的少年。

司徒立油畫作品《佳柔山-西班牙大風(fēng)景》
中西方文化藝術(shù)交流的“擺渡者”
“我屬牛,要干活兒的,所以一干就是20多年。這是我的國(guó)家,我小時(shí)候在這里受過教育,我當(dāng)然最后要落葉歸根,我要把我學(xué)到的東西還回來的。就是這樣的一個(gè)心愿,就是這樣的一個(gè)古老的情結(jié)。”司徒立說。
司徒立在法國(guó)生活了40年,在中國(guó)工作了20多年。他是第一個(gè)在巴黎國(guó)家現(xiàn)代博物館舉辦個(gè)展的華人藝術(shù)家,先后獲得意大利“盧比欣”繪畫大獎(jiǎng)、法國(guó)巴黎學(xué)院“費(fèi)里翁”繪畫大獎(jiǎng)、法蘭西學(xué)院繪畫最高獎(jiǎng)等眾多藝術(shù)大獎(jiǎng),并于2004年被授予法蘭西共和國(guó)“藝術(shù)與文學(xué)騎士”勛章。他從1991年起與中國(guó)美術(shù)學(xué)院開展全方位合作交流,1992年任客座教授,2000年他在中國(guó)美術(shù)學(xué)院創(chuàng)辦了藝術(shù)現(xiàn)象學(xué)研究所并擔(dān)任所長(zhǎng),倡導(dǎo)匯通藝?yán)怼R通中西的學(xué)術(shù)精神。
在司徒立的積極倡導(dǎo)下,中國(guó)美術(shù)學(xué)院在全國(guó)乃至全球,首開“美術(shù)學(xué)實(shí)踐與理論復(fù)合型博士研究生培養(yǎng)”的先河。迄今為止,司徒立為中國(guó)培養(yǎng)了43位博士和一大批青年藝術(shù)家,其中大多數(shù)已成為中國(guó)畫壇上極具影響力的領(lǐng)軍人物與中青年學(xué)術(shù)骨干。多年來,他輔導(dǎo)的學(xué)生科研成果30多項(xiàng)獲獎(jiǎng),尤其是在5年一屆的代表中國(guó)最高創(chuàng)作水平的全國(guó)美展中成果顯著:蔡楓作品《古樹祭》獲第九屆全國(guó)美展金獎(jiǎng),孔國(guó)橋作品《口述歷史》、蔣梁作品《祈思》、陳欣作品《事象地平線》獲第十屆全國(guó)美展銀獎(jiǎng)等。
與司徒立一同來京的中國(guó)美術(shù)學(xué)院油畫系副教授余旭鴻為我們介紹說:“司徒教授一直積極為中法友誼牽線搭橋,在他的引薦下,引進(jìn)國(guó)際一流藝術(shù)家來華擔(dān)任客座教授,法國(guó)駐滬領(lǐng)事館也在1996年把一批珍貴的圖書贈(zèng)送給中國(guó)。國(guó)內(nèi)眾多著名藝術(shù)家在巴黎留學(xué)期間,都得到他的幫助和教誨。他多次策劃了在國(guó)內(nèi)外學(xué)界有重大影響的‘法國(guó)·中國(guó)具象表現(xiàn)繪畫特展’,在中西方藝術(shù)對(duì)話中,向西方傳播當(dāng)代中國(guó)藝術(shù)創(chuàng)作成果。”
“司徒教授是中西方文化藝術(shù)交流的‘?dāng)[渡者’。”余旭鴻說。

法籍華裔畫家司徒立近照
畫家是用眼睛思考的人
“其實(shí)繪畫這個(gè)東西,不是一般的語(yǔ)言,也就是塞尚說的,用眼睛去思考去理解世界的一種手段,一種方式。也就是說,我們畫家就是用眼睛去思考這個(gè)世界的人。”司徒立說。
他分享了早年徜徉在法國(guó)的畫廊里的那段歲月與領(lǐng)悟。“當(dāng)我看到賈科梅蒂那瘦瘦的、單薄的、顫動(dòng)著詩(shī)意氣質(zhì)的雕塑,我真實(shí)地感受到了震撼,甚至有一點(diǎn)發(fā)抖。”司徒立回憶說。
司徒立說:“當(dāng)時(shí)我沒有能夠弄懂,一件作品,怎么會(huì)有那樣的,好像能夠腐蝕我們生命的那種力量。”但不久之后,他明白了,那種力量是經(jīng)歷了二次大戰(zhàn)的賈科梅蒂對(duì)于人、對(duì)戰(zhàn)爭(zhēng)深刻剖析的結(jié)果,反映的正是20世紀(jì)人類的軟弱和不堪一擊。
“二戰(zhàn)后,西方的人們把人分析,剝開來,把所有不相關(guān)的東西都剔除掉,直到最后,剩下一個(gè)人的純粹的存在。”司徒立領(lǐng)會(huì)到繪畫不僅是一個(gè)表達(dá)事物有多么美麗的工具,而且是思想的一種語(yǔ)言,是用思想對(duì)真實(shí)存在的表達(dá)和反思。借著這種啟發(fā),他開始反觀中國(guó)的社會(huì),反觀中國(guó)的繪畫創(chuàng)作。“所以我后來的整個(gè)事業(yè),就是圍繞這個(gè)藝術(shù)真理性的問題,什么是藝術(shù)真理的問題進(jìn)行的。”司徒立說。
帶著這個(gè)問題,司徒立試圖從具象表現(xiàn)繪畫的方法里面找到答案,他一步步探索著,以求得什么情況下看到的事情才是真實(shí)的,如何才能夠還原一個(gè)東西的本質(zhì)。
他在唐末畫家荊浩的《筆法記》里找到了答案的線索。“真,就是氣質(zhì)俱盛。有氣、有質(zhì)那就是一種真,生命力都存在啦。如果‘得其形’而‘遺其氣’,就是只有形,沒有氣,就沒真啦,好像一段枯木。”他說,“很多人畫得形很像,逼真得要命,但就是沒有生命力。”
與現(xiàn)象學(xué)結(jié)合起來看,那么“一是要回到事情的本身,二是用你純粹的直觀的,不經(jīng)過污染不戴有色眼鏡地去看東西,視其所是。”司徒立總結(jié)說。
司徒立認(rèn)為,學(xué)繪畫的時(shí)候,不應(yīng)該過分強(qiáng)調(diào)繪畫的意義、價(jià)值,或者說如何表現(xiàn)美的東西。因?yàn)槿绻鞍阉囆g(shù)變成了一門語(yǔ)言,那么藝術(shù)就局限在了溝通的功能上。”
他說,實(shí)際上,畫家的使命,是“用眼睛去思考這個(gè)世界”,尤其是思考這個(gè)世界上一些人類共同面對(duì)的問題。
就在采訪的幾天前,司徒立的小女兒打電話來,說自己的畫參加畫展,6幅畫賣掉了4幅。昨天又打電話來,說剩下的兩幅也賣掉了。女兒很開心,他心里也替她開心,這證明了她的實(shí)力——當(dāng)初的選擇并不是啃老爹。不過嘴上他還是給女兒潑了潑冷水:“這說明你的畫太商業(yè)化了。”作為一個(gè)畫家,司徒立覺得自己也沒有任何理由反對(duì)女兒做一個(gè)畫家。“我家的傳統(tǒng)就是,從不干涉?zhèn)€人的自由發(fā)展。”
盡管如此,他還是在女兒當(dāng)年讀大學(xué)選專業(yè)的時(shí)候給了自己的建議:“我們家姓司徒,司徒是管文教的,不學(xué)商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