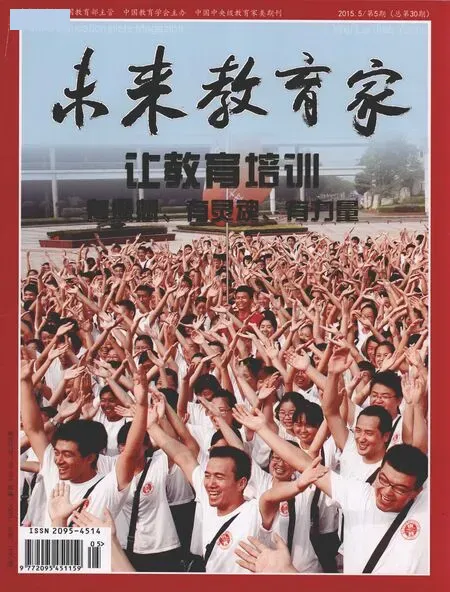循著文風走近蘇霍姆林斯基
孫孔懿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
循著文風走近蘇霍姆林斯基
孫孔懿
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蘇霍們念情、感姆都觀、林是感點斯通受、基、過疑說情自問緒過、己、:思狀的“想況人信、、彼此之間的關系以及對活生生的、可感受到的世界的關系來表現自己……在成績與失敗、希望與失望、滿意與不滿意、高興與苦惱、憐憫與冷漠、悲觀與懊悔、委屈與傷心、善意與難以容忍之中表現自己。”人的表現、表達是反映內心世界的唯一通道,是生命內容的顯示。在某種意義上,人以表達的方式存在著。換言之,人的表達就是人本身。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達風格。一種成熟的文風,總是由含有無窮意蘊的內在靈魂產生出來,是作者靈魂的準確標志。蘇霍姆林斯基在談到自己的著作時說:這些話語是從我的心靈里流淌而出的;我寫的一切,我確認的一切,那是我用鮮血寫成的。他的著作風格正是他教育風格、研究風格以及與人相處風格的書面表現,是他生命的另一種存在形式。所謂讀書,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與作者對話,就是透過文字去認識作者其人,直接點說,就是“讀人”。我們閱讀蘇霍姆林斯基的著作,也就是以他的著作為中介,去認識一個真實的蘇霍姆林斯基,走進他豐富瑰麗的精神世界。
他的敘述風格是他細膩教風的真實再現。他很少做抽象論理,而較多地注重具體敘事。他的教育信念之一就是重視教育的對象性和情境性。這一信念源于他的一個基本判斷:教育過程“具有深刻的個性特點:一條教育真理在一種情況下是正確的,在另一種情況下是中性的,而在第三種情況下則變成荒謬的”。他從孩子的多樣性出發,堅信“教育不僅是一門科學,而且是一種藝術,而教育藝術的全部復雜性,是要善于感覺到一個人身上那種純屬個性的東西”。他還認為:“教育是人跟人的細致入微的心靈接觸”。兒童特別像一株株幼苗,“這些幼苗是非常嬌嫩,需要細心照料的。它們需要光和熱,需要營養豐富的汁液,它們經受不住陰暗和寒冷”。要“善于委婉地、細致地、非強加地去啟發孩子”——“是細致的提示,而不是喋喋不休的說教”。每個教師都“必須具有觀察學生、細心感受學生心靈的微妙活動的高超技能”,“必須深刻地了解每一個學生的個性,甚至其中的細微末節”。他為了深入了解孩子復雜的精神世界,經常花費較長時間撰寫某個學生的“個性報告”,并請有關老師作詳細補充。在教育過程中,他形成了若干極具說服力的教育學案例,幾乎每個案例都有生動曲折的情節、讓人牽掛的懸念、具體入微的細節。這些細節的力量不但能夠打動學生,也能打動讀者。請看他筆下這個傳神的片段:
小朋友奧列霞很喜歡蝴蝶。每天清晨,當朝霞把玫瑰染成金黃色時,她便走進花園,她看到色彩鮮艷的蝴蝶停在玫瑰花上,輕輕地振動著翅膀。她不敢出氣,生怕嚇跑了這些嬌柔美麗的蝴蝶。可是今天上課時老師帶來了一幅掛圖,邊指著掛圖邊解釋,蝴蝶是如何變成丑陋而有害的毛蟲的。老師說“蝴蝶是害蟲,必須消滅它”。這堂課對于小朋友奧列霞來說是多么殘酷,多么不可想象!夜里,她哭了……早晨,她又去看盛開的玫瑰,欣賞美麗的蝴蝶,同時又左顧右盼,生怕有人看見自己正在欣賞害蟲……
他對小姑娘充滿同情!他認為教師固然需要向兒童揭示科學真理的實質,但切不可破壞兒童的情感、理智與美感等領域之間的和諧,務必使兒童明白,除了有益與有害的概念之外,還存在著美與丑的概念。
他的敘述風格是他尊重事實的研究風格的體現。在他的認識論中,“事實”占有重要地位。事實既是他教育信念產生的土壤,又是豐潤他教育信念的血肉。他重視事實,從鮮明、確鑿、有趣、生動活潑的事實,到反常、令人不解、嚴峻而冷酷的事實,他都不肯輕易放過,都會加以記錄、核實、分析、提煉。他說:“收集和處理事實,是一種特殊技能,它能使知識經常處于發展狀態”。“以考察的態度對待周圍世界的各種現象,具有著特別重大的意義”,這是“思維方法的基礎”,要“通過積累、分析、對照和比較事實去認識科學真理”,即使在使用抽象概念時,思想上也要“回顧作為抽象概念基礎的那些印象、形象和景象”。“形象地說,事實猶如思維的翅膀所依托的空氣”。“只有當一個用頭腦理解事實的人,能轉而用全副心思和整個心靈感受種種觀念,在教育中起著十分重要作用的真理才能變成他的信念、觀點和人的立場。”這樣的研究之風,自然會轉化為他善用事實說話的文風。
他的敘述風格是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風格的表現。他身為校長,從不盛氣凌人,而是相信人,尊重人。他的著作常常采用第二人稱,喜歡使用“親愛的朋友”,“親愛的同行”等稱呼。他對讀者不是說教,而是一種“我與你”式的對話,一種推心置腹的促膝談心。例如:
我親愛的同行,整體來說,兒童世界是美好的……要學會用心靈去傾聽、理解和感受被稱為兒童世界的這種音樂,首先是其中光明愉快的曲調。不要只當兒童世界音樂的聽眾、欣賞者,還要當它的創作家——作曲家。要在兒童世界音樂中創造光明愉快的曲調,因為這種音樂關系到你的健康、你的精神力量、你的內心狀況。
親愛的成年人同志們,請把自己擺在某某學生的位子上,你想想看,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人們都向你說:你什么都不成,你落后,你低能,你力所不及的事而別人卻做得很漂亮,那么你將會有什么樣的心情呢?
這些話語情真意誠,是教育學教科書中沒有見過的,是教授的講義中沒有寫進的,它產生于教師的心田里,并染有情感的色彩。他鼓勵同行們說:“如果你的那些道德訓誡的話語,是發自你內心的精神世界,是充滿你的信念的崇高精神,那么,這些話語就會像磁石一樣,對于那些不信賴人的人產生吸引力,而你也就會成為他們的支柱和指路燈。”他引以為豪的是:“我在學校工作了35年,我的言語和感情觸動了上千顆心。”
他的敘述風格也是他愛好文學情感的自然流露。他善于想象和聯想,寫作時總能將活躍于心中的熟悉身影和生動場面準確地再現出來,讓讀者如臨其境。他的著作中,奇特優美的比喻比比皆是,給讀者以豐富啟示。例如:
要做到了解學生這一點,一輩子也不夠啊!當一群六歲的幼童入學前一年來到我面前,并成為我的小小學生時,我對他們感知世界的差異驚詫不已。我凝視著那一雙雙烏黑、淺藍、墨綠、淺灰色的眼睛,覺得每個兒童此刻都打開了通往世界的小窗口,在入迷地觀看著藍天和大地、太陽和月亮、鮮花和飛鳥,而且每一個小窗口互不相同,各有特色。
兒童對教師的信任,猶如玫瑰花上的一滴潔凈的露珠。請不要把這一滴露珠抖落。要珍惜信任,這也就是說,要珍惜兒童對人不加防備的心。這種教育智慧應該貫穿于我們全部工作之中。
讓我們設想一下這樣的情景:復雜的外科手術正在進行中,一位技術高超的外科醫生俯身在露出的傷口上動手術,突然,一個腰插斧頭的屠夫闖進了手術室,他拔出斧頭就朝傷口砍去。這把臟斧頭就是教育中的皮帶和拳頭。
他深厚的文學功底源于他對文學名著的非凡喜愛和深度鑒賞。他說過:當我感到困難和難忍的痛苦時,我就背誦俄羅斯文學的偉大著作,不僅從中找到了安慰,還有精神力量的高漲。“我不止一次地讀過列夫·托爾斯泰的《復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癡》和《罪與罰》、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第一次讀這些作品的時候,我16歲。第二次讀的時候,我20歲。當我30歲第三次讀這些作品的時候,感受就完全不同了。”
當年司馬遷說過:“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今天我們品味蘇霍姆林斯基的文風,如聞其聲,如見其人,這或許是讀書的一種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