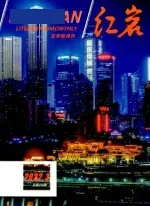傳統是可以繼承的遺產
2015-08-15 00:49:33歐陽斌
紅巖
2015年5期
歐陽斌
夏夜深長,讀完一摞來稿時已至凌晨,睡意卻遲遲不來,依然有些興奮,于是開啟了閑聊模式。此間和一位有愛的朋友,于微信平臺散吹,話題照例會涉及愛和欲望。隨后,性格特質中帶著些宿命意味的他,把交談引向生與死的終極命題,有些沉重,但同時也變得生動起來。嗯,相似的人生境況大約是這樣的,極具破壞性的青年時代連尾巴根兒也找不見了,青春已死,實物不再,能說明我們也曾經歷過這樣的和那樣的青春的,如今只有維持的現實,維持那些被青春破壞過,又在被破壞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生命意識……。這樣說的時候,已經在談及文學了,然后,話題很快轉向詩人之死。朋友舉例說到斯塔福德的絕筆詩《“你是威廉?斯塔福德先生?”》,令我想起索列斯庫臨終前寫下的《天梯》。我們近乎絕望地看見,一個詩人的最后一首詩,基本上就是對他健在人生中所有詩的否認,是死對生的否認,同時也是認領,是生死最終朝向“天梯”。就像牛頓于臨終前,用神學意識否定了他的物理學成就那樣,生的傳統受到質疑。
即便如此,我們一生都擺脫不了傳統的影響和呵護,尤其是,那些起初用“壞小孩”的方式,頑皮的方式,隨后用破壞的方式,最后用顛覆的方式,與文學傳統發生深度關聯,并由此建立個人傳統的詩人。富有意味的是,他們幾乎開啟和運行著同一種命運——不僅于最初,且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寫下否定的詩!而證實了偉大的傳統和“向死而生”個人的創造力,將同時伴隨著詩人的一生。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