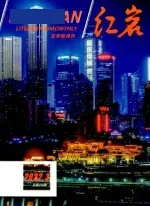足球記
2015-08-15 00:49:33于堅
紅巖
2015年5期
于堅
今夜光州在下雨。昆明星光燦爛。里斯本有人在寫詩,他的鄰居在看足球。世界各地氣候不同,但一個美妙的夜晚注定降臨。對于我來說,這種美妙是由一個濕淋淋的足球帶來的。在光州的足球場上,葡萄牙人踢得快感極了,以至我不斷地聽到解說員不斷地說到“射”這個字。還沒有射,來不及射,射偏了,轉身射,直接射,他射進了!等等。那個不看足球的詩人如果聽到這場解說,他會誤以為這世界怎么如此風流。漢語的解說詞一向一本正經,但這個夜晚我聽出張解說員有些情不自禁。葡萄牙是一只漂亮的球隊,我不是只說球技,我是說他們長得非常古典,就像是一群國王、王子在踢足球,就像紅色的火焰,光州的傾盆大雨猶如汽油,令這支球隊燃燒得更加猛烈。波蘭人并不是膽小鬼,他們也拼出了昔日血戰華沙的氣概,但終究技不如人,沒辦法,他們的球門有一個足球場那么大。光州在下雨。昆明星光燦爛。我不知道里斯本天氣如何,但我知道那邊將陷入狂歡,數百萬個屁股會同時從椅子上彈起來,數百萬的啤酒瓶蓋會飛進天空,成為另一種雨。在一瞬間改變一個國家的表情,除了上帝,恐怕只有足球可以做到。
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是1978年。當時我所在工廠的工會有一臺電視機,一個乳黃色的小箱子,放在工會的播音室,三千人的工廠里唯一的一臺,歸鉗工老肖管著。老肖是我初中同學,我們剛滿16歲,初一還沒有上完,就被國家分到這家工廠來做工。……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