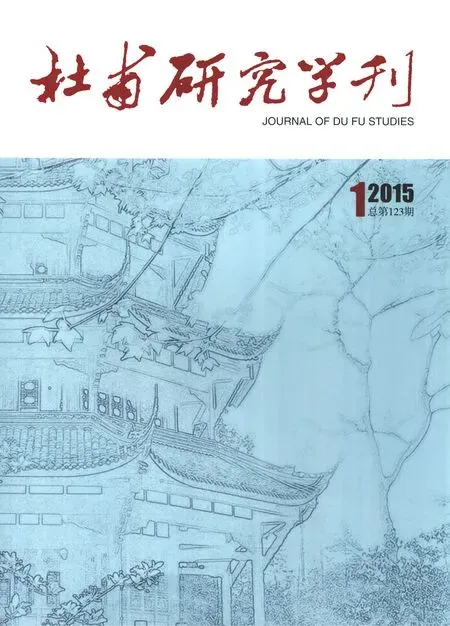楊慎杜詩考證三則
白建忠
作者:白建忠,山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041004。
近些年來,楊慎杜詩學的研究,已取得了許多可喜的成果。不過,概觀這些成果,大多是理論方面的闡述,而對楊慎杜詩考證的探究,尚顯不足。本文試拈取楊慎杜詩考證三則,然后對其進行辨析,并提出一些補充性的意見,甚至不盡一致的理解與看法,以此略窺楊慎杜詩考證方面的成就與不足。
一、“玉佩仍當歌”
用杜詩與其它作品進行對比、互證,是楊慎杜詩考據學中一個突出的內容。曹操《短歌行》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其中的“當”字該如何注解,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圍繞“對酒當歌”中的“當”字,明清時期的爭論是比較大的。楊慎援引杜詩加以對比性的說明。他說:“孟德詩云: ‘對酒當歌’,而杜子美云:‘玉佩仍當歌’,非杜子美一闡明之,讀者皆以‘當歌’為該當之當矣。”曹操“對酒當歌”與杜甫“玉佩仍當歌”中兩個“當”字的意思是否一致,歷來頗有爭議。宋代趙次公“玉佩仍當歌”下注曰:“魏武帝《短歌行》:‘對酒當歌。’”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卷一“玉佩仍當歌”下引曹操:“對酒當歌,人生幾何。”黃希、黃鶴《補注杜詩》卷一“玉佩仍當歌”下引尹洙語曰:“魏武帝《短歌行》: ‘對酒當歌。’”顯然,上引宋代幾家的注解,皆認為杜甫的“玉佩仍當歌”之“當歌”出自曹操的“對酒當歌”。楊慎則指出這兩個“當”字的意思并不相同,他認為“對酒當歌”中的“當”字是“合當”、“該當”之意;“玉佩仍當歌”中的“當”字是“對當”之意。
“玉佩仍當歌”出自杜甫《陪李北海宴歷下亭》一詩,趙次公注曰:“言既有云山之清興,又有玉佩之人歌以侑酒,取《詩》‘瓊琚’、‘玉佩’者也。”楊倫《杜詩鏡詮》云:“玉佩指侑酒者。”“玉佩仍當歌”之“當歌”是指侑酒者對筵而歌之意。仇兆鰲《杜詩詳注》贊同楊慎的觀點,他說:“‘玉佩仍當歌’,當歌,當筵而歌也。楊慎曰: ‘此是對當之當,非合當之當。與魏武樂府‘對酒當歌’不同。’”仇氏亦認為“對酒當歌”中的“當”字是“合當”之意,“玉佩仍當歌”中的“當”字是對當之意。
有贊成的,當然亦有批評的。如明人王世貞《藝苑卮言》針對楊慎的觀點說:
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二語妙絕。老杜:“玉珮仍當歌。”“當”字出此,然不甚合作,可與知者道也。用修引孟德“對酒當歌”云:“子美一闡明之,不然,讀者以為該當之當矣。”大聵聵可笑。孟德正謂遇酒即當歌也,下云“人生幾何”可見矣。若以“對酒當歌”作去聲,有何趣味?
王世貞認為“玉珮仍當歌”中的“當”字出自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作去聲,乃當作之意。王世貞的解釋亦有一定的道理,《禮記·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劉勰《文心雕龍·聲律》云:“古之佩玉,左宮右徵,以節其步,聲不失序。”依照王世貞的理解,“玉佩仍當歌”是指把玉佩所發之聲當作歌聲。王世貞又從字音與字義兩個方面對“對酒當歌”中的“當”字作了闡明,他認為“當”字不應讀作去聲,應讀作平聲。此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王世貞著意強調“對酒當歌”中的“當”字理所當然作“該當”、“合當”之意來解,即他所說的“孟德正謂遇酒即當歌也”。為何這么說呢?因為如果這里的“當”字作“對著”、“面對”解的話,意即面對酒筵、面對歌舞,就無法與下文“人生幾何”的語意構成一句完整的表述(“幾何”一般作“無多時”解),造成上下二句的內在意脈不連貫。曹操的意思是說因為人生短暫,所以遇酒即當歌,這二句之間構成一種因果關系。考察曹操詩文中所用“當”字,大多是“合當”、“該當”之意。試拈幾例,如《氣出唱》其一:“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當專之。”《步出夏門行》:“臨觀異同,心意懷游豫,不知當復何從。”《上書謝策命魏公》:“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與韓遂教》:“當早來,共匡輔國朝。”《封功臣令》:“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春祠令》:“議者以為祠廟上殿當解履。”《與荀彧書追傷郭嘉》:“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荊。”《報劉廙》:“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因此,“對酒當歌”中的“當”字應讀作平聲,是“該當”、“合當”之意。
王世貞認為楊慎徒費筆墨口舌,“大聵聵可笑”,其實,這里王氏誤解了楊慎之意,楊慎引用杜甫“玉佩仍當歌”是為了反駁宋人的觀點,宋人認為“玉佩仍當歌”之“當”出自于“對酒當歌”,而楊慎認為這兩處“當”字的含義不同,而且楊慎也主張“對酒當歌”之“當”是該當之意。因此,清人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二十四又進一步糾正王世貞的說法,他說:“焦弱侯謂元美此言誤會用修之意矣。用修正讀當為平聲,如當時之當,言人生對酒,與當歌之時無幾耳,何嘗作去聲。如當泣、當歸之當哉,子美詩當亦作平聲,若如元美讀,不成詩矣。”吳氏引用焦竑之觀點,指出王氏誤會楊慎之意,楊慎“正讀當為平聲”,而且如果將“玉佩仍當歌”之“當”讀作去聲,“讀不成詩矣”。
綜上所述,在古代,楊慎比較早地指出了這兩個“當”字的區別,“對酒當歌”之“當”為“該當”、“合當”之意,“玉佩仍當歌”之“當”為“對著”、“面對”之意,其中王世貞將“玉佩仍當歌”之“當”解釋為當作之意,亦可備一說,而且這兩個當字皆應讀作平聲。
二、“苔臥綠沉鎗”
楊慎的杜詩考證,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即他往往能綜合各家之注而為說。楊慎《升庵詩話》卷十二《綠沉》云:
杜少陵《游何將軍山林》詩:“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鎗。”竹坡周少隱《詩話》云:“甲拋于雨,為金所鎖。鎗臥于苔,為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此瞽者之言也。薛氏《補遺》云:“綠沉,精鐵也。”引《隋書》文帝賜張淵綠沉之甲。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沉為竹,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雖少有據,然亦非也。予考“綠沉”乃畫工設色之名。《鄴中記》云:“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紫紺色,或郁金色。”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沉漆竹管見遺。”《南史》梁武帝西園食綠沉瓜,是綠沉即西瓜皮色也。梁簡文詩:“吳戈夏服箭,驥馬綠沉弓。”虞世南詩:“綠沉明月弦。”劉邵《趙都賦》:“弩有黃間綠沉。”若如薛與趙之說,鐵與竹豈可為弓弦耶?楊巨源詩:“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沉槍。”與杜少陵之句同,皆謂以綠沉色為漆飾鎗柄。
杜甫《重過何氏五首》其四:“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鎗。”其中的“綠沉”究竟是何意?在宋代,就引起了激烈的辯說。據宋代《九家集注杜詩》、《補注杜詩》等書的注釋,可以歸納出“綠沉”主要有以下幾種含義:第一,精鐵;第二,漆;第三,用綠為飾;第四,古弓名;第五,竹。對于這五種觀點,楊慎比較認同第三種,他認為“綠沉”是一種顏色名稱,即他所謂的“畫工設色之名”。楊慎此說本宋人姚寬《西溪叢語》,其書卷上云:“恐綠沉如今以漆調雌黃之類,若調綠漆之,其色深沉,故謂之綠沉,非精鐵也。”姚氏從字面來解讀“綠沉”之義,有一定道理。
宋代王楙《野客叢書》卷五有“竹坡言綠沉鎗”一條,他認為“綠沉”不可專指一物,他列舉了綠沉瓜、綠沉筆、綠沉弓、綠沉屏風、綠沉扇,又說:“然則綠沉又不可專謂精鐵,蓋有物色之深者,為綠沉也。”宋代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四亦認為“綠沈”并非竹、鐵或弓等具體的器物,而是“用綠沈飾之耳”,他又指出“六典,鼔吹工人之服,亦有綠沉”,“此以綠沈飾器服也”明代胡應麟對王楙的考證極為贊賞,乃至不無感嘆地說:“續讀王楙叢書論綠沉,乃知古人已先得矣。”不過,胡氏又對王氏之說作了補充與說明,他說:“王說自當,但云物色深者為綠沉稍未安,不若言綠色深者為綠沉也。”“綠色深者為綠沉”,胡氏的解釋更為精確。其實,除了王氏所列之外,還有綠沉槍、綠沉甲、綠沉漆、綠沉漆榼、綠沉書案等。比如“綠沉漆”,明代黃成《髹飾錄·坤集·質色第三》云:“綠髹,一名綠沉漆,即綠漆也。其色有淺深,綠欲沉。”顯然,“綠沉”是指一種顏色。明代鄧伯羔《藝彀》卷下云:“綠沈,言其色沈而不浮。”明代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二十八解釋“綠沉”曰:“蓋色綠而深沉云耳。”清代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三十四“綠沈”條基本贊同楊慎的觀點,他說:“楊升庵以綠沈色為漆,飾鎗柄。……余觀《武庫賦》云:‘綠沈之鎗。’殷文圭《贈戰將》詩:‘綠沈鎗利雪峰尖,犀甲軍裝稱紫髯。’則鎗自屬鐵,其色乃綠沈耳。”
那么,“綠沉”究竟是一種什么顏色,明代方以智的解釋尤為明確,其《通雅》卷三十七認為“綠沉”“其為色明矣”,“綠沈,言其色沈,正今之苦綠色,其以黃加玄者,曰油綠黑綠。”“綠沉”就是油綠色或黑綠色。通過比較以上諸家之說,可以發現,楊慎的解釋頗為合理,“綠沉”是指濃綠色,或者理解為凡器物之濃綠或被漆、染為濃綠色者,即可冠以“綠沉”。這種解釋在古代詩文中亦可得到證明,如金鉷《銅鼓記》:“而宏壯之模、縝密之文、綠沉之色,要非秦漢以下物也。”黃宗羲《海市賦》:“其后幻為染肆,綠沉紅淺,羅綺繽紛。”《陜西通志》卷六十四《隱逸·雷祥傳》:“土人間掘得祥遺器,形制古質,色綠沉隱秀。”以上所引詩文中的“綠沉”,皆指一種顏色。
杜詩所用“綠沉槍”,對后世的詩文創作也產生了很大影響,以至于逐漸形成了一個含有特定內涵的典故,在古代詩詞中頻頻出現。如釋貫休《送鄭使君》:“綠沈槍卓妖星落,白玉壺澄苦霧開。”林逋《新竹》:“粉環勻束綠沉槍,裊露差煙山雙山雙長。”黃庭堅《水龍吟》:“青驄寶勒,綠沈金鎖,曾瞻天仗。”洪適《次韻梁門》:“時平且得無爭戰,苔上戈槍臥綠沈。”陸游《雪夜感舊》:“綠沉金鎖俱塵委,雪灑寒燈淚數行。”張以寧《伏波廟》:“丹荔黃蕉長盛祭,綠沉金鎖尚英風。”皇甫汸《送阮將軍北上》:“屏居一自藍田后,綠沈久臥蒼苔前。”王世貞《文皇御槍歌》:“隆凖重瞳美髯秀,如云黑幟綠沈槍。”謝肇淛《溫泉》:“滑增紅膩玉,色沁綠沉槍。”王士禎《南浦·寄興》:“苔臥綠沉槍澀,秋水冷并刀。”等等。
三、“大家東征逐子回”
在楊慎的杜詩考據中,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即他對杜詩的改字。《升庵詩話》卷七《逐子》云:
杜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劉須溪云:“‘逐’字不佳。”予思之,杜詩無一字無來處,所以佳,此“逐”字無來處,所以不佳也。今稱人之母隨子就養曰逐子,可乎?然亦未有他好字易之。近有語予以“將”字易之,《詩》云“不遑將母”,蓋反言見義,若《春秋》杞伯姬以其子來朝,而書杞伯姬來朝其子之例也。為文富于萬篇,貧于一字,其難如此。古樂府有“一母將九雛”之句,則“將”字其愜,當試與知音訂之。
又《升庵集》卷五十二《古詩文宜改定字》云:
顏延年《赭白馬賦》:“戒出豕之敗駕,惕飛鳥之跱衡。”“出”字不如“突”字。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逐子回。”“逐”字不如“將”字。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始”字不如“才”字。詩文有作者未工而后人改定者勝,如此類多有之。使作者復生,亦必心服也。
“大家東征逐子回”出自杜甫《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一詩,此詩主要寫王判官奉母歸黔中,其中“大家東征”一句用曹大家隨子東征之事。楊慎認為“逐”字無來處,所以不佳,他依照《詩經》“不遑將母”以及古樂府“一母將九雛”等詩句,主張“逐”字應改為“將”字,并指出“詩文有作者未工而后人改定者勝”。楊慎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就“逐”字是否應該改為“將”字,明清時期頗有爭議。一般來說,明清士人反對楊慎的改字。張萱《疑耀》卷三《楊用修妄改杜詩》云:
楊用修謂顏延年《赭白馬賦》“駴出豕之敗駕”,后人改出為突乃佳;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后人改逐為將乃佳;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后人改始為才乃佳,此癡笨人前說風流也。突字拙,出字巧;才字俚,始字文,惟作者自知之耳。獨以逐為將,雖《詩》有“不遑將母”及古樂府“一母將九雛”,杜豈不知者?其用逐字原有深意,婦人三從,其一從子,逐即從義也。意不在將而在從,語不以從而以逐,此正詩家三昧,以將字易之,不亦淺乎。
張氏認為杜甫用“逐”字自有深意,“婦人三從,其一從子”,“逐”乃“從”義也。明末清初人盧元昌《杜詩闡》卷十五注曰:“昔漢曹大家隨子至官,作《東征賦》,判官之母即大家也,其東征者,以隨子回家。”“逐子”即“隨子”之義。仇兆鰲《杜詩詳注》卷十二引朱注曰:“曹大家《東征賦》:‘維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逐子,即隨子義也。”又引顧注曰:“婦人三從,其一從子。逐即從義。楊用修因古樂府有一母將九雛,欲改逐為將。將子,領子也。”若改為“將子”的話,似乎與原詩詩意不合,張萱亦指出杜甫“意不在將而在從,語不以從而以逐”。史炳《杜詩瑣證》卷上“東征逐子”曰:
《送王判官扶侍還黔中》云:“大家東征逐子回”,《丹鉛錄》取或說改為將子,朱注非之,引《東征賦》“余隨子乎東征”,謂逐子即隨子之義是也。澤州陳氏則云:“依賦直當作隨子”,案隨子固現成,然用逐字,句法為健。而朱翰至謂逐字無出,不知此亦何須出典。唐詩以隨為逐者甚多,而用之于人則如蘇味道:《正月十五夜》“明月逐人來。”李太白《贈崔秋浦》:“地逐名賢好”之類,又有何語病。而周賀《送張諲之睦州》云:“東征逐子去,俱隱薜蘿間。”則正用杜語,蓋唐人使熟不怪,必欲易之,千載更無人知。
史氏的考證更有說服力,他認為用“逐”字,不僅“句法為健”,而且“唐詩以隨為逐者甚多”。《玉篇·辵部》:“逐,從也。”考察古代詩文中所用“逐”字,有“從”之意,如《楚辭·九歌·河伯》:“靈何為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王逸注:“逐,從也。”《史記·匈奴列傳》:“而單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南朝梁吳均《同柳吳興何山集送劉馀杭》:“君隨綠波遠,我逐清風歸。”此外,我們在杜甫的詩集中,亦可找到“逐”字作跟隨之義來講的,如《絕句漫興九首》其五:“顛狂柳絮隨風去,輕薄桃花逐水流。”“逐水”對“隨風”,“逐”乃跟隨之義。又如《青絲》:“靑絲白馬誰家子,麤豪且逐風塵起。”“風塵”比喻亂離,宋代鮑彪注曰:“豈懷恩之反有從亂者。”可見,“逐”乃從之義。再如《諸將五首》其五:“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麂》:“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廚。”等等。因此,楊慎所說的杜甫所用“逐”字無來處,是不恰當的。
杜甫的“東征逐子”對后世詩文創作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如楊萬里《答蕭國博》:“而三子出仕,中男次公去秋之官雁峰,長男長孺今茲六月又之官南浦,小男幼輿九月又之官澧浦,其勢不容不東征逐子如曹大家也。”周賀《送張諲之睦州》:“東征逐子去,俱隱薜蘿間。”朱多炡《送梁傳之從襄陽將母南還》:“夫人城外漢江平,逐子南回五兩輕。”胡應麟《送盛山人泰父奉母南歸》:“將親南下非潘岳,逐子東還是大姑。”王世貞《張太史明成送母還豫章》:“侍臣中禁少,逐子大家歸。”羅洪先《壽桃林一愚伯八十》:“情忘逐子東征日,道合嬰兒太上篇。”何景明《懷姊》:“逐子東歸日,輶軒惜路岐。”羅玘《黎太監永思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子如從龍母當來。”錢謙益《曹能始為先夫人立傳寄謝》:“逐子東征杳莫從,機殘績泠泣尸饔。”等等。
以上所選、所論是楊慎杜詩考據中具有代表性的三則,從中可發現,在杜詩的考據方面,楊慎雖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也存在著一定的不足。
注釋:
①蕭統選,郭正域批點,凌濛初輯評《選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751頁。楊慎此則評語亦見于《丹鉛總錄》卷十二“太白楊叛兒曲”。
②⑤杜甫著,趙次公注,林繼中輯校《杜詩趙次公先后解輯校》(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頁。

④黃希原注,黃鶴補注《補注杜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頁。
⑥楊倫《杜詩鏡詮》,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2頁。

⑧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三,見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989頁。
⑨孫系旦《禮記集解》,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820頁。
⑩王運熙、周鋒《文心雕龍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頁。
?曹操《曹操集》,中華書局,1974年。


?姚寬《西溪叢語》,見王云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第4頁。
?王楙《野客叢書》,見王云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第45頁。
?吳曾《能改齋漫錄》,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73頁。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68頁。
?王世襄《髹飾錄解說:中國傳統漆工藝研究》,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72頁。
?鄧伯羔《藝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頁。
?徐應秋《玉芝堂談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78頁。
?方以智《通雅》,中國書店,1990年版,第455頁。
?金鉷等監修《廣西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79頁。
?黃宗羲《黃梨洲文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05頁。
?劉於義等監修,沈青崖等編纂《陜西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913頁。
?楊慎《升庵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頁。
?張萱《疑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頁。
?盧元昌《杜詩闡》,臺北大通書局,1974年版,第742頁。
?史炳《杜詩瑣證》,上海書店,1988年版,第101頁。
?顧野王撰,孫強增補,陳彭年等重修《重修玉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