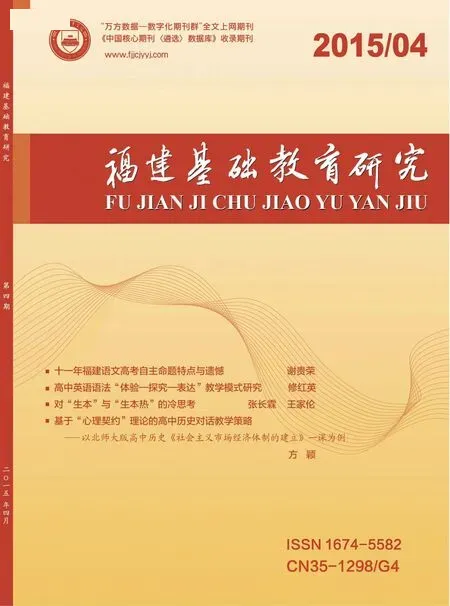儒風道骨賦赤壁*關于《赤壁賦》中“水”與“月”啟示的解讀
◎福建省福州三中金山校區 葛莉茜
儒風道骨賦赤壁*關于《赤壁賦》中“水”與“月”啟示的解讀
◎福建省福州三中金山校區 葛莉茜
《赤壁賦》中,主客因“水”與“月”的永恒聯想到人生命之永恒因而釋懷于功業難就、人生短暫,這種思維是因蘇軾內心道家的宇宙觀而起。但筆者認為《赤壁賦》只是蘇軾短暫的自我解脫,在《赤壁賦》前后皆有作品表明蘇軾并不因官場受挫而放棄儒家的進取之志。筆者試從《赤壁賦》中“水”與“月”對主客的啟示談談自己的理解,并對蘇軾的人生哲學做一點探討。
《赤壁賦》;水;月;儒;道
蘇軾的《赤壁賦》中,對客的“悲嘆”的勸慰來自“水”與“月”給予的啟發,“水”與“月”的永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怎么從“水”與“月”的永恒聯想到人的生命的永恒呢?筆者想談談自己的理解。
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
前面各句不難理解,但怎么理解“物與我皆無盡”呢?也像看待“水”與“月”的方式看待人的生命。以“一瞬”來考察人的生命,那么生命每一瞬間都在變化,但是,如果給予足夠大的空間,足夠長的時間,也就是立足于永生永世的角度來考量人的生命,那么人的生命將生生世世與天地萬物共存。所以,“我”和物一樣也是無盡的。
為什么可以這樣解釋呢?
在蘇軾所生活的宋代,人們熱衷于參禪悟道,那是他們讓自己從現實社會的苦痛中解脫出來的有效途徑。因此,與其說蘇軾沒有寫明悟道的過程,不如說,今人對中國傳統哲學思想過于疏遠。
在蘇轍為蘇軾寫的《東坡先生墓志銘》中有一段這樣的記載:
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
可見,蘇軾對道家學說的悟性是與生俱來的。還是這篇墓志銘,記載了另一個細節:
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末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后事,不答,溘然而逝。
這種面對死亡的從容,其實也是莊子提倡的任由造化的態度。莊子對生死的認識是這樣的: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莊子·外篇·至樂》
人的生死就像四季一樣運行,人既不必為生而歡,也不必為死而哀,生與死都是存在的一種方式。蘇軾的生死觀、宇宙觀顯然傳承于莊子。我們可以理解,蘇軾在他可以進取的時候,采取的是儒家面對世界的態度,努力進取、勇于擔當;在他處境最艱難、只能退守的時候,他投身佛道以求心靈的寧靜。佛道,對于蘇軾而言,與其說是一種信仰,不如說是一種獨特的思維方式,它讓蘇軾既面對現實,又超越了現實。
蘇軾意識到立足于永生永世的角度來看,人和萬物都是生生不息的。人之所以有生命短暫的痛楚,是因為將自身的短暫的“變”與天地萬物的宇宙時間里的“不變”做了并不具備可比性的比照。有了這個境界作為前提,才能正確理解下文“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不屬于自己的“物”,該怎么理解是關鍵。如果只是具象的某物,不是自己的,不取,這不是難事,既然不是難事,那一定不是蘇子所說的“生命不能承受之痛”,聯系蘇軾當下的境遇,這個“物”,恐怕更多地指向未完成之功業。人常常渴盼那些并不屬于或還不屬于自己的“物”,這種渴盼越熱切就越痛苦。所以,就像絲毫不取非吾所有的實在之物一樣,對于念想中的“功業”乃至來自帝王的垂青等等一切“物”,都不要為之渴盼或因盼而不得而不安,這叫“莫取”,就是不要拿更不要想,不要把未得到的、想象中可以得到的當作定要得到的或理所應當要得到的,這叫“雖一毫而莫取”。
只有這樣,人才能將面目轉向已經擁有的一切——“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李白說:“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且“江上之清風”有聲,“山間之明月”有色,江山無盡,天地無私,風月長存,聲色俱美,人面對這樣的自然萬物,不要故作悲聲,而應當順應自然給予的享受,盡情地享用。在這一番內心掙扎中,如果說“自其變者而觀之,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是理論上的解答,那么最后“(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就是行為上的回答。
盡管如此,但蘇軾的內心始終有不能拋開的煩惱。因為,對道佛思想的接受也不是蘇軾人生觀的全部。所以,筆者以為,蘇軾的《赤壁賦》是他對當下了悟的一種加持,是暫時的,它并不代表蘇軾對人生思考的全部。蘇軾在寫完《赤壁賦》之后兩個月,又寫下了《念奴嬌·赤壁懷古》。“豪杰”中最出眾的非周公瑾莫屬,他年少得志,從容之中就能獲得所有人都想得到的功業。蘇軾一想起這些,就難以釋懷,所以“早生華發”,但有了這樣的功業又怎樣,“人生如夢”,終歸虛無,還是與江月共享這美酒吧。
其實,對于“人生如夢”的感受,蘇軾早已有之。三年前,蘇軾被貶謫至黃州的路上在《西江月·平山堂》里回想恩師歐陽修時說道:“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雖然在“烏臺詩案”后,“人生如夢”之感就時時困擾著蘇軾,但建功立業、致君堯舜上,卻一直是蘇軾“才下眉頭,卻上心頭”的揮之不去的念想。我們一起來看一則幾乎所有有關蘇軾的傳記都會記載的故事: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
范滂,后漢時期人,少年時便懷澄清天下之志。疾惡如仇,為官清厲,貪官污吏望風解印綬而逃。任汝南郡功曹時,抑制豪強,制裁不軌,結交士人,反對宦官。第一次黨錮之禍起,與李膺同時被捕,被釋還鄉時,迎接他的士大夫的車有數千輛。黨錮之禍再起,朝廷下令捉拿他,縣令郭揖欲棄官與他一起逃亡,他不肯連累別人,自己投案,死于獄中,時年三十三。范滂就義之前與母親訣別:
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其弟)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其父,曾為龍舒侯相,此時已逝)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李膺、杜密,都是敢于同宦官進行堅決斗爭而被殺害的東漢官員,時人合稱“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后漢書·黨錮傳》
蘇軾從小立志以范滂為榜樣,得到母親的贊賞。所以,儒家用世的思想對蘇東坡而言雖不像道家思想那樣像是與生俱來的,卻也根深蒂固,成為他無論遭受怎樣的境遇也無法拋卻的念想。他只有在仕途受阻、理想遇挫的時候,才想借助佛道得以暫時解脫。他日,再有“清風徐來,水波不興”之月圓夜,他定要再一次“望美人兮天一方”了,這恐怕也是我們愿意見到的蘇軾。在寫完《赤壁賦》后兩個月(元豐五年九月),蘇軾寫下了膾炙人口的《臨江仙》: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彀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
宋人筆記中傳說,蘇軾作了這首詞后,“掛冠服江邊,拏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聞之驚且懼,以為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正睡大覺呢,根本沒有去“江海寄余生”。
由此可見,《赤壁賦》里所得到的了悟只是蘇軾對失意的現在暫時的了悟,寄身江海只是說說而已,不過是借助宗教的思維給予自己暫時的安慰和解脫。所以,筆者更愿意相信《赤壁賦》是蘇軾對自己當下的了悟的一種加持,他把當下的這一念、這一悟寫下來,好讓自己能更堅定于此時的了悟,試圖借此把白日里清晰的、不得不面對的煩惱拋得遠遠的。但不管怎樣,這種身處逆境卻不怨天尤人,不消極頹喪,樂觀曠達、隨緣任化的心態確是讓人激賞,它影響了中國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并成為了一種民族心理。
蘇軾的偉大就在于雖然他天生擁有對天、地、人以及生死這樣大命題的領悟,使他在“退”的時候還能豁達從容地活,但他卻一點也不因為受道家的影響而棄世絕塵,而是將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圓融在自己的內心,既不拋卻儒家的進取之志而寄身江海,也不拋棄道家給予的天地智慧而染垢世塵,進退得宜,懷中和之氣,又不失天地氣概。
(責任編輯:石修銀)
*本文系2013年度福建省教育科學“十二五”課題“高中語文古代詩歌教學有效性方法研究”(項目編號:FJJKXB1-097)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