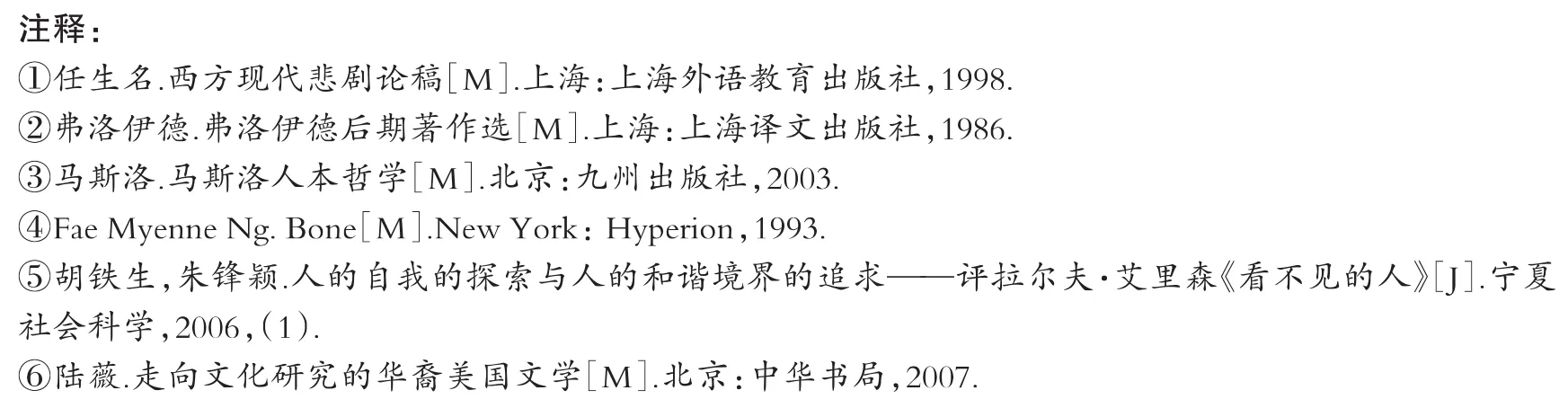從身份的迷失到和諧人格的建構——評美國華裔作家伍慧明的《骨》
朱峰穎 吳憲忠
《骨》是美國華裔小說家伍慧明(Fae Myenne Ng)的處女作。這部小說具有典型中國文化隱喻的作品,所代表的是華裔美國文學對西方主流文化的話語霸權進行的不露聲色的隱性滲透,先將其結構,繼而重構美國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在美國社會中建立了自己獨特的價值與文化身份。從心理哲學和后殖民理論的角度出發,評價這部獨具特色的華裔美國文學作品,解讀華裔美國人從身份的迷失到和諧人格的建構過程,對于促進中美文化交流及文化全球化的健康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一、華裔美國人身份的迷失
美國在建國時發表的《獨立宣言》確立了“人生來平等并應有平等的權利”,但是在其歷史發展進程中,這個理想一直受到諸如政治、經濟、文化及民族發展等因素的影響,沒有真正得以實現。而在二十世紀40年代后,美國的統治階級對中國移民及其后代進行的是與殖民主義相似的種族主義和東方主義的壓迫,是在多元文化的華麗外衣之下對華裔進行的更為隱蔽的文化意義上的殖民主義。華裔美國人身處中美兩種文化之間,經歷了激烈的文化碰撞,遭遇了來自于主流社會的種族歧視與刻板化東方主義的迫害,在探求文化身份的艱難歷程中,他們徘徊于美國主流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之間而難得其所,成為美國主流社會的他者。因此解構與重構華裔美國人的文化身份已成為華美文學的首要任務。
美國華裔作家伍慧明的小說《骨》揭示出了華裔美國人的生存困境。人的生存困境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及時代的變遷而不斷變化的。這種困境更是一出社會悲劇,體現出人處于生存困境中的物質與精神,客觀與主觀,可見與不可見的矛盾沖突,形成了一種張力。這種張力是由兩極構成的。即人的本體存在和威脅人的存在和人本體意義上的發展與延續的各種因素。這兩極的沖突與相互制衡的集合就形成了人的生存困境的張力。這里所說的種種因素包括自然的,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倫理道德的,宗教的,精神心理的,人本體的等等。這種張力始終處于動態之中,因為人與他周圍的世界二者在相互作用中都是發展演變的。”
伍慧明塑造的人物父親利昂,是華裔美國小說中常常出現的典型:一個錯置在美國的被邊緣化的父親形象,也是具有文化隱喻的一個典型。通過對他的經歷的描述,小說隱性地回顧了中美歷史對移民的作用,反映了華人在美國扎根的艱難歷程。利昂的非法身份正是美國對華移民政策的產物,他的悲劇是歷史的悲劇。他花錢買得“紙契兒子”身份進入美國,從而取得了美國公民身份,他似乎應該獲得明確身份了,然而假身份具有隱喻層面上的否定,建立在謊言基礎上的身份使利昂在美國社會中喪失了自我,處在沒有自我的不穩定的不安全境地。他要忘記屬于自己真實的一切,卻要記住代表自己美國身份的假信息。
弗洛伊德認為,人是一個由“本我”、“自我”和“超我”組成的統一體。只有當三者處于和諧狀態時,人才能有效地應對外界的自然及人文環境。相反,當三者發生沖突時,人就處于一種自我的失調狀態。“本我”只接受“快樂原則”的統治,能依靠想象、幻想、幻覺和夢來滿足自己的愿望。“自我”則按照“現實原則”行事,以理性的方式來實現“本我”的目的。“超我”由“自我理想”和“良心”組成,是人性中的道德警察。利昂付出巨大的金錢代價買了一個假身份到美國,就是受了“快樂原則”的左右,用“美國夢”的幻想來滿足自己的愿望。到美國后經歷了種種挫折,美國夢一點點破滅,直到拿出畢生積蓄與人合伙開的洗衣店在營業不久后就破產,利昂的希望之火被殘酷的現實徹底澆滅。當萊拉打開裝有利昂文件的小提箱時,她發現了許多利昂找工作和租房被拒絕的通知,它們正是利昂所遭受的種族歧視的證據。以利昂為代表的老一代中國移民,不論他們居住在美國的時間有多久,取得的社會成就有多大,他們也永遠擺脫不了主流社會的偏見,其邊緣地位也難以得到改變。他們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之中,深受“身份”問題的困擾。利昂只有在遠洋輪上工作時才暫時逃離了沒有身份的恐懼,卻又要承受繁重得只有沒有身份的“奴隸”才會做的工作。利昂成不了真正意義上的美國人,卻又在移民后失去了自己原有的中國人身份。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認為,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強烈、最明顯的就是對生存的需求。利昂的“自我”遵循了“現實原則”的支配:解決溫飽的生存問題。利昂的“美國夢”在生存問題面前顯得那樣遙不可及。為了生存,利昂只能從事繁重的體力體力勞動。利昂“超我”中的道德監督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他只能通過試圖保留中國人的文化傳統來保留他的中國人的身份。移民在最初與異域文化接觸時,往往有一個“蜜月期”,這時他們努力融入美國文化,不惜拋棄已經在自己身上根深蒂固,已經融入自己血液之中,烙印在自己的“骨子”之中的中國傳統文化。但是,當過了這段“蜜月期”,移民還是要回到自己的文化傳統之中去尋找依靠。在他獨居的三番公寓,利昂固守著自己的宗教信仰,供奉著孔子的畫像。在異國他鄉歡度春節時他還要請八仙、觀音、戰神、書神等各路神仙。安娜死后,她的骨灰被放在孔子的祭壇上祭奠,利昂還想為她辦一個中國式的守靈。就這樣,移民美國的利昂“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相互沖突,使他處于失調狀態,在美國的主流文化中喪失了身份。
如果說第一代移民利昂的生存困境的張力是物質的,可見的,那么已經獲得合法美國公民身份的第二代華人,三個女兒所面對的則更多的來自于精神,是無形的身份迷失。她們的經歷反映了華夏文化與美國主流文化之間的沖突與碰撞,和華人力求加入美國社會而不得其所的困境。第二代華裔已經擁有了合法的美國公民身份,從小就接受了美國教育,但是這些并不能保證她們在美國可以快樂地生活。大女兒萊拉對自己在中國文化背景的地位是懷疑的:“我們是一個三個女兒的家庭,這用中國的標準可不是什么幸運的事情”。安娜死后,萊拉在母親與男友梅森之間被拉來拉去,無法在兩者之間求得平衡。在困頓之中,為求減輕精神的壓力,獲得暫時的逃離,萊拉跟華人男友一起吸食大麻和海洛因,做愛,開快車。“快樂原則”統治著“本我”,讓他們在幻覺中生活,卻在清醒后更加迷失,更加痛苦。二女兒安娜選擇了自殺,正是由于自我功能減弱、人格的三部分失去平衡彼此相互沖突,才導致她心理疾患的發生,而最終她采取了極端的方式徹底地放棄了自我,成為文化沖突的犧牲品。三女兒尼娜去紐約作了空中小姐,試圖以“飛翔”來擺脫過去的陰影,與代表中國文化的唐人街徹底脫離,放棄作為中國人的文化身份,用美國文化來支配她的“超我”。然而作了空中小姐的尼娜并沒有獲得自己渴望的自由,反而有了“生命不可承受之輕”。因為她丟失了自身的中國文化傳統,把自己的身份建立在美國主流文化的價值觀之上,但是這種放棄與妥協,并沒有給她帶來自由。作為華裔后代,她只能是喪失自我的身份。
雖然老一代移民和其移民后代處于不同的生存困境中,卻都有身份迷失的困惑。他們試圖改變這種困境,改換方式,不斷努力,卻不斷失敗,從一個困境陷入另一個困境,似乎永遠到達不了幸福的理想國,只能不斷體驗人本體論上的二律背反。因為移民的本質意義就是一種放棄,放棄的同時才能真正開始尋找,才會有新的身份認同。健全的“本我”就是要能尋求到某種方式,把這種內心沖突和生存困境降低到最低限度。
二、華裔美國人和諧人格的建構
出生在美國的新一代移民,首先面對的是文化移植的困惑,由此而展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正面反思和突破。他們在美國主流文化的分裂對峙中經歷了身份迷失的痛苦,他們開始尋找個體人的生存空間,在邊緣狀態的獨立清醒中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尋找新的生命理想,從而實現人格的和諧。他們的經歷反映了全球化語境下美國華裔逐漸加入美國主流社會,提倡多元文化并存與融合的不懈努力。對于建構華裔美國人的身份問題,伍慧明沒有像其他的族裔作家那樣在中/美文化二元對立中選擇一元,如非裔作家艾里森在《看不見的人》中所做出的選擇。艾里森通過“看不見的人”探索自我的過程,確立了黑人只有遵從自己的傳統文化,發揚積極健康的價值觀,才能在白人的主流社會中找到自我,發揮自己應有的價值,從而進入人的自我和諧、人和他人及社會的和諧境界。伍慧明通過萊拉的覺醒與選擇表達了自己超越二元對立的的選擇:即一種含混矛盾的,水乳交融的霍米·巴巴所稱的“第三度空間”。當她的兩個妹妹各自采取不同方式逃避文化沖突的矛盾時,萊拉選擇了接受二元對立的同時存在。當混雜的傳統對她提出互相抵觸的要求時,她用調停者或翻譯者身份去除兩者互不相容的成分,尋找二者的和諧存在,從而形成了自己的和諧人格。
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諧人格”是指人格內部結構及人格與所處環境的和諧。我們看到覺醒后的萊拉無論其個體內部,或是個體與他人、社會還是與歷史、文化互動中都形成了和諧。首先,在其人格內部,萊拉用理性接受了安娜的死亡是安娜自己的選擇,她無法改變,于是她不再內疚,終于沖破了感性的桎梏求得了心理平衡,個體調控機制獲得了完善。其次,萊拉與他人及社會的相處的方式和她的態度也有轉變,她努力兼收并蓄外界的不同方面而獲得力量,學會同世界各種矛盾和諧相處。由于萊拉可以使用中英兩種語言,作為社區教育咨詢員,她協調學校與學生家長之間的關系和溝通,為他們打開交流的渠道;在家里,她使不懂英文的父母獲得與美國社會的交流,她協調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使大家保持接觸。擁有兩種語言及兩種不同文化背景的萊拉在翻譯時,采取了讓大家都“生活得更容易”的翻譯方法,通過增補、刪除,轉換等方法讓思想變得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對于漢語中的成語之類的隱喻和英語中帶有很濃的文化色彩的隱喻等更是巧妙地轉化,從而實現了跨文化交流的成功。不論何種語言,其所承載的文化的翻譯都是雙方共同協商的結果。陸薇認為每種語言、文化都有其他語言、文化無法進入或破譯的領地,改變話語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就成了解決問題的最好途徑。因此,從萊拉身上我們看到她已從華人的失敗與挫折中吸取了經驗教訓,將法制與情理結合,成為更加成熟的一代。她不斷地從華夏文化中汲取精華,又深深植根于美國文化。她是東方價值觀與西方價值觀的完美結合體,在多元的美國社會中,萊拉確立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實現了人格的和諧。
最后,作為少數族裔群體中的成員,萊拉在中美兩種文化的互動中,懂得了尊重和接納,在第三度空間里建構了和諧人格。為了人類社會的未來,處于邊緣地位的民族更需要保持自身的傳統文化,在保證生存的基礎之上,建立自己的平和心態,與主流社會及文化和諧共處。正是自身的傳統文化讓處于弱勢地位的民族與個人找到了平衡及力量。當萊拉最后決定離開父母,離開唐人街,與丈夫梅森開始新生活時,她的心是平靜的。因為她清楚自己是華裔美國移民的女兒,是紙生仔的后代,但她更是一個美國人。此刻她明確把握了自己的社會文化屬性,自信地踏入了美國社會。萊拉在向前的同時也記住了過去,但這并不削弱她前進的能力。伍慧明通過對萊拉這一形象的塑造,確立了自己心中跨文化生存的理想形象,標志著新一代華人在美國社會中獨立健康的發展,真正融入美國的多元文化中。
三、結語
在全球化過程中,世界各種文化共同發展和各族人民的和諧相處是人類獲得進步,實現共贏的最好途徑。然而在此進程中,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霸權通過思想意識、教育等隱蔽方式對弱勢文化進行侵襲,形成新殖民主義。伍慧明通過其塑造的新一代華裔形象,證明了只有用尊重和接納的多元文化融合的態度,才能在沖突和差異的世界中,在迷失身份后建構和諧人格。這部文學作品不僅在美國本土的中美文化交流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而且超越了時代和民族的界限,對文化全球化的發展和建構多元文化的真正和諧具有積極意義,對于我們實行“中國夢”有著很大的借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