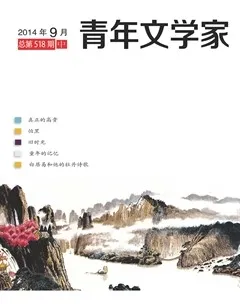《慈悲》中弗洛倫斯的自我找尋之路
李丹
摘 要:托尼· 莫里森在《慈悲》中一如既往地表達(dá)了對女性的關(guān)懷,在父權(quán)文化的背景下,女性或做男人的附庸,或在尋愛的過程中開始女性書寫,進(jìn)行女性主體的建構(gòu)。本文主要介紹了故事女主人公弗洛倫斯自我尋找的艱難之路。
關(guān)鍵詞:《慈悲》;弗洛倫斯;黑人女性;自我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4)-26-0-02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年2月18日-),是美國當(dāng)代最偉大的非裔女作家之一,其選集于1993年獲諾貝爾文學(xué)獎。《慈悲》是她于2008年出版的最新力作,小說聚焦在17世紀(jì)的北美大陸,特別關(guān)注了故事中女性的生存狀態(tài)及命運。這部小說以故事女主人公弗洛倫斯的自我找尋為線索描繪了蓄奴制初期不同族裔人的生存狀況探討了黑人女性尋找自我的主題。從而表現(xiàn)出女性在困境中重新發(fā)現(xiàn)自我,重塑自我形象的艱難性和必要性,也看到了建構(gòu)身心解放獨立自主的黑人女性的理想自我的可能。
一、弗洛倫斯的心靈創(chuàng)傷
文中弗洛倫斯被帶到農(nóng)場的時候只有七八歲,當(dāng)時,農(nóng)場主雅各布拒絕生意伙伴奧爾特加提出的以奴隸抵債,但見他無意還清欠款,于是雅各布提出帶走黑女奴抵債。令雅各布沒有想到的是,這位背著一個男嬰,領(lǐng)著一個女孩的黑奴跪地懇求他帶走她的女兒。“求你了,先生。別要我。要她吧。要我女兒吧。”對于當(dāng)時只有七八歲的弗洛倫斯來說,這無疑是對她幼小心靈的強烈打擊。她肯定會認(rèn)為母親在這種情況下選擇了弟弟而拋棄了她,母親是不愛她的。雖然弗洛倫斯很想待在母親身邊,而在這種情況下無力挽回的她只能等待命運安排,最終農(nóng)場主雅各布將她帶走。不明白母親真正用意的她始終認(rèn)為她是被拋棄的,導(dǎo)致后來弗洛倫斯心靈一度缺少關(guān)愛,由此給弗洛倫斯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創(chuàng)傷。“被拋棄”的心里創(chuàng)傷使弗洛倫斯變得更加依賴別人,更加需要別人的呵護(hù)與關(guān)愛。的確,這一情感上的拋棄成為了弗洛倫斯心中永遠(yuǎn)的傷痛。
二、弗洛倫斯自我意識的覺醒
雖然弗洛倫斯遭遇了母親的拋棄,但對于她來說仍然算是幸運的。在農(nóng)場她還有莉娜給予的愛,就如同是母愛一樣的溫暖。莉娜對她細(xì)心關(guān)愛與呵護(hù),彌補了弗洛倫斯從小缺失的母愛。遇到鐵匠后,弗洛倫斯更是迷失了自我。只要有鐵匠在她才能感覺得到自己還活著。她對鐵匠產(chǎn)生本能的強烈愛慕,使她完全無視其它,只要能看見鐵匠,她的生活似乎就變得有意義。她不愿意體驗“自由”和“自我”的存在,直到鐵匠沖她大喊“擁有你自己,女人,離我們遠(yuǎn)點”,她的主體意識才被喚醒,方才意識到“為我”的存在。在與鐵匠的爭辯中,弗洛倫斯才意識到,原來她在鐵匠的心目中一直都沒有擺脫奴隸的身份,而只把她看作外表強悍粗野的奴隸。鐵匠曾告訴弗洛倫斯,“內(nèi)在的苦味使人受奴役,為野蠻打開了門”。在被鐵匠趕走后,穿越森林的途中,她的自我意識逐漸覺醒:她不再依靠任何人、任何的保護(hù),她要獨立。弗洛倫斯開始從自己的角度觀察周圍,學(xué)會讀懂人和世界。“你讀這個世界,卻不讀這些訴說的文字。你不知道怎么讀。”她深深地為鐵匠對她真摯愛的不理解而悲哀而惋惜。在父權(quán)制社會,男性擁有話語權(quán),操縱整個語義系統(tǒng),創(chuàng)造了關(guān)于女性的符號、女性的價值、女性形象和行為規(guī)范,而女人只為“符號服務(wù),以忠誠、耐心和絕對沉默表達(dá)了符號。她自己本人卻被一筆勾銷”。
在瓦爾克農(nóng)場乃至當(dāng)時整個美洲大陸上的女性從來都是毫無話語權(quán)的,對待丈夫或男主人的話從來都是沒有反駁和表達(dá)自己意愿的權(quán)利。而弗洛倫斯歷經(jīng)艱辛找到鐵匠后,因為她不小心拽疼了鐵匠收養(yǎng)的男孩胳膊,而與鐵匠爭論的時候,她的自我意識已經(jīng)覺醒了。弗洛倫斯沒有因為鐵匠的呵斥而退縮,相反據(jù)理力爭,她堅持要解釋原因,爭取自己的話語權(quán)。
“為什么你要殺我,我問你。”
“我要你走。”
“讓我解釋。”
“不。現(xiàn)在就走。”
“為什么?為什么?”
“因為你是個奴隸。”
……
“你的腦瓜空空,舉止粗野。”
……
“除了舉止粗野,你一無所有。沒有自制力。沒有頭腦。”
鐵匠不問緣由地因為弗洛倫斯將小男孩弄哭就要趕她離開,弗洛倫斯不明白為什么,她急迫地追問鐵匠,得到的回答卻是“因為你是個奴隸……你的腦瓜空空,舉止粗野……”。“我震驚了。”弗洛倫斯適才意識到她在鐵匠心目中只是一個舉止粗野的奴隸,鐵匠從未感受到弗洛倫斯對他癡情的愛意,她也就明白為什么鐵匠會那樣對她。這無疑是對弗洛倫斯心靈的又一次打擊,但在回去的路上,弗洛倫斯精神上的自我找尋也由此開始。“不過,失去你之后,我的路清晰了……”。弗洛倫斯?jié)u漸開始讀懂自己的內(nèi)心和這個復(fù)雜的世界,自我意識開始覺醒。
三、弗洛倫斯找到自我,真正得到“自由”
在尋找自我的旅途中,弗洛倫斯從自我意識的覺醒,逐漸變得更加勇敢,前行的路也愈加清晰。穿過森林回到農(nóng)場的弗洛倫斯每晚都在被禁入的新房子墻上一釘一釘?shù)乜滔伦约旱慕?jīng)歷與心聲。平等對待和相互尊重正是兩性間讀懂對方、和諧交流的基本前提。弗洛倫斯不僅勇敢地爭取話語權(quán),更是通過書寫的方式充分表達(dá)自己的感受。在經(jīng)過一系列遭遇之后,復(fù)雜的感受與心靈的沖擊使弗洛倫斯急于宣泄與表達(dá),在沒有人能理解她的情況下,她只能通過書寫來記錄自己的心路歷程。通過這種方式弗洛倫斯充分感受到了精神上的自由,也感受到了逐漸認(rèn)識到自我的過程。通過言說,她經(jīng)歷了從卑微屈膝到自信成熟的精神發(fā)展,確認(rèn)了自己的主體地位,最終自我意識得到升華,從內(nèi)心發(fā)出了成為自己的吶喊:“我變野了,可我還是弗洛倫斯。從頭到腳。不被原諒。不肯原諒。不要憐憫,我的愛。決不要。聽到我了嗎?奴隸。自由。我延續(xù)著。”
弗洛倫斯要活出一個完全有別于過去的自我。“通過寫作,婦女從遠(yuǎn)處,從常規(guī)回來了;從‘外面回來了;從女巫還活著的荒野中回來了;從潛層,從‘文化的彼岸回來了;從男人們拼命讓他們忘記并宣告其‘永遠(yuǎn)安息的童年回來了。”
弗洛倫斯已經(jīng)完全超越了過去的自我,以前那個完全沒有自我的毫無安全感和自信的小女孩已經(jīng)漸漸成熟。在經(jīng)歷各種痛苦與打擊之后,她逐漸清楚地看待這個世界,以及自己的內(nèi)心。她勇敢與鐵匠爭辯,爭取自己的話語權(quán),她堅持每晚刻下自己的心聲,書寫自己的自由。在被母親呢“拋棄”后,弗洛倫斯堅強得面對生活中的各種艱辛,而從不后退,即使遍體鱗傷,也要堅持靠自己的雙腳穿過恐怖的森林。她學(xué)會了不穿“鞋子”也毫不畏懼地走到自己的目的地。弗洛倫斯是勇敢的,是堅強的,是智慧的,也是自由的,她已經(jīng)長成母親期望的那樣強壯,她的身體里流淌的已是更新的血液與生命。弗羅倫斯尋找鐵匠的艱辛旅程,前提是為了拯救女主人麗貝卡,結(jié)果卻成了她主體意識覺醒、精神上從奴隸到自由人——拯救自我的旅程。
四、結(jié)語
“接收支配他人的權(quán)利是一件難事;強行奪取支配他人的權(quán)利是一件錯事;把自我支配權(quán)交給他人是一件邪惡的事。”這是小說末尾母親一直想要告訴弗洛倫斯的話。最后弗洛倫斯也會理解母親當(dāng)時“拋棄”她的舉動,其實是在保護(hù)她。在生活中只有“自救”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依靠別人永遠(yuǎn)無法實現(xiàn)。在小說中雖然 “保護(hù)傘”雅各布死了,我們卻看到了莫里森筆下的每一個受奴役的女性特別是弗洛倫斯,都能通過一種適合自己的方式賦權(quán)自己,設(shè)法自救,最終實現(xiàn)自我意識覺醒,重新塑造自我。在選擇的基本態(tài)度上,莫里森強調(diào):“認(rèn)同祖先,認(rèn)同集體,黑人們個體可在精神上獲得圓滿和勝利。”黑人女性應(yīng)重新發(fā)現(xiàn)自我,建構(gòu)身心解放獨立自主的黑人女性的理想形象。
參考文獻(xiàn):
[1] 托尼·莫里森,胡允桓(譯).恩惠[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
[2] 王春艷.試析托尼·莫里森小說中的美國黑人文化身份主題[J]. 作家,2011( 02) .
[3] 王守仁,吳新云.性別·種族·文化[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4.
[4] 王守仁,吳新云. 超越種族: 莫里森新作《慈悲》中的 “奴役” 解析[J].當(dāng)代外國文學(xué),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