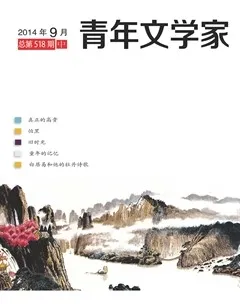阿里斯托芬政治喜劇中的悲劇意味
摘 要:古希臘戲劇家阿里斯托芬以其政治喜劇而聞名。然而由于其作品題材的獨特性,這些政治喜劇中不無悲劇意味。《騎士》雖不是阿氏最為著名的作品,但卻充分地體現了其政治喜劇中的悲劇性。本文即以此為例,從三個不同的層次分析這種因政治題材而特有的悲劇意味。
關鍵詞:阿里斯托芬;喜劇;悲劇意味;政治
作者簡介:褚萌萌,女,本科生,天津市人。研究方向:英美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4)-26-0-02
阿里斯托芬(約前446~前385年),是雅典公民,古希臘早期的戲劇代表作家。他有著“喜劇之父”之稱,被賀拉斯稱為“希臘舊喜劇時代最偉大的三位詩人之一”。然而,與同時期許多喜劇作家不同的是,他的目光是開闊的,他對雅典現實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的批判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他被認為是世界戲劇史上開創政治喜劇的第一人。也正是因為這種題材的獨特性,他的智慧,他的諷刺,他的措辭,得到了更充分的體現和更廣泛的贊美。
一、阿里斯托芬喜劇中的悲劇意味
古希臘戲劇源自古希臘人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民間歌舞。可以說,古希臘戲劇最初體現的就是“一種自由狂歡的精神”[1]。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詩學》中談到喜劇的特征:“戲劇模仿的是比一般人較差的人物,所謂‘較差,并非指一般意義上的‘壞,而是指丑的一種形式,即可笑性(或滑稽),可笑的東西是一種對旁人無傷,不至引起痛感的丑陋或乖訛。”[2] 這說明了喜劇其實是以夸張的手法、巧妙的結構、詼諧的臺詞或對滑稽性格的刻畫,從而引起人對丑的、滑稽的予以嘲笑,最終對正常的人生和美好的理想予以肯定。
與此相對,悲劇則是由酒神節祭禱儀式中的酒神頌歌演變而來。與喜劇的描寫對象是普通人乃至“較差”的人物不同,悲劇則多取材于神話、傳說、民族史詩,通過他們的悲劇故事來表現激烈的感情、崇高的思想、偉大的人格、不朽的精神。
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指出,悲劇是酒神精神與日神精神共同締造的,是不斷走向日神形象世界的酒神歌隊。他否定阿里斯托芬的舊喜劇,認為樂觀主義因素“一度侵入悲劇,逐漸蔓延覆蓋其酒神世界,必然迫使悲劇自我毀滅——于縱身跳入市民劇而喪命”[3]。然而我們認為,正是由于阿里斯托芬政治喜劇的題材獨特性,使得這些喜劇中的悲劇因素成為可能。
首先,從詩人本身來看,正如W. Geoffrey. Arnott所說,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劇中,“都插入一些段落,集中展現當下政治、歷史、信仰和藝術的真實情況,并就真實的爭端向在狄俄尼索斯劇場中的觀眾,提出建議”;正是由于舊喜劇這種“強大的現實感”以及對于現實嚴肅問題“不嚴肅”的討論,造就了這種悲劇意味的可能性。
其次,從觀眾的角度來說,“喜劇令他們愉悅”,因為在喜劇中,詩人“諷刺那些被城里人視為寵兒,而被城市的農民視為怪頭怪腦的家伙”。[4] 對于這些人物的諷刺能使觀眾獲得樂趣,這必然是由某些現實的社會問題所導致的。因此,綜合戲劇內容和觀眾反應雙方面進行考慮,阿里斯托芬政治喜劇的悲劇意味又添加了一層。
二、《騎士》中的悲劇意味
公演于前424年的《騎士》,是一部直接反映雅典當時內戰史實與政治斗爭的喜劇。《騎士》首度公演便取得頭獎,這是阿里斯托芬最得意的勝利,也是當時民眾對其喜愛程度最好的證明。它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德謨斯新近買的奴隸帕弗拉工善于欺騙主人、壓迫同伴;于是其他兩個仆人,得摩斯忒涅斯和尼喀阿斯,根據神示找來一個臘腸販,他在三次爭辯后打倒了帕弗拉工、擔任了統治雅典城的政治使命。誠然,《騎士》不是阿里斯托芬最為知名、藝術成就最高的作品,然而在其中直接、大膽地展現的政治比喻卻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不妨以這部喜劇為例,進一步探究阿里斯托芬政治喜劇。以人物為分類依據,我們可以找到以下三種悲劇因素。
1、帕弗拉工:政治煽動家的性格悲劇意味
帕弗拉工無疑是當時雅典當權者克勒翁的象征。他是一個典型的政治煽動家形象,兇惡、貪婪、空口說大話、有辯才、有手段、善于誣告同伴,欺騙德謨斯……他不止一次地在劇中濫用淫威、恐嚇他人,“你倒會說話”、“我告發這家伙”,指控別人“你們非受懲罰不可”。他的個性也從其他人物的描述中可見一斑,如“自從他進了家門,就叫我們這些仆人老是挨皮鞭”、“他奉承主人,擺尾巴,恭維他,用‘皮屑來哄騙他”。[5] 這些刻畫都是對克勒翁直接、鮮明的影射。
可以這么說,《騎士》的主要政治作用就在于揭露克勒翁這樣的政治煽動家的本質。他本是“人民領袖”,是激進的民主派的領袖;但隨著雅典政治的演變,階級斗爭的劇烈化,這些頗具野心的政客便利用戰時的不安定心理,憑借他們的口才騙取人民的信仰。詩人認為,他們是戰爭的罪魁禍首,是人民的敵人。
“悲劇人物的行為的目的與手段基本上是協調一致的,而喜劇人物卻是自相矛盾的。悲劇人物為了達到自身的目的所采取的多是直接的沖突方式,其態度也是認真堅決的,并且在其超越過程中和陷入困境時,都始終能保持激烈的抗爭意識和九死不悔的執著精神。”[6] 從這個意義上說,帕弗拉工這個喜劇人物具有悲劇人物的意味。誠如帕弗拉工自己在劇中所辯解的那樣,他“原是為城邦的利益而偷竊啊”[7],雖說阿里斯托芬在這里不無諷刺的意味,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這里有真實的成分。作為激進民主派的領袖,克勒翁發動戰爭、爭奪霸權、壓迫寡頭黨,都是他自認的有益于城邦的統治方式。超脫出歷史的局限,拋開他本人營私舞弊、收取賄賂這一點,他與寡頭黨之間的爭斗則更是一種政治理念的分歧、權力的爭奪。然而由于社會發展的大趨勢、民主政治的衰落,克勒翁對于其治邦理念的堅持已是徒勞,最終只能如帕弗拉工一樣被推下臺。這不得不說是一個悲劇。
2、德謨斯:人民的社會性悲劇
阿里斯托芬反對克勒翁的戰爭政策,反對他對人民的壓迫態度。由此推測,他是重視人民,熱愛人民的。然而,在《騎士》中,人民的代表德謨斯卻被塑造成一個稀里糊涂、粗魯無禮、性情急躁、難以相處、耳朵不靈的家伙;他任由一個粗俗的流氓奴隸擺布,他只有讓一個同樣粗俗的流氓來取代這個奴隸方能獲救。
其實,這并不說明阿里斯托芬對于人民的態度是消極的。對德謨斯的塑造實質上表現了民主政治日漸衰弱下的一個社會悲劇,那就是,黨派斗爭激烈,政治局勢不明朗,人民對于社會現實缺乏足夠的認識,對于城邦社會的未來比較迷茫。阿里斯托芬是信任人民的,這是他的理想;然而人民的現狀卻是一個無法避免的現實,理想與現實的沖突恰恰造成了這個社會悲劇。
在全劇的高潮、第三次爭辯到來之前,德謨斯與歌隊的一段對唱可以被視作是阿里斯托芬對于人民的忠誠信任熱愛、對于人民的認識會變得明智的積極態度的最好證據:“你們認為我是個傻瓜,可見你們的頭發地下沒有頭腦。我不過是有意裝傻……我就抓住他,一拳頭打破他的腦袋……我巧妙地捉弄他們,他們卻自以為夠聰明,騙得了我。他們偷竊的時候,我總是注意到他們,卻假裝沒有看見;然后用法院里的漏票管通進他們的喉嚨里,逼著他們把他們從我這里偷去的統統吐出來”。[8]
3、臘腸販:寡頭派的命運悲劇
從表面看來,臘腸販應該是悲劇意味最少的一個角色。他以卑賤的身份、骯臟的性格一躍成為城邦的統治者,而這個過程貌似順利無比。然而,在這個問題之前,首先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為什么要讓臘腸販這個不但缺乏教養而且舉止異常卑鄙的人物充當劇中的“英雄”、驅動劇情的發展呢?
施特勞斯認為,“他是個小流氓,是個庸俗的家伙;他知道這點,他知道自己的位置;他知道,他正當地屬于他生活于其中的貧民區,因此他尊重比他好的人。他對克勒翁也沒有強烈的憎恨;他因為尊重比他好的人,才攻擊克勒翁”。[9] 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即使這樣能為臘腸販的性格正言,也絕無可能為他的身份正言。得摩斯忒涅斯從帕弗拉工屋里偷出來的神示說,歷史上統治雅典的是賣碎麻、賣羊肉、賣皮革和賣臘腸的。這神示顯示出雅典政治的不斷墮落、統治者一個比一個卑劣;更有甚者,如同騎士們這些“一般而言上好的人”剝奪帕弗拉工的權力也需要借助一個臘腸販的力量。由此可見,雖然本劇的重點是對于克勒翁那樣的政治煽動家的批判,但阿里斯托芬對于如同臘腸販這樣的寡頭政治的“幫傭”也持有消極態度。即使贏得了勝利,也沒有贏得正義,這不得不說是命運的悲劇。
三、小結
魯迅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中說道,“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在阿氏的政治喜劇中,政治斗爭、社會矛盾、政客言行被撕扯下原有光鮮的外衣,赤裸裸地展示給眾人;然而,在政治的舞臺上,“有無價值”的標準并非一成不變,劃分也并非涇渭分明,這也許就是造成政治喜劇中悲劇意味的終極原因吧。
參考文獻:
[1]劉明厚. 阿里斯托芬與戲劇精神[J]. 戲劇文學, 2007(12): 31-35.
[2]朱光潛. 談美書簡[M]. 江蘇:江蘇文藝出版社, 2007.
[3]尼采著、周國平譯. 悲劇的誕生:尼采美學文選[M]. 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86: 60.
[4]克諾瓦賽. Aristophanes and the Political Parties. 收錄于A. W. Gomme.著、黃薇薇譯. 阿里斯托芬與政治. 收錄于劉小楓主編. 雅典民主的諧劇.[C]. 北京:華夏出版社, 2008:5.
[5]、[7] 、[8]阿里斯托芬著、羅念生譯. 阿里斯托芬喜劇六種. 收錄于羅念生全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6]柳征. 悲劇喜劇的美學特征比較.[J]. 外國文學研究, 1995(1): 116-120.
[9]施特勞斯著、李小均譯. 蘇格拉底與阿里斯托芬.[M]. 北京:華夏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