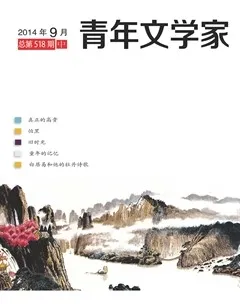從“緣情綺靡”到“且須放蕩”
摘 要: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的自覺促使詩學思想異常活躍。陸機《文賦》提出“詩緣情而綺靡”,使詩沖破儒家禮義的束縛,朝著敢于抒情、文辭華美的方向發展。蕭梁一代,蕭綱繼承并發展了陸機的詩學理論,以“文章且須放蕩”為旗號,引導詩文創作繼續吟詠情性。但由于蕭綱個人生活的局限,受文學發展的制約,“緣情”最終走向艷情,“綺靡”最終變為浮靡。“放蕩”文學客觀上為宮體詩的出現奠定了理論基礎。
關鍵詞:緣情;綺靡;放蕩;宮體詩
作者簡介:杜顏璞(1989-),男,河南新蔡人,河南大學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4)-26-0-02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思想活躍,個人情性得以盡情釋放。陸機的“詩緣情而綺靡”說不僅道出了魏晉南北朝“文學的自覺”下重視情感的理論特點,也點出了詩歌辭采華美的美學特征。從陸機起,詩開始沖破儒家教義的束縛,朝著抒發情性的方向發展。蕭梁一代,文學全面沖破儒家詩學禁錮,走上了不拘禮義的“放蕩”之路,在“放蕩”文學觀的指引下,宮體詩的創作達到了全盛時期。作為宮體詩領袖的蕭綱,他的創作實踐和詩學理論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是受了陸機的影響。
一
陸機開一代風氣之先,“詩緣情”是沖破封建道義束縛后自由抒發感情的第一聲吶喊,“綺靡”則強調了詩的美學特性,指出詩應該是文辭華美的“精妙之言”。自陸機提出這一“緣情綺靡”的觀點后,后人對其借鑒吸收乃至批評爭議就沒有停止過。“緣情”本指指詩歌創作因情而發,是隨著詩歌情感的逐漸宣泄,不再拘泥于傳統的儒家禮義下的釋放。只因“緣情”后緊跟“綺靡”二字,這一“情”字經過后代蕭綱的吸收和發揮以后,轉而發展為被后人所詬病的“艷情”、“閑情”。
作為太康文學的代表,文藻綺麗是陸機作品的一個突出特征。結合當時文風及時代特征來看,西晉士人缺乏建安文人那種激昂慷慨的進取精神,又沒有正始詩人深沉悲慨的憂患意識,詩壇上大興擬古之風,繁縟雕飾成為詩歌主流。陸機“綺靡”說的提出,不僅在當時被人過度放大,為詩歌繁復縟麗找尋依托,也被后世的蕭綱所借鑒吸收,轉而為自己的理論找到了切入點。所以人們批評六朝的采麗競繁時常常追溯其源,認為它肇始于陸機也是基于此。
如果說陸機“詩緣情而綺靡”的提出只是不經意間“濫”情,那么蕭綱的“文章且須放蕩”則是刻意為之了。盡管已有不少學者替陸機辯解,認為其無意于引領宮體詩的寫作,但從蕭綱當時的文學觀念及文學活動來看,他受到了陸機的影響,確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且須放蕩”在一定意義上是源于蕭綱對其所理解的“緣情綺靡”說的繼承、發展。
梁簡文帝蕭綱,自幼愛好文學,因其特殊的身份,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以他的幕僚為主的、主張鮮明的文學集團。南朝時期,對于詩歌吟詠情性、摒棄利義的認識繼“緣情綺靡”后繼續發展,理性精神的弱化鑄成了相對寬松的道德氛圍。簡文帝蕭綱和他的文學集團在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推動下反叛儒家傳統道德,其不拘禮義的言說方式和創作姿態形成了毀譽參半的“放蕩”文學觀。
蕭綱這一觀點的提出與他當時所處的生活環境也有很大的聯系。蕭綱不同于一般的貴族少年,因為是帝王之子,從幼年出閣時期開始,他的生活和文學趣味就與幕僚聯系在一起。“生自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①的蕭綱,六歲能著文且“辭采華美”,“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②。徐摛因文學俱長而出任晉安王蕭綱侍讀,但其詩文創作卻是“好為新變,不拘舊體”③。在他的影響下,蕭綱作文也慢慢流于輕艷,為君子所不取。據《南史》載,初“帝聞之,怒。召徐摛將誚責”。又見摛能“應對明敏,辭以可觀,乃意釋。”接著武帝“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記,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結果“帝甚加嘆異,更加親狎,寵遇日隆”。顯然從這一富有戲劇性的一幕中,梁武帝也是在無形中默認了“立身”與“為文”不相為一的觀點。進而推斷,這種文身殊途的觀點,在當時應該是普遍存在的。這位政治上力行儒教的皇帝似乎也有其子蕭綱那種文歸文、行歸行的態度,對道德和文章的看法遠無后世那樣捆綁對待的程度。從這個意義上看,文與行的區別其實是一種寫作手法上的創新,只有這樣去認識才能在文學史上給宮體詩人一個地位,才能正確看待“文章且須放蕩”這個觀點。
由此可知,蕭綱“文章且須放蕩”最初反映的是不主故常,不拘成法的文學取向,并非意味著與儒家思想的徹底決裂。正如沈玉成所論:“這里所‘放蕩,指的是不受拘檢,任性而行的意思,同于蕭道成對謝靈運‘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位中的‘放蕩,而和‘形式主義、‘色情等等了不相涉。”④如果不是如此認識,將大謬不然。
二
蕭綱認為,文學的基本特點就是吟詠情性,這與陸機“詩緣情”的觀點一脈相承。他說:“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兇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⑤這里蕭綱指出文學創作與哲學著作之間有本質區別。文學要吟詠情性,這無疑是繼陸機之后對緣情的再次發聲,具有重要意義。
六朝時期,文學雖已進入自覺時代,但是創作以六經為旨歸的思想卻時時禁錮著人們的頭腦。為沖破情感抒發的限制,改變這種“朱藍共妍,不相祖述”⑥的局面,蕭綱努力為情性說張目。“短歌雖可裁,緣情非霧榖”,這是蕭綱在《登城》詩中結尾處表達的文學觀點。蕭綱襲用“緣情”一詞,說明了他對陸機“詩緣情而綺靡”這一觀點的繼承。蕭綱對陸機的詩作持肯定態度,他就曾評價陸機“氣含珠璧,情蘊云霧”⑦。“霧榖”一詞來自楊雄《法言·吾子》。楊雄從文學的諷刺作用出發,把那些“霧榖之組麗”⑧,即拋棄內容僅追求形式的作品,概括為“女工之蠹”⑨因此,“霧榖”正是楊雄反對的。但蕭綱的態度則與之相反,他從“緣情”出發,拋棄諷諫說的內核,偏偏認為“霧榖”應該加以提倡。這不僅是為他理解的“情性”說尋找理由,也在一定程度上對當時的形式主義文風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蕭綱作為宮體詩創作的一員主將,又因其得天獨厚的貴族身份,更是將大部分精力傾注于秾詞艷語的描繪之中。蕭綱曾令徐摛編《玉臺新詠》,廣收漢魏以來艷詩,為宮體詩“以大其體”。入主東宮后,寫文章對當時京師文體進行了批判,認為其“儒鈍舒常,競學浮疏,競為闡緩”,指責這些”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嘆息”,旗幟鮮明地為自己表明了立場。他還積極提倡并寫作宮體詩,這些作品多以女性體貌、日常生活為描繪對象,綺秾靡麗的詞藻已被蕭綱玩弄的淋漓盡致,這是繼陸機“綺靡”之后蕭綱對詩歌語言的“放蕩”宣泄。
三
在南朝文學風氣的轉變過程中,蕭綱起了關鍵的作用。在蕭綱之前,齊梁詩以山水羈游、贈別詠懷為主要內容,雖然徐摛等人已有一部分專門的詠物和吟詠女性的詩文出現,但是還沒有到這種“后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為‘宮體”的地步。從蕭綱起提倡并寫作宮體詩,這些作品多以女性的體貌、日常生活為描寫對象,蕩漾著輕靡綺艷的氣氛和風流輕佻的情調。自此南朝文學走入了秾艷放蕩的形式主義。
蕭綱的“放蕩”理論是在宮體詩的創作已經積累了相當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的,并非是為宮體詩的崛起而吹響的號角。語言華美、詞藻秾麗是宮體詩文的重要追求,纖細工巧的筆法、明艷夸飾的語言,正是蕭綱繼陸機之后對詩的美學價值的審視。吟風月、狎池苑、詠美人,描服飾等綺碎刻畫背離了陸機提倡的文辭華美的初衷,轉而走向了濃詞艷語的放蕩之路。“破粉”、“細腰”、“好面”、“嬌靨”等極富畫面感和視覺沖擊力的詞藻堆砌成篇,在滿足了讀者獵艷心理的背后,也造成了朝野上下,競相學習的局面,削弱了詩歌反映現實的能力,使詩歌淪為了淫文艷語。
不消說,蕭綱后期“文章放蕩”的消極影響是世顯而易見的,盡管他在最初并未有意提倡色情文學,但在《玉臺新詠》的創作實踐和“文章且須放蕩”的理論指導下,“放蕩”文學在以宮體詩的主流引導下逐漸涉及過多色情。“吟詠情性“是蕭綱對文學言情特征的自覺認識,他的詩作沖破了傳統思想束縛,但是他的理解卻比較膚淺。當他把無聊之情、放蕩艷情融入進創作領域之時,就促使他走上了放蕩之路,“緣情”便獨沽一味地成為了艷情甚至是色情。時隔多年后入主東宮,蕭綱多作艷詩,則完全是因情隨境遷的緣故,這也是“且須放蕩”之使然和“詩緣情”的繼續和蛻變。最終緣情”變成了艷情,“綺靡”變為了浮靡,“放蕩”文學觀發展到最后被宮體詩引入了一條綺靡輕艷的“不歸路”。客觀上給后人留下了一個指責陸機的口實。
吟詠情性的文學觀念掙脫了傳統詩教的思想束縛,“文的自覺”促進詩的美學意義的發現,從“詩緣情綺靡”到“文章且須放蕩”,詩學創作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蕭綱繼承并發展了陸機的詩學理論,把詩的抒情特征及唯美特征進一步強化。由于特定的時代特征,皇室成員的獨特身份及幕僚創作的推動,“放蕩”文學雖然最終成為了宮體詩的理論支撐,但它對詩文創作的推動,對吟詠情性的繼續提倡,仍然在文學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績。
注釋:
1.(梁)蕭繹著 陳伉,張恩科譯疏:《金言》,呼和浩特市: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8頁。
2.(唐)姚思廉撰:《梁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74年,第73頁。
3.(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520頁。
4.曹道衡 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第250頁。
5.(明) 張溥編 (清) 吳汝綸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2頁。
6.(梁)蕭子顯撰:《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908頁。
7.(明)張溥編 (清)吳汝綸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7頁。
8.(漢)揚雄撰 韓敬注:《法言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25頁。
9.(漢)揚雄撰 韓敬注:《法言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25頁。
參考文獻:
[1](唐)姚思廉撰:《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2]吳宏一、葉慶炳編輯,國立編譯館主編:《清代文學批評資料匯編》,臺灣:成文出版社,1979年。
[3](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4]曹道衡 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
[5](明)張溥編 (清)吳汝綸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6](梁)蕭繹著 陳伉 張恩科譯疏:《金言》,呼和浩特市: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
[7](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
[8](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鑒 》第4卷,北京 :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年。
[9]穆克宏,郭丹編著:《魏晉南北朝文論全編》,南京市: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
[10]陳宏天主編:《昭明文選譯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