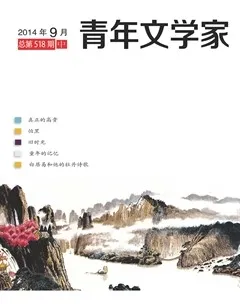“走不出泥土的是根”
摘 要:鄉土是詩人何兆輪精神的故鄉,是詩人生命中的一種信仰和宗教般的情結。
關鍵詞:泥土;母親;鄉愁;生命之根
作者簡介:張翠(1969-),女,文學碩士,錦州師范高等專科學校中文系副教授,從事文學評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4)-26-0-01
也許詩人的天職就是返鄉,何兆輪是遼西大地黑泥沃土養育出來的鄉土詩人,無論身在何處,何兆輪都把鄉土和母親作為精神的故鄉。“再向前靠進一步的鄉土/是母親,再向前靠近一步就是來生”,詩人以宗教般虔誠的情懷來書寫心靈的鄉愁。
美學家朱光潛先生提出過“美就是想象”的命題,審美想象在詩歌中的作用不言而喻。詩歌想象的規律有兩類:一是明顯的變形變質,像波浪里反映的風景一樣,像米釀成酒一樣;二是表面上看起來像白描,沒有大的形質變化,語義也沒有明顯的陌生化,但從根本上講,那些詩句還是變異了,是作家心境的一種載體。何兆輪筆下爹的酒壺、娘的剪紙、蟋蟀的唱腔、黃狗的舌頭、指甲縫里的泥土以及羊群、云朵等,是詩人鄉魂的寄托,是詩人哲學觀的表達。
在《羊在關東》一詩中詩人寫道:羊在關東/活得幸福/遠遠望去/聽羊的叫/一聲比一聲/白/像,一年到頭/積滿農歷的瑞雪/云朵掉進民間不走了/爹娘和我/與它們,成群結隊/一如走路的石頭。此時,我的鄉村,羊啊/鋪寫大地一生/憨實的部分。在何兆輪的“鄉土詩”中,會發現描寫羊的比例很高,何兆輪以羊大為美、羊多為美,羊成為他特有的標簽。細讀這幾句詩,不難理解,羊,絕非我們常說的動物,而是關東大地吉祥的圖騰,是一切祥瑞的征兆,是關東人的美好質樸生活的體現。
何兆輪寫狗也很獨特,詩中的老黃狗之所以令人過目難忘是因為老黃狗體現了詩人對死亡的理解。“老黃狗的舌頭是村莊的火苗/春播夏鋤秋收冬藏/四季都有取之不盡的/干柴。點亮終生/守口如瓶的燈盞/從不放棄才過的風吹草動/不能亂說的話寧可化成灰燼”。乍看這首詩,很難捕捉到“死亡”的感覺,但如果我們把火苗、干柴、灰燼聯系起來,就不難發現,在這層層遞進的關系背后就是死亡。死亡在一切生物出生時就開始了,造物主其實是公平的,假如動物和人都能活百歲千歲,這地球承受不起。何兆輪明知如此,卻對死亡采取了溫和的表達方式,這樣的手法大概是源于中國傳統對死亡的認知,源于詩人對自然、對生靈、對理想鄉土的深入骨髓的摯愛,而這份愛使他走不出故土的鄉根。
何兆輪在《泥土》一詩中這樣寫道:“葉落的時候/才知道/自己屬于泥土/是根/我的內心/有一片純潔的泥土/長著不凋謝的/一株春天/葉是童年的候鳥/根是家園”。“走不出泥土的根”是何兆輪“鄉土詩”的主題,他的詩行間溢滿著泥土的濕氣、溫度和芳香,細膩馥郁的鄉歌村韻、綿柔深邈的鄉戀鄉情,釀制醉人身心的甘露香醇。對詩人而言,泥土就是魂魄,就是命脈,就是詩人的今世來生,“從泥吹到土,一直吹到來生。”盡管詩人并不常在鄉村,但正是這種距離感強化著詩人對故土的思念和思考。
張建永在《鄉土文學中的都市理念和鄉土精神》一文中指出:“從嚴格意義上講,真正的鄉土文學不是真正鄉下人所喜歡的文學。盡管鄉土文學表達了他們的部分心聲,但是,在他們的欣賞習慣中,那種常常被作家津津樂道的農村生活,哪怕寫得再細致入微,對慣常在這種生活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民來說,無法撩撥起他們的審美興趣。”寫作并喜愛鄉土文學的人是那些經過城市文明洗禮,并被城市文化所撞擊、所擠壓、所脅迫、所煩擾,因而生出濃郁鄉愁的城市邊緣人。
社會的快速發展使人們獲得了物質上的豐足,心靈卻難以安寧。許多人缺失的不是物質和金錢,只是輕視了血液里流淌的情感,淡漠了血濃于水的文字。當人們習慣了用光滑油膩的句子來粉飾生活的時候,卻忘了把心靈的滋養還給我們的鄉土。何兆輪就是將世代繁衍我們的根和泥土作為紐帶,讓我們不至于在紛擾的塵世中喪失方向,他的詩自始至終都在詮釋,無論貧窮和富有,都不能割舍最初的感動。貪婪的物欲生活的背后,退去現世浮華的表層,就是正在消逝了的、被遺忘了的土地,是從我們靈魂中短暫抽離出的精神。用何兆輪的話來說,“我們這一輩子就像從不遠走的麻雀、從不偷懶的黃牛和黃狗,憨實的驢溫順的羊一樣,活著是愛死去是愛,從來沒有背叛的理由。”無論活著或者死去,最后的最后我們都要回到泥土,我們永遠不能擺脫土地,永遠不能擺脫大地的悲憫和恩澤。
何兆輪的母親意象是和泥土意象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我和母親繼續在村莊里活/繼續在村莊里死/向前靠近一步也好,再向前一步也好/認定泥土捏造的命”母親的命連著泥土,泥土連著母親的生活。母親認為泥土遠比金子珍貴,“攢夠一把泥土要比攢足金子安穩多了”。“躬身麥地的倒影攢動/恰好與母親相似,大地齊肩/說說她微弱的鼻息。”在詩人的眼中,母親與大地與麥浪融為一體,詩人對母親像對鄉土一樣依賴。“恍如隔世/我不想說地道的家鄉話/母親聽見了/她會躲在泥土里哭”。這種血肉相連、神魂相依的骨肉親情感人至深,這種對母親的愛與依戀是詩人內心真實而獨特的體驗。
記憶中漸行漸遠的鄉土、越來越老的父母,是何兆輪的精神支點。他習慣于“左手摘落夕陽/右手拽回月亮”的過程與節奏,去品味“鄉村吸一縷炊煙/老井盛一壺燒酒”的閑得與自然,把“帶淚的歌/唱在大地的骨頭里”,從中尋覓“鍋碗瓢盆無弦樂,酸甜苦辣有味詩”的境界,這些都是詩人在大地上尋覓到的自然情感。鄉土是纏繞在詩人生命乃至骨髓里的一種信仰,是詩人無法擺脫的宗教般的情結。何兆輪給人們描繪的絕不僅僅是鄉土風光,更多的應該是我們本身該追尋的生命之根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