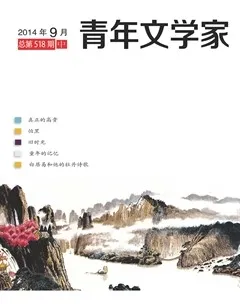光影中晶瑩的人生
楊明月
摘 要:在王小妮的詩歌中,“光”是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光”也成為了詩人表達詩情的獨特意象,并隨著她自己創作的不同階段而呈現出不同的意象表征。本文將以王小妮創作的不同階段為線索,分析“光”意象的獨特內涵,進入王小妮的詩情世界。
關鍵詞:王小妮;“光”意象; 詩歌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4)-26-0-03
在王小妮的詩歌中,“光”是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如“一走路/陽光就湊來照耀。我身上,頓然生長出自己的溫暖。”(《一走路,我就覺得我還算偉大》),“我活著。空氣還從我的手指走過。手指正像金子/一樣閃光”(《死了的人就不再有朋友》),“我說這就是真實。宮殿就恢宏地變成真實。我說這是我/宮殿就閃光。使我看見我正在其中。”(《睡著了的宮殿是輝煌的紫色》),“從清晨活到晚上/人不能總是見到光。我說,我要追求發暗。”(《經歷沉悶有黑暗的夜晚》),“男人們沉重的時刻/我站起來。太陽說它看見了別的光。用手溫暖/比甲殼蟲更小的甲殼蟲。”(《我愛看香煙排列的形狀》),更不用說直接用光作為詩的題目,如《我感到了陽光》,《我看不見自己的光》。《這世上沒有光》,《那個人的目光》,《昏黃的太陽下》。
這些光,有些是太陽光、蠟燭光、燈光、月光,有些是普遍化了的光,更有些是一些詩人內心感受里的光亮。詩人借助“光”,表達著自己的詩情。她的詩,更如“光”一般晶瑩透亮。徐敬亞曾對此評價道:“她把那些字,從天堂的辭典里,像沙場秋點兵那樣輕柔地取出來,巧妙地抽出一絲絲纖細的光。她靠紡織著那些光,額外地活著。她自造了帝王的高傲,用來默默地抵御著漆黑無邊的庸碌和盲昧。……那些像一幅幅寫意畫一樣的漢字,像她一樣柔和、靈透。在用手一撇一捺寫出來的筆劃中,散發著我妻子那一層常人看不見的、藍幽幽的光暈。……這光暈,是她唯一的、無二的詩的光暈。在當代中國藝術界,沒有一個人能取代她。我只知道——唯一,就是自制的光榮,是任何藝術必備的真理。在那光暈中,她可能走向了誰也沒到達的地方,走出了人們已經習慣的視野。”1可以說,王小妮在自己創造出的光影中,實現著自己晶瑩般的人生。
一、自然之光:陽光的真誠與清新
王小妮詩歌寫作起步于1979年大學二年級,其時正值朦朧詩浮上水面。當時的中國,剛剛從濃霧走出,似乎新生活即將開始。徐敬亞所說:“最初的王小妮,寫的是“善良”。她的詩,彌散著青年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的善意之光,它帶著一個誠實機敏的人的真摯與誠懇,也帶著那時代耿耿直直的憂患。她的詩,浮動出一層早餐空氣一樣的清新”(《王小妮的光暈》徐敬亞)。的確,在王小妮早期詩歌中,“光”所表達的就是陽光的溫暖和明亮。如她早期的《我感到了陽光》。
長期處于黑暗中的人,對陽光有種特殊的敏感與強烈的企盼;所以當詩人從“長長的走廊”即漫漫冗長的昏暗走下去,看到“刺眼的窗子”與“反光的墻壁“時不由得十分興奮驚喜,產生一種奇異的感覺“我和陽光站在一起”。霎時發霉陰暗的記憶心事頓消,感到“全宇宙的光腳在這聚集”,這是夸張的真實、藝術的真實。
詩人是以這樣日常的描述開始了對陽光的親密感知。“迎面是刺眼的窗子,兩邊是反光的墻壁”都在暗示著人對陽光需求的物化。
接下來詩人獨特地體驗到“陽光,我,我和陽光站在一起!”鮮活而智性的轉換帶來的消息,足以讓我們感到文字背后詩人的內心,精神世界對于陽光的歡喜和給予人性化的尊重和敬仰,詩歌捕捉的妙處也在于此,把陽光擬人化地站在一起,陽光此時成為人的化身,仿佛陽光是至愛的親人,站在一起互相關愛,悲閔與感恩。而不是詩人以自身單一的關系在把個體寫大。同時也為“陽光”這個意象在以下的行進中能夠呼吸起來埋下伏筆:
啊,陽光原是這樣強烈,
暖的讓人凝住了腳步,
亮的讓人憋住了呼吸。
全宇宙的人都在這里集聚
這些思維活動繼續推進著上面的那些經驗的意味和意義的資源,“暖”和“亮”則是“陽光”這個意象的再生和延續,是意象在抒發在說話在回響,有了如此生動的細節化的傳達之后,讓人感覺陽光的溫暖和明亮是那樣的強大,充滿誘惑和美妙的力量,所以才推出了“全宇宙的人都在這里集聚”的幻影,為我們對人世的愛惜和未來提供了全新的美學走向和和平理想的層面。
然后詩人的情緒還在感染著別人,詩人因珍貴陽光而迷醉到了“我不知道還有什么存在,只有我,靠著陽光,站了十秒鐘”是啊,這十秒鐘該是有著怎樣的感激和吉祥的寓意以至于“我沖下樓梯,推開門,奔走在春天的陽光里……”這樣的收束也讓人感動并余音繚繞,詩人推開門,并不是簡單地只想奔走在陽光里,而是詩人不想私吞那份與陽光交流而獲得的感應、熱愛和呼喚生活、呼喚未來的情愫與能量,她急于把自己的喜悅與人分享,因為那份喜悅是洗滌俗塵的粗礪和荒涼的瓊漿,是洗滌心靈的陰影和污濁的玉液。在這樣將語言和自身融于陽光里所蔓延的喜悅面前,一切的冷漠無情和抗訴都將黯然失色。
詩人追求的是沉靜、明凈與自然。說《我感到了陽光》達到了這境界恐怕并不為過。返歸自然的口語、原始性的意識流動、直覺感的意象三位一體,這就如光給人的感受一樣。
這首詩歌,詩境也如陽光般閃閃發亮,充滿魅力,把光亮和明凈透進了人的內心深處。詩風也如陽光般樸實質以及真誠。
二、光與影:藏匿在陰影中的頑強與平淡
從85年起,王小妮詩風大變,詩人洞悉到了現實的險惡,人生無法規避的傷痛,可以說一次從天而降的災禍,一下子就劈開了她被生活蒙蔽的雙眼。但她對光亮和明凈的想象和體驗是異乎尋常的強烈,以至于當她不再表達陽光般的溫暖時,她也沒放棄“光”這個意象。如:“日光靠慣性往返于天地,而背影卻從來不堪復述。(《告別冬夜》)”,在善與惡的對抗中,詩人發現了人性的復雜,但她并未就此屈服,而是以頑強之資去面對生活的挑戰。她曾說過:“森林巨大的旋渦,把人連夜磨成一盞長明燈,我要試探黑夜的最深處,舉著我這束自然光。”、“我要留有一個空間,在漆黑里從容地用劍,試試各種弧光。”2
既然面對著光,那么,它的對立面——黑暗,也就無可避免地成為詩人的關注對象。她經常收人討論的“黑色”意象,如在《黑暗又是一本哲學》:從這個題目中,我們應該會想到另一層含義,即:光明本來就是一個我們要持續追問的東西。在這首詩中,王小妮寫到:“黑暗從高處叫你/黑暗也從低處叫你/你是一截/在石階上猶豫的小黑暗/光只配照耀臺階/石頭嗡嗡得意/擁擠的時間尖刻冰冷……”
光意味著無處躲藏,詩人必須自己去尋找答案。王小妮看穿人只是“一截在臺階上猶豫的小黑暗”,還有更大的黑暗包裹著他,“黑暗黑暗從高處叫你/黑暗也從低處叫你”,而光芒卻“只配照耀臺階”。正因為詩人直視光芒,向往光明,才特為敏感地感受到了光之后的黑暗和傷痛。在這無奈的現實面前,她不渴求外部陽光的照耀,而是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她并不希望別人把她定義為一個女性主義詩人,她只是抗爭,要有面對最真實的自我和對抗顯現與潛存苦痛的意志力。
在《重新做一個詩人》中,王小妮寫到:“淘米的時候 /米漿像奶滴在我的紙上。瓜類為新生出手指/而驚叫。窗外,陽光帶著刀傷/天堂走滿冷血。”
她把自己一邊縮小,一邊放大成一個提水挑擔的禪師一樣的家庭主婦。在最日常化的生活中,她以平凡的文字震懾人心,其真情源自內心,見于筆端。她的詩作,因此可以看作是對“光”這一主題的一次又一次重寫,不管它是帶著溫暖,還是帶著刀傷。
其實,光作為一種透明的背景一種啟示性的語象,無疑具有一種開放性的人性源泉,屬于人賴以有質量地生活而不是勾且偷生于世的那些神奇偉大的保證者之一,是人性朝人轉過臉來使人真正感覺到自己的存在是一種人的內心故鄉,一種被感情奉為神圣的存在的極致。因此,在光與影的較量中,詩人不管怎樣,內心充盈著仍然是隱匿在陰影中的頑強。所以她寫道:“我和我的頭發/鼓舞起來。世界被我的節奏吹拂。一走路/陽光就湊來照耀。我身上/頓然生長出自己的溫暖。”(《一走路,我就覺得偉大》)
這時,她的詩進入到了平和、達觀、睿智的境界,恰如陽光般自然流淌。苦難的精神煉獄,給詩人的生命的精神思維添了幾許滄桑,但也使她實現了藝術上的涅槃。
三、自由之光:釋放自己,安放靈魂
“光”無疑是王小妮詩歌中最基本的內核,她對“光”地體驗到了超過其他一切體驗的經歷的地步,而且無涯無渚,幾乎接近某種神秘主義的境界。
在《月光白得很》,她這樣寫:
月光在深夜照進了一切的骨頭。
我呼進了清白的氣息。
人間的瑣碎皮毛
變成下墜的螢火蟲。
城市是一具死去的骨架。
沒有哪個生命
配得上這樣的夜色。
打開窗簾
天地正在眼前交接白銀
月光使我忘記我是一個人。
生命的最后一幕
在一片素色里靜靜地彩排。
月光來到地板上
我的兩只腳已經預先白了。
這首詩寫得如此晶瑩剔透而又深徹悠遠,不僅淋漓盡致地傳達了生命個體在面對“白月光”時一剎那的直覺體驗,尤為可貴的是還對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直覺體驗作了形而上的玄想和升華,展示出世界和心靈最本質的一面。
這正表明了詩是在思想之海有如刀鋒般的邊緣、在水的最薄的部位的一種滑行、銳利、痛快、澄明、通透,但也因此而立足異常艱難,充滿了高危性。雖然詩人從中獲得很大滿足,感到極大快意,有很高的自由度,但這種飄然有如神子般的、精神上的極度自由的快感,是無法或者干脆拒絕與人分享的。王小妮始終認為寫詩是“個人的事情”,她甚至寫道:“作為一條巨大的履帶之外的游離者,我自己退出來。讓它像一條河那樣在身邊流動,我,只和自己的感受在一起。”(《詩人的空間》)這正如光一樣,而光又無所不在,它包容萬物,也意味著一種自由,這種自由狀態,也是王小妮一直追尋的。李振聲曾對她評價道:“正是憑借了詩的那種將人排拒在外的、壁立千仞般的‘陡峭性,詩人的身心才為一種‘意外的‘喜悅所充盈。一方面是把自己拼命地往深里藏,一方面卻又從中獲得很大程度上的自由感。詩人因內斂而變得自如,復又以封閉而獲得放達。諸如此類,在局外人看來絕難通融的一些悖論性因素,卻在王小妮這里達成了一種幾近完美的和解。”3這種“和解”,正是一種敞開、呈現,同時又是一種遮蔽、限制。在《月光白得很》中,人的自然本性中的兩種基本動力交替出現:一方面是節制,要求經過凈化和接受控制的想象和情感,詞語成為清澈、簡練、簡樸和自然的心路披露,簡短靈活的句子代替那種面面俱到、枝葉繁茂的句子;另一方面則要求無拘無束地、自由地表達想象和詩情,渴求尋一塊安放之地。整首詩正如月光一樣,皎潔可觸但又縹緲不可捉摸。
正是在這種苛刻的寫作中,詩人在詩中小心地釋放自己,安放自己的靈魂。但釋放詩情,安放靈魂豈是容易之事,如光一樣,它是如此的耀眼,卻又如此地敏感,它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一切顏色的侵入,可能都會使它失去純正性。因此,在王小妮的詩歌中,有時也可看見孤清、冷寂之味。徐敬亞曾說:“她的性格中,有一種喜歡寒冷、清灌、倔強的怪癖,像喜歡瘦瘦而孤傲的骨頭。”(《王小妮的光暈》)在她的詩中,可看到許多素色的詞匯,如“白”、“青”、“白雪”等,因為這些詞在“光”面前才清晰可見,都帶著“光”的表征。這些詞匯,都可以歸為同一類范疇,雖然清醒地看穿,卻懷著巨大的悲憫。可以說,她運用這些詞匯,透進了人的心靈深處。
四、小結
“光”意象在王小妮詩歌中還有多處體現,而王小妮對“光”的描寫也經歷了不同階段,但可以肯定的是,王小妮在“光”中一直尋找著真實,不僅是語言的真實,也是自己人生的真實。她的詩歌精神可以說就是那么一束光,永遠照耀著生活,照耀著我們察覺不到的詩意,但愿我們可以借助它的光,發現生活中存在的詩意,照亮我們的內心世界。
注釋:
[1]徐敬亞:《王小妮的光暈》,載《詩探索》,1997年第2期
[2]王小妮:《我的紙里包著我的火》,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頁
[3]李振聲:《王小妮讀札》,載《當代作家評論》,2008年第5期
參考文獻:
[1].王小妮.我的紙里包著我的火[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
[2].王小妮.王小妮的詩:半個我正在疼痛[M].北京:華藝出版社,2005
[3].王小妮.安放[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
[4].徐敬亞.王小妮的光暈[J].詩探索,1997(2)
[5].李振聲.王小妮讀札[J].當代作家評論,2008年(5)
[6].于堅.王小妮,基本情緒[J].當代作家評論,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