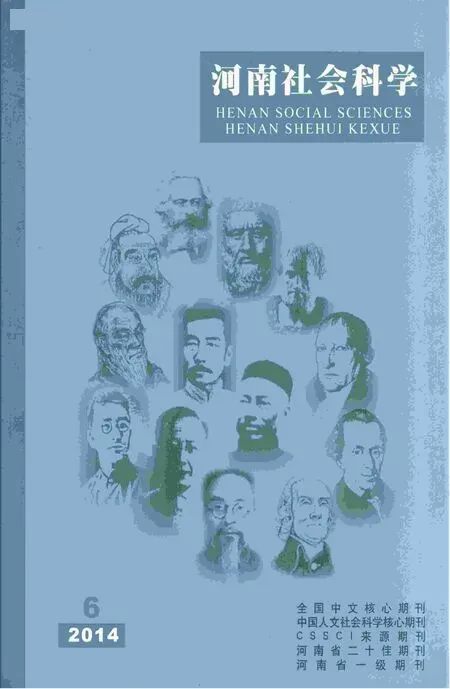湯用彤與新人文主義關系新證——兼論湯用彤與學衡派的關系
趙建永
(1.天津市社會科學院 哲學所,天津 300191;2.北京大學 哲學系,北京 100871)
學衡派是受美國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新人文主義影響而產生的一個學派,活躍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文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學衡》發刊詞中規定凡為該刊寫稿者即是《學衡》社員。雖然《學衡》的100多位作者學術性格各異,但他們的思想有其內在的一致性。因此,可將之合稱為學衡派。以往學界對學衡派存在較多誤解,過于強調學衡派與新文化派的對立。實際上,《學衡》的重點不只是批評新文化運動的不足,更根本的是其在新人文主義指引下的學術研究。無論從數量還是從質量上看,后者都不亞于前者。近年學界對陳寅恪、柳詒徵等《學衡》社員學術思想研究的發掘,就體現了對于學衡派的學術成就開始引起重視。然而對于學衡派成員中進行學術思想研究的典型代表湯用彤的發掘依然十分不夠,以致學界對湯用彤與新人文主義和學衡派關系出現不少質疑。本文根據新舊史料對湯用彤與新人文主義及學衡派的歷史淵源進行梳理,并將之放在現代文化思想史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以期拓展和深化學衡派的研究,對中國現代學術史、思想史的研究和當前文化建設有所裨益。
一、學界對學衡派的反思——《學衡》重估中的湯用彤
學衡派自誕生起的60多年里,一直被視作新文化運動的敵人。1922年《學衡》創刊伊始,魯迅即撰《估〈學衡〉》批判道:“夫所謂《學衡》者,據我看來,實不過聚在‘聚寶之門’左近的幾個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雖然自稱為‘衡’,而本身的稱星尚且未曾釘好,更何論于他所衡的輕重的是非。”①文末總結說:“諸公抨擊新文化而張皇舊學問,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為一種主張。可惜的是于舊學并無門徑,并主張也還不配。”其實,學衡派主將們大多是學貫中西的學術文化大師,并非反對新文化。這表明魯迅對于學衡派融合新舊的基本理念沒有全面的認識和同情的理解。魯迅在寫此文時,只看到《學衡》第1期,他主要是對這期中某些文章的文字進行了一些就事論事的批評。單憑一期雜志來評估整個學衡派,難免失之偏頗。但由于魯迅的地位,他的評價成為否定學衡派的經典話語,長期以來有著重大影響。隨后,學衡派被茅盾、周作人、鄭振鐸、鄧中夏等人定性為“復古派”“反動運動”,遭到激進派和西化派的共同圍攻,原因是其提出了不同于新文化運動的文化建構理想,且對新文化派持批評態度。新中國成立后的評價承其余緒,將學衡派徹底否定,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學衡派被視為“頑固保守”“反動復古”的守舊勢力而備受批判和冷落。湯用彤在1959年還被迫檢討了自己“過去參加《學衡》是走反動路線”[1]的錯誤。
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化激進主義受挫,“國學熱”等形式的保守主義勃興,學界開始反思新文化運動中激進主義的負面影響,學衡派也開始受到重視。樂黛云教授是國內為學衡派平反的先行者,早在1980年,她去哈佛大學進修,尋覓“哈佛三杰”的足跡,收集了不少《學衡》的材料,重點研究了湯用彤的思想,發現他那時就特別強調古今中外的文化交會,提出要了解世界的問題在哪里,自身的問題在哪里;要了解各自最好的東西是什么,還要知道怎么才能適合各自的需要。這種既未造成斷裂,也未形成封閉的文化理念之魅力,促使她將《學衡》全部79期雜志通覽了一遍,研究《學衡》也成為她做比較文學和跨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礎。1989年,樂黛云率先發表了《重估〈學衡〉——兼論現代保守主義》,為國內的《學衡》研究啟封。隨后,湯一介的《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紀念湯用彤先生誕生100周年》一文,認為從湯用彤一生之為學都是在探索和實踐《學衡》雜志“昌明國故,融會新知”的宗旨,并闡釋了其深刻內涵。在此基礎上,樂黛云又發表《“昌明國粹,融化新知”——湯用彤與〈學衡〉雜志》和《世界文化對話中的中國現代保守主義》兩文,認為在學衡派眾多成員里,足可稱為靈魂和核心的是吳宓、湯用彤、梅光迪、柳詒徵、陳寅恪等人。在“昌明國粹”方面,學衡派不同意自由派的“棄舊圖新”,更不同意激進派的“破舊立新”,而認同于以“存舊立新”“推陳出新”或“層層遞嬗而為新”的新人文主義;在“融化新知”方面,學衡派反對“窺時俯仰”“惟新是騖”,強調摒除西洋文明根據其特殊之歷史、民情等為解決一時一地問題而發的部分,而尋求其具有普遍永久性的、真正屬于世界的西方文化。在古今中西的坐標上,學衡派一方面不同意革命論和直線進化論,與激進派和自由派相抗衡;另一方面強調變化和發展,因而超越了當時的舊保守主義。學衡派在引介西學方面則以全面考察,深及根底,取我所需,拋棄長期糾纏的“體用”框架而獨樹一幟,代表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另一潮流,與激進派、自由派和保守派實際上共同構成了中國20世紀初期的文化啟蒙。
樂黛云與湯一介的上述文章,被多次轉載,影響廣泛。研究者多沿用其觀點,將學衡派放在世界文化對話的語境下來看待,把學衡派當作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是對激進派的制衡和有益補充。在此之前,研究者視野中的學衡派基本上只是梅光迪、吳宓等少數最活躍的人物對于新文化運動的批評。而此后,學衡派在學術研究和文化建設方面的貢獻逐漸引起學界重視并得到承認。學衡派的內涵也在不斷拓展,湯用彤、陳寅恪、王國維等其他《學衡》作者也開始被納入學衡派范圍內,學衡派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不斷加大,對學衡派的評價也日趨公正。現在至少在學界,正處于向學衡理念回歸的階段。有學者提出“守成主義”“折中派”“會通派”“改良派”等與“保守主義”不同的說法,以回避“保守”一詞的貶義色彩。徐葆耕認為學衡派是從文化意義上對“中西會通”展開全面研究之最早者,因此名之為“會通派”[2]。筆者認為“會通派”這一提法最為準確,更為符合《學衡》雜志論衡百家、自成一家的包容品格。學衡派的新人文主義的國際視野和由此而具備的當時最新且最全面的知識結構,是把他們和國粹派、東方文化派、甲寅派、孔教會乃至新儒家區別開來的標志。
雖然近年學衡派引起學術界較多關注,出現了一個《學衡》研究熱潮,研究成果已相當豐富,但作為一個蘊含豐厚的文化資源,學衡派研究的潛力依然巨大。其中較為突出的不足是湯用彤與學衡派及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關系少有人注意。由于難度較大和缺乏材料,學衡派研究中往往對湯用彤只是一帶而過,點到即止。如:沈衛威的《回眸“學衡派”——文化保守主義的現代命運》是大陸第一本整體性研究學衡派的專著,對梅光迪、胡先骕、吳宓作了個案分析,而對湯用彤僅略陳數語;鄭師渠的《在歐化與國粹之間——學衡派文化思想研究》一書是他主持的1991年立項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學衡派文化思想研究”的最終成果,該書從文學、史學、教育多方面論述學衡派的文化思想,將學衡派研究推向了一個新水準,但其中關于湯用彤的內容不過數頁。
國內研究白璧德新人文主義與學衡派關系的專著、文章也日漸增多,而直接有關湯用彤的論述卻極少。一些學者還對湯用彤與白璧德的思想淵源提出質疑。由于材料發掘不足,以致有些學者認為湯用彤不算是學衡派重要成員,與白璧德關系不密切,也不刻意宣傳白璧德,更談不上是其弟子。筆者認為,這些論斷既與湯用彤作為學衡派“靈魂和核心”的地位極不相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研究者對學衡派認識的拓展,因而有必要對此做一番全面的考察。上述持反對意見者,往往忽視了湯用彤與白璧德在思想上的密切聯系,以及湯用彤未刊稿中與白璧德直接相關的材料。實際上,湯用彤與吳宓一樣都全面繼承了其師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思想,并身體力行,投身教育,以圖通過經典文化的傳承和道德人格的提升來實現民族復興。近來在新編《湯用彤全集》的過程中,筆者對湯用彤留學文稿及歸國后的講義等未刊稿進行了梳理,新發現的史料為細致而深入地考察湯用彤新人文主義思想及實踐提供了可能,它表明了湯用彤與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深厚淵源,以及湯用彤在學衡派中的核心地位。
二、湯用彤與新人文主義的學脈淵源——新史料的發掘與印證
新人文主義是20世紀初形成于美國的文化守成主義思潮,因其源于古典人文主義而又賦予新闡釋而得名,一度與杜威的實用主義相抗衡。其代表人物美國新人文主義批評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6—1933)針對近代西方功利主義和泛情主義帶來的道德淪喪、物欲橫流的現實,系統提出解決方案:以品德修養為中心,重倡古典文明,融會東西文化規范,通過人文教育重建“人事之律”,強調在同情和選擇之間保持一種適度平衡的訓練(discipline),以挽回西方文化道德意識的衰退。他倡導為學必須從涵養人格始,以東西古今圣賢為榜樣,并對儒道釋三家的學說有多方面的認同。他培養了湯用彤、吳宓、梅光迪、梁實秋等一代中國學人,被學衡派奉為精神導師,開啟了新人文主義與中國文化溝通交會的廣闊空間,經過學衡派與新月派的傳播,在中國文化現代化進程中起到獨特的作用。
湯用彤在拜會白璧德之前,已在研讀他的著作。湯用彤的《1918—1919年寫于漢姆林大學的論文集》特意征引了白璧德的名著《新拉奧孔》,湯用彤把它排在各類參考文獻之首,而此時他尚未轉去哈佛大學。《新拉奧孔》一書承接《文學與美國的大學》(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里的新人文主義思想,另辟角度,以萊辛(Lessing)的名作《拉奧孔》對偽古典主義藝術形式混亂的批判為引,批評了自盧梭以來19世紀浪漫主義運動忽視藝術類型(genre)之間的界限,缺乏約束(restraint)所造成的不同藝術形式間的浪漫主義混亂(the Romantic confusion of the arts)。而這種藝術領域的混亂與社會生活領域缺乏道德約束其實都是息息相關的。對此,他倡導內在制約以克制人的本能沖動,實現自律,從而調治混亂。白璧德抨擊對西方近現代文化影響甚巨的以培根為代表的科學人道主義(scientific humanitarianism)和以盧梭為代表的泛情人道主義(sentimental humanitarianism),呼吁人文學術的復興。湯用彤文化觀的形成與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關系,確如樂黛云所論,是他受白璧德學說的吸引而后轉入哈佛大學的,“并不是白璧德塑造了《學衡》諸人的思想,而是某些已初步形成的想法使他們主動選擇了白璧德”[3]。此類初步碰撞迸發的思想火花,在這冊論文集的字里行間已有不少展現。新人文主義不但強化了湯用彤對傳統文化的自信,而且使他的眼界更為開闊,從而能夠提出世界性的文化理想。
湯用彤1919年初入哈佛,沒等到開學,即于7月14日由吳宓、梅光迪引見,與陳寅恪一起拜會了白璧德教授,當晚談至11時半始歸。白氏認為中西文化傳統在人文方面應“互為表里”,對孔子尤為稱贊,并希望中國學人能采擷中西文化精華,以求救亡圖存,而免蹈西方之覆轍。湯用彤一開學就選修了白璧德開設的“19世紀的浪漫主義運動”一課。湯用彤的文化觀和治學態度,基本上與白氏相契合。湯用彤主要從事的印度哲學與佛教研究是他于哈佛大學時期在白璧德的鼓勵啟發下開展的。白氏于留美中國學生年會上講:“吾少時,以欲研究佛教而苦攻巴利文與梵文時,吾每覺本來之佛教,比之中國通行之大乘佛教,實較合于近日精確之批評精神。中國學生亟宜學習巴利文(今留美學生中,習之者已有二三人),以求知中國佛教之往史,且可望發明佛教中尚有何精義,可為今日社會之綱維。”②這番話可謂昭示了湯用彤發掘整理和研究印度哲學與佛教的初衷。湯用彤與陳寅恪即演講中所提及留學生中習巴利文之人。在白氏新人文主義的指引下,中國這批青年學子對于通過佛教振興中國思想和社會抱有共同的期望。湯用彤在哈佛期間逐漸由西方哲學史轉向以印度語言學為核心的印度哲學與佛教,師從梵學大師蘭曼深造梵文、巴利文。1920年8月,湯用彤在哈佛大學曾單獨為吳宓講授“印度哲學與佛教”③。《吳宓日記》中多處記載他與湯用彤、陳寅恪等人一起探討佛學的情形。這一方面說明湯用彤已能把所學知識消化并系統表述出來,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們對白璧德師訓的重視與落實。1921年2月,吳宓記述:“巴師(白璧德)謂于中國事,至切關心。東西各國之儒者(Humanist)應聯為一氣,協力行事,則淑世易俗之功或可冀成。故渠于中國學生在此者,如張(鑫海)、湯(錫予)、樓(光來)、陳(寅恪)及宓等,期望至殷云云。”[4]在哈佛期間,在湯用彤、吳宓周圍逐步形成了一個以融合新舊文化為志向的留學生群體,他們時常聚會交流讀書的心得體會。湯用彤還時常研讀新人文主義的另一位領袖穆爾(Paul Elmer More,1864-1937,白璧德的終生摯友)的論著。現存湯用彤的外文藏書盡管已散失近半,但其中仍保存下來他留學哈佛前后所獲穆爾的《柏拉圖主義》(Platonis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17)和《新約中的基督》(The Christ of the New Testament,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24)兩本著作。他們以上種種學術活動都為學衡派的成立做了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
林偉博士近年遠赴美國查閱有關學衡派的原始文獻,成績斐然,發現了許多新材料[5]。然而,他以哈佛大學所藏白璧德檔案中未曾見到多少與湯用彤直接相關的材料為由,來質疑湯用彤之于白璧德的師承淵源,并以哈佛的蘭曼檔案中湯用彤的材料最豐富為據來推測,在哈佛諸師中,蘭曼對湯用彤的影響最大,且遠甚于白璧德。筆者認為僅憑檔案材料尚不能做此論斷,尤其是在思想方面。理由有三:其一是哈佛現藏白璧德檔案的材料構成,在年份和種類上并不完全,由于有些材料可能已佚失,因此不能判定湯用彤與白璧德的關系疏遠。這正如我們在湯用彤留學文稿及歸國后的講義中,沒有發現與蘭曼直接相關的材料,但這并不能否認湯用彤曾受到蘭曼的巨大影響。其二是蘭曼、白璧德與湯用彤交往的記錄方式不同。由于蘭曼是個非常細心的人,他不僅保持寫日記的習慣,還將學生的上課記錄和信件悉數保存妥當,而白璧德卻沒有這一習慣,因而,蘭曼保存與湯用彤交往的材料最多。其三是相關材料不僅要看數量,更要看材料背后所體現的思想影響的深度。這可以通過蘭曼、白璧德的學術思想同湯用彤學術思想的交集來參證。對照湯用彤與哈佛諸師各類著述的比較,才能理清湯用彤對他們的繼承和發展。可以說白璧德和蘭曼是對湯用彤影響最為深遠的兩位美國導師,蘭曼的影響主要為語言學等具體的學術知識,而白璧德的影響則不僅包括學術知識,而且更主要的是體現在文化理念和學術方向的指引上。
白璧德檔案中雖沒有保存下來他與湯用彤直接往來的信函,但通過吳宓與白璧德的函件,依然可以折射出湯用彤與白璧德的師生情誼。吳宓在《學衡》創刊之際,致函白璧德抱怨該刊稿源匱乏,白璧德1922年9月17日復函為之出謀劃策,并推薦湯用彤所撰叔本華哲學及佛教方面的文章。其中有關湯用彤的評論如下:
聽聞哈佛的中國學人對你新辦的《學衡》雜志評價甚高,我感覺這正是當下所需。以后不知道你能否召集到充足的作者群。去年冬天,你來信提及所遇到的諸多困難和挫折。在這種情形之下,明智的辦法似應是,只要總體觀點一致者,就可以與之合作。湯用彤先生難道不是證明對《學衡》雜志大有輔佐之功嗎?在他離開坎布里奇回國之前,我與他就中國哲學進行了一次的談話。我感覺他比我遇到的任何其他中國人都更通曉這一領域。他在《中國留學生月刊》上發表的關于叔本華與佛教的論文(或者相應的文章)對于你們《學衡》不是很好的稿源嗎?樓光來先生關于笑的理論的大作打動了我,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或許適宜介紹給中國的讀者。湯先生和樓先生也許沒有目前中國似乎需要的那種激進性,但不管怎么說,他們皆是非常有用的人才。……順便說一下,我希望你們能對約翰·杜威新出的兩卷本發表評論,以揭露其膚淺性。他在美國影響殊惡,我懷疑在中國亦復如是。但愿湯先生能對你有所幫助。④
白璧德常與湯用彤討論東西方哲學,而湯用彤的勤勉與聰慧給白璧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白璧德稱湯用彤是他所遇“最通達中國哲學之人”,并寄予厚望。信中所推薦的湯文是指:“Schopenhauer’s Philosophy of Genius”(《叔本華天才哲學述評》)⑤、“Oriental Elements in Schopenhauer”(《叔本華哲學中東方思想成分考原》)⑥。前者作于1921年1月17日,原文收于湯用彤哈佛時期文集《哲學專輯》第1冊之第2篇。該文提要以《叔本華之天才主義》為題,發表于《文哲學報》(1923年3月,第3期)⑦。文中認為,當時學界有過分強調叔本華思想中柏拉圖和東方思想因素的傾向。此時他已發現宗教性的奧義書、佛教與屬于浪漫主義的叔本華哲學之間的根本差異。隨后他繼續研究這一問題,并寫成專文《叔本華哲學中東方思想成分考原》,于1921年12月發表在《留美學生月報》(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與前文專門分析叔本華思想的西方思想因素正相呼應,合而觀之正得其全。白璧德在函中還期望湯用彤等《學衡》成員全面評介杜威,肅清其實用主義在中國的流弊。可見,湯用彤歸國后講義中對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批判性引介,深受白璧德的影響。
盡管白璧德檔案直接提到湯用彤的材料不多,但是該檔案的發掘還是大有可為。白璧德檔案中如下文稿都是湯用彤相關西方哲學講義的主題:《盧梭與浪漫主義》(Rousseau and Romanticism)、《柏格森與盧梭》(Bergson and Rousseau)、《浪漫主義運動》(Romantic Movement)、《中西方的人文主義》(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等等。湯用彤歸國后即將白璧德新人文主義付諸學術實踐,他的各種講義多次講到白氏的思想。湯用彤在白璧德講授的“19世紀的浪漫主義運動”課程基礎上加以擴展,開設了《19世紀哲學》課程,把19世紀的浪漫主義運動放在當時哲學文化變遷的整體大背景下加以深化。其中涉及的浪漫主義作家很多,且相關文學批評家也幾乎是最新的一些人物,反映出湯用彤對于浪漫主義運動的諳熟。對照現存白璧德檔案的相關講稿,可以看出湯用彤的講義是在白璧德的講稿和自己的讀書筆記基礎上寫成的。將白璧德檔案材料與湯用彤的講義進行比對,還需要考慮湯用彤對所學新知的自我理解和創造性,他并不是完全照搬美國諸師的學說。白璧德“19世紀的浪漫主義運動”這門課主要講的是各時期的文學流派和代表人物,湯用彤則將其中的阿諾德、施萊格爾等文學家著重與哲學思潮聯系起來講述。該講義一大特色是文史哲的會通,這方面很像白璧德的淵博貫通的風格。湯用彤在《反理智主義》(Activism)講義中認為“浪漫主義是反理智主義的先導”,因此,湯用彤哈佛手稿和講義中關于反理智主義的內容可以看作是對白璧德浪漫主義研究的一種拓展。其中直接引述白璧德所著《盧梭與浪漫主義》(Rousseau and Romanticism)即為一個例證。
白璧德在湯用彤回國后并未與他失去聯系,仍保持書信往來并寄贈自己于1924年首版的新書《民治與領袖》(Democracy and Leadership)。白璧德該書將他的道德和美學思想與政治學的基本主張聯系成一體而完備起來,使其成為一個真正的時代文化批評大師。湯用彤的《唯心論》講義也講到該書的思想。從湯用彤現存講義,以及白璧德與吳宓的往來書信中,可以看到他們為新人文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為維持《學衡》雜志所作的種種努力。1933年,吳宓在《悼白璧德先生》一文中列出白璧德的八位中國“及門弟子”⑧,其中就有湯用彤,可謂實至名歸。
總之,湯用彤把白璧德師訓和《學衡》座右銘“論究學術,闡求真知,昌明國粹,融化新知”貫穿于畢生的學術探索和實踐,成為學衡派的中堅力量。湯用彤既看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缺陷,也看到了其長處,避免了激進派與保守派的偏頗,臻于平和而又公允的圓融境界。在當時各類學說的紛爭中,表現出更為健全、開放、成熟的文化心態。他會通東西的努力,成為20世紀中國文化啟蒙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促進了中國學術的現代轉型。他的各項學術研究都是其新人文主義思想的具體落實和體現。其結論宏通平正,對今人學術文化研究和中國文化建設都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和啟迪意義。
注釋:
①彼時魯迅署名“風聲”發表于《晨報副刊》1922年2月9日。后收入《熱風》,《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77頁。
②白璧德撰,胡先骕譯《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談》,《學衡》第3期(1922年3月)。
③吳宓將湯用彤手寫此課概略及應讀書目連同其他聽講筆記、論文,“編訂成一甚厚且重之巨冊。題曰 Harvard Lecture Series,Vol.V(1920-1921)。今存”。吳宓:《吳宓自編年譜》,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08頁。
④Xuezhao Wu,The Birth of a Chinese Cultural Movement:Letters Between Babbitt and Wu Mi,Humanitas 17.1—2(Spring—Fall 2004).
⑤由趙建永漢譯,刊于《世界哲學》2007年第4期。
⑥由錢文忠漢譯,刊于《跨文化對話》第7輯,2001年9月。
⑦后收進《湯用彤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4—547頁。
⑧吳宓:《悼白璧德先生》,《大公報·文藝副刊》(132),1933年12月25日。
[1]湯用彤.印度哲學史略·后記[M].北京:中華書局,1960.
[2]徐葆耕.會通派如是說——吳宓集·前言[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3]樂黛云.世界文化對話中的現代保守主義[A].跨文化之橋[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4]吳宓.吳宓日記(第2冊)[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5]林偉.陳寅恪的哈佛經歷與研習印度語文學的緣起[J].世界哲學,2012,(1):137—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