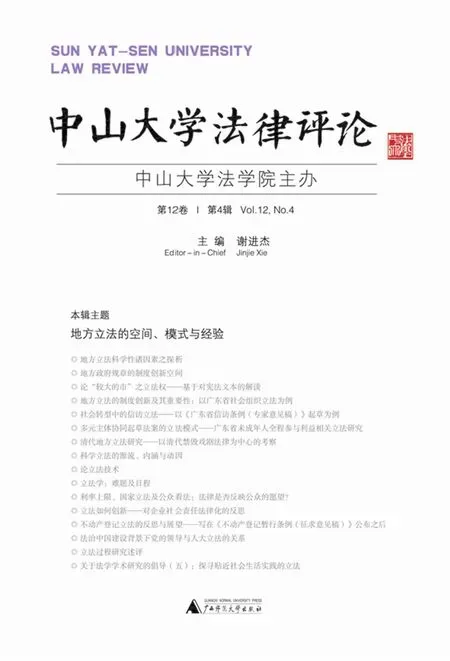立法學:難題及日程
尤里烏斯·科恩(著) 孫競超(譯)
立法學:難題及日程
尤里烏斯·科恩(著) 孫競超(譯)[1]
本國法理學研究主要集中于法律秩序的司法方面——關于確認司法權威的法律秩序之形式結構,關于裁判法的概念工具,關于司法機構的行為方式和歷史沿革,關于司法推理的邏輯,關于法庭聲稱其所服務的社會目的,關于他們應該為之奮斗的道德理想,關于法官造法的批判和評價,等等。各式各樣的“學派”標簽經常伴隨著相應的一些智識上的努力,例如,分析學派、社會學學派、歷史法學派、哲理學派,每一派常常以謙遜的真理為代價宣稱自己的優越性,換句話說,它們各自呈現出的不過是對于給定研究對象的一種不同的、極力強調的但又是非競爭性的關注而已。廣義上來講,如果法理學在其實質和規范方面均是一種對法律秩序的理論解釋,那么我們在邏輯上可以預期法律秩序的立法方面也在法理學的研究范圍之內。然而,從法理學著作主題的智識產量來看,情況并非如此;相當少的寫作精力被投入到了法律秩序立法方面的研究之中。[2]For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see“Symposium on Judicial Law Making in Relation to Statutes”,36 IND.L.J.411(1961).實際上法理學僅僅是以法院為方向,僅強調了法律秩序的一部分——盡管是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有人要給這種有限視野的法理學事業貼標簽,它只好被稱為司法法理學,亦即一種關于法律秩序中司法成分的理論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立法學,[1]My earlier use of the term is in the piece,Cohen,“Towards Realism in Legisprudence”,59 YALE L.J.886(1950).作為與司法法理學相應的法律秩序的立法部分正隨風凋零[2]For the especially salutary contributions of Ernst Freund and Frank E.Horack,see E.FREUND,STANDARDS OF AMERICAN LEGISLATION(1917);Horack,“The Common Law of Legislation”,23 IOWA L.REV.41(1937).。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法學院中學習的“法”基本上是從法庭中得來的“法”這一事實。這種片面的學術關注基于一種假設,該假設認為法律人解決沖突的場所主要是司法舞臺。霍姆斯大法官那頗具影響力,盡管被誤解了的觀察“我們的法律就是法院事實上將做什么的預言,而絕不是空話”[3]Holmes,“The Path of the Law”,10 HARV.L.REV.457,461(1897)(emphasis added).This could be wrongly taken by some to imply that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actitioner interested in the outcome of litigation is the only perspective on“the law.”The statement obviously does not address itself to the judge who is not concerned with how he will decide a case,but how he ought to decide it——a normative,not a predictive task.On the latter,much of what Holmes had to say was significant,but in the context of a judicial,and not a legislative,orientation.See id.at 461-78.,助長了司法是法律宇宙中心這種說法的氣勢。約翰·奇普曼·格雷一句“法庭宣布的意思,而不是其他意思,方使得[法令]成為加諸于共同體之上的法”[4]J.C.GRAY,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THE LAW 170(1909)(emphasis in original).更是為上述說法添柴加薪。
以下情況——即便是經過司法評判的嚴格測試也理由充分——現在已經成為常識:正如在司法舞臺上一樣,在立法和行政舞臺上奮戰的法律人常能牢靠而明確地解決沖突,并且大多數法律規范都能在無需司法解釋或合憲審查的情況下十分明確地付諸實際履行。更進一步,作為不連續司法判決基礎的原則——判決中真正的法——與作為不連續成文法規基礎的原則擁有相同的公用源。二者最終都要對更大共同體的同一公有理想負責,在這個共同體中法律共同體只是一個部分,盡管是一個突出的部分。
由于這種共享公用源和公有責任的親緣關系,取法律秩序中兩塊分立而相互競爭的封地這種局面而代之,有人提議司法和立法應該基于政策連貫性的利益考慮在它們的決策過程中整合為一體。這樣的建議仍待完全實行。即便是龐德早在1908年預言——認為成文法律最終將被視為原則而不僅僅是不連續的規則,并將被以與司法規則及其背后原則[5]See Pound,“Common Law and Legislation”,21 HARV.L.REV.383,385-86(1908).相同的標準類推出來——仍然沒有確定而充分地實現。
除去由于司法法理學遮蓋而導致立法學所面臨的身份認同難題不談,立法學仍存在其他兩種類型的難題。第一種主要是環境方面的,涉及立法學繁榮發展所需的領域、智識及專業氣候——這是一個外在于領域研究主題的難題。第二種類型的難題——關于內在本質——涉及領域自身之內需要被提出的突出問題以及處理這些問題時可能面臨的困境。
Ⅰ.領域難題
立法學領域相比于司法法理學領域要粗糙許多。法律秩序的立法分支令人想到偏見、感情用事、不擇手段、操縱權力、妥協等形象。而處于最好狀態的司法分支則被視為是深思的、審慎的、客觀的,特別是理性的。立法者被認為是易受情緒或權力影響的;關于立法提案的聽證會必須獲得優勢黨派的承認;最終的投票結果很少受到辯論的影響;沒有言之有據的成文意見為最終的決定辯護。[1]See Cohen,“Hearing on a Bill:Legislative Folklore?”,37 MINN.L.REV.34(1952).
由于上述因素都被加入到一種以“政治”為特征的程序之中,可能有人會問,如此不守規矩的程序何以可能在知性上為立法學研究所馴服。這個問題的回應多半是,立法程序的相對任性對理論研究的阻礙,與狂暴的天氣對氣象學研究的影響相差無幾。事實上,立法程序可能在某些方面要比司法決策程序復雜。許多意愿必須被傾聽并以某種方式歸納起來,經過妥協,成為法令形式表達的集合體。相比而言司法意愿在數量上更少——在立法動蕩結束之后開始活動,故而司法程序有助于更冷靜的商討和深思,因為所面對的問題不同了。總政策和原則并不是首先要面對的問題,而是要等到關于政策和原則的含義、應用、精煉性、一致性和/或有效性等難題呈現出來時司法機關才會被激活去處理它們。質詢被設定在經過特殊訓練的對手間進行有秩序辯論的范圍之內;判決在多數情形下都附有書面的辯護意見。就像批發商和零售者,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經營、處理同一件商品,但顯然以不同的方式。
然而,在比較司法程序的深思冷靜和審慎與立法程序的政治緊張氣氛時常被忽視的一點是這兩種形象都僅僅是諷刺畫——部分是真的,但都存在某種程度的夸大。立法程序大部分表面的動蕩之下存在“相對穩定和逐步穩定化的因素”[1]This expression was the hallmark of Karl Llewellyn's influential work,K.LLEWELLYN,THE COMMON LAW TRADITION:DECIDING APPEALS(1960),in which he sought to demonstrate that appellate courts,long criticized for the intrusion of an arbitrary“political”element in its decision-making process,were actually governed by“relatively stable and strongly stabilizing factors”.This author postulates that similar discoverable factors would be found to be at work in the day-to-day operations of the legislative process.;同樣,“政治”考量一直迂回地潛入到司法決策之中。[2]See generally C.PRITCHETT,THE ROOSEVELT COURT:A STUDY IN JUDICIAL POLITICS AND VALUES,1937-1947(1948);G.SCHUBERT,THE JUDICIAL MIND(1965).因此,問題不在于立法程序達不到司法程序理想的程度,或者二者之間是否存在些許家族相似和重疊;問題在于兩種程序必須被視為兩種不同但互為補充的功能,因而,它們需要被對舉而不是被比較。秉持這種想法,如果在寬泛意義上法理學理應擁有更深入更普遍理解法律程序的權限的話,它們都需要被分析,被概念化,被綜合,被批判。
Ⅱ.立法學的氣候
作為一個同等重要的法理學分支,立法學必然是一門理論學科,該學科要求將更多精力投入到對普遍抽象事物的哲學分析或批判上而不是要關注法律從業者或立法者。有理論家爭辯說實踐背后的理論越完善,實踐就會越成功。[3]See Holmes,supra note 4,at 477.不管這樣的抽象主張多么正確,理論家與從業者之間的隔閡遠甚于理論和實踐之間的隔閡。從業者對理論術語和理論界提出的問題感到不適。它們似乎疏離于問題的即刻解決;而且,一個人可以列舉出很多拋開“入門”教程,不去深挖更多理論或“洞悉”法學院課程的成功從業者來。律師資格考試的陰影——一種死記硬背和情境“邏輯”訓練——使得精力和資源都有限的法學院倍感壓力,它們同時要應付立志從業者更為切近的關注和專業人才的高技術要求。工程師和醫務從業者作為一般階層的從業者在與他們各自事業的理論研究保持距離方面與此相同。在法學院里,理論導向需求的出現常常是將案例教學體系變為無止境追求技術包裝場地的無聊的二三年級課程之副產品。而對立法學,也對司法法理學行使研究和批判功能來說,理想環境則是這樣的:上述功能被支持,被維護并且為教學功能獨立配備人員。
這并不排除有天賦的教師同時也是一個有天賦的研究者和批判者的情況。然而,它的確表明研究和批判工作必須持之以恒,不能間斷。據悉,一些研究室和智庫是全天候工作的;[1]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in Washington,D.C.,the Urban Institute in Washington,D.C.,and the Hoover Institute in Palo Alto,California,are obvious examples.但以從業者為主的學校大可不必向那個方向發展。誠然,理論家和從業者的努力最終必須交融貫通起來。實踐最終將受惠于理論的指導(如社會需求或目的)和概念化;而理論則將從實踐提供的原始材料和其檢驗理論是否“合適”的功能中受益。因而,研究和批判工作最好是與教學計劃和從業者的工作相結合。
立法學和司法法理學都應該不只是為了它們實際的效用而進行研究,還應該為它們所關注的人類處境中的更大問題而進行研究。一位敏銳的觀察者曾說過:“即便出于正直的理由,若文學被全然用于廣告或宣傳,亦或藝術僅僅被用于實用而非出于它們自身應豐富生命之享受的目的,那么文明生活將悲哀地走向衰竭。”[2]M.COHEN,LAW AND THE SOCIAL ORDER:ESSAYS IN LEGAL PHILOSOPHY 197(1933).基于多數社會關系都可能是法定的這一假設——事實上包含了人類思維和活動的所有分支——立法學的理論事業,如果加以認真對待,將能涵蓋一個不可思議的智識活動領域,也將包含許多相關學科。然而,我們無需站在起點便覺得不知所措。謙遜求索仍有益處,這片廣闊的空間終將為有效管理才干、精力和資源分配的配制方法征服。
Ⅲ.內部難題:立法學日程
在立法學領域所要關注的許多難題之中,一些是彼此相關的,一些似乎是重疊或類似的,也有一些是獨立于其他學術訓練關注問題的。并不存在嚴格的領域界線來區隔這些難題,如果給這些難題人為劃界也是費力不討好的。不管這些難題是類似的或是有重疊的,如果說研究目的僅僅是從一個不同——這里是立法學的——角度觀察這些難題則應該是沒有管轄權異議的。
A.對立法含義的控制
令立法的規則制定機關感到最惱火也是最普遍的困難之一,是其對于事先制定出涵蓋所有適用特殊情況的規則表現出一種與生俱來的無能。一項規則不能先驗地涵蓋所有適用情形,因此便出現了無法避免的解釋適用的人為需求。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因為它最終關涉立法和司法共享法律共同體控制權的程度。有句古諺說控制了法律解釋權的人,自然而然是法律的主人。從法院解釋一項表述含糊不清法令的輸家的角度看,這個問題也非常重要。盡管在一些特殊情形中法院有自由并且已經表示它們的解釋是預期性的,[1]See,e.g.,Mapp v.Ohio,367 U.S.643(1961).但在大部分情況下法院的解釋是有溯及力的,[2]United States v.Dotterweich,320 U.S.277(1943),one of a myriad number of examples,exemplifies the problem.The Federal Food,Drug and Cosmetic Act,21 U.S.C.§§331(a),333(a)(1976)provides criminal penalties for“any person”who introduces adulterated or misbranded drugs into interstate commerce.Dotterweich,president and general manager of a pharmaceutical corporation,was charged with a violation.Dotterweich,320 U.S.at 278.The controversy centered on whether Dotterweich was a“person”as technically defined in the Act.The Court,splitting five to four,held that Dotterweich was a“person”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Act and therefore,subject to criminal penalties.See id.at 284-85.Before the decision,Dotterweich,even with the help of learned counsel,could not have known beforehand the correct meaning of the law.The decision,nevertheless,followed the normal course of retroactive application.通常會導致對那些猜錯——盡管猜得很合理——立法法令含義的人嚴重的權利剝奪。通常這種“猜測”會達到四人一致,盡管是異議意見,因此,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是僅憑一票決勝負的。于是,立法機關越是對立法含義控制得嚴格,在立法法令之前一個人需要做些什么來避免法律制裁或其他權利剝奪的合理預告就越能得到保證,亦即計劃某人的行為,事先知悉某人的自由將以何種方式受到限制。
如果,如凱爾森所言,一項規則像包含不同解釋的框架一樣運作是可能的,[1]H.KELSEN,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STATE 146(A.Wedberg trans.1945)(“The judge is,therefore,always a legislator also in the sense that the contents of his decision never can be completely determined by the preexisting norm of substantive law.”).那么司法權力憑借“解釋”的職責超越于立法決策的情形將無法消除。法院使用的許多所謂的“解釋規則”[2]A typical example is that statutes in derogation of the common law,and penal statutes,should,in the event of indeterminate meaning,be given a“strict construction.”See United States v.Campos-Serrano,404 U.S.293,298(1971)(penal statute);Coral Gables v.Christopher,108 Vt.414,189 A.147(1937) (statute in derogation of common law).See generally Llewellyn,“Remarks on the Theory of Appellate Decision and the Rules or Canons About How Statutes Are to Be Construed”,3 VAND.L.REV.395(1950).事實上都無助于立法真實意圖的發現,毋寧說它們是法官們用以從模糊含混的法令中制造立法的公共政策格言。在此意義上,司法權力壓倒立法決策意味著前者在與立法者相同的領域耕種,不過是使用了更小更精細的工具而已。這里面臨的問題是這種權力能否被限制或約束,如果可以,將是何種程度。
人們總是認為語言的慣常用法,如果被嚴格地遵守,將完美地實現必要的約束任務。[3]See Dickerson,“The Diseases of Legislative Language”,1 HARV.J.ON LEGIS.2,5(1964).然而,即便是在公認慣常用語表面上“清晰”的情形中,人們也常常難以知悉究竟是慣常的普通用法還是專門的用法在起約束作用,或者很難判斷究竟是在討論過程中對目的的強調,還是混合在法令自身中的內容在目的語言和慣常用語出現沖突時,放棄了慣常的語言用法。[4]But see id.at 6(while task of writing clear statutes remains formidable,problems of language are largely curable).規則和應用二者關系的難題來源于附著在語言符號上含義無可避免的不完全性。不完全語言符號在道德和立法領域相當普遍且十分重要——立法原則和政策經常與道德規則并行不悖。例如,“盜竊”這一表述,包含了他人財產的概念,充滿了業權和契約問題的無窮無盡的分歧。[5]See,e.g.,18 PA.CONS.STAT.ANN.§§3921-31(Purdon 1973&Supp.1982)(nine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theft,differentiated by nature of property taken,title or possession,and means employed).“生命”這一表述,在立法、司法和道德領域關涉墮胎問題,至今懸而未決。[1]Two recent attempts were made in Congress to declare legislatively that human life be deemed to exist from the moment of conception.See S.2148,97th.Cong.,2d Sess.§1(j)(1982);S.158,97th.Cong.,1st Sess.§1(1981).與此類似,“危險工具”的概念遠未能達至定論。[2]See W.PROSSER,HANDBOOK OF THE LAW OF TORTS§78(1971).
在立法中使用不完全語言符號有幾個原因。在一些情形中,不可能建立確定的標準,則對于法官、陪審團或者行政機構依法履行職責來說必須使用諸如“合理的”這類模糊性標準。因為精確的科學標準或慣常約定尚不存在,如“合理程度”這類模糊標準就成為了應用于這些情形中的唯一貌似可行的表述。[3]See Cohen,supra note 2,at 895-97;Merton,“The Role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 in the Formation of Policy:A Research Memorandum”,16 PHIL.SCI.161,174(1949).然而,在其他情形中,當立法領域中不同的競爭者難以達成一致,并且知道立法含義問題被訴諸法院才能停止圍繞決策地位的紛爭時,立法就必須使用適當的意思不明確的表述。因此可能被稱為“藝術的模糊焦點”的表述方式經常得以應用。這里,法院的職責與仲裁程序別無二致,在這一程序之中競爭雙方事實上以妥協的方式彼此作出約定,以便允許一個公允的第三方介入來解決紛爭。
即便孜孜以求,語言的局限已注定了明晰和確定性只能是一種理想,遠非人類能力所及。然而,一個尚未得出答案的問題是,立法程序何以被盡可能好地組織起來,以在事實上追求立法的明晰時至少使表述的清晰度最大化。嚴謹的法律起草者的作品,無論多么專注并精于對清晰度的追求,在為立法機關批準之前都毫無用處。當然,以修正立法的方式改變不宜的司法判決在理論上是可能的。盡管在一些情形中上述改變已經實現了,[4]For example,Congress can expressly declare that a particular state regulation which affects interstate commerce is nonetheless a valid exercise of the state's police power and not a violation of the Commerce Clause,U.S.CONST.art.I,§8,thereby effectively overruling a prior Supreme Court decision to the contrary.In Leisy v.Hardin,135 U.S.100(1890),the Supreme Court invalidated an Iowa statute prohibiting sale of intoxicating liquors as applied to sealed kegs stored in Iowa but shipped in from out of state.The Wilson Act,ch.728,26 Stat.313(1890)(codified at 27 U.S.C.§121(1976)),was subsequently enacted,authorizing states to regulate the use,consumption,sale,or storage of liquor located within the state,no matter how it was packaged.The validity of the Wilson Act was then upheld by the Court in the case,In re Rahrer,140 U.S.545(1891).Corrective legislation has also surfaced at the state level.See MacDonald,“The Position of Statutory Construction in Present Day Law Practice”,3 VAND.L.REV.369,377-80(1950)(discussing New York Law Revision Commission's attempts to draft legislation overruling various judicial precedents).但將此舉措視為常規進程實際上困難重重,該舉措可能夭折,并將吸干計劃和解決新問題所需的精力。以法令解釋法律的工作大量存在,[1]See,e.g.,1 PA.CONS.STAT.ANN.§§1501-1991(Purdon Supp.1982)(statutory construction provisions).反映出立法機關試圖建立超越于法官解釋規則的法律權威;但這些法令自身亦充滿了模棱兩可,因而這些法令亦成為了司法機關善于利用的東西。[2]See,e.g.,Smith v.Messner,372 Pa.60,92 A.2d 417(1952)(interpreting phrase,“or otherwise conveyed,”in statutory construction statute);Commonwealth v.Massini,200 Pa.Super.257,188 A.2d 816 (1963)(definition of“domestic animal”in statutory construction statute interpreted not to include cats).
對于上述立法和解釋持續困境的一種建議性的解決方案是立法機關設立一個特別常務委員會來澄清產生了沖突解釋的現行法律。[3]See Greenhouse,“Probing Congressional Intent Seems at Best to Be Untidy”,N.Y.Times,Oct.22,1982,at A16,col.3.不管怎樣,這樣做高估了立法程序中妥協的作用——事實上立法語言中的妥協經常是邀請法院來解決僵持狀態的信號。在這一困境中的許多挫折是該問題長期存在的副產品。事實上,考特尼·伊爾伯特爵士數年前的論述在今日依然意義非凡:“妥協和合作在政治上的極好的東西,但它們最終不一定趨向于文學作品中的清晰性或文風的精準性,編排的邏輯性或一致性。”[4]C.ILBERT,LEGISLATIVE METHODS AND FORMS 230(1901).總而言之,經歷過政治或立法程序作用于其形成過程之纏斗和抨擊的嚴謹開明的起草者使用的謹慎語言,常常變得面目全非。
展現這樣一幅令人氣餒的圖景并不是要說明改進毫無可能,也不是說因而立法學理論家們試圖將立法語言中的模棱兩可減到最少的努力一無是處。正相反,這些理論家必須意識到并直面難題,即便充分認識到勝率堪比凡人得道升仙。用圖爾圖龍的話來說,一個人不應該“把不適于神之圣壇的一切都扔給狗”[5]P.DE TOURTOULON,PHILOSOPHY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W 348(M.Read trans.1922).。
B.“公共利益”
從與立法提案和法令相結合的“公共利益”概念之普遍應用與濫用判斷,立法學的一項重要任務是對此概念進行澄清并對其作為評估標準的職能進行評價。有一些人將公共利益的概念扔進了垃圾堆,因為他們將其應用視為欺騙麻痹大意者以攫取權力和權威的修辭策略。[1]See,e.g.,G.SCHUBERT,THE PUBLIC INTEREST 219-24(1960).然而,人們肆無忌憚地使用這一用語的事實,正是對其規范力量的暗示性認可——誠如偽善者對于偽裝的需求正是對真理說服力的一種暗示性認可一樣。
經由嚴肅的分析,一些理論家得出結論認為賦予“公共利益”這一概念含義是不可能的——這個抽象概念的含義如此模糊以至于不具備任何實用目的。[2]See,e.g.,id.at 220.因而,上述理論家得出結論認為從這個概念的使用中得到的一切都是令人困惑的概念混沌。[3]See,e.g.,id;see also Sorauf,“The Conceptual Muddle”,in NOMOS V:THE PUBLIC INTEREST 186 (C.Friedrich ed.1962).或許,這后一個難題大多來源于一種錯誤的預設,這一預設認為為了消除“混沌”,該抽象概念必須有一種單一且純粹化的含義。一定程度上來講,許多宣稱是該概念“真實”含義的競爭性主張不過是盲人對于大象的“真實”描述——每個人都確信自己檢查的部分就是全部。更技術地說,經過細致檢查,大量關于“公共利益”概念的說法不過是不同的約定定義,亦即每一位特定的理論家以特定主張或預設目的討論方式使用該概念。不同的視角無需競爭,亦無需產生困惑;它們僅僅是該主題復雜性的暗示性確認,用以作為闡明整體之分立但又聯合的來源。
一些人由下述推論否認任何關于“公共利益”概念的可能含義:(1)利益和欲求是同義詞;(2)“公共”意味著政治共同體中的所有個體;(3)不存在出于每個人利益的單一欲求;(4)立法決策是一項競爭性的,包含沖突性權力的職能;(5)因此,不可能存在公共的利益——只有個人或團體的利益。從上述觀點看,這個概念僅僅作為掩蓋一種內在的政治多元主義分裂的修辭策略時有價值。其他一些人或許認為“公共利益”這一術語的含義并非任何實質性的目標,而是涉及程序問題——所有的利益經由這些程序得以聲調一致,并且反映出競爭性主張的調整或調和。[4]See,e.g.,Sorauf,“The Public Interest Reconsidered”,19 J.POL.616,633(1957).一些人堅持認為認真分析欲求、需求和利益之間的差別要優于把“公共利益”的含義關進牢籠的任何嘗試。[5]See,e.g.,J.PLAMENATZ,MAN AND SOCIETY 311-18(1963).另一些人則認為“公共”不等同于任何數字上的計算,而應被視為一種理想的公民共同體,該共同體要求個人和團體超越于其特殊的、私人關心的事物,適應一種更加“受人支配的”普遍的利益觀念——一種公共的利益觀。[1]See,e.g.,Cassinelli,“The Public Interest in Political Ethics”,in THE PUBLIC INTEREST,NOMOS V45-46(C.Friedrich ed.1962).或許這種普遍觀念的選項會像基于現代道德理論多樣性的道德立場一樣多種多樣。“公共”常常與“共同體”等價——一些人認為“共同體”是比其所有部分的加和更多的東西;[2]See,e.g.,Cairns,“The Community as the Legal Order”,in NOMOS II:COMMUNITY 29(C.Friedrich ed.1959).而另一些人堅持認為“共同體”不過是許多個體之間關系模式中的一種,否認任何賦予該概念自身如“國家”或“主權”概念一樣神秘的的獨立具體人格的嘗試。[3]See,e.g.,J.BENTHAM,ANINTRODUCTIONTOTHEPRINCIPLESOFMORALSAND LEGISLATION 3(Hafner trans.1984).簡言之,“公共利益”的概念包含許多競爭性的,但又經常不一致的觀點。
立法學理論家面對圍繞“公共利益”這一術語的分析及其他復雜問題時責無旁貸。這個術語是律師、法官和立法者專業術語固有的一部分。該概念不僅經常在法庭上為訴諸“公共利益”或“公共政策”的主張以填補模棱兩可的語言所造成的法律空白的法律人所使用,也為立法聽證會上發表正當主張的法律人所使用——它出現在報告里,或者出現在立法程序的辯論中。立法學似乎擔負著特殊的使命,旨在幫助解開一些圍繞該概念的分析和辯護難題,并為關注該概念作為一個關鍵概念有效性的辯論——亦即該概念究竟是一個值得敬畏并值得審慎對待的概念,還是一個應該宣布其最終滅亡的概念——作出貢獻。
C.立法或司法至上的難題:人權領域
已有許多關于政策和原則之間區別的論述,前者一般認為與社會福利、經濟問題相關,而后者與基本個人人權的保護——常與反對多數人權力的過度使用問題相關。[4]See R.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 22-23(1977).這種出于分析問題便利的區分,盡管在應用中模糊不清,已經不由自主地成為憲法秩序下各種關于終局性和至高權威的競爭性主張之間“終極性”歸屬的基本判斷標準。[1]See id.at 131-49.盡管最高法院在本世紀初期持不同想法,[2]See New State Ice Co.v.Liebmann,285 U.S.262(1932)(regulation of entry into business violates liberty of contract);Williams v.Standard Oil Co.,278 U.S.235(1929)(regulation of gasoline prices violates due process);Adkins v.Children's Hospital,261 U.S.525(1923)(regulation of wages violates fifth amendment);Lochner v.New York,198 U.S.45(1905)(regulation of working hours violates liberty of contract).現在人們普遍認為關于社會福利的政策問題主要是立法分支的職責,[3]See Day-Brite Lighting,Inc.v.Missouri,342 U.S.421(1952)(adopting general“hands off”approach to legislative decisions in areas of business,economy and social affairs);Cox,“The Role of 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Society”,50 MARQ.L.REV.575,582-84(1967).而保護個體人權則是司法分支的主要及最終職責。[4]In recent years,the Supreme Court has handled down a number of decisions championing individual rights.See,e.g.,Roe v.Wade,410 U.S.113(1973)(right to privacy);Wisconsin v.Yoder,406 U.S.205 (1972)(right to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Brandenburg v.Ohio,395 U.S.444(1969)(right to free speech);Griswold v.Connecticut,381 U.S.479(1965)(right to privacy).For a discussion of the role of the Court in individual rights controversies,see Wright,Professor Bickel,“The Scholarly Tradition,and the Supreme Court”,84 HARV.L.REV.769,787-89(1971).結果,最高法院近來激進時期的許多行動反映出了一種信念,即司法分支而不是立法分支才是保護基本權利諸原則的最終發言人和守護者。[5]See cases cited supra note 41.
如果司法機關是個體權利的更好守護者這一主張是基于歷史用法,則其證據有些慘淡——以一些如德雷德·斯科特訴桑福德案[6]60 U.S.(19 How.)393(1857)(a slave,as property,cannot claim rights as a“citizen”).和普萊西訴弗格森案[7]163 U.S.537(1896)(“separate but equal”segregated school system was not in violation of equal protection clause).等意義深遠的案件為證,在這些案件中最高法院扮演的是個人權利的征服者。最高法院在美國歷史中的這種起伏不定,令人們對司法程序中存在一些固有特質,使其成為保護基本人權的基本原則之終極奠定者這樣的說法保持警惕。在英國歷史中是議會而不是司法機關塑造了不列顛不成文憲法的基本原則,[8]See L.FRIEDMAN,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17-18(1973).并且也促進了美國憲法下許多基本權利的形成。[9]See generally id.at 42-78.Page 13.對司法角色的歷史性自滿,亦或觸發對即刻關注問題的當下批判之缺失都不應該使人否認立法學自始至終具有確定下述問題的批判任務:(1)如此自滿的行為是否與民主理論一致;(2)這樣的行為是否應該與民主理論一致。如果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而第二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則立法學有提供修正措施的附加任務。
上述問題的復雜性之一與“基本人權”這一概念本身的性質和定位有關。認為可以從憲法語言中發現一些關于這些權利的不連續原則這類過于簡單的想法已讓位于以下現實主義的觀點:(1)只有總體框架的語言是可以被發現的;(2)出于所有實用目的,是個案,而不是框架組成了這些權利的實質內容;(3)個案中的詳細情況是一種創造行動——具有價值選擇——不管這種行動是否被“解釋”的標簽所軟化。人們常常認為“人權”的一般原則包括像言論、出版、宗教自由這類的公民自由,但在過去,最高法院曾毫不猶豫地將財產權視為另一項基本人權,并因此將立法政策限制財產權的舉措視為對財產所有者人權的侵犯。[1]See cases cited supra note 39.相應地,政策和原則的界線取決于觀察者的視角——尤其要緊的是觀察者的權力。當樹立基本“權利”原則成為使得個體免受全體選民干涉,而這些選民經常以外表作出區分,并且可以憑借僅多一人形成的多數即可否決立法機關中占壓倒性多數所表達出的原則時,民主原理中一致性的問題出現了。這個問題并不新穎,它也將繼續存在,立法學理論家們需對其保有一種長遠的看法和一種智識的監測。這是一個標準和評價的問題,而不是一個描述的問題;這個問題要比涉及立法原則表達時的司法節制問題更為深入;它要探求測度這些在民主理論框架內的原則時“終決權”的歸屬問題;它提出關于司法和立法機關各自的相對無過錯份額問題。[2]“We are not final because we are infallible,but we are infallible only because we are final.”Brown v.Allen,344 U.S.443,540(1953)(Jackson,J.,concurring).從前托馬斯·杰斐遜曾在一封答復信中提出一個觀點:“你似乎認為法官才是所有憲法性問題的最終裁決者;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學說,事實上,這是一個將我們置于寡頭暴政之下的學說。”[3]“Letter from Thomas Jefferson to William Jarvis”(Sept.28,1820)in 10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160-61(Ford ed.1897).今天的我們要想像杰斐遜時代一樣思考這個問題則需要從習慣和自滿中實現某種糾正。在考慮“終決權”問題時,如果我們認為“終決權”屬于立法機關,則不僅應強調使得立法機關濫權可能性減到最小的努力。毋寧說,如果有問題的話,那么這個問題要求我們去關注在不犧牲民主原則的情況下,設計出理想的機構來抑制濫權何以可能——不管濫權來自立法機關還是司法機關。
D.立法和判決的統一
許多先前關于立法和判決統一的討論著眼于提示法院檢察不同的不連續規則背后的原則,并使得這些原則潛移默化地影響修改僵化普通法,是否適宜的決定。[1]See Douglas,“State Decisis”,49 COLUM.L.REV.735(1949).Justice Douglas stated:[J]udges have been admonished to hold steadfast to ancient precedents....This search for static security...is misguided.The fact is that security can only be achieved through constant change,through the wise discarding of old ideas that have outlived their usefulness,and through the adapting of others to current facts.There is only an illusion of safety in a Maginot Line.Id.at 735.今日,相關問題的討論更少地關注致力于普通法的法官們的棘手操作,轉而關注將立法在法律權威上與法官造法視為平等或同等的需求,[2]See,e.g.,Horack,supra note 3,at 53-56.更有甚者,關注將前者視為并發且更高級的法律權威的需求。[3]See Katzenbach v.Morgan,384 U.S.641(1966)(upholding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the 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42 U.S.C.§1973b(e)(1976),under section 5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disputed section of the Act in effect overruled the Court's previous holding in Lassiter v.Northampton County Bd.of Elections,360 U.S.45(1959)).See also Cox,“The Role of Congress In Constitutional Determinations”,40 U.CIN.L.REV.199(1971).這樣的關于立法和判決統一的討論也強調像法院已然將司法先例吸納進入司法推理過程一樣——亦即從一系列不連續司法判例中歸納出模式和原則——將立法先例吸納進入司法推理過程之需要。[4]See Horack,supra note 3,at 41-49.See also Cohen,Judicial“Legisputation”and the Dimensions of Legislative Meaning,36 IND.L.J.414,416-19(1961).更高級法律權威的說法為近期立法臂力的施展所印證,立法工作試圖限制上訴司法審查的范圍,[5]See,e.g.,H.R.13915,92d Cong.,2d Sess.(1972)(forbidding court-ordered busing of students);S.4058,90th Cong.,2d Sess.(1968)(limiting jurisdiction in obscenity cases);see generally Eisenberg,“Congressional Authority to Restrict Lower Federal Court Jurisdiction”,83 YALE L.J.498(1974).并以推翻一些制定法[6]See,e.g.,H.J.Res.1035,92d Cong.,2d Sess.(1972)(banning busing of school children);S.J.Res.165,92d Cong.,1st Sess.(1971)(banninb busing of school children).See also supra note 20.和提出憲法修正案的方式徹底改變司法判決的走向。[7]See S.J.Res.110,97th Cong.,1st Sess.(1981)(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to allow states to restrict right to abortion which would,if adopted,negate Roe v.Wade,410 U.S.113(1973)).The twenty-sixth amendment,allowing eighteen year olds to vote in all state elections negated Oregon v.Mitchell,400 U.S.112(1970).當在訴訟中遇到特定的解釋問題或者是合憲性問題時,從一系列不連續立法法案中吸納模式和原則的任務主要歸屬于法院。除了立法學理論家們達成共識的上述統一過程是一項不間斷的任務這一事實,將司法吸納原則的方式與從立法角度進行原則吸納的工作進行對比也是非常有趣并且十分有價值的。
E.批判的難題
立法可根據以下標準進行評價:(1)是否有效地實現了其公布的目的或一些目的,(2)是否與總體立法政策中的其他表述一致,(3)是否在道德上是正當的。第一種技術評價類型,包含了一種對寬泛和不同層面上的社會工程效率的評估。除了那些有意為之的結果,缺乏適當研究的后果常常是破壞了立法的目的——例如,為窮人設計的租金控制不知不覺釀成了財產權狀況惡化和形成永久性貧民窟的苦果;旨在幫助農民的補助金不知不覺間助長了公司制農場的投機行為,亦導致了農民數量的減少。一項關于立法機構是否應該管控麻醉品的生產和銷售、街頭犯罪或重犯問題的決定若想獲得豐厚的成果且效果顯著,其中則包含大量的經驗研究資源并且需要特別訓練的技能。立法學的一個主要難題是如何獲得并利用必要的資源和能力來進行上述評價任務。很多批判研究都推動了對多數慣常立法態度進行的反思——關于死刑影響[1]See,e.g.,THE DEATH PENALTY IN AMERICA(H.Bedau ed.1964);Ehrlich&Gibbons,“O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Deterrent Effect of Capital Punishment and the Theory of Deterrence”,6 J.LEGAL STUD.35(1977);Forst,“The Deterrent Effect of Capital Punishment:A Cross-State Analysis of the 1960's”,61 MINN.L.REV.743(1977).或關于作為疾病的酗酒行為的研究即為例證。[2]See,e.g.,Blinder&Kornblum,“The Alocholic Driver:A proposal for Treatment as an Alternative to Punishment”,56 JUDICATURE 24(1972);Committee on Problems Relating to Persons Under Disability and Their Property,“Alcoholics and the Mentally Ill:Their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De-Institutionalization”,7 REAL PROP,PROB.&TR.J.532(1972).若使得立法工程的效率最大化還需要完成大量計劃性的工作。令人難以捉摸的制裁效力問題即排在需要批判研究的問題列表前端。
對立法政策不一致問題的批判研究工作是為了維護一種人類事物的理性秩序。不一致是具有破壞性的,不一致產生不確定并且經常導致不正義主張和對法律不尊重行為的出現。法令統一的司法原則并不總能對出現的缺陷和不和諧產生的結果作出適當的調整。這個問題體現在恩斯特·弗羅因德在20世紀初寫就的關于立法的經典著作之中,以下是書中的例子:
當立法使得妻子成為她自己財產或收入的主人時,應該同時規定她有供養住戶和家庭的相關義務。這些內容已經寫進了《德國民法典》,但沒有寫進美國或英國關于已婚婦女的法案之中。因而我們便見到了一位富有的妻子基于無力供養家庭的理由與一位貧窮的丈夫離婚這樣的咄咄怪事。[1]E.FREUND,STANDARDS OF AMERICAN LEGISLATION 228(1917).
問題顯然持續存在,而且它是立法程序本質和固有復雜性的體現。一般的立法者及其立法班子鮮有時間或意愿翻閱法規書籍中不相干的內容以便認識政策和原則的更大格局,進而來判斷一個不連續的提案是否適合這一格局亦或這個提案成為導致不一致出現的不和諧音符。立法委員會的成員偶爾會在提案聽證會后準備提供更長遠考慮的報告,[2]See,e.g.,S.REP.NO.167,95th Cong.,2d Sess.,reprinted in 1978 U.S.CODE CONG.&AD.NEWS 557(committee report on child abuse prevention);S.REP.NO.493,95th Cong.,2d Sess.,reprinted in 1978 U.S.CODE CONG.&AD.NEWS 504(committee report on age discrimination).但這樣的情形屈指可數。由更為超脫的批判者進行必要的調查和批判工作就顯得格外必要。法律評論中的許多內容都專注于審查司法判決中的不一致或從不同的司法宣判中反映出的長期格局;法學雜志也能將類似的精力投入立法主題之中,而不是偶爾或從外圍處理立法本身的問題。[3]The Harvard Journal on Legislation is a rare exception to the prevailing practice at law schools.
立法學與司法法理學都面臨程序、原則及作為法律秩序產物的實質政策的道德性問題。對于立法學而言,道德批判直指法律秩序中的立法成分。首先,區分傳統道德(正面的)和批判道德十分重要。以傳統道德實踐違反理想原則——據支持者認為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并且經過理性討論最終將為暫時懷疑者接受的原則——為標準,傳統道德本身可能就是批判的對象。因而,舉例來說,我們可以用兩個道德標準批判基于種族、膚色或宗教教義確立二等公民身份的立法:(1)因為它與美國的(傳統的)道德原則存在差異;或者(2)因為它與據信是理性人普遍看重的原則——不考慮被任一特定法律秩序所采納的事實——存在差異。一些立法實踐背后的基本原則——如,法無明文者不罰;除非由公有的善進行評判則不能實施法律強制措施——經常被認為是不僅包含了美國的道德信條,也包括了據信可以為全人類普遍接受的原則。
朗·富勒提出了八項程序要求,借以將有法律效力的法令與歹徒或膺主的命令區別開來,[1]These relate to generality,publication,retroactivity,understandability,contradiction,possibility of conformity,abruptness of change,and coherence between rules and their administration.See L.FULLER,THE MORALITY OF LAW 38-39(1964).他的做法為評價立法的形式要素之規則表達開了個好頭。這些如明晰性、公開性,或預期可操作性的程序要求不僅是法令法律效力的最低條件,也是區別于目的的方法之道德性的表達。不管影響道德目的或需求的原則如何多種多樣,這些理論在關于達成這些目的或需求之程序性方法的道德性問題上存在更為寬泛的一致。
基于道德標準對立法提案和法令實質內容進行的批判需要涉足茂密且爭議不斷的倫理學理論叢林。許多關于特殊問題的道德判斷集中于一點,即便它們來自不同的理論前提——康德主義[2]See I.KANT,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T.Abbott trans.6th ed.1909).、功利主義[3]See J.BENTHAM,supra note 36;J.MILL,ON LIBERTY(1859).、羅爾斯主義[4]See J.RAWLS,A THEORY OF JUSTICE(1971).、自然法[5]See A.P.D'ENTREVES,NATURAL LAW(1951).等等。當它們不集中于一點時,立法學的難題即是倫理學理論的難題:例如,在尋求道德停泊處的過程中,如何從許多不同的關于客觀性(這個術語有許多不同的含義)的主張里獲得有說服力的認識;如果有區別的話,如何區別道德原則的“發現”與勸導和告誡行為;如何從世俗并經常是科學的偽裝下辨識出道德“解救”;倫理學理論是否如類似科學理論一樣是可證偽或證明為真的。當前三個關于實質立法及其相關倫理學理論的問題成為討論的焦點:(1)政府在私人道德領域立法的程度——該問題涉及密爾的理論[6]See J.MILL,supra note 64.、德夫林的理論[7]See P.DEVLIN,THE ENFORCEMENT OF MORALS(1965).、哈特的理論[8]See H.HART,LAW,LIBERTY AND MORALITY(1963).及其他;(2)功利最大化屈從于正義需求的程度——該問題涉及康德[9]See I.KANT,supra note 63.、邊沁[10]See J.BENTHAM,supra note 36.、羅爾斯[11]See J.RAWLS,supra note 65.等人的理論;(3)道德過失責任的缺失是否在任何情形中均可免除法律責任——該問題涉及過失、因果、決定論和自由等復雜而矛盾的概念。這些問題為當下關于實質立法議案的討論設定了具體現實。第一個問題涉及管控色情物品、墮胎及同性戀的立法問題。第二個問題涉及機會平等問題,一些人認為弱勢群體需求和關注弱勢群體屬于道德權利范疇,而另一些人認為這個問題不過是與實現功利最大化相關的因變量。最后,第三個問題涉及犯罪意圖是否缺失,例如,是否應該免除精神錯亂或患有其他精神疾病者的法律責任問題;如果免除,則達至何種程度;對防控反社會行為(例如,使用罪行防范措施)的迫切需求是否可以讓我們盡量減少或完全無視過失犯罪的主張。在非實質性的方面中,一個重中之重而又經常發生的問題即是,選舉立法者及確立立法政策和原則的程序在多大程度上偏離了民主理想背后的平等公平道德原則。這一問題具體體現在近期對于私人利益群體利用增殖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方式繞開對于競選者開支的經濟限制,進而扭曲了政治參與民主程序這一做法的批判之中。[1]See Etzioni,“Congress P.A.C.'d”,N.Y.Times,Nov.23,1982,at A29,col.2.
若立法學不至在這些基本的立法問題上畏首畏尾,則其不能對批判和評價工作背后的倫理學理論視若無睹。這些理論是立法學批判和評價工作的必備工具。離開了它們,立法學將被有正當理由地視為一門隨波逐流的學科——失卻了停泊處或基石。
IV.結論
本文提出的立法學日程是啟發性的,而且該日程遠非完善。其他難題或許在別的觀察者眼中更加突出。超越可能由這份日程激起或喚醒的熱情,要完成日程內容并不僅僅是在法學院的課程表里加一門課的問題這么簡單。需要做得更多,這其中不僅包括法官和律師關注立法決策程序時觀念的徹底改變,還包括讓法學院在行使專業和批判職能處理法律秩序問題時采取一個更為寬廣的視角,而不光是司法導向的視角。
(初審:劉誠)
[1]作者尤里烏斯·科恩,男,羅格斯大學法學院榮休法學教授,西加利福尼亞法學院特聘訪問法學教授,研究領域為法理學、立法學。譯者孫競超,女,中山大學法學院法學理論專業在讀研究生。本譯稿原文出版信息為Julius Cohen,LEGISPRUDENCE:PROBLEMS AND AGENDA,11 Hofstra L.Rev.1163(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