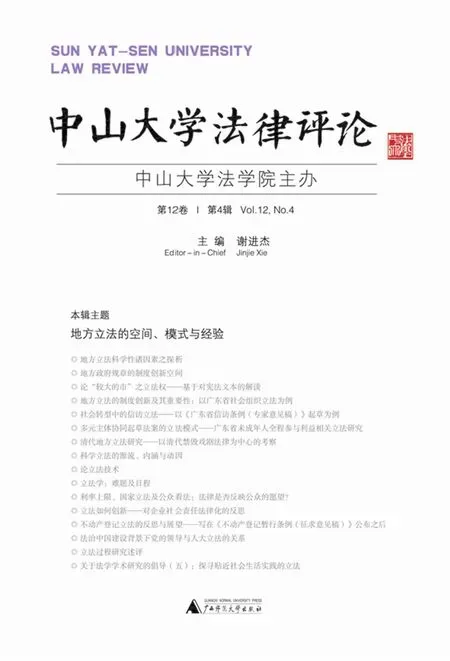地方政府規章的制度創新空間
劉文靜
地方政府規章的制度創新空間
劉文靜[1]
地方政府規章本不具有制度創新的法定權限,在目前立法體制中卻最具創新動力和條件,實踐中也最為活躍。本文基于地方政府規章制度創新的現狀,分析其創新的客觀條件與主觀動因,以及創新性規章的實施效果和面臨的法律困境;主張肯定地方政府規章對制度創新的積極作用,同時通過推廣規章制定過程中的公眾參與、強化權力機關對規章的備案審查制度和法院的監督作用,讓地方政府規章在有序和有效的監督下實現制度創新的法治化。
地方政府;規章;制度創新;監督
一、問題的提出:地方政府規章有沒有制度創新的空間?
地方政府行使立法權,是行政權與立法權的交叉:一方面,可以說是行政機關在一定程度上被賦予了立法權;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行政活動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被賦予了“法”的效力。地方政府通過制定規章的形式實現制度創新,實際上是中央和地方之間、立法權和行政權之間雙重緊張的結果。
從立法活動自身的規律來看,法原本是各方利益沖突與妥協的產物:沖突是立法活動的內在動力或者說必要性,妥協是立法活動的最終結果。在理想狀態下,制度創新和立法之間存在著一個悖論:一切制度創新在成為“法”之前,都是“違法”的;而一旦成為“法”,就不再具有“創新”的意義。因此,立法上的制度創新,并非相對于同一立法主體以前所立之法而言(同級別的新法與舊法不一致的,新法的生效應當以舊法的廢止為前提),而一定是相對于以下兩種情況而言:一是上位法,二是同一層級不同立法主體所立之法。只有一部新法與上述二者不一致時,才能體現立法中的制度創新。就我國目前的地方立法而言,制度創新的直接表現無非是:第一,突破了上位法的規定;第二,在同一層級的其他立法中“脫穎而出”。由于“脫穎而出”本身需要對上位法的突破,它的“創新性”是派生的和相對的,基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討論第一種情況。
地方立法(包括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地方性法規的權力和地方政府制定規章的權力)對上位法的突破,可能出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調整事項上整體突破上位法關于地方立法權限的規定,即該項立法本來應當制定上位法;二是整體權限沒大問題,但具體規定與上位法不一致。
我國地方政府行使立法權的依據是《立法法》第七十三條。[1]《立法法》第七十三條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方性法規,制定規章。”地方政府規章可以就下列事項作出規定:(一)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規定需要制定規章的事項;(二)屬于本行政區域的具體行政管理事項。”根據
這條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和較大的市[1]根據《立法法》第六十三條第四款的規定,較大的市“是指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目前國務院一共批準了18個城市為“較大的市”,它們分別是:1984年批準的12個(原為13個:唐山、大同、包頭、大連、鞍山、撫順、吉林、齊齊哈爾、青島、無錫、淮南、洛陽、重慶。重慶升為直轄市后應當行使直轄市政府的立法權,不再屬于“較大的市”),1988年批準的1個(寧波),1992年批準的3個(邯鄲、本溪、淄博),和1993年批準的2個(蘇州、徐州)。人民政府被賦予了制定地方政府規章的權力,地方政府規章成為我國法源的一部分,盡管屬于最低層級的“法”。地方政府規章的制定權限受到兩個限制:一是要有上位法依據,即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或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2]《立法法》第七十三條第一款。二是要在法定調整事項范圍內。《立法法》第七十三條第二款關于地方政府規章調整事項(立法權限),列舉了兩類:一是“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規定需要制定規章的事項”;二是“屬于本行政區域的具體行政管理事項”。這兩項規定,究竟應當同時適用,還是只要符合其中一項即可?法理的分析似乎并無太多爭議的空間。在我國的憲法框架下,無論是從行政機關作為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來看,還是從地方政府作為中央人民政府的下級政府來看,地方政府規章都需要上位法的依據;兼之對比《立法法》第六十四條第二款對地方性法規的“創制性立法權”或者“自主性立法權”的規定,[3]《立法法》第六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第二款規定“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據此,地方性法規可以在沒有上位法直接依據的情況下,根據地方需要進行“先行先試”的立法,即學術界所說的“創制性立法”或者“自主性立法”,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后施行。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報請批準的地方性法規,應當對其合法性進行審查,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不抵觸的,應當在四個月內予以批準。地方政府顯然沒有獲得此類權力。結論是,地方政府規章在法律上沒有創制性立法權,只能作執行性立法。然而,事實又是如何呢?
二、實踐中的地方政府規章創新
(一)地方政府規章事實上的“創制性”
2000年7月1日《立法法》實施之前,地方政府規章所調整的事項范圍可謂無所不包,其中不乏涉及公民法人基本權利義務、民事基本制度、訴訟和仲裁制度的規定;[1]例如國務院1982年5月12日頒布《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后,許多地方都據此制定地方立法,其中至少有海南、云南、北京、長沙、哈爾濱、蘇州、汕頭、南京等省、直轄市和較大的市制定了關于收容遣送的地方政府規章。這些政府規章都涉及公民基本權利(人身權)。2003年6月18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國務院自行撤消后,上述地方政府規章(以及類似內容的規范性文件)均已被廢止。詳見北大法律信息網,網址:http://www.pkulaw.cn/cluster-call-form.aspx? menu-item=law&EncodingName=&key-word=%B9%E3%B6%AB%CA%A1%BC%AF%BB%E1% D3%CE%D0%D0%CA%BE%CD%FE%B9%E6%B6%A8&range=0,訪問時間:2014年6月2日。更有甚者,上述事項在一些政府或者政府部門頒布的規范性文件,甚至民間組織的文件中也曾有過規定。[2]例如山東省政府、黑龍江省政府、烏魯木齊市政府辦公廳、上海市公安局等單位曾頒布過關于收容遣送的相關規范性文件(2003年以后均已廢止);又如1987年《福建省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條例》(福建省人大常委會頒布,1990年曾作出修改,1994年根據《福建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辦法〉》廢止)實施后,福建省消費者協會甚至根據這部地方性法規制定了《福建省消費者委員會小額投訴仲裁辦法》,對仲裁制度作具體規定。《福建省消費者委員會小額投訴仲裁辦法》原文可在http://www.110.com/fagui/law-268610.html獲得,訪問時間:2014年6月2日。這些規定在《立法法》生效后基本上都被修改或者廢止了。《立法法》實施后,《廣州市政府信息公開規定》(廣州市政府規章,2003年1月1日實施)和《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湖南省政府規章,2008年10月1日實施),作為頗具轟動效應的兩部行政程序方面的地方政府規章,其所調整的事項是否屬于《立法法》第八條所列舉的應當制定法律的事項之外,就很值得關注了。
僅從字面上看,行政程序制度并未被明確列舉在《立法法》第八條中——該條和行政法方面的立法有關的,僅僅是第(二)項中關于“人民政府的產生、組織和職權”的規定,以及第(八)項中列出的“財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而行政程序顯然不屬于上述兩項中的任何一項。剩下的就只有第(十)項的“兜底”陳述了——“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此類事項的范圍有多大,其裁量權在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就統一行政程序的立法而言,全國人大常委
會既然曾將其列入立法規劃,就是用實際行動說明此類事項應當制定法律。[1]2003年,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將《行政程序法》列入立法計劃第二類“研究起草、成熟時安排審議的法律草案”;2004年11月,全國人大法工委專門組織會議討論《行政程序法(試擬稿)》。就在各方以為《行政程序法》即將進入正式立法程序時,2008年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卻將《行政程序法》從立法計劃中刪除了。全國人大有關負責人公開對媒體表示,此后《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工作處于停滯狀態。參見申欣旺《行政程序法難產25年背后:權力不愿自縛手腳》,登載于中國新聞網,2010年5月14日報道,網址: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10/05-14/2283088.shtml,訪問時間:2014年5月18日。從法理上看,行政程序屬于國家基本行政制度,當然應當制定法律;而立法實踐卻表明,對本應制定法律的行政程序制度和作為行政程序重要組成部分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地方政府規章不僅大行其道,而且這種突破立法權限的制度創新,事實上也得到了認可。從2003年《廣州市政府信息公開規定》實施后到2007年4月國務院頒布《政府信息公開條例》(2008年5月1日實施)前,全國有二十多個省、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紛紛就信息政府信息公開進行地方立法,除了大同市制定的是地方性法規[2]《大同市政務信息公開條例》由大同市人大常委會制定,2004年8月1日實施。,其余相關立法都是由地方政府制定的規章。[3]參見劉文靜等著《WTO透明度原則與我國行政公開制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40—41頁。而《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頒布并實施后,先后又有汕頭市、山東省、西安市和海口市等地用地方政府規章的形式規范本地的行政程序制度。[4]以頒布和生效的時間為序,這些以“行政程序規定”為名稱的地方政府規章分別是:《汕頭市行政程序規定》(汕頭市政府,2011年4月17日頒布,同年5月1日實施);《山東省行政程序規定》(山東省政府,2011年6月22日頒布,次年1月1日實施);《西安市行政程序規定》(西安市政府,2013年3月25日頒布,同年5月1日實施);《海口市行政程序規定》(2013年6月7日頒布,同年8月1日實施)。詳見北大法律信息網,網址:http://www.pkulaw.cn/cluster-call-form.aspx?menu-item= law&EncodingName=&key-word=%B9%E3%B6%AB%CA%A1%BC%AF%BB%E1%D3%CE%D0% D0%CA%BE%CD%FE%B9%E6%B6%A8&range=0,訪問時間:2014年6月2日。從政府信息公開立法的經驗看,有理由推斷,在國家層面的《行政程序法》未能進入正式立法程序之前,此類地方立法很有可能會持續下去,更多的關于行政程序一般規定的地方政府規章仍有可能出現。[5]也有部分地方正在醞釀以地方性法規的形式規定本地的行政程序制度,例如北京市人大常委會正在制定《北京市行政程序條例》。見“法治政府網”2014年6月1日報道:《〈北京市行政程序條例〉立法研討會在北京順利召開》,網址:http://law.china.cn/features/2014-06/01/content-6949721.htm,訪問時間:2014年6月2日。
(二)“執行性”地方政府規章的創新
在地方政府規章層面上,為執行上位法而制定的規章(即學術界所稱之“執行性立法”)中,對其所執行、本應嚴格遵守的上位法的突破,也是司空見慣。為實施《廣告法》(主要是第三十二、三十三條關于戶外廣告的規定)而進行的地方立法,是一個由一系列相關地方政府規章共同組成的非常典型的案例。
《廣告法》(1994)對戶外廣告的設置和管理的規定非常簡略,僅僅規定了不得設置戶外廣告的五類情形(第三十二條),但明確授權“戶外廣告的設置和規劃和管理辦法,由當地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組織廣告監督管理、城市建設、環境保護、公安等有關部門制定”(第三十三條)。[1]這一授權其實是對1987年12月1日起實施的《廣告管理條例》(國務院1987年10月26日發布)第十三條的重申。《廣告法》于1995年2月1日起實施。截至本文完成之日(2014年6月3日),生效時間比《廣告法》早7年多的《廣告管理條例》仍然有效。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雖然頒布了《戶外廣告登記管理規定》(1995年頒布,1998年曾修訂,2006年修改后于當年7月1日實施),但國務院部門規章并不能限制地方政府根據《廣告法》制定相關管理辦法。[2]按照《立法法》第七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地方政府規章的制定依據是“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方性法規”,不包括部門規章;同時,第八十二條又明確規定了“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之間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權限范圍內施行”。2000年以來,各地紛紛修改或者重新立法,對戶外廣告管理事項進行規制,[3]截至本文完成之日(2014年6月3日),目前有效的有關戶外廣告管理的地方政府規章有108部。統計數據來自北大法律信息網,網址:http://www.pkulaw.cn/cluster-call-form.aspx?menu-item= law&EncodingName=&key-word=%BB%A7%CD%E2%B9%E3%B8%E6&range=0,最后訪問時間: 2014年6月2日,20時30分。其中很多規章都涉及戶外廣告位置使用權有償出讓的規定。2002年3月1日實施的《蘇州市市區戶外廣告管理辦法》(蘇州市政府2002年2月5日頒布)第九條規定“市區范圍戶外廣告設施(陣地)的使用權以有償方式取得,由政府通過指定的單位采取拍賣、招標等合法方式公開競爭取得。單位或個人利用自由建(構)筑物設置戶外商業廣告設施的,依本辦法出讓”,很可能是首開政府介入戶外廣告位置有償出讓之先河。三個月后生效的《太原市戶外廣告陣地有償使用管理暫行辦法》(太原市政府頒布,2002年6月1日生效)規定,除店堂牌匾廣告和軟體廣告、公益廣告的位置使用權可以采取協議出讓的方式外,其余幾乎所有戶外廣告位置的使用權(即“戶外廣告陣地”)都納入了招標、拍賣范圍(第四條),由市政府委托市規劃局統一進行招標或者拍賣(第十一條,第十四條)。隨后,《珠海市戶外廣告設置管理規定》(珠海市政府頒布,2003年9月1日生效,已廢止)明確規定“戶外商業廣告設置使用權實行有償使用原則”(第七條),“經規劃批準的戶外商業廣告設置使用權實行公開招標、拍賣、掛牌交易”(第十一條第一款)。[1]2004年7月8日實施的珠海市人民政府《廢止〈珠海市戶外廣告設置管理規定〉》以“為了貫徹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為由廢止了《珠海市戶外廣告設置管理規定》。2005年6月1日,珠海市人大常委會制定的《珠海市戶外廣告設施設置管理條例》實施,其中關于戶外廣告位置有償出讓的制度繼續實施,但對公共場地和非公共場地的“戶外商業廣告設施設置權”作了區別處理:“公共場地的戶外商業廣告設施設置權出讓依法實行公開招標、拍賣、公開競價、掛牌等方式公開交易”(第十五條),“經申請批準的非公共場地的戶外商業廣告設施,其設置權可由該場地的產權人自行行使或者協議出讓,但應當按照同一區域戶外商業廣告設置和使用權平均出讓價格的百分之三十向市政府繳納空間資源利用費”(第二十條)。《北京市戶外廣告設置管理辦法》(北京市政府頒布,2004年10月1日生效)規定對設置在公共場所的戶外廣告設施的使用權出讓實行特許經營制度,可以采取招標方式或者拍賣方式(第二十一條)。《上海市戶外廣告設施管理辦法》(上海市人民政府2004年12月發布,次年4月1日施行)則規定“利用公共陣地設置戶外廣告設施的,陣地使用權應當通過拍賣、招標的方式取得。利用非公共陣地設置戶外廣告設施的,陣地使用權應當可以拍賣、招標的方式取得”(第八條第一款、第二款),由市市容環衛局或者區、縣市容環衛局進行拍賣、招標(第九條);值得關注的是,6年后該規章進行了修改,但上述規定幾乎完全保留下來了。[2]修改后的《上海市戶外廣告設施管理辦法》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12月30日公布,2011年1月7日施行。其中第十二條規定:“利用公共陣地設置戶外廣告設施的,陣地使用權應當通過拍賣、招標的方式取得。利用非公共陣地設置戶外廣告設施的,陣地使用權可以通過協議、拍賣、招標等方式取得。公共陣地的范圍由市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會同市規劃行政管理部門提出方案,報市人民政府批準后執行。公共陣地使用權拍賣、招標的具體辦法,由市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會同其他有關行政管理部門制定。”
三、地方政府規章制度創新的客觀條件與主觀動因
如前所述,地方政府規章的創制性立法權在法理分析上并不占優勢,實踐中的例證卻俯拾皆是。背后的原因可以從客觀條件和主觀動因兩方面進行分析。其中,客觀原因是立法體制所提供的;就制度創新問題而言,主觀動因更值得關注。
(一)客觀條件
立法程序的便利是地方政府通過制定規章的形式實現創新的客觀條件。由于地方政府規章的制定程序比地方性法規的制定程序要便捷、迅速,[1]“地方政府規章應當經政府常務會議或者全體會議決定”(《立法法》第七十五條第二款),實踐中絕大多數地方政府規章是經政府常務會議討論通過的。這個程序比起需要經過地方人大主席團或者地方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地方性法規的制定程序(《立法法》第六十八、六十九條)而言,要簡單便捷很多。特別是對于較大的市而言,由于其制定的政府規章不需要經過批準程序,導致創制性立法在規章層面上比在地方性法規層面上更容易通過,客觀上對市一級的行政立法創新起到了極大的鼓勵作用——《立法法》所設定的規章備案程序(第八十九條第四項)畢竟要比較大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的審查批準程序(第六十三條第二款)寬松得多:省級人大常委會在審查市級地方性法規時作出修改是很正常的事(事實上考慮到審查批準程序的制約,市級地方性法規在制定過程中的自我審查、自我約束自然都要嚴格很多);而在規章制定方面,迄今尚未見任何規章被有權的審查機關撤銷的公開案例。在省、市兩級地方立法上,地方政府規章對立法權限的突破其實更具有客觀便利性。
(二)主觀動因
考察《立法法》實施以來地方政府規章在制度創新方面的實踐,特別是結合前文對地方政府規章在創制性(例如信息公開和行政程序立法)和執行性(例如戶外廣告位置管理的立法)這兩個方面事實上均有創新的分析,可以看到,地方政府規章的制度創新實際上會受到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一是規章所調整事項在我國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二是創新性制度與地方事務關系的密切程度;三是該政府或者該部門在執行新制度中的利益;四是制度創新的前期準備程度。以下分述之。
1.規章所調整事項在我國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
行政程序(包括政府信息公開制度)通過地方政府規章來規范,本來是超越了地方政府規章的制定權限(甚至也超越了地方權力機關的立法權限),卻得到中央政府的肯定和鼓勵,這并不能簡單地從現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立法權限中找到答案。真正的原因是:首先,這些被“越權立法”的事項,不僅順應了法律體系自身發展的規律,而且更重要的是,符合中央政策文件的精神;[1]時任廣州市政府法制辦公室主任李力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時直言,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公開透明”作為一個原則被提出來,再加上我們建立法治國家,依法行政、防止腐敗的要求,信息公開問題越來越迫切;《廣州市政府信息公開規定》制定的直接動因就是為了落實中央下達的政務公開文件。見段文《政府信息公開法保障公民知情權》,載《21世紀經濟報道》2003年03月18日,轉引自網易財經頻道財經首頁,網址:http://money.163.com/editor/030318/030318-131971.html,訪問時間:2014年9月17日。其次,在一個仍在不斷健全的法律體系中,本來需要通過中央立法來調整的新事項,小范圍內的地方試驗卻往往可以獲得較高的性價比——“先行先試”的地方立法不僅為隨后的中央立法積累了寶貴經驗,而且,就行政程序這一特殊領域而言,地方政府對他們自己制定的規章無疑有更大的執行動力,特別是那些限制行政機關權力的規章;[2]《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頒布和實施前后,湖南省政府采取了動員、宣傳、培訓等措施,推動該規章的實施;并在政務公開、行政審批和收費、規范性文件清理、行政效能提升、相關配套制度和加強行政機關等方面著重深入貫徹該規章。參見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制定實施評估報告》(2009年8月4日),網址:http://www.hnsfzb.gov.cn/Item/3325.aspx,訪問時間:2014年3月21日。不論實施效果如何,規章制定本身就是對相關制度最好的普法宣傳,更不用說一個地方的“先行先試”所引發的連鎖效應。
2.創新性制度與地方事務關系的密切程度
通過地方立法而確立的新制度,與地方事務關系越密切,地方政府或其相關部門的執行動力就越大。前文討論過的“戶外廣告位置使用權”的立法,就是與地方事務密切相關的一類典型范例。這里的“地方事務”,應當從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上理解,而不是狹義地理解為“本地方事務”或者“地方特色”的事務。戶外廣告管理,其實是廣告和規劃兩個領域的綜合性行政管理。由于一般情況下的規劃管理與行政區劃有直接關系,是典型的地方事務;而廣告管理又是需要當地主管部門直接執行的具體事務,地方政府選擇這個領域進行制度創新,有比較便利的客觀條件。
3.政府及其部門的利益
從對政府的“經濟人”假設出發,政府制度創新的利益驅動不容忽視。以“戶外廣告位置使用權”的地方立法為例,從前文所述幾個地方的相關政府規章情況來看,各地“不約而同”地在戶外廣告位置使用權出讓方面展開了創新,而且創新的內容和方式非常接近(只有西安的有比較明顯的不同),就是通過創設一個“戶外廣告位置使用權”或者“陣地使用權”的概念,規定這項“權”由政府統一分配,市場主體有償取得。前文引述的地方政府規章的條文,不僅創設了一項行政許可,而且規定了這類行政許可的有償取得制度(本質上是設定了政府可以從中獲利,盡管獲利的方式和比例各異),這與《行政許可法》明確規定的行政許可只能由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設定,國務院規定(即規范性文件)和省級政府規章僅可設置臨時性行政許可的規定直接相沖突;[1]見《行政許可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該法第十七條還規定:“除本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規定的外,其他規范性文件一律不得設定行政許可。”更重要的是,政府從有償許可中所獲得的利益,與戶外廣告位置所依托的建筑物、構筑物或者其他設施的所有權人和使用權人的利益密切相關——戶外廣告位置使用權的有償出讓,規定了處分公民、法人自由簽訂合同和利用私人物業收益的民事權利。上述內容,不僅在法理上遠遠超出了《廣告法》第三十三條授權地方政府制定戶外廣告的“設置規劃和管理”辦法的范圍,違背了《立法法》第八條第(七)項民事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的精神,而且與《合同法》第四條“當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訂立合同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所確立的意思自治原則。[2]據筆者查證,2004年《行政許可法》實施前頒布的有關戶外廣告位置管理的地方立法中,只有西安市采用了地方性法規的立法形式(《西安市戶外廣告設置管理條例》(西安市人大常委會2000年制定,2004年修改)。西安市的這部地方性法規在創設行政許可事項方面是合乎立法權限的;并且,它在我國的相關地方立法中,首次對公共場所、市政公用設施的戶外廣告設置與其他場所的戶外廣告設置作了區分處理:對前者,規定了通過招標、拍賣或者協議(投標人、競買人不足三人時)的出讓方式;對后者,則要求戶外廣告經營者與建筑物、構筑物所有權人或者場所土地使用權人簽訂租賃合同,并向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在繳納戶外廣告設置空間使用費后,取得戶外廣告設置權(第九條)。這種作法被后來的《珠海市戶外廣告設置管理條例》(2005)所借鑒。2004年7月1日《行政許可法》生效前后,除少數地方對相關地方政府規章采取了修改或者廢止的處理方式外,[3]如前文注釋中提到的2005年6月1日生效的《珠海市戶外廣告設置管理條例》(珠海市人大常委會制定)取代了《珠海市戶外廣告設置管理規定》,但關于戶外商業廣告有償出讓的基本原則和方式均保留了下來,只是主管部門從建設行政管理部門換成了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門(第十四—十七條)。相當數量的此類規章至今仍然有效。
4.前期準備
制度創新的前期準備程度也直接影響執法機關的實施動力。如果一項創新制度在通過地方立法被確立起來之前,有大量的前期創新作基礎性鋪墊,則新制度的實施將水到渠成,無論是動力還是順暢程度都會比較好。漸進式的改革通常具有這樣的優點。《深圳市公用事業特許經營辦法》(深圳市政府2003年3月21日發布,同年5月1日施行)的實施就有一定的代表性。[1]建設部《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2004年5月1日才生效,比《深圳市公用事業特許經營辦法》(2003年5月1日生效)整整晚了一年。又,深圳市人大常委會頒布的《深圳市公用事業特許經營條例》于2006年3月1日生效。這部規章制定之前,深圳市已經在水資源開發、排水網管、污水處理、燃氣網管、固體廢物處理、生活垃圾處理、醫療垃圾處理、公共大巴經營等公用事業的具體事項上陸續進行特許經營的嘗試,并頒布了一系列相關規定。《深圳市公用事業特許經營辦法》實際上是在總結前期經驗基礎上的一個公用事業特許經營方面的“集中立法”。由于整個過程都是在政府相關部門推動下進行,新法的實施在當時就迅速見效。[2]參見俞可平主編《中國地方政府創新案例研究報告(2003—2004)》,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9—35頁。
(三)主觀動因與客觀條件的綜合作用
規章所調整事項在我國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創新性制度與地方事務的密切程度,政府利益和前期準備,這四個因素對于地方立法實施動力的影響,再加上現行立法體系提供的客觀條件,這些因素對地方政府規章制度創新的影響,應當進行綜合的考慮評估。當某一方面的因素影響力比較強的時候,也會對創新性地方立法的實施動力形成主導性影響。在整個調整事項上完全突破地方政府規章立法權限的政府信息公開和行政程序立法,是最典型的例子。政府信息公開屬于行政程序立法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們不僅不屬于地方事務,而且對廣大的行政機關來講,是一部“限權”的法,只會為行政機關增加義務而不會增設權力的法,由地方政府來立法,本來不具有“先天的”動力。但是相關立法的大趨勢和全國性立法的暫時缺位,不僅為地方政府規章提供了制度創新的空間,更是地方政府創造業績,特別是在全國范圍內制造影響的絕佳機會。[1]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領銜起草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2008)和廣州市政府法制辦領銜起草的《廣州市政府信息公開規定》(2003)項目均獲得首屆“中國法治政府獎”,見財新網報道(記者葉逗逗)《首屆“中國法治政府獎”出爐》,網址:http://china.caixin.com/2011-01-17/100217525.html,最后訪問時間:2014年6月2日,19時19分。“中國法治政府獎”雖然是由中國政法大學發起的民間獎勵,但對于政府業績的宣傳有不可忽視的功效。
《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2008)或許是一個很難復制的特例,卻很好地體現了地方政府規章制度創新的主觀動因和客觀條件的綜合作用。以我國學術界為主要力量,制定統一行政程序法的呼聲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持續至今。學者們紛紛建言獻策。層出不窮的專著、論文自不必說,僅《行政程序法》的專家建議稿也紛至沓來。2000年前后,北京大學姜明安教授執筆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程序法(試擬稿)》[2]姜明安:《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程序法(試擬稿)》,登載于北大法律信息網,網址:http://vip.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gid=335570530&db=art,訪問時間:2014年6月2日。、時任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長江必新主持起草的《重慶市行政程序暫行條例(試擬稿)》[3]江必新主持起草的《重慶市行政程序暫行條例(試擬稿)》全文及相關說明,見江必新、鄭傳坤、王學輝《先地方后中央:中國行政程序立法的一種思路——兼論〈重慶市行政程序暫行條例〉(試擬稿)的問題》,《現代法學》第25卷第2期,2003年4月,第151—163頁。、中國政法大學馬懷德教授主持起草的《行政程序法(草案建議稿)》[4]參見馬懷德主編《行政程序立法研究——〈行政程序法〉草案建議稿及理由說明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先后亮相,引起學術界和實務界的熱烈討論。當全國人大《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程序停滯后,在具有法學博士學位的時任湖南省省長周強的親自過問下,曾經主持起草過《行政程序法》試擬稿、專家建議稿的知名學者和實務界人士均被邀請參加《湖南省行政程序》的起草和論證工作。[5]參見申欣旺、白祖偕《〈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出臺獲中央肯定》,中國新聞網2010年5月14日報道,網址: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10/05-14/2283077.shtml,訪問時間:2014年6月2日。雖然地方政府官員特別強調這部地方政府規章的“湖南本土化意義的創新”,[6]參見申欣旺、白祖偕《〈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出臺獲中央肯定》,中國新聞網2010年5月14日報道,網址: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10/05-14/2283077.shtml,訪問時間:2014年6月2日。但為全國性立法而作準備的前期積累的作用,是這部規章能在短期內通過的一個重要原因。[7]全文共十章一百七十八條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2007年初開始起草,次年4月18日就正式公布,整個立法程序只用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參見奉清清、鄢振剛《〈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正式公布》,《湖南日報》2008年4月17日,A1版。
四、創新性地方政府規章的實施效果與前景展望
(一)實施效果
制度創新以地方政府規章的形式獲得通過,只是走出了第一步;這些新制度的實施效果則是另一個更復雜的問題。一般而言,行政機關對于能夠為他們創設新權力,或者帶來更多政績的制度,總是有更大的積極性去推動其實施;反之,對那些約束行政機關權力的創新性制度,盡管相關的立法能夠為政府帶來政績,具體制度的實施卻顯示了明顯的動力不足。“戶外廣告位置使用權”的有償許可,直接為地方政府帶來財政收入,雖然明顯違反了地方政府規章的立法權限,[1]見本文第三部分第(二)項“主觀動因”分析的第4點“政府利益”的相關論述。卻至今大行其道。[2]更為極端的例子是地方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對機動車車牌號碼的拍賣——這項“創新性”制度的實施迄今未見通過地方立法的形式,而是用規范性文件直接付諸實施。根據《行政許可法》第五十九條的規定,行政許可收費只能依據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機動車號牌發放的法律依據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二者均未規定機動車號牌可以有償發放(更不用說通過拍賣的方式);很多地方卻通過規范性文件的方式對機動車號牌號碼進行拍賣。參見《廣東省小汽車號牌競價發放管理暫行辦法》(廣東省公安廳、監察廳、財政廳2007年11月6日以粵公通字〔2007〕284號發布,自2007年11月6日起施行)、《深圳市小型汽車號牌號碼競價發放管理暫行辦法》(深圳市公安局深圳市監察局深圳市財政委員會2014年1月9日發布,深公(交)字2014年6號)等。更多的地方拍賣機動車車牌號碼的文件很難找到。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機動車車牌號碼拍賣的報道在媒體不斷曝光,其中不乏“天價”競得“吉祥號牌”的報道。例如在沒有立法權的河南信陽市,某“吉祥號牌”曾拍出67萬元高價。參見張詩綺《我市吉祥車牌號拍賣現高價豫SR7777拍出67萬元》,《信陽日報》2014年5月29日,第5版。與此形成對照的是預算公開。2003—2007年間,政府信息公開方面的地方立法層出不窮,各地關于政府主動公開的信息范圍的規定也大同小異。其中,關于財政預決算和機構設置、職能及調整情況兩項內容的公開就很值得關注。那些在地方立法中明文列出公開這兩類信息的地方政府,[3]關于地方信息公開立法中關于財政預決算公開和機構職能公開的內容的例子,可查閱《廣州市政府信息公開條例》(2003)第九條第一款第(四)項和第二款第(一)項;《上海市政府信息公開規定》(2004)第八條第(三)項第3點和第(四)項第1點;《武漢市政府信息公開暫行規定》(2004)第七條第(三)項和第(四)項;以及《成都市政府信息公開規定》(2004)第十條第(四)項和第(十六)項。實際上類似的規定在當時幾乎所有同類地方立法中都有,措辭大同小異。幾乎從未主動公開過其財政預決算方案;直到《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生效后,廣州市財政局才成為第一個依申請公開財政預決算方案的行政機關。[1]關于地方政府依申請公開財政預決算方案的情況,參見《南方周末》記者黃河的兩篇相關報道:《深圳公民的“公共預算之旅”》(《南方周末》2008年11月6日,第C13版)和《廣州政府網上“曬”賬本》(《南方周末》2009年10月22日,第D17版)。而作為行政機關機構設置、職能安排及其變動的官方依據的“三定規定”[2]“三定規定”的全稱是《關于XXXX(行政機關名稱——筆者注)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的規定》,這是一類由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一個黨政合一的機構)制定的規范性文件,作為每一個行政機關設立的直接規范性文件依據。,則至今仍是“選擇性公開”——并非每個行政機關的“三定規定”都可以在法定公開媒介上找到。公開財政和職權、人事上的信息,并不能給相關行政機關帶來明顯的政治利益,而且會在一定程度上將行政機關置身于更加易于被監督的境地。此類義務雖然是制度創新中深受公眾歡迎的極大亮點,但有關行政機關實施的動力顯然不足。
(二)法律困境
法律上本來沒有創制權或者創新空間、實踐中卻具有最大創新動力并兼具便利的地方政府規章,在制度創新上一直就處在合法性與合理性的夾縫之間。用合法或者合憲的尺度來衡量,幾乎所有創新性的地方政府規章都不應該通過;如果通過了,也應當被上級政府或者本級人大常委會撤銷。[3]《立法法》第八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國務院有權改變或者撤銷不適當的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第(五)項規定:“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撤銷本級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適當的規章”;第(六)項規定:“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有權改變或者撤銷下一級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適當的規章。”實際情況卻是,至今未見任何規章(包括部門規章)被撤銷的官方消息。未被撤銷即意味著被接受,至少是被容忍。那么,暫且撇開對規章的審查程序尚待健全這一技術原因不談,地方政府規章創新的現實合理性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地方試驗”的積極支持者不惜以“國家法律乃至憲法有什么理由約束有益的地方法治試驗”的質問來呼吁憲法為鼓勵地方積極創新而作出變通,[4]參見張千帆《憲法變通與地方試驗》,《法學研究》2007年第1期,第63—73頁。但這個立足于“轉變有關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思維”[5]參見張千帆《憲法變通與地方試驗》,《法學研究》2007年第1期,第64頁。的憲法變革建議顯然是宏觀和長遠的,如何落實到制度層面,倡導者并未給出具體路徑。首先,地方立法權在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之間的分配并未被考慮到——例如,地方試驗的主體應當是地方政府還是地方權力機關,以及二者誰更具有制度創新的沖動以及便利性——這類“技術問題”,而這些貌似“技術性”的因素對地方立法的制度創新實際上有直接影響:如果地方政府沒有規章制定權,很可能大部分的地方立法制度創新都不會發生,或者說以更為粗糙的違法形式出現(如前文第31頁注釋[2]提到的機動車號牌號碼拍賣)。其次,“有益的地方法治試驗”或者說“良性違憲”[1]關于“良性違憲”的含義,參見郝鐵川《論良性違憲》,《法學研究》1996年第4期,第89—91頁。中的“有益”和“良性”的判斷標準,畢竟不能僅僅停留在法理論證的層面,而需要客觀的范圍界定和可操作的實際程序。[2]一些學者指出,實踐中地方“先行先試”權的事項和范圍,應當有來自中央的明確授權,或者說需要“一個堅固的法律支點”。參見封麗霞《地方“先行先試”的法治困境》,載《法律方法與法律思維》第六輯,第15—21頁。本文對地方政府規章制度創新的幾類實例分析則表明,立法權限與立法的品質(是否“有益”、對誰“有益”)之間,并沒有必然聯系。換言之,通過地方政府規章而創新的制度,其現實合理性仍有不小的爭議空間(例如戶外廣告設置權立法和政府信息公開立法可以形成鮮明的對照)。
(三)有序監督下的制度創新
承認地方政府制度創新的現實需求和便利,肯定地方政府制度創新的積極作用,是社會變革仍在進行、法律制度尚不完備情況下的現實選擇。在某種意義上,鼓勵地方政府規章的制度創新,對于減少和防止以“創新”的名義濫用行政權是有益的——規章制定需要經過法定程序、規范性文件甚至行政命令則更加簡便易行。但這并不意味著地方政府規章的制度創新就可以不受約束。鼓勵公眾參與、加強備案審查和司法監督,都可以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實現對地方政府規章的有效監督。
1.公眾參與
由行政機關制定的規章,本質上體現的是行政機關的意志。如果在制定程序中加入民意的參與,則可以彌補其天然缺陷。有序、有效的公眾參與,不僅可以在一般意義上擴大直接民主和提升規章的科學性與可行性,而且對于制度創新的合理性可以起到良性制約。這方面不僅有國外的經驗可供借鑒,[1]例如,美國的行政機關雖然不具有立法權,但他們制定普遍適用的規則(rules)的行為卻受到法定程序的約束,《聯邦行政程序法》專門對規則制定中的公眾參與程序作了詳細規定(See 5 U.S.C.,§553 Rule Making)。關于美國聯邦行政機關規則制定中公眾參與程序的理論與實踐,參見Jeffery Lubbers,A Guide to Federal Agency Rulemaking,American Bar Association,2006。而且國內也有現成的實例可供推廣: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的《廣州市規章制定公眾參與辦法》(2010年10月修訂,同年12月施行修訂后的版本)是在經過了充分論證和實驗的基礎上制定的首部關于地方立法公眾參與的地方政府規章,至今運行良好。[2]2006年,筆者曾作為專家組成員參與了《廣州市規章制定公眾參與辦法》的論證,并親歷了作為該規章實施前的實驗案例的《廣州市商品交易市場管理規定》(2007年1月1日施行)的公眾參與程序。此后至今(2014年6月),筆者在參與起草和論證數十部廣州市政府規章草案的過程中,公眾參與程序一直有序地進行。關于《廣州市規章制定公眾參與辦法》的論證與制定的詳細過程,參見陳里程主編《廣州公眾參與行政立法實踐探索》,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年。遺憾的是,這也是我國迄今為止唯一一部規章制定公眾參與的立法。值得注意的是,至少自2007年起,廣州市政府通過規章制定實現的制度創新,都是在這部約束規章制定程序的規章的規范下進行的。換言之,《廣州市規章制定公眾參與辦法》本身就是制度創新的一部分,或許是因為這部規章所創新的制度,對于地方政府實在沒有明顯的利益誘惑,以至于這樣一項幾乎不會引起爭議的制度,至今未被其他地方政府所效仿。[3]2005年11月沈陽市政府曾頒布《沈陽市公眾參與環境保護辦法》(2006年1月1日施行),但這部規章所涉及的公眾參與,與規章制定毫無關系。2013年7月甘肅省人大常委會頒布了《甘肅省公眾參與制定地方性法規辦法》(同年10月1日實施),但這部地方性法規所涉及的公眾參與,僅適用于地方性法規的制定。此外,國務院一些部門和一些省市都頒布過含有“公眾參與”內容的規范性文件,但無一與規章制定有關。詳情可見北大法律信息網統計資料,網址:http://www.pkulaw.cn/ cluster-call-form.aspx?menu-item=law&EncodingName=&key-word=%B9%AB%D6%DA%B2%CE% D3%EB&range=0,最后訪問時間:2014年6月3日,16時50分。2007年3月,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發布了《關于進一步提高政府立法工作公眾參與程度有關事項的通知》(國法函[2007]41號),其中第(二)項提到“對于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切身利益或者涉及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直接關系到社會公共利益的部門規章草案,可以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表明最高行政機關對規章制定公眾參與已經給予一定程度的重視。或許國務院可以考慮以鼓勵的形式(例如先發布不具有強制約束力的政策性文件),將規章制定公眾參與的范圍從國務院部門擴大到地方政府;待時機成熟時再通過修改《規章制定程序》,將公眾參與作為規章制定的法定程序。
2.備案審查
《立法法》規定了最高行政機關和地方權力機關對地方政府規章的監督權。這種監督是通過對規章的備案審查[1]《立法法》第八十九條第(四)項規定:“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報國務院備案;地方政府規章應當同時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應當同時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人民政府備案。”、改變或者撤銷[2]《立法法》第八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國務院有權改變或者撤銷不適當的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第(五)項規定:“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撤銷本級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適當的規章”;第(六)項規定:“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有權改變或者撤銷下一級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適當的規章。”來行使的。有監督權的機關在接受地方政府規章備案時,要求規章制定機關對該規章的制度創新情況進行主動說明,不僅有利于對制度創新的有效的監督審查,而且符合《立法法》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2007)的立法精神與相關規定。設置規章備案的“制度創新說明”程序,可以由接受備案的機關通過規范性文件的方式實現,簡便易行。如果再加上對審查結果的定期公布制度,則監督審查不僅對個案有效,其影響力將及于所有可能被納入審查范圍的規章。
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對規范性文件(包括規章)的主動審查制度,同樣值得關注。2013年1月1日施行的《廣州市人大常委會規范性文件主動審查辦法》,明確了該市人大常委會“在沒有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提出審查要求或者審查建議的情況下,常委會有關工作機構主動履行法律監督職責,依照本辦法規定的程序和方式,對有關國家機關報送備案的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確認其是否存在不適當情形”[3]《廣州市人大常委會規范性文件主動審查辦法》(2013)第二條。的權力,將規范性文件的審查范圍和審查程序制度化、常規化。一個在積極有為的同時又自愿接受約束的地方政府,再加上一個積極行使監督權的地方權力機關,這樣的權力架構,對于地方制度創新法治化(當然也包含“良性”化)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在現行憲法和法律框架下,這樣的制度創新經驗值得推廣。[4]2014年1月,法治政府協同創新中心和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在北京共同發布《中國法治政府評估報告2013》,廣州市政府名列榜首。參見張洋、余哲西《〈中國法治政府評估報告2013〉發布提出法治政府評估指標體系》,載《人民日報》2014年1月7日,第11版。
3.司法監督
在所有的法律環節中,法律沖突在個案訴訟中無疑表現得最明顯,也最充分、最集中——法院則是最容易發現法律沖突的國家機關,法官的專業知識也為他們發現法律沖突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在我國現行憲法制度和訴訟制度框架下,審判機關對立法行為沒有直接監督的權力,[1]《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三條雖然規定法院審理行政案件要“參照”規章,而非像對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那樣需要“根據”(第五十二條),似乎暗示了法院對規章的選擇使用權。然而,在裁判文書必須說理的前提下,選擇適用規章的過程本身已經包含了對規章合法性的評判。當事人也不能在訴訟中質疑現行立法的合憲性(哪怕是位于法的最低位階的規章)。但這并不意味著法院對立法,特別是對規章的合憲性監督就完全無所作為。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司法解釋的形式,要求法院對案件中發現的規章的合憲性問題向上級法院報告,并由上級法院分別向相應級別的政府或者人大常委會提交司法建議,能夠既有利于充分發揮法院在地方立法的審查監督中的積極作用,又不必對現行政治體制作大的調整或者變動,具有可行性。同時,如果再要求接到司法建議的機關應當在規定時間內向提出建議的法院反饋處理情況并說明理由,可以更好地鼓勵各級法院積極行使對地方政府規章的司法監督權。
(初審:毛瑋)
[1] 作者劉文靜,女,暨南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哲學學士、哲學碩士、法學博士,廣東省法學會行政法研究會副會長、廣州市政府法律咨詢專家,研究領域為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立法學、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等,長期參與地方立法事務,曾主持起草多部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專家建議稿,近期出版的代表性作品有“The role of the courts in China's progress towards transparency”,RESEARCH HANDBOOK ON TRANSPARENCY(Edited by Padieh Ala'i&Robert Vaughn),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2014;“Approaching democracy through transparency:acomparative law study on Chinese open government information”,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Vol.26(4).2011;“Government information sharing:principles,practice,and problem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Vol.28(3),2011;等等,Email:gzliuwenji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