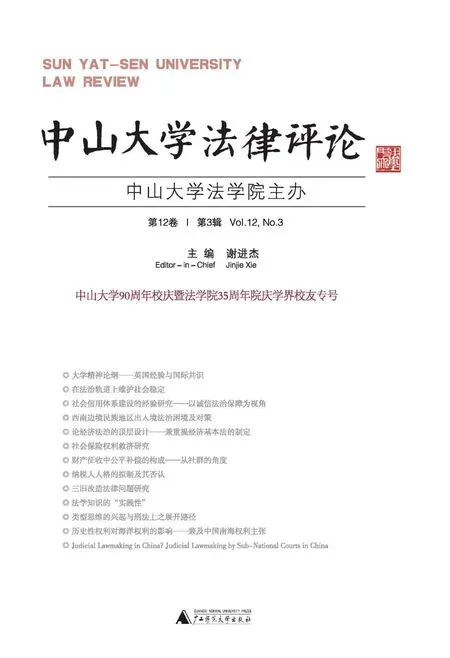歷史性權利對海洋權利的影響
——兼及中國南海權利主張
袁古潔/李任遠
歷史性權利對海洋權利的影響
——兼及中國南海權利主張
袁古潔/李任遠[1]
歷史性權利包括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以及非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兩種類型。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構成領海、專屬經濟區與大陸架劃界中的“相關情況”或“特殊情況”。沿海國可以依據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主張對專屬經濟區或大陸架的權利。中國在南海的歷史性權利是以資源的開發、利用以及海域管理為主要內容的主權權利的綜合體,中國依據歷史性權利享有U形線內水域和大陸架的主權權利。
歷史性權利;海洋權利;南海
引言
歷史性權利是一項國際習慣法中的權利。國際社會未能制定出關于歷史性權利的條約規則,實踐未對該問題做出全面、直接的回應,學者也未系統探討該問題。當前各國對海洋資源爭奪的日益激烈,歷史性權利對領海、專屬經濟區及大陸架權利的影響,成為國際法中一個突出的問題。中國在南海面臨復雜的海洋爭端,中國在U形線內的歷史性權利對中國南海權利主張有何種影響,也是中國所面臨的現實問題,本文著重探討歷史性權利對各種海洋權利的影響,同時分析中國歷史性權利對南海權利主張的影響。
國家在不同海域中的權利,性質與內容存在差異,歷史性權利對不同海域權利的影響,與歷史性權利的形態和性質有直接關系。明確歷史性權利的“個案化”特點,分析歷史性權利的具體形態與性質,是研究歷史性權利對海洋權利影響的第一步。
一、歷史性權利的形態與性質
歷史性權利并不是一項形態單一的權利,每一個慣例決定了歷史性權利的形態與性質。誠如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1962年在一項題為“歷史性水域(包括歷史性海灣)的法律制度”的研究報告中所言,在邏輯上,國家所行使的權力,構成一項歷史性權利主張的基礎,國家行使權力的范圍與提出主張的范圍應當是相符的。[1]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Juridical regime of Historic waters.1962 UNYB.U.N.Doc.A/CN.4/143:5.
(一)歷史性權利形態的“個案化”特點
大部分歷史性權利來源于國家對某一地域通過長期和平的統治所建立起來的慣例,慣例的產生時間遠遠早于近現代海洋法規則的確立時間,故而,歷史性權利與現代條約法所規定的各類海洋權利在權利的具體形態上并非一一對應關系,權利的具體形態與性質需要根據個案的具體情況確定。
一般認為,近代海洋法肇始于格老秀斯提出的海洋自由原則(公元1606年),并逐步建立起公海與領海制度;而現代海洋法制度在1958年以后才逐步建立起來。對于歷史性權利,國家在某一區域行使權利的慣例遠早于近現代海洋法確立的時間。其中,部分慣例確立的年代相當久遠,與國家與民族在陸地定居與繁衍的進程系同一過程,如中國在對南海地區的管轄,如斯里蘭卡在保克灣(Polk Bay)與馬納爾灣(Gulf of Mannar)的歷史性權利。[1]英國在殖民時期曾對斯里蘭卡附近海域提出歷史性權利。這種主張的依據是錫蘭從無法憶及的時候已經對這些珍珠漁場享有排他性主權,并且從公元前6世紀到20世紀初的記錄可以從法院的判決中找到。參見希金斯、哥倫伯斯《海上國際法》(第一版),王強生譯,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年,第112頁。邏輯上,歷史性權利的產生并非依據一個業已確立的規則創設一項權利,而是法律依據一項已經長久存在的事實,為了保持一種穩定的秩序,將其確認為一項法律權利,這是歷史性權利制度的基本價值。如Blum所言,這事實上不是創設一個新的權利,而是對已經存在的權利的確認。[2]Yehuda.Z.Blum,Historic Titles in International Law.Hague:MartinusNijhoff Publishers,1965,P.17.歷史性權利確立與依據既有條約所創設的權利,在邏輯上是相反的。正因此,歷史性權利的形態是一個個案化確定的過程。在1982年國際法院突尼斯/利比亞的大陸架劃界案中,國際法院就認為歷史性權利必須受到尊重并保持其按照慣例所確定的狀態。[3]Case concerning the Continental Shelf(Tunisia/Libya Arab Jamahiriya),Judgment,I.C.J.Rep.1982,72 (24thFeberary).
(二)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
在實踐中,大部分歷史性權利屬于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該類權利存在于海灣、群島水域、海峽等不同海域。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既包括完整的主權,也包括雖然非完整主權但具有某種主權屬性的主權權利。
主權性歷史性權利常見于海灣中,形成歷史性海灣。加拿大哈德遜灣的歷史性權利是此類權利的典型。1610年,英國人哈德遜發現了哈德遜灣。其后,英國人根據皇家特許令狀在此地設立了哈德遜灣公司。哈德遜灣公司是一家官辦公司,在其后兩百年的時間里維持著該地區毛皮的壟斷貿易,且事實上在北美的部分地區行使著政府的職能。[4]Wikipedia.Hudson's Bay Company http://en.wikipedia.org/wiki/Hudson%27s-Bay-Company.2013-03-08.1870年,加拿大繼承了英國對哈德遜灣的統治,[5]“Hudson Bay”,登載于“Wikipedia”,網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Hudson-Bay#cite-note-3訪問時間:2014年5月21日。并從1906年起主張哈德遜灣為歷史性海灣。[1]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Juridical regime of Historic waters.1962 UNYB.U.N.Doc.A/CN.4/143:5.1913年,加拿大開始了對海灣的大范圍測量。為了便利小麥出口,加拿大在1923年建立了丘吉爾港,丘吉爾港是哈德遜灣唯一的深水港口。[2]“Hudson Bay”,登載于“Wikipedia”,網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Hudson-Bay#cite-note-3,訪問時間:2014年5月21日。從1668年開始,英國通過哈德遜灣公司管轄海灣及其周圍地區。在英國將該地區轉讓給加拿大時,所移交的也為該地區的完整主權。加拿大在取得主權以后,繼續通過立法以及各種行政行為維持著對海灣的主權。兩個國家用各自的行為表明,沿海國通過長達300年的慣例,建立起對海灣持續不間斷的主權。
主權性歷史性權利也存在于某些群島周圍水域。加拿大在北極群島的歷史性權利即屬于此類。英國在1553年首先開始了北極群島的探險。據學者研究,至1859年英國探險者已經發現了所有的島嶼,其足跡也覆蓋了整個北極群島地區。[3]PHARAND,DONAT.Canada's Arctic Waters in International Law.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111.1880年,加拿大從英國繼承了北極群島(包括哈德遜海峽)的主權。此后,加拿大通過多次宣示主權、科學考察、頒發漁業許可、建立哨所、巡航、管理過往船舶等方式維持對島嶼和水域的控制,[4]Donat.Pharand,Canada's Arctic Waters in International Law.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114—120.北極群島水域為加拿大的歷史性內水,加拿大對其享有主權。群島歷史性水域的例子還有美國的Lower Cook Inlet。該水域位于美國阿拉斯加州,阿拉斯加州與美國聯邦因水域是否為州的歷史性水域產生爭端,訴至地區法院。法院認定該水域為州的歷史性內水,最主要的依據是,1962年,一艘日本漁船在該水域捕魚,聯邦表示對此不用行使管轄,而阿拉斯加州逮捕了該漁船。[5]United States/State of Alaska(1972)P.5.在該水域中,州一直享有并維持著完整主權,故而,該歷史性權利也是一種完整的主權。
然而,并非所有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均與現代意義上的完整主權完全一致,部分歷史性權利可能稱之為主權,或具有較強的主權屬性,但其內容與現代意義上的主權仍有一定差異。豐塞卡灣中,沿海國的歷史權利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
依據國際法院1992年在陸地、島嶼與海洋邊界案中判決,豐塞卡灣是閉海性質的歷史性海灣,[1]Case concerning the Land,Island and Maritime Frontier Dispute.(El Salvador/Honduras),Judgment,I. C.J.Rep.1992,589—590(11thSeptember).具有內水地位。但其具體情況與一般內水有較大差異。其一是沿岸國各自對3海里之內的水域享有專屬權,但三個沿岸國之間的船舶在各自的3海里水域中允許無害通過。[2]Case concerning the Land,Island and Maritime Frontier Dispute.(El Salvador/Honduras),Judgment,I. C.J.Rep.1992,593(11thSeptember).其二是在沿岸3海里以外的水域,三個國家享有共有權。[3]Case concerning the Land,Island and Maritime Frontier Dispute.(El Salvador/Honduras),Judgment,I. C.J.Rep.1992,601(11thSeptember).而且,在沿岸3海里以外的灣內水域,三個國家之間的船舶也允許無害通過。對于豐塞卡灣歷史性權利的特殊形態,國際法院明確認為:“3海里的海岸帶的法律地位是經過實踐所牢固樹立起來的。”[4]Case concerning the Land,Island and Maritime Frontier Dispute.(El Salvador/Honduras),Judgment,I. C.J.Rep.1992,592(11thSeptember).
雖然目前實踐中的大部分歷史性權利屬于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但也存在某些非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這些非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主要是對某些陸地或海域的使用權。
(三)非主權性歷史性權利
非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主要是對某些陸地或海域的使用權,在實踐中的例子少于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非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在實踐中既存在于陸地,也存在于海域中。陸地中的非主權性歷史性權利如1960年國際法院的印度領土通過權案中,葡萄牙的私人、貨物、政府文職人員所享有的,為進出達曼及飛地達德拉——阿維利而在印度領土上同行的權利。該權利經過一百多年的實踐,已經被雙方接受為一項法律權利。[5]Id.,p.40.該案中的歷史性權利是一種非主權性的國際地役權。
海洋中的非主權性歷史性權利也體現為對某些海域的使用權。如1998年,國際常設仲裁院在厄立特里亞/也門仲裁案中認為:“當事國幾個世紀以來在紅海南獲取漁業資源的歷史性權利,經由歷史得以鞏固,是一種不具有主權性質的國際地役權。”[1]Award of the Case between Eritrea and Yemen(Award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 in the First Stage)(Eritrea/ Yemen),1998,38(19thOctober).與此類似的例子還有伊朗歷史性捕魚權,伊朗依據歷史性權利,于1973年在波斯灣與阿曼海建立了專屬漁區。[2]Third United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Summary record of the 23rd Plenary Meeting.Official records of the Third United Nations on the Law of the Sea.(Vol.I),U.N.Doc.A/CONF.62/C.2/SR.23,1974,72.
在領海、專屬經濟區與大陸架中,沿海國所享有的權利為主權或者主權權利,因而,從歷史性權利是否為主權性歷史性權利這一視角,考察歷史性權利對海洋權利的影響,是恰當的。
二、歷史性權利對沿海國海洋權利的影響
目前鮮有關于歷史性權利在領海、專屬經濟區與大陸架劃界中的作用的相關研究,實踐也未直接回應該問題,本文主要從權利性質的視角,結合國際立法過程中的相關材料分析問題。
(一)歷史性權利對沿海國領海權利的影響
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條,沿海國對領海范圍內的水域、上空與底土享有主權。在領海范圍內,無論是存在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或非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該權利與沿海國在領海中所享有的主權不存在沖突,實際上為領海主權所吸收,沿海國在領海以內享有的各項權利沒有實質影響。但是,當歷史性權利一直延伸至12海里以外的水域時,有可能影響領海劃界。
根據《領海與毗連區公約》第11條,以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5條的規定,在一般情況下領海的邊界為中間線,但若存在歷史性所有權,則可按照其他方法劃界。兩個公約關于領海劃界采用的措辭均是“歷史性所有權”,這表明本條所指的歷史性權利必須是具有主權性質的歷史性權利,原因就在于該條是關于領海劃界的規定,適用該規定的結果將使領海劃界爭端的當事方基于歷史性權利,享有更大范圍的領海。而沿海國在領海享有主權,在領海劃界爭端中只有沿海國享有主權性質的歷史性權利才能適用該條款,非主權性質的歷史性權利在領海劃界中不影響領海界線的劃定,但歷史性權利的存續宜由雙方協商解決。
該條表明,歷史性權利在領海劃界的具體實踐中可能起到兩種作用,第一種作用是,在劃界中適用中間線方法,但歷史性所有權作為“中間線/特殊情況”規則中的“特殊情況”對中間線進行調整,其結果是爭端當事方由于歷史性所有權享有更大面積的領海。第二種作用是,歷史性所有權存在時中間線的方法不再適用,劃界采用其他方法。
故而,當歷史性權利存在于領海范圍以內,對沿海國的領海權利沒有影響;當歷史性權利存在于領海中,并延伸至領海以外時,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構成領海劃界中的“特殊情況”,非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不構成領海劃界的“特殊情況”,但劃界并不取消該權利。權利如何繼續存續,目前尚無先例,宜由當事方協商解決。
(二)歷史性權利對專屬經濟區權利的影響
歷史性權利對專屬經濟區權利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歷史性權利與專屬經濟區劃界的問題上。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56條,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中主要有以下幾項權利:以勘探和開發、養護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資源為目的主權權利,以及關于在該區內從事經濟性開發和勘探,如利用海水、海流和風力生產能等其他活動的主權權利;同時享有對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的建造和使用權,對海洋科學研究,海洋環境的保護和保全享有管轄權。
那么,歷史性權利對專屬經濟區的劃界有何種影響呢?就目前的劃界實踐而言,專屬經濟區與大陸架的劃界一般先選定某種方法(中間線、垂直線、角平分線)劃定臨時界線,然后依據“相關情況”(Relevant Circumstances)對臨時界線進行調整。若采用的劃界方法為中間線法,則將相關因素稱為“特殊情況”(Special Circumstances)。一旦歷史性權利構成劃界時的“相關情況”或“特殊情況”,意味著沿海國可以依據歷史性權利,取得更大面積的專屬經濟區,從而享有專屬經濟區中的各項權利。在專屬經濟區中,沿海國所享有的權利均不是完整的主權,而是具有排他性的主權權利,因而,只有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才能構成專屬經濟區劃界中的“相關情況”或“特殊情況”,從而影響專屬經濟區邊界的確定。非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不能影響專屬經濟區邊界的確定。倘若非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構成專屬經濟區劃界中的“相關情況”或“特殊情況”,則意味著沿海國原先非主權性的權利通過劃界轉化為一項主權性的權利,這等于通過劃界擴大了沿海國原有權利的范圍,改變了原有權利的性質,顯然不符合劃界的基本目的。盡管非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不影響專屬經濟區的劃定,但由于專屬經濟區與歷史性權利是國際法中兩項不同的制度,專屬經濟區制度并不廢除原有的歷史性權利,理論上,原來的歷史性權利應當繼續存在。
在2006年國際常設仲裁院巴巴多斯/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劃界案中,巴巴多斯主張的歷史性捕魚權與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專屬經濟區發生重疊,巴巴多斯主張其歷史性捕魚權構成專屬經濟區劃界中的“特殊情況”。由于巴巴多斯所主張的歷史性權利不成立,仲裁庭沒有詳細討論歷史性權利在專屬經濟區劃界中的作用。仲裁院認為,巴巴多斯的捕魚行為,距離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群島水域法》的頒布有6~8年的時間,不足以成為一項歷史性捕魚權。[1]Award of the Case between Barbados and the 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Barbados/Trinidad and Tobago),2006,82(11thApril).而且在該案中,仲裁庭對歷史性捕魚權能否影響專屬經濟區的劃界沒有持明確的態度,只是認為即使巴巴多斯主張的歷史性捕魚權能夠成立也不一定將歷史性捕魚權作為一項調整臨時中間線的“特殊情況”。
仲裁庭的這一觀點為問題留下了很大的討論空間。將巴巴多斯所主張的歷史性捕魚權與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基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享有的權利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巴巴多斯所主張的歷史性捕魚權只是在特立尼達和多巴哥主張的專屬經濟區的海域內捕獲漁類資源,準確而言是捕獲飛魚的歷史性捕魚權。而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56條的規定,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內除享有勘探和開發海洋及其底土的自然資源的主權權利以外,還享有建造和管理人工島嶼及設施的權利,對海洋科學研究的管轄權,保護和保全環境的管轄權。
在該案件中,沿海國依據專屬經濟區制度所享有的權利和所主張的歷史性捕魚權存在兩個方面的區別:第一是權利范圍的區別,沿海國根據專屬經濟區所享有的權利范圍遠遠大于案件所涉及的捕魚權。在權利性質上,根據專屬經濟區所享有的權利為主權權利或者專屬權利,而巴巴多斯所主張的歷史性捕魚權并不是排他的歷史性權利而是允許與其他國家共享的捕魚權,這種捕魚權的性質是國際地役。一旦將這種歷史性權利作為調整臨時中間線的“特殊情況”,就意味著基于歷史性捕魚權,劃給另一個國家更多的專屬經濟區,一國將因為一項非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而在劃界中取得專屬經濟區中極為廣泛的權利。這實際上改變了這項非主權性的歷史性捕魚權的內容和性質,使一個國家一項本來范圍狹小的權利經過劃界擴張成為一項范圍廣大的主權性權利,這明顯不符合海洋劃界的本義,也有違海洋劃界的公平原則。但是,另一方面,歷史性捕魚權確實不應該被專屬經濟區制度所廢除,它應該保持其原來的歷史性狀態。綜合考慮兩方面,仲裁庭最終并沒有對該案中如果存在歷史性捕魚權是否構成調整臨時中間線的理由這一點做出明確答復。這源于具體個案中歷史性捕魚權與專屬經濟區權利的差異。
基于上述分析,在專屬經濟區劃界中,歷史性權利是否構成海洋劃界中的“相關情況”或“特殊情況”,必須考察歷史性權利的性質、內容與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中的權利之間的關系。當一國主張的歷史性權利性質僅為對特定資源的非主權性權利時,歷史性權利的存在并不足以構成劃界中的“相關情況”或者“特殊情況”;當一國在海域中的歷史性權利具有專屬性質或者具有主權性質時,只要權利與專屬經濟區中所享有的權利較為接近,應當構成劃界中的“相關情況”或者“特殊情況”。建造人工島嶼和設施以及海洋環境保護是現代才出現的社會活動,不能要求歷史性權利中包含這兩種行為,只要國家對海域中的自然資源享有較為廣泛的專屬權利或者主權權利,而且對海域實施專屬的管轄就應當作為劃界中的一項“相關情況”或者“特殊情況”進行考慮,成為海洋劃界中所要考慮的因素。當存在非專屬性的歷史性權利的情況下,一國在別國的專屬經濟區內行使其歷史性權利可能引起沖突,這種情況下由雙方通過協議將歷史性權利轉化為條約權利,是行使權利時避免沖突的一個有效途徑。
(三)歷史性權利對大陸架權利的影響
大陸架上蘊藏著大量的自然資源,對沿海國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沿海國是否可以基于歷史性權利對大陸架提出主張呢?分析這個問題,應從1958年《聯合國大陸架公約》(簡稱《大陸架公約》)的制定過程、司法實踐以及權利的性質入手。
1958年制定《大陸架公約》的過程中,與會國家總體上承認國家在大陸架上可以享有歷史性權利。多米尼加共和國代表認為,在制定關于大陸架的法律時,經濟、歷史因素應當與地理因素并重考慮。[1]Official Record of the(First)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s on the Law of the Sea.(Vol.IV),U.N.Doc. A/CONF.13/42,1958,9.瑞典代表認為,在實踐中,沿海國對大陸架上的某些定居物種行使主權,如果存在這樣的歷史性權利,在制定大陸架的法律時,國家此項權利不應被剝奪。[2]Official Record of the(First)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s on the Law of the Sea.(Vol.IV),U.N.Doc. A/CONF.13/42,1958,62.美國代表承認國家對生活在大陸架上的某些生物的歷史性權利。[3]Official Record of the(First)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s on the Law of the Sea.(Vol.IV),U.N.Doc. A/CONF.13/42,1958,62.荷蘭代表特別提到了斯里蘭卡在大陸架上捕獲珍珠的歷史性權利。[4]Official Record of the(First)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s on the Law of the Sea.(Vol.IV),U.N.Doc.A/ CONF.13/42,1958,65.以色列認為,國家可以基于歷史性權利而享有在大陸架上捕獲底棲魚類的權利。[5]Official Record of the(First)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s on the Law of the Sea.(Vol.IV),U.N.Doc. A/CONF.13/42,1958,71.
該會議上,沿海國對大陸架權利范圍是爭論的問題之一,該問題涉及了歷史性權利與大陸架問題。部分國家(如美國)認為,在界定沿海國對大陸架資源的權利范圍時,大陸架表層的生物資源不應歸屬于沿海國對大陸架的權利范圍。故此,美國主張,沿海國對大陸架的權利應限定為對礦藏資源(Mineral Resource)的權利,而不是對自然資源(Natural Resource)的權利。[6]Official Record of the(First)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s on the Law of the Sea.(Vol.IV),U.N.Doc. A/CONF.13/42,1958,62.而另一部分國家則主張,沿海國對大陸架表層生物資源的權利屬于沿海國對大陸架的權利之一。[7]Official Record of the(First)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s on the Law of the Sea.(Vol.IV),U.N.Doc. A/CONF.13/42,1958,62.這兩種觀點的差異意味著,如果國家對大陸架表層生物資源的權利不屬于國家在大陸架上享有權利的范圍,則國家對大陸架表層生物資源的開發,不屬于開發、利用大陸架的行為;如果國家對大陸架表層生物資源的權利,屬于其在大陸架上享有的權利范圍,則對該資源的開發、利用構成了開發、利用大陸架的行為。經過討論,《大陸架公約》涉及沿海國對資源權利范圍的條款所采用的措辭均為“自然資源”。《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該問題上的規定也與《大陸架公約》一致。這表明,首先,《大陸架公約》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沿海國對大陸架資源的權利方面,對大陸架表層的資源以及大陸架內部的礦藏資源是同等對待的,并沒有適用不同的制度。其次,沿海國對大陸架表層的生物資源的權利是沿海國對大陸架權利的一部分,對該資源的開采與利用行為,構成了對大陸架的開采和利用行為。
司法實踐同樣證明了這一點。Arechaga法官在1982年的突尼斯/利比亞大陸架案的個別意見中認為,按照《大陸架公約》第2條第4款的規定,[1]1958年《大陸架公約》第2條第4款規定:“本條款所稱自然資源包括在海床及底土之礦物及其他無生資源以及定著類之有生機體,亦即于可予采捕時期,在海床上下固定不動,或非與海床或底土在形體上經常接觸即不能移動之有機體。”在特定的案件中,當考慮到捕獲附著于海床的海綿構成一種開采大陸架的行為,捕獲海綿的歷史性權利在個案中是至關重要的,這一條款同時也是國際法院在1969年北海大陸架案中所承認的國際習慣法的一部分。[2]Case concerning the Continental Shelf(Tunisia/Libya Arab Jamahiriya),Separate Opinion,I.C.J.Rep. 1982,123(24thFebruary).按照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的看法以及1958年《大陸架公約》的界定,捕獲海綿的行為并不是作為一種附著物種的捕魚行為,而是作為對大陸架的一種開采行為,這種行為和在大陸架上抽取油氣資源是同等性質的。”[3]Case concerning the Continental Shelf(Tunisia/Libya Arab Jamahiriya),Judgment,I.C.J.Rep.1982,123(24thFebruary).美國國內法院也曾經在判決中認為,歷史性權利應當是及于底土的權利。[4]希金斯、哥倫伯斯:《海上國際法》(第一版),王強生譯,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年,第113頁。而且1958年《大陸架公約》的預備工作資料(travauxpreparatoires)顯示,歷史性權利應該被作為一項劃界的“特殊情況”。1958年《大陸架公約》和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均沒有在劃界中寫入歷史性權利,不是因為歷史性權利與大陸架劃界無關或者不重要,而是因為歷史性權利與其他“特殊情況”同等重要。[1]因為1958年的《大陸架公約》對大陸架劃界問題只規定了中間線方法,所以此處的措辭是“特殊情況”而沒有采用“相關情況”一詞。Case concerning the Continental Shelf(Tunisia/Libya Arab Jamahiriya),Separate Opinion,I.C.J.Rep.1982,77(24thFebruary).
一個潛在的問題是,沿海國依據大陸架制度享有的權利是一種固有的權利,這種固有的權利與其他國家在大陸架上的歷史性權利,在性質上是否存在沖突呢?從法律規則產生的時間上看,大陸架制度是在20世紀40年代《杜魯門宣言》發布以后漸漸成為法律規則的。大陸架制度中的權利固有原則也是在這一時期產生的,歷史性權利產生的時間要遠遠早于大陸架制度。新制度的產生并不能取代一項產生時間較早且依然有效的權利。Arechaga法官在突尼斯/利比亞大陸架案的單獨意見中對這個問題發表了相似的見解:“(大陸架權利的)‘固有’原則是在日內瓦召開的第一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上才開始出現的,適用這個原則的目的是保護沿岸國的權利,這些沿岸國既沒有對其在大陸架上的權利發表任何聲明,也沒有能力勘探與開采大陸架上的資源。大陸架制度的提倡者,包括杜魯門總統的顧問,最初提出該制度時,均從歷史性捕魚權,包括對附著于海床的資源的開采權中,尋求依據。1958年《大陸架公約》中引入的,大陸架權利固有這一原則,不能減損或廢除一項已經取得的、現存的權利。若非如此,則將有悖于基本的法律理念與基本的時際法規則。認為《杜魯門宣言》或《大陸架公約》減損或否定了先前存在于大陸架上的權利的觀點是荒謬的;事實正好與這種觀點相反,這個原則吸取、包含了這些權利的因素。”[2]Case concerning the Continental Shelf(Tunisia/Libya Arab Jamahiriya),Separate Opinion,I.C.J.Rep. 1982,123—124(24thFeberary).
由于沿海國在大陸架上享有的權利是主權權利,因而,只有主權性質的歷史性權利才能構成大陸架劃界中的“相關情況”或者“特殊情況”,從而影響大陸架界線的劃定。如果歷史性權利不是主權性的,此種情況下則不宜將歷史性權利作為劃界中的一個“相關情況”來考慮,因為將這種非專屬性的權利作為“相關情況”從而授予沿海國更大范圍的大陸架,實際上擴大了歷史性權利的內容,并將一項非專屬性的權利通過劃界轉化為一項專屬性的權利,這與歷史性權利本來的內涵不相符,也與劃界的目的不相符。盡管非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不能影響大陸架界線的劃定,但劃界本身并不取消歷史性權利,這種非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如何繼續享有,宜由當事國協議解決。
通過分析可見,大陸架制度和歷史性權利制度有重要聯系,從相關條約的起草過程以及相關的司法實踐考察,基于歷史性權利而對海底表層資源的捕獲與利用構成了開發、利用大陸架的行為。只要沿海國對大陸架表層資源的開發、利用的歷史性權利帶有主權屬性,是一項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沿海國就可以依據該歷史性權利,對大陸架提出主張。該歷史性權利構成大陸架劃界中的“相關情況”或“特殊情況”。倘若該歷史性權利為非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則不能構成劃界中的相關情況,但劃界不應取消既存的歷史性權利,該權利如存續并無先例,宜由當事國協商解決。
中國主張南海U形線內的歷史性權利,究竟中國在U形線內的歷史性權利屬于哪種性質,對中國的權利主張有何影響,是一個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問題。
三、歷史性權利對中國南海權利主張的影響
中國在南海地區的活動范圍包括了東沙、中沙、西沙與南沙四大群島及其周圍水域。中國在南海地區的權利性質取決于中國在該地區的行為所形成的慣例。
(一)中國在南海地區的活動與歷史性權利
關于中國在南海地區的活動情況,學者有大量研究,本文只就歷史性權利問題,依據歷代的重要史料,作簡要分析。中國在南海地區,包括南海的島礁與水域中,進行的活動有以下幾類:
其一,派遣水師巡航島嶼與水域。三國時期,吳國將領康泰曾奉命巡視南海諸島,[1]韓振華編:《我國南海諸島史料匯編》,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第25頁。隋唐時期由官方下令編撰的《隋書》、《通典》等書記載了關于巡視南海地區的情況。記載類似情況的史籍還包括《元史》、《廣東通志》等重要史書[1]《隋書》由唐朝名臣魏征奉命修訂,《通典》則由唐朝宰相杜佑奉命修訂。參見韓振華編《我國南海諸島史料匯編》,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第29—37、52頁。,表明在古代,中國一直派遣水師巡視南海地區的島嶼和水域。
其二,利用海洋資源的行為。如記載三國時期吳國的《吳錄》中記載漁民在南海中捕獲玳帽;《爾雅注》中記載漁民在南海捕獲海螺;《初學記》(唐)記載漁民在南海獲取珊瑚。[2]參見韓振華編《我國南海諸島史料匯編》,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第26—27頁。這表明南海自古是中國的傳統漁場,中國人民在南海大量開發利用海洋資源。《更路簿》是明清時代漁民的航海指南。根據不同版本的《更路簿》記載,西沙、南沙群島的航線超過百條,[3]曾昭璇、曾憲珊:《清〈順風得利〉(王國昌)抄本更路簿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一期,第86—103頁。表明中國漁民經常在U形線內的幾乎所有地區捕魚作業。筆者2013年底從廣東省湛江市海洋與漁業局的相關工作人員處了解到,目前中國仍定期派遣公務船舶,保護在南海捕魚的中國漁民。
其三,通航。南海自古以來是中國官方與民間的重要航道。南北朝的《萬州異物志》、《南越志》等記載了早期中國政府與民間船舶在南海通航的情況。《隋書》、《廣州通海夷道》(唐)、《方輿御覽》(宋)、《元史》等均記載了相關通航情況。[4]參見韓振華編《我國南海諸島史料匯編》,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第28—44頁。明清以后,關于中國船舶在南海航行的記錄更是數不勝數。而且外國船舶在南海航行,受中國保護。僅明朝一個時期,中國政府護送外國貢船的記錄就多達18次。[5]韓振華編:《我國南海諸島史料匯編》,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第52頁。
其四,打擊海盜或救助外國遇難船舶。明清時期,中國在南海地區有大量的救助外國船舶與打擊海盜的行為。《廣東通志》詳細記載了明朝打擊海盜的情況。《清實錄》記載了清政府多次打擊海盜的情況。[6]云南歷史研究所:《〈清實錄〉越南緬甸泰國老撾史料摘抄》,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9、300—307頁。清代救助外國船舶已經形成固定制度,依據公元1775年清朝乾隆年間的一份題本記載,[7]韓振華編:《我國南海諸島史料匯編》,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第68頁。此時救助外國船舶已是清政府的一項長期政策,救助的費用由國家統一撥款。
其五,海洋科學測量與調查。中國對南海地區的海洋科學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據《元史》記載,元代太守郭守敬曾奉命在南海地區進行天文測量。[1]韓振華編:《我國南海諸島史料匯編》,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第47頁。近代關于海洋科學考察的記錄較多。1928年,廣東省政府聯合有關單位對西沙群島進行全面調查,調查的內容涉及西沙群島的位置、地形、海流、交通、物產等。[2]參見陳銘樞、曾蹇《海南島志》,上海:神州國光社,1933年,第553—558頁。20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水陸地圖審查委員會公布了《南海諸島各島嶼中英地名對照表》,覆蓋132個島礁。[3]韓振華編:《我國南海諸島史料匯編》,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第174—179頁。1935年,該委員會出版了《中國南海各島嶼圖》。[4]韓振華編:《我國南海諸島史料匯編》,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第320頁。1947年,國民政府內政部方域司制定了《南海諸島新舊名稱對照表》,[5]鄭資約:《南海諸島地理志略》,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第83—94頁。島礁數量由原來的132個增加至168個,《南海諸島位置圖》正式標有一條U形疆界線,將上述四群島包括在內。[6]傅崐成:我國南海歷史性水域法律地位之研究.臺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9年第14頁。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府先后設立了“西南中沙群島辦事處”、“廣東省西沙、南沙、中沙群島革命委員會”等機構管轄南海諸島與海域。2007年11月,經國務院批準設立縣級市三沙市。[7]“三沙市”,登載于“百度百科”,網址:http://baike.baidu.com/view/1265463.htm?fr=ala0-1-1,訪問時間:2014年5月21日。2012年6月,民政部發布《民政部關于國務院批準設立地級三沙市的公告》,[8]“民政部關于國務院批準設立地級三沙市的公告”登載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網站”,網址:http:// 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206/20120600325063.shtml,訪問時間:2014年5月21日。設立地級市三沙市。
依據中國歷代在南海地區的活動情況,南海地區歷來處在中國水師或海軍力量控制之下,中國在該海域承擔管理、維持海上安全、救助外國船舶的義務,U形線內的整個海域總體處在中國的主權控制之下。中國在南海進行科學測量與考察,中國漁民長期在海域中獲取各種海洋資源。中國歷來允許南海U形線內水域的國際通航,因此中國在U形線內的權利,不是完全的主權;總體而言該權利是一種帶有很強主權性質的準主權,包括了海域的開發利用與管理等多項主權權利,該權利對中國主張水域權利與大陸架權利有重要意義。
(二)歷史性權利對中國主張U形線內水域權利的影響
在水域的權利方面,中國對U形線的水域的資源享有權利,依據歷史性權利,中國長期開發U形線內的漁業資源的權利,而且,在歷史上,開發利用資源的行為具有獨占性。這種獨占性雖然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受到了部分東南亞國家的侵犯,但是中國的歷史性權利早已形成,并持續了上千年,權利的合法性不因個別國家的侵權行為而受到影響。基于中國歷史上長期巡航、打擊海盜、護送外國船舶的行為,中國享有管理U形線內水域的權利,這也是歷史性權利的內容之一。中國長期在南海地區進行測量和科考,科學考察及對科學考察的管理權也是歷史性權利的應有之義。那么,中國在水域中的歷史性權利能否成為專屬經濟區劃界中的“相關情況”,從而影響專屬經濟區的劃定呢?
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56條,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中的權利主要包括對自然資源的專屬權利、對科學研究的管轄權、關于人工島嶼方面的專屬權利以及對自然環境的保護和保全的管轄權。較之中國在U形線內的歷史性權利,兩者在自然資源、科學研究的管轄權是一致的。但是歷史性權利中并未包含與人工島嶼相關的權利以及海洋環境的保護和保全方面的權利。而專屬經濟區制度里未涵蓋歷史性權利中對整個海域總體的管理權利。造成兩者差異的原因在于,歷史性權利制度的形成早于專屬經濟區制度,兩者在形態上不可能完全對應。盡管如此,兩者在權利的性質上均具有主權屬性,涵蓋多種主權權利,且在經濟性的主權權利方面高度吻合。在進行專屬經濟區劃界時,中國將歷史性權利作為一項劃界的“相關情況”,主張U形線內的權利,一則符合專屬經濟區設立的根本目的;二則兩者權利性質相同,內容相近,是合法的。
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57條的規定,沿海國可以主張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根據該條,同時基于歷史性權利,中國在U形線內可以主張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同時,依據歷史性權利,中國在整個南海U形線內的水域可以主張對資源的主權性權利,以及對水域的管轄權。
(三)歷史性權利對中國主張U形線內大陸架權利的影響
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77條的規定,沿海國享有以勘探大陸架和開發其自然資源為目的的主權權利。那么,在大陸架劃界中,中國的歷史性權利能否構成劃界的“相關情況”呢?
依上文的分析,中國在U形線內的歷史性權利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對自然資源進行開發、利用的主權性權利。這些自然資源既包括魚類,也包定居物種。珊瑚是典型的海底定居物種,玳帽生活在珊瑚礁中,以海綿等海底定居物種為食,海參也是典型的定居物種。如上文分析,中國人民在南海中捕獲此類海洋生物已持續了上千年。依據上文對《大陸架公約》制定過程的分析,以及1982年國際法院利比亞/突尼斯案中,Arechaga法官的意見,捕獲海綿的行為構成開采大陸架資源的行為,與開采大陸架內部的石油的性質是一樣的。[1]Case concerning the Continental Shelf(Tunisia/Libya Arab Jamahiriya),Judgment,I.C.J.Rep.1982,123(24thFebruary).因此,中國在南海捕獲珊瑚、玳帽、海參等定居物種,與該案中捕獲海綿的性質相同。所以,在大陸架劃界中,中國可以依據開采U形線內定居物種的行為,主張U形線內的歷史性權利,該歷史性權利構成劃界中的“相關情況”,中國依據歷史性權利享有U形線內大陸架的權利。
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78條的規定,沿海依據領土的自然延伸,最多可以主張350海里的大陸架。依據該條,以及中國在大陸架中的歷史性權利,中國可以在U形線內主張350海里的大陸架。同時,如上文所述,大陸架固有原則與大陸架中的歷史性權利并不沖突,歷史性權利在大陸架制度確立之后仍然存在。所以,依據歷史性權利,在350海里以外,中國仍可以依據歷史性權利主張U形線內大陸架的主權權利。
四、結論
歷史性權利并不是一種形態單一的權利,權利的內容取決于慣例。從權利性質的角度分類,歷史性權利總體可劃分為主權性歷史性權利與非主權性歷史性權利。不同類型的歷史性權利對海洋劃界有不同影響,根據海域的不同與劃界方法的差異,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在領海、專屬經濟區與大陸架劃界中分別構成劃界中的“相關情況”或“特殊情況”,直接影響海洋邊界的劃定。非主權性的歷史性權利不影響海洋界線的確定,但劃界本身并不取消一項既有的權利,該歷史性權利繼續存在。中國在南海地區的歷史性權利是以資源的開發、利用與海域管理為主導的多種主權權利的綜合體。歷史性權利構成中國在海域與大陸架劃界中的“相關情況”或“特殊情況”,中國可以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主張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同時,在距離領海基線200海里以外的水域,中國依據歷史性權利享有對資源的主權權利以及對海域的管轄權。中國可以依據歷史性權利,主張對整個U形線內大陸架自然資源的權利。
(初審:張亮)
[1] 作者袁古潔,女,華南師范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法學學士、中山大學法學碩士、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研究領域為國際法、體育法,代表作有《國際海洋劃界的理論與實踐》《條約在中國內地與港澳臺適用之比較》《我國體育法制建設發展的現狀、問題與對策》等,E-mail:yuangj @sc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