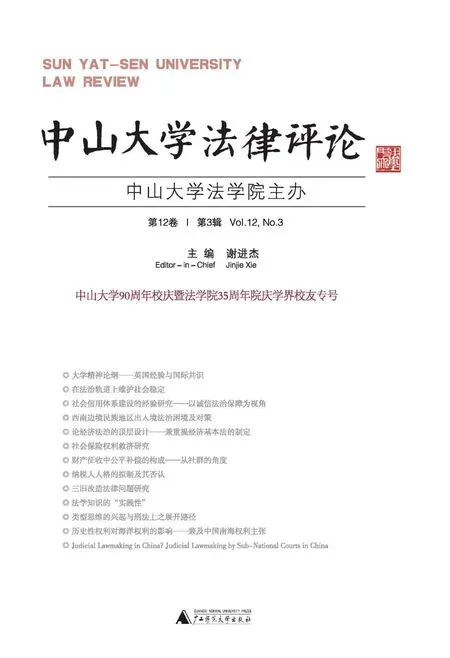法學(xué)知識的“實(shí)踐性”
劉星
法學(xué)知識的“實(shí)踐性”
劉星[1]
理論中存在法律知識,實(shí)踐中亦存在法律知識。理論中的法律知識,盡管是“理論中”的,其生產(chǎn)者,盡管常被稱為“進(jìn)行單純理論知識生產(chǎn)”,但在理論表達(dá)的過程中,及被認(rèn)為“進(jìn)行單純理論知識生產(chǎn)”時(shí),其依然“正在實(shí)踐中”,其依然“正在”實(shí)踐中表達(dá)實(shí)踐立場,并且,此為應(yīng)當(dāng)。
法學(xué)知識;法律知識;實(shí)踐;客觀中立;立場
若作一點(diǎn)有關(guān)學(xué)者的譜系分析——那些收集、記錄事實(shí)的學(xué)者,那些進(jìn)行證明和駁斥的學(xué)者——那么,他們的Herkunft(出身)很快就會(huì)表明,在他們表面無私的關(guān)注中,在他們對客觀性的“純粹的”執(zhí)著追求中,留下的盡是些法院書記員的記錄和律師——他們的父親——的訟辭。[2][法]福柯:《尼采、譜系學(xué)、歷史》(王簡譯),杜小真選編《福柯集》,上海:上海遠(yuǎn)東出版社,1998年,第152頁。“Herkunft”一詞的中文含義為“出身”。
一、思路和經(jīng)驗(yàn)樣本
理論中存在法律知識,實(shí)踐中亦存在法律知識。本文將討論兩者關(guān)系,意在思考“法學(xué)知識如何實(shí)踐”。這種思考或與人們通常設(shè)想的有些不同,涉及某些追問:兩類法律知識以功能論,是否的確具有實(shí)質(zhì)區(qū)別,及兩類法律知識的生產(chǎn)者,以社會(huì)角色擔(dān)當(dāng)論,是否的確具有實(shí)質(zhì)不同,正如“理論中”和“實(shí)踐中”這些限定詞所表達(dá)的?通過各節(jié)分析、論證,本文可能會(huì)將思路引向某些目標(biāo):理論中的法律知識,盡管是“理論中”的,其生產(chǎn)者,盡管常被稱為“進(jìn)行單純理論知識生產(chǎn)”,但在理論表達(dá)的過程中,及被認(rèn)為“進(jìn)行單純理論知識生產(chǎn)”時(shí),其依然“正在實(shí)踐中”,其依然“正在”實(shí)踐中表達(dá)實(shí)踐立場,并且,此為應(yīng)當(dāng)。這意味著,對于本文的敘述邏輯而言,兩類知識,兩類知識生產(chǎn)者,實(shí)際上極可能變?yōu)椤耙粋€(gè)事物的兩個(gè)方面”;深入講,兩類知識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及兩類知識的生產(chǎn)者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極可能不是簡單的“對照”“吸取”“借鑒”等語詞可描述清晰的。[1]顯然,上述追問、目標(biāo)期待,及上述敘述邏輯,對中國的法學(xué)理論而言,可能有些“不易理解”。因?yàn)椋袊▽W(xué)理論習(xí)慣認(rèn)為,雖然可不斷講述“理論來源于實(shí)踐,高于實(shí)踐,又將返回實(shí)踐進(jìn)而指導(dǎo)實(shí)踐”的故事,但不斷宣稱,“理論可轉(zhuǎn)為實(shí)踐的力量推動(dòng)實(shí)踐”,甚至直言“知識就是力量”,但理論終歸理論,實(shí)踐終歸實(shí)踐。在理論和實(shí)踐之間,一條界線非常明確;而且,在理論生產(chǎn)者和實(shí)踐參與者的角色之間,另外一條界線同樣明確。
先來閱讀一份“理論中的法律知識”的經(jīng)驗(yàn)樣本。
這份經(jīng)驗(yàn)樣本,涉及我國民事訴訟證明責(zé)任。現(xiàn)行《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guī)定,“當(dāng)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zé)任提供證據(jù)”。此為人們熟知的“誰主張誰舉證”的證明原則。但針對為何如此規(guī)定的問題,需闡述理論上的理由。如果闡述出來的理由表現(xiàn)了一種原理性質(zhì),則這種理由,即可成為一種“法律知識”。而法律知識的基本含義,在于其表現(xiàn)了一種關(guān)于法律原理性質(zhì)的認(rèn)識和理解。[2]本文研究中,作為定義,“法律知識”主要指關(guān)于法律現(xiàn)象的原理性質(zhì)的認(rèn)識和理解;具體而言,涉及法律現(xiàn)象的“是什么”“為什么”“做什么”的思想把握。關(guān)于法律知識的精確定義,盡管可做出各種描述和界定,但我指稱的含義,總是大致存在。
再有一份樣本為一本法學(xué)著作。其中,作者提到,“誰主張誰舉證”的理由至少包含如下兩點(diǎn):第一,法院必須依據(jù)證據(jù)認(rèn)定事實(shí),當(dāng)事人主張的事實(shí)是否真實(shí),法院既無法先驗(yàn)感知,也無法事后猜想,只能借助證據(jù)來判斷;第二,法院非偵查機(jī)關(guān),沒有專門的偵查人員,而全部或主要由法院負(fù)擔(dān)調(diào)查和收集證據(jù),既不可能,又不合理。[1]參見李浩《民事證明責(zé)任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3、82頁。作者另認(rèn)為,民事訴訟中的證明責(zé)任有其自身規(guī)律。[2]參見李浩《民事證明責(zé)任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63、67、83頁。顯然,作者提到的第一點(diǎn)、第二點(diǎn)及“自身規(guī)律”,表達(dá)了一種“法律知識”的認(rèn)識和理解。其又表達(dá)了關(guān)于在證據(jù)問題上法院角色的定位原理,并且以此為基礎(chǔ),較細(xì)致地說明了“當(dāng)事人證明責(zé)任”的主要學(xué)理根據(jù)。
一般來看,閱讀這樣一類“法律知識”,我們通常會(huì)認(rèn)為,其為“理論中”的法律知識的描述。這種描述,既屬于對歷史及現(xiàn)實(shí)中的民事證明責(zé)任的概括和分析[3]就“歷史”而言,作為輔助、且作為本文提到的學(xué)術(shù)知識生產(chǎn)的例子,作者的確從許多歷史經(jīng)驗(yàn),特別是西方的歷史經(jīng)驗(yàn)中,進(jìn)行歸納總結(jié)。參見李浩《民事證明責(zé)任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12、38、39、83—84、112—128頁。就“現(xiàn)實(shí)”而言,參見下文。,也屬于對其中的規(guī)律、特征的把握和提煉。其亦可成為后來人們學(xué)習(xí)“舉證責(zé)任”知識的一個(gè)對象。此外,我們通常會(huì)認(rèn)為:這種理論中的法律知識,因其對“自身規(guī)律”的把握和提煉,主要目的在于類似自然科學(xué)以瞄向?qū)ο蟮钠饰?故無明顯的“當(dāng)下的實(shí)踐參與欲望”,即沒有明顯的“當(dāng)下實(shí)踐立場”的表達(dá)和宣揚(yáng),其動(dòng)機(jī)主要在于“法律知識的學(xué)術(shù)生產(chǎn)”。并且,其以學(xué)術(shù)話語作為表達(dá)方式。而更重要的,其是“客觀”“中立”的。廣泛說,法學(xué)中,類似的知識描述非常普遍,并且均不約而同地默認(rèn)作為一般知識傳播的上述“自我特征”。
當(dāng)然,我們通常又會(huì)認(rèn)為,獲得這樣的法律知識,其目的并非僅為了“認(rèn)識”“理解”,并非僅為了知識的“客觀”“中立”的表達(dá);在“認(rèn)識”“理解”之后,法律知識還可作為一種理論話語來指導(dǎo)現(xiàn)實(shí)中的法律操作。它們的確來自實(shí)踐,揭示實(shí)踐中的“實(shí)質(zhì)”,但又高于實(shí)踐,又將返回實(shí)踐中指導(dǎo)實(shí)踐。如上述“證明責(zé)任知識”的闡述者即認(rèn)為,在中國的民事證明責(zé)任實(shí)踐中,應(yīng)注意具有自身規(guī)律的“證明責(zé)任認(rèn)識”的指導(dǎo)意義,否則,這類實(shí)踐,便會(huì)出現(xiàn)怪異狀態(tài),且對實(shí)踐本身非常不利,而怪異狀態(tài)如: (一)當(dāng)事人提出事實(shí),人民法院調(diào)查收集證據(jù);(二)當(dāng)事人一動(dòng)嘴,審判人員便跑斷腿;(三)法院調(diào)查取證,律師閱卷并對法院收集的證據(jù)進(jìn)行審查并提出問題。[1]參見李浩《民事證明責(zé)任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3、82頁。在其他理論化法律知識的描述中,人們一般同樣會(huì)發(fā)現(xiàn)類似的“指導(dǎo)現(xiàn)實(shí)法律操作”的觀念。
在此,更核心的則是這種觀念暗含的一個(gè)命題:通過理論中法律知識的不斷討論、探索,法學(xué)學(xué)術(shù)可把握法律知識的準(zhǔn)確性和真理性;進(jìn)一步,在極其富有“準(zhǔn)確性”、“真理性”的法律知識闡述中,可推出普遍性的思想權(quán)威。
現(xiàn)在,閱讀一份“實(shí)踐中的法律知識”的經(jīng)驗(yàn)樣本。
2003年,某省發(fā)生一起刑事案件審判。該審判當(dāng)時(shí)引起了廣泛爭議。案情涉及一名基層法院法官的行為是否構(gòu)成玩忽職守罪。此刑事案件審判,源自一起民事審判。作為被告人的法官,在一起民事審判過程中,是獨(dú)任法官,負(fù)責(zé)審理一起債務(wù)糾紛。在關(guān)于這起債務(wù)糾紛的民事審判中,原告以借據(jù)為證主張被告欠債。被告提出,借據(jù)是在原告脅迫下簽署的,故無效。該法官要求被告就“脅迫”問題提供證據(jù)。被告無法提供。該法官進(jìn)而詢問被告是否已向公安機(jī)關(guān)報(bào)案;被告稱否。該法官依照《民事訴訟法》“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判決債務(wù)成立。案件進(jìn)入執(zhí)行程序。此時(shí),被告中的兩個(gè)當(dāng)事人,頗具象征性地在法院——作為刑事案件被告人的法官所在的法院——門口服毒自殺。后公安機(jī)關(guān)介入,詢問原告;原告承認(rèn)曾脅迫被告寫下借據(jù)。有鑒于此,民事審判便被認(rèn)為存在問題,其判決也被認(rèn)為錯(cuò)誤;而檢察機(jī)關(guān)指控,該法官行為構(gòu)成玩忽職守罪。此案即為當(dāng)時(shí)著名的“莫兆軍案”。[2]該案詳情,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書》(編號:[2004]粵高法刑二終字第24號)。
刑事審判過程中,檢察機(jī)關(guān)提出許多理由,以論證罪名成立。作為被告人,法官莫兆軍同樣提出許多理由,以說明自己的行為未構(gòu)成犯罪。最后,經(jīng)二審終審,法院判決莫兆軍無罪。在陳述終審判決理由時(shí),法院引用了一些“法律知識”。對本文主題而言,值得注意的“法律知識”是:
民事訴訟中的法官,不可能像公安機(jī)關(guān)一樣收集“脅迫”一類的刑事犯罪證據(jù);因?yàn)椋涔δ堋⒙氊?zé)及本身所具有的能力,與后者存在重要差異。民事訴訟中的法官,依據(jù)“誰主張誰舉證”的民事訴訟原則審理案件,是正確的職業(yè)角色分工表現(xiàn)。[1]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書》(編號:[2004]粵高法刑二終字第24號)。這里引用的不是原文,而是為本文敘述便利而進(jìn)行修訂的和原文一致的一個(gè)表述。
將上述判決理由視為“法律知識”,是因?yàn)?在現(xiàn)行的中國法律制度中,并無相應(yīng)的明確條文規(guī)定;另因?yàn)?法院的這種表述,與前述“理論中的法律知識”樣本里的“學(xué)者闡述”一樣,表達(dá)了法院對法律現(xiàn)象的“何以如此”的思想把握,表現(xiàn)了法院關(guān)于法律現(xiàn)象的原理性質(zhì)的認(rèn)識和理解。
但其在實(shí)踐中,所謂實(shí)踐中,意思是其目的在于通過“原理”的闡述,更準(zhǔn)確的說,是通過“原理”式的話語宣布,以論證一種司法判決為正確,試圖解決實(shí)踐的法律紛爭,而非僅表達(dá)對“法律現(xiàn)象中的規(guī)律”的認(rèn)識,亦非僅表達(dá)“原理”本身的內(nèi)容涵義。就此“目的”而言,可清晰發(fā)現(xiàn),其具有明顯的“當(dāng)下的實(shí)踐參與欲望”,具有明顯“當(dāng)下實(shí)踐立場”的表達(dá)、宣揚(yáng),試圖論證作為被告人的法官,及處于類似境地的其他“被告人”法官,在其行為中,并不存在公訴一方指控的“玩忽職守罪”。
二、實(shí)踐法律知識的“非中立性”
閱讀經(jīng)驗(yàn)樣本,不僅意在使敘述成為具體實(shí)在的敘述,此并非重要;重要的是對本文主題而言,意在提示源自法律實(shí)踐本身的經(jīng)驗(yàn)樣本必定是不可回避的切入路徑,是理解實(shí)質(zhì)問題的基本場所,并且是論證的關(guān)鍵起點(diǎn)。
展開對比,可看到,關(guān)于“當(dāng)事人證明責(zé)任”或“舉證責(zé)任”,作為“法律知識”的具體內(nèi)容,如“法官職能的原理”,或“法官格守職能的意義”等,在理論樣本和實(shí)踐樣本中,非常類似。換言之,兩個(gè)樣本中的知識表達(dá)及知識的論證,包括邏輯意向、說理結(jié)構(gòu)、敘述機(jī)制,甚至關(guān)鍵詞的使用,均十分接近。它們本身給人們的印象,正是闡述同一涵義的“原理”性內(nèi)容的“法律知識”。
問題是什么?
首先可指出,盡管在“實(shí)踐樣本”中可讀到“原理”性的且可能是“規(guī)律”性的“法律知識”,但這些“法律知識”,不是“中立性”的,并非每個(gè)人均會(huì)贊同,它們具有爭議性質(zhì)。因?yàn)?在上述案例的關(guān)于法律糾紛和法律審判的實(shí)踐中運(yùn)用“法律知識”,實(shí)際上是法院正在運(yùn)用一種理由去論證自己的法律觀點(diǎn),同時(shí),用其去對抗他者——公訴一方——的法律觀點(diǎn)。為說明這點(diǎn),進(jìn)而為本文導(dǎo)論主題闡述鋪平道路,需再返回到上述實(shí)踐性的案例中。
在起訴作為被告人的法官時(shí),公訴一方具有兩個(gè)主要觀點(diǎn)(當(dāng)然,還有其他不是特別重要的觀點(diǎn)):第一,作為一名職業(yè)的、且從事16年審判工作的法官,被告人應(yīng)在民事訴訟中發(fā)覺“民事被告宣稱被脅迫簽署借據(jù)”的嚴(yán)重性;同時(shí),因?yàn)榫哂休^豐富的審判經(jīng)驗(yàn),被告人應(yīng)在民事被告宣稱自己被脅迫時(shí),預(yù)見判決可能出現(xiàn)錯(cuò)誤,進(jìn)而預(yù)見可能出現(xiàn)不幸后果,如被后來事實(shí)證明的自殺后果;第二,民事訴訟中“誰主張誰舉證”,是針對一般民事訴訟而言的;當(dāng)民事訴訟涉及刑事問題時(shí),法官應(yīng)以例外方式遵循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1]這里指《刑事訴訟法》第84條規(guī)定:“任何單位和個(gè)人發(fā)現(xiàn)有犯罪事實(shí)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權(quán)利也有義務(wù)向公安機(jī)關(guān)、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報(bào)案或者舉報(bào)。”將案件移交其他司法機(jī)關(guān),否則,便未認(rèn)真履行自己的職責(zé)。[2]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書》(編號:[2004]粵高法刑二終字第24號)。這里引用的,也非原文,而是經(jīng)過修訂的與原文意思一致的表述。
可發(fā)現(xiàn),公訴一方實(shí)質(zhì)上認(rèn)為,在涉及刑事問題時(shí),民事訴訟中的法官,尤其是具有多年審判經(jīng)驗(yàn)的法官莫兆軍[3]關(guān)于莫兆軍的“多年審判經(jīng)驗(yàn)”,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書》(編號:[2004]粵高法刑二終字第24號)。此外,莫兆軍是法院民庭副庭長。參見余亞蓮、朱艷秀、鄭碧容《無罪法官回家養(yǎng)豬:莫兆軍的悲劇結(jié)束了嗎?》,《新快報(bào)》2003年8月3日,第A11版。,不能僵化地固守“誰主張誰舉證”,進(jìn)而僵化地固守自己民事審判者的角色。因此,公訴一方是在潛在地陳述另外一種“法律知識”:民事訴訟中,“誰主張誰舉證”的運(yùn)用,并非沒有例外情形;此外,必要時(shí),法官角色可發(fā)生變化,如追查可能存在的刑事問題或證據(jù)。
這種“法律知識”和法院提出的“法律知識”,在案件具體語境中彼此沖突,至少不甚協(xié)調(diào)。而且,事實(shí)上,當(dāng)一審法院作出判決,表達(dá)自己類似上述二審法院提出的“法律知識”時(shí),公訴一方提出了抗訴,在抗訴中,進(jìn)一步表達(dá)了上面提到的己方“法律觀點(diǎn)”。公訴一方依然認(rèn)為,無論以刑事訴訟法等法律條文論,還是以其他經(jīng)驗(yàn)常識論,作為被告人的法官,均應(yīng)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此外,終審判決后,同樣依然有人認(rèn)為法院以自己的“法律知識”作為判決理由,不能成立。[1]例子,參見朱志達(dá)《莫兆軍案的價(jià)值》,《廈門晚報(bào)》,2004年7月3日,第6版;另見蟬娟(編輯)《莫兆軍,為何你的命運(yùn)總牽動(dòng)著我們》,中國法院網(wǎng)《法治論壇》第八期電子雜志,2006年4月28日發(fā)布,其中許多網(wǎng)友都提出類似看法。
一個(gè)枝節(jié)問題需要澄清。此案中,公訴一方和法院一方,均另外提出法律的明文規(guī)定作為自己的直接對抗依據(jù)。公訴一方提到《刑事訴訟法》第84條的規(guī)定:任何單位和個(gè)人發(fā)現(xiàn)有犯罪事實(shí)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權(quán)利也有義務(wù)向公安機(jī)關(guān)、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報(bào)案或者舉報(bào)。法院一方提到《民事訴訟法》第64條的規(guī)定:當(dāng)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zé)任提供證據(jù)。如果堅(jiān)持法條主義[2]所以提到法條主義,因?yàn)椋藗兛蔂庌q,《刑事訴訟法》第84條規(guī)定中的“任何單位和個(gè)人”,未必包含了法院和法官;這條規(guī)定閱讀起來,尤其是和其他條文相互對應(yīng)地閱讀,可發(fā)覺這里的“任何單位和個(gè)人”,似乎是指公安司法機(jī)構(gòu)之外的“任何單位和個(gè)人”,至少,可這樣理解。否則,我們也就可認(rèn)為,如果“公安機(jī)關(guān)”發(fā)現(xiàn)了“犯罪事實(shí)”或“犯罪嫌疑人”,可向檢察機(jī)關(guān)或法院“報(bào)案”或“舉報(bào)”;如果“檢察機(jī)關(guān)”發(fā)現(xiàn)了“犯罪事實(shí)”或“犯罪嫌疑人”,可向法院“報(bào)案”或“舉報(bào)”。顯然,這樣理解非常古怪。法條主義主要主張,以明文的文字規(guī)定為根據(jù)最適宜。如果根據(jù)明文文字,“任何單位和個(gè)人”,當(dāng)然包含了“法院和法官”。,則雙方在此均扎實(shí)地屹立在自己的直接法律規(guī)定的依據(jù)上;而且,兩條法律規(guī)定,均可直接支持各自的法律觀點(diǎn)。[3]當(dāng)然,關(guān)于《刑事訴訟法》第84條的規(guī)定,作為被告人的法官,是否在民事訴訟中的確屬于“發(fā)現(xiàn)有犯罪事實(shí)或犯罪嫌疑人”,也是可爭論的。僅依據(jù)民事訴訟中的被告宣稱“對方涉嫌犯罪”,可能不能認(rèn)為這就等于作為被告人的法官面對了“犯罪事實(shí)或犯罪嫌疑人”,因?yàn)椋胺缸锸聦?shí)或犯罪嫌疑人”的認(rèn)定,需要一定證據(jù),而民事訴訟中的被告并未提出證據(jù)。與此相對,關(guān)于《民事訴訟法》第64條的規(guī)定,眾所周知,其中第2款規(guī)定,“當(dāng)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jù),或者人民法院認(rèn)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jù),人民法院應(yīng)當(dāng)調(diào)查收集”。作為被告人的法官,在審理民事案件中,遇到被告提出對方涉嫌犯罪,是否應(yīng)當(dāng)自行調(diào)查收集證據(jù),也是可爭論的。這位法官的確詢問了當(dāng)事人,但這也許不夠。但正是因?yàn)楦髯跃鶕碛兄苯拥姆梢?guī)定作為依據(jù),同時(shí),兩個(gè)法律規(guī)定,在這個(gè)案件中,[4]所以在“在這個(gè)案件中”底下加上著重符號,因?yàn)椋氡砻髟谄渌讣形幢厝绱恕?沙蔀橄嗷骨易C明力量對等的硬性依據(jù)(在此,當(dāng)然并非認(rèn)為它們相互矛盾),故提出其他論證理由,如“法律知識”,則為雙方不得不努力爭取的一個(gè)法律策略。
這個(gè)意義上,如同上面所述,人們勢必需要且特別側(cè)重將視線焦點(diǎn)轉(zhuǎn)向“法律知識”(當(dāng)然,可能還有其他觀點(diǎn)論證[1]雙方另外提出的理由,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書》(編號:[2004]粵高法刑二終字第24號),及我的一篇論文歸納,請見劉星《司法中的法律論證資源辨析:在“充分”上追問——基于一份終審裁定書》,《法制與社會(huì)發(fā)展》2005年第1期,第103—110頁。也需注意)。如果這樣轉(zhuǎn)向,經(jīng)過前面關(guān)于“法律知識”的分析,重復(fù)而言,可看出法院在審判中運(yùn)用的“法律知識”,并非沒有爭議,并非可作為“中立”的知識進(jìn)而廣泛地為他者接受。
三、實(shí)踐法律知識的“立場”
提出上述“實(shí)踐中”的法律知識“并非沒有爭議”,并非可作為“中立”的知識廣泛地為他者接受,這意味著什么?
一個(gè)思路,或許可逐漸清晰,即需要看到且深入理解“實(shí)踐中”的法律知識的“實(shí)踐立場”,及“實(shí)踐目的”。我們依然從上述案件審理本身進(jìn)入,其中,至少可注意四個(gè)背景。第一,如果判決被告人莫兆軍法官的“玩忽職守罪”成立,則日后,其他法官在民事訴訟中,便可能非常擔(dān)心類似情形再次出現(xiàn)。實(shí)踐中,當(dāng)事人以“對方涉嫌犯罪”為由,要求法官調(diào)查,并且宣稱自己冤枉,又以“極端形式”要求法官作出對自己有利的審理,可能時(shí)常發(fā)生。這種情況下,其他法官鑒于“玩忽職守罪”的判決,為保護(hù)自己,會(huì)盡力采取各種方式放棄原來應(yīng)進(jìn)行的審判程序,如將自己獨(dú)任審判的案件,以其“復(fù)雜”的方式,提議交給合議庭,甚至審判委員會(huì)。即便合議庭,也完全可能為減少自己幾個(gè)人的壓力,盡力將案件提議交給審判委員會(huì)。因?yàn)?法官均知道,此時(shí),“集體出面”是保護(hù)自己、減少風(fēng)險(xiǎn)的最好方式。而民事訴訟的獨(dú)任審判、簡易審判,均有可能因此而形同虛設(shè)。事實(shí)上,在上述案件審理過程中,作為被告人法官的當(dāng)?shù)胤ㄔ?其中一些法官,在該法官被捕后,便思考如何躲避獨(dú)任審判、簡易審判。[2]參見賴穎寧《被告自殺法官受審追蹤:法官稱原審改判不算錯(cuò)案》,《南方都市報(bào)》2003年4月26日,第A18版。類似擔(dān)憂,參見李富金《法官——職業(yè)與風(fēng)險(xiǎn)同在》,《法制日報(bào)》2003年12月11日,第11版。這里,可清晰發(fā)現(xiàn)對法官的負(fù)面激勵(lì)。對此背景,法院在審判“玩忽職守罪”是否成立時(shí),勢必需要考慮。
第二,負(fù)面激勵(lì)不僅對法官存在,對某類當(dāng)事人亦存在。如果當(dāng)事人——一般而言可能是被告——發(fā)現(xiàn),提出“對方涉嫌犯罪”等理由,可促使法官停止民事訴訟,轉(zhuǎn)而調(diào)查刑事問題,或轉(zhuǎn)而進(jìn)入其他較復(fù)雜的程序,從而可使自己處于較有利的訴訟處境,則他們常會(huì)發(fā)覺此為“拖延審判”的較佳方案。故法院期待的審判效率,及作為對方當(dāng)事人——一般而言可能是原告——所期待的“及時(shí)審判”,便可能化作泡影。審判“玩忽職守罪”是否成立的法院,對此實(shí)踐背景,同樣不能忽略不計(jì)。
第三,與第二點(diǎn)相關(guān),如果某類當(dāng)事人基于“判決法官玩忽職守罪”的激勵(lì),不斷在民事訴訟中提出“對方涉嫌犯罪”,則在法院看來,這極可能導(dǎo)致民事訴訟制度出現(xiàn)根本性的失靈。因?yàn)?所有民事訴訟均有可能因?yàn)椤皩Ψ缴嫦臃缸铩钡闹鲝?轉(zhuǎn)入諸如刑事訴訟等其他法律程序。應(yīng)注意,在判決“玩忽職守罪”是否成立時(shí),法院的確提到:如果在民事訴訟中,一方提出對方涉嫌犯罪,將其作為自己抗辯理由,要求法官必須終止民事訴訟,將案件轉(zhuǎn)入諸如刑事偵查等程序,則任何當(dāng)事人均有可能運(yùn)用“僅指稱對方涉嫌犯罪”的方式或機(jī)會(huì),要求終止民事訴訟;如此,民事訴訟制度完全可能癱瘓。[1]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書》(編號:[2004]粵高法刑二終字第24號)。這里引用的,也非原文,而是修訂過的與原文意思一致的表述。
第四,公訴意見指出,“因?yàn)榫哂休^豐富的審判經(jīng)驗(yàn),被告人應(yīng)在民事被告宣稱自己被脅迫時(shí),預(yù)見判決可能出現(xiàn)錯(cuò)誤,進(jìn)而預(yù)見可能出現(xiàn)不幸后果”。但站在法院角度,公訴意見等于對法官提出了不切實(shí)際甚至嚴(yán)厲苛刻的要求。民事訴訟中的法官,為此將會(huì)感到巨大的精神壓力,并且常會(huì)感到困惑迷惘,如“怎樣預(yù)見”?[2]有的民庭法官,即表達(dá)了類似擔(dān)憂。他們說:“對于我和我的同事而言,莫法官的入獄使我們很敏感,甚至很不安,因?yàn)槲覀円彩敲裢サ姆ü佟!眳⒁姺ㄖ握搲W(wǎng)友ZOSU《誰來關(guān)注“莫兆軍后遺癥”》(2003年7月7日發(fā)布),登載于中國法院網(wǎng),網(wǎng)址: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 =66704,訪問時(shí)間:2007年2月1日。這對民事審判非常不利。審理“玩忽職守罪”是否成立的法院,對此背景,同樣不能視而不見。
除上述四個(gè)背景,當(dāng)然可提到進(jìn)而分析其他可能的背景。但上面四個(gè)背景及其分析,足以提示問題的關(guān)鍵:必須看到且深入理解“實(shí)踐立場”“實(shí)踐目的”所包含的意義。
凸顯“實(shí)踐立場”“實(shí)踐目的”,意味著需傳遞這樣一個(gè)信息:法律語境中,“立場”“目的”,總是針對某方或某一群體的利益愿望而言。此不僅對法律訴訟中的當(dāng)事人來說頗為明確,而且對法律共同體內(nèi)部的法律人來說亦可看到;盡管,此非必然。在法律共同體內(nèi)部,因?yàn)槁殬I(yè)分工,階層團(tuán)體性的“利益期待”的形成,在某些情況下不言而喻。當(dāng)然,需要說明的,則是“利益”并不一定體現(xiàn)為社會(huì)物質(zhì)資源的直接的份額占有,其也能體現(xiàn)為對自己的某一層面的“順利”“便利”“成效”等隱性收益。
如果這樣展開,在上述四個(gè)背景中,則可清晰發(fā)現(xiàn)法院作為群體的“利益期待”。第一個(gè)背景,說明法院擔(dān)心判決的負(fù)面激勵(lì):因?yàn)榉ü贀?dān)心承擔(dān)責(zé)任,從而將本應(yīng)適用的審判方式設(shè)法轉(zhuǎn)變?yōu)槠渌麑徟蟹绞?故法院可能面對內(nèi)部壓力集中(主要對審判委員會(huì))的困境。第二個(gè)背景,說明法院擔(dān)心審判效率降低,盡管首先是“公共效率”問題,但也部分包含法院自己“便利與否”的問題。第三個(gè)背景,至少說明法院擔(dān)心面臨不易處理的、因當(dāng)事人不斷提出“對方涉嫌犯罪”而引發(fā)的審判障礙,此障礙,又在沖抵法院自己的“便利”期待。第四個(gè)背景,說明法院不希望作為階層內(nèi)部成員的法官常面對巨大的精神壓力,這種壓力,和法院自己期待的“順利”“便利”“成效”,同樣相互矛盾。
自然,對上述展開的辨析,有人可能并不認(rèn)同。有人可能指出,上述四個(gè)背景,實(shí)際上恰恰體現(xiàn)了審判“玩忽職守罪”是否成立的法院,對一般法官能“公正”“有效率”地審判案件的愿望,同時(shí)亦體現(xiàn)了社會(huì)一般公眾對法院的普遍要求,故未必應(yīng)從“利益期待”的實(shí)踐立場、實(shí)踐目的的角度來揣測其中的傾向。但從對立面特別是在這一具體案件中公訴一方的角度深入討論,依然且進(jìn)一步可發(fā)現(xiàn)其中的確存在傾向問題。
公訴一方可認(rèn)為,首先,民事訴訟中的當(dāng)事人,特別是被告,并不一定都會(huì)由于這一判決而采用“宣稱對方涉嫌犯罪”的策略。因?yàn)?其中總包含一定的遭遇公共權(quán)力制裁的風(fēng)險(xiǎn)。如果宣稱對方涉嫌犯罪,而國家機(jī)構(gòu)調(diào)動(dòng)審查程序,審查結(jié)果是“誣告”等,則“宣稱對方涉嫌犯罪”需付出沉重代價(jià)。其次,在獨(dú)任審判和簡易審判中,法官盡到自己謹(jǐn)慎職責(zé),不會(huì)存在被定為“玩忽職守”行為的可能性。這里問題的關(guān)鍵是,其一,在于國家完全可運(yùn)用公共權(quán)力嚴(yán)厲地對付“誣稱對方涉嫌犯罪”,提高“誣稱”的沉重成本;其二,法官完全可以沒有過多負(fù)擔(dān)以盡職盡責(zé),何況要求具有豐富經(jīng)驗(yàn)的法官在民事訴訟中盡職盡責(zé),并非苛刻。故法院一方的“背景”考慮,無法回避被認(rèn)為具有“傾向”的質(zhì)疑。
其實(shí),更深入的證據(jù),在于判決作為被告人的法官“玩忽職守罪”不成立時(shí),法院明顯否定了“以自殺作為表征的民事訴訟中的被告群體”的利益。在此,事實(shí)上,法院表達(dá)了這樣一個(gè)“立場”“目的”的含義:被告群體自己應(yīng)具有必要的法律自我保護(hù)意識,否則,只能自己承擔(dān)不利后果。判決書中,法院的確指出:民事訴訟中的被告不行使法律賦予的各項(xiàng)權(quán)利,不向公安機(jī)關(guān)報(bào)案,在一審判決明顯不利于自己的情況下依然沒有上訴、申訴,使判決結(jié)果進(jìn)入執(zhí)行程序,對此,被告自己負(fù)有明顯的責(zé)任。[1]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書》(編號:[2004]粵高法刑二終字第24號)。引用的不是原文,是經(jīng)過文字整理、與原文意思一致的表述。
顯然可發(fā)現(xiàn),針對“對方涉嫌犯罪”的問題,在公民自主救濟(jì)和國家主動(dòng)救濟(jì)之間——如果提升,可說在這樣兩個(gè)同樣重要、同樣需重視的社會(huì)價(jià)值之間——法院實(shí)際上是在強(qiáng)調(diào)前者。而強(qiáng)調(diào)前者,我們再次可認(rèn)為,不是純粹“中立”的,“沒有立場”的,因?yàn)?對那些具有足夠法律意識且具有各種便利條件的當(dāng)事人而言,它是有利的,且是有效的,反之,對那些缺乏必要的法律意識且缺乏必要的便利條件的當(dāng)事人而言,其未必有利、有效。這意味著,人們當(dāng)然可反問,對那些非常貧困、文化水平極低的當(dāng)事人來說,難道的確應(yīng)主張“公民自主救濟(jì)”,而不主張“國家主動(dòng)救濟(jì)”?
如果對照公訴一方的主張,可更為清晰地發(fā)現(xiàn)法院一方在上述兩個(gè)重要社會(huì)價(jià)值選擇問題上的“傾向”。公訴一方,在提出“不能僵化固守‘誰主張誰舉證’,進(jìn)而僵化固守自己民事審判者的角色”時(shí),特別暗含了對應(yīng)性的重要社會(huì)價(jià)值的選擇:至少對某些缺乏法律資源支持的當(dāng)事人而言,或?qū)δ切┴叫璺ㄔ禾峁┓蓭椭纳鐣?huì)群體而言,如其缺乏法律意識,甚至不主動(dòng)想到“法律協(xié)助”,民事訴訟中的法官體現(xiàn)“國家主動(dòng)救濟(jì)”依然非常必要;一味強(qiáng)調(diào)“公民自主救濟(jì)”,實(shí)質(zhì)上,等于忽略一類當(dāng)事人或社會(huì)群體的需求,進(jìn)一步,等于否定其重要利益;如果措辭嚴(yán)厲,則其等于忘記“人民法官”中的“人民”修飾一詞的根本要求。[1]有人也的確這樣認(rèn)為。例子,參見簫志《葫蘆僧判斷葫蘆案現(xiàn)代版》,《方圓》2003年第2期,第10—16頁。
概言之,“誰主張誰舉證”,其背后深層的“實(shí)踐立場”“實(shí)踐目的”的內(nèi)容,實(shí)際上包含了自由主義政治觀的程序正義主義。[2]這里用“包含了”的表述,意味著我不完全排除“強(qiáng)調(diào)法院審判效率”也包含了“為民服務(wù)”的意思,而“為民服務(wù)”,未必就一定是自由主義政治觀的內(nèi)容。而認(rèn)為法院適當(dāng)時(shí)主動(dòng)調(diào)查證據(jù),其背后深層的“實(shí)踐立場”“實(shí)踐目的”的內(nèi)容,實(shí)際上包含了左翼民眾政治觀的實(shí)體正義主義。[3]有人就指出過,應(yīng)當(dāng)且必須緩解群眾對法院審判的不滿,許多當(dāng)事人上訪,是因?yàn)樽C據(jù)不足的問題,而且自己沒有舉證能力。例子,參見尚曉宇《杜崇煙代表:適用“誰主張誰舉證”要結(jié)合國情》,《檢察日報(bào)》,2006年3月10日,第002版。
四、理論者思考的“法律實(shí)踐知識”與實(shí)踐者思考的“法學(xué)理論知識”
在此,如果“實(shí)踐中的法律知識”包含“實(shí)踐立場”“實(shí)踐目的”,則“理論中的法律知識”會(huì)怎樣?
前文提到,法學(xué)樣本中關(guān)于“民事訴訟證明責(zé)任”的“法律知識”,和上述案件中關(guān)于“民事訴訟證明責(zé)任”的“法律知識”,在“邏輯意向”“說理結(jié)構(gòu)”“敘述機(jī)制”,甚至“關(guān)鍵詞的使用”等方面,基本相同。其實(shí),此已暗示,可以且必須在“相互對應(yīng)”中挖掘、揭示“理論中的法律知識”的同樣性質(zhì),即同樣的“實(shí)踐立場”“實(shí)踐目的”。
首先,轉(zhuǎn)換角色,設(shè)想——實(shí)際上是考察——法學(xué)知識者如何思考“實(shí)踐問題”。
我們可設(shè)想,其不純?yōu)樗枷朐囼?yàn),且其亦具有現(xiàn)實(shí)意圖。因?yàn)?可發(fā)現(xiàn)許多法學(xué)理論研究者面對“實(shí)踐問題”時(shí),的確會(huì)提出觀點(diǎn)和論證,在中國,當(dāng)然包括在西方,均如此。而問題的關(guān)鍵,則是當(dāng)提出觀點(diǎn)和論證時(shí),其討論盡管可能具有“學(xué)術(shù)話語”的包裝、“知識精英”的外表,甚至還有“科學(xué)知識表達(dá)”的印跡,但“解決實(shí)踐問題”的訴求,使其必須像法律實(shí)踐者一樣,具體說明如何解決“實(shí)踐問題”。如當(dāng)中國發(fā)生“劉涌案”[1]參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編號:[2003]刑提字第5號)。、“黃碟案”[2]關(guān)于這一眾所周知的、富有爭議的案件,參見蘇力《也許正在發(fā)生:轉(zhuǎn)向中國的法學(xué)》,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25—126頁。、“孫志剛案”[3]可參見《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編號:[2003]穗中法刑初字第134號)。,及前面討論的“莫兆軍案”等實(shí)踐問題時(shí),又如當(dāng)美國發(fā)生“辛普森案”[4]可參見Walter Hixson,“Black and White:The O.J.Simpson Case(1995)”,in Annette Gordon-Reed (ed.),Race on Trial:Law and Justice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總統(tǒng)選票糾紛案”[5]可參見Christopher Banks,David Cohen,and John Green(eds.),The Final Arbier:The Consequences of Bush v.Gore for Law and Politc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5。等實(shí)踐問題時(shí),盡管眾多學(xué)者展現(xiàn)了“學(xué)術(shù)”、“知識”和“科學(xué)”的面相,但仍可清晰發(fā)現(xiàn),其均有積極、具體的“解決實(shí)踐問題”的意向,表達(dá)了如何解決實(shí)踐問題的思考,且此為不可避免。[6]討論這些案件的例子是人們熟知的。而關(guān)于“莫兆軍案”,學(xué)者討論的例子,參見栩(編輯)《反思:莫兆軍案誰之錯(cuò)》,《新快報(bào)》,2003年8月3日,第A11版。故這里,便逐漸通向了“實(shí)踐立場”“實(shí)踐目的”的道路。
更深入的問題關(guān)鍵,則是如果法學(xué)知識者積極表達(dá)了對“實(shí)踐”的意見,則意見中必然包含了“知識路向”。法學(xué)知識者不可能,亦不會(huì)使自己對“實(shí)踐”的意見和自己的“知識路向”發(fā)生矛盾,即使部分的不協(xié)調(diào),或在表達(dá)對“實(shí)踐”的意見時(shí),不運(yùn)用自己的“知識路向”(當(dāng)然,有時(shí)會(huì)出現(xiàn)個(gè)別意外)。這個(gè)意義上,法學(xué)知識者的“知識路向”,實(shí)際上是自己對“實(shí)踐”的意見的前提、基礎(chǔ),當(dāng)然,亦為論證資源。故一個(gè)深層結(jié)構(gòu)逐漸浮現(xiàn)出來:其“知識路向”和“實(shí)踐立場”“實(shí)踐目的”,存在著某種直接相通的關(guān)系。
當(dāng)然不能認(rèn)為,法學(xué)知識者在討論“實(shí)踐問題”時(shí),本身即必然預(yù)先確立自己的“實(shí)踐立場”“實(shí)踐目的”,以“實(shí)踐立場”“實(shí)踐目的”作為出發(fā)點(diǎn)。但“實(shí)踐問題”中的“對立性”“爭議性”,使法學(xué)知識者,亦使作為前提、基礎(chǔ)、論證資源的“知識路向”,無法逃避“實(shí)踐立場”“實(shí)踐目的”的選擇。所謂“對立性”“爭議性”,實(shí)際上是源于法律語境中的社會(huì)糾紛的基本特征。社會(huì)糾紛的存在,意味著利益的不同和矛盾,同時(shí)也意味著價(jià)值觀念的不同和矛盾;而利益和價(jià)值觀念的不同和矛盾,本身即為日常實(shí)踐的組成部分。故法學(xué)知識者、“知識路向”支持一個(gè)實(shí)踐觀點(diǎn),在較普遍的意義上,即為支持一個(gè)利益,或一個(gè)價(jià)值觀念。法學(xué)知識者及這種“知識路向”,在此,至少外在地和一種“實(shí)踐立場”“實(shí)踐目的”出現(xiàn)“合謀”。
進(jìn)一步,還需深入追究的是:如果集中于“知識路向”本身,則可發(fā)現(xiàn),這種“知識”其實(shí)在邏輯上必然支撐著某一實(shí)踐觀點(diǎn),進(jìn)而支撐著某一利益,或某一價(jià)值觀念。因?yàn)?其能成為某一實(shí)踐觀點(diǎn)、利益、價(jià)值觀念的有效的具體支持理由。
關(guān)于支持理由的問題,應(yīng)看到,即使“在理論中”,理論思考又在呈現(xiàn)“可辯性”。“可辯性”包含這樣一個(gè)意思:知識可不斷反思、對抗;故知識也需在反思、對抗中證明自己的正當(dāng)性。嚴(yán)格說,任何知識均如此。而在法律理論中,因?yàn)榉伞⒎▽W(xué)語境更為充滿實(shí)踐爭議、更需務(wù)實(shí)(解決現(xiàn)實(shí)問題),故其也更為明顯。因此,對法學(xué)理論,“知識路向”本身成為某一實(shí)踐觀點(diǎn)、利益、價(jià)值觀念的有效的具體支持理由,不足為奇。
究其根本,可注意,在論證某一實(shí)踐觀點(diǎn)時(shí),人們在一般性的社會(huì)觀念——如倫理、經(jīng)濟(jì)、文化的普遍性觀念——不能成為有效的直接依據(jù)之際,必然會(huì)依賴“說理性”的“知識路向”,以展現(xiàn)自己的“根據(jù)厚重”;而最需注意的,則是如果己方可提出“知識路向”的根據(jù)而對方不能提出,則說服力及可信度,會(huì)向“可提出者”發(fā)生傾斜。故“知識路向”和實(shí)踐觀點(diǎn)的邏輯關(guān)聯(lián),根本無法忽略。在此進(jìn)一步的結(jié)果,則是當(dāng)人們認(rèn)為一方可信時(shí),也就默認(rèn)了一方的某一利益或某一價(jià)值觀念。
再看前面討論的具體法學(xué)樣本。可發(fā)現(xiàn),盡管此樣本提出了“規(guī)律性”的意思,表達(dá)了“客觀性”的欲望,但其也依然暗示,自己提出的諸如與民事訴訟證明責(zé)任相關(guān)的“法律知識”,具有實(shí)踐意義;換言之,其是支持某個(gè)實(shí)踐觀點(diǎn)的。如該樣本提到,這一知識有利于避免“影響法院的審判效率”。[1]李浩:《民事證明責(zé)任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3、81頁。此外,該樣本提出,這一知識具有如下幾點(diǎn)價(jià)值:(一)有利于發(fā)揮當(dāng)事人舉證的主動(dòng)性……訴訟中的任何一方當(dāng)事人都不希望自己承擔(dān)不利的訴訟結(jié)果,正是這種力求避免承擔(dān)不利訴訟結(jié)果的動(dòng)機(jī),推動(dòng)著當(dāng)事人在訴訟中積極地舉證;(二)有利于使當(dāng)事人對裁判中的事實(shí)負(fù)擔(dān)起責(zé)任……因?yàn)槿绻颜{(diào)查收集證據(jù)的責(zé)任置于法院,當(dāng)事實(shí)真?zhèn)尾幻鲿r(shí),當(dāng)事人就會(huì)指責(zé)法院未盡力收集證據(jù),把自己敗訴歸咎于法院;(三)有利于實(shí)現(xiàn)法院在證明活動(dòng)中的職能……如果證據(jù)材料不是由……當(dāng)事人提出,而是由法院去收集和提出,就會(huì)破壞訴訟的基本構(gòu)造,使法院在證明活動(dòng)中處于當(dāng)事人的地位;(四)有利于防止濫行訴訟……防止當(dāng)事人提出子虛烏有的“事實(shí)”。[1]李浩:《民事證明責(zé)任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80—83頁。當(dāng)然還有其他意義,我在這里沒有全部列出。
另外,該樣本提出,如果放棄這一知識,則某些當(dāng)事人便會(huì)故意提出某些實(shí)際上不存在但又難以證明其不存在的事實(shí),阻擾訴訟。[2]李浩:《民事證明責(zé)任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6頁。
而從宏觀出發(fā),該樣本進(jìn)一步分析了“國家主義”的證明責(zé)任和“當(dāng)事人主義”的證明責(zé)任的歷史變遷。針對歷史中諸如蘇聯(lián)、東歐社會(huì)主義國家民事訴訟的價(jià)值傾向,該樣本指出:法院在一定情形下主動(dòng)介入調(diào)查取證活動(dòng),既可以為那些在收集證據(jù)活動(dòng)中遇到困難的當(dāng)事人提供有效的幫助,使真正享有權(quán)利的當(dāng)事人不會(huì)由于收集證據(jù)時(shí)遇到客觀上的障礙而受到不利裁判,也有利于法院查明案件的真實(shí)情況。社會(huì)主義訴訟模式的倫理價(jià)值觀也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3]李浩:《民事證明責(zé)任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86—87頁。
顯然,通過樣本的直接表達(dá),可看到,前面提到的該法學(xué)樣本的關(guān)于民事訴訟證明責(zé)任的“知識路向”,即關(guān)于“法院職責(zé)原理”的“法律知識”,背后勾連著重要的某種實(shí)踐觀點(diǎn),或某種價(jià)值觀念,直至某種利益;其要么包含著自由主義政治觀的程序正義主義,要么包含著左翼民眾政治觀的實(shí)體正義主義,而從其文本看,顯然是前者。
如果聯(lián)系前述案例樣本,還能看到,其一,該法學(xué)樣本所表達(dá)的上述“意義價(jià)值”,和前面一節(jié)所討論的法院所表達(dá)的“背景考慮”,頗為類似;此從側(cè)面印證其和實(shí)踐意圖存在必然性的邏輯連接。其二,更重要的,可看到,該法學(xué)樣本所表達(dá)的關(guān)于民事訴訟證明責(zé)任的“知識路向”,在邏輯上,完全可成為前面討論的法院一方的具體支持理由;并且,不能排除一種可能:正因?yàn)橐活惱碚撝械摹胺芍R”的傳播,如通過法律教育、法學(xué)思想的被閱讀,這種“知識路向”,成為了實(shí)踐活動(dòng)中的話語意義的邏輯依據(jù)。這個(gè)意義上,結(jié)合前面一節(jié)分析的法院一方體現(xiàn)的支持一種“實(shí)踐立場”“實(shí)踐目的”,及一種價(jià)值觀念和利益的結(jié)構(gòu)機(jī)制,則可認(rèn)定:這里提到的理論中的“知識路向”,亦在支持一種實(shí)踐立場、實(shí)踐目的,及一種價(jià)值觀念和利益。
其次,轉(zhuǎn)換角色,設(shè)想——實(shí)際上是考察——法律實(shí)踐者如何思考“理論問題”。
某些情況下,法律實(shí)踐者如法官、檢察官,完全可較為“純粹法學(xué)”地討論法律問題,換言之,其某些討論,可能和實(shí)踐中的具體問題沒有直接關(guān)系,如撰寫理論性文章、著作,在法學(xué)期刊上發(fā)表學(xué)術(shù)性見解,而中國讀者現(xiàn)在非常熟悉的美國法官波斯納(Richard A.Posner)常撰寫純學(xué)術(shù)著述,或許是最明顯的例子。在此,實(shí)踐者的法學(xué)討論,其功能既在于理論素養(yǎng)的培育、表達(dá),又在于將司法實(shí)踐中發(fā)現(xiàn)的具體問題予以提升,且加以理論化。
但特別重要的,第一,一般情況下,如果足夠自覺,則法律實(shí)踐者常期待將“理論問題”的思考結(jié)果變?yōu)槿蘸髮?shí)踐活動(dòng)的一個(gè)知識根據(jù)。盡管總會(huì)看到,一些法律實(shí)踐者使用“理論大詞”思考、撰寫、討論“理論問題”[1]在最近幾年法院系統(tǒng)論文評選中,可看到大量例子。作為具體例子,可參見萬鄂湘(編)《民商法理論與審判實(shí)務(wù)研究——全國法院第十五屆學(xué)術(shù)討論會(huì)獲獎(jiǎng)?wù)撐摹罚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似乎沒有“具體實(shí)踐”目的,但上述“期待”則更常見。因?yàn)?容易理解,法律共同體內(nèi)部的職業(yè)分工,尤其是“法學(xué)理論工作者”和“法律實(shí)踐工作者”的職業(yè)分工,要求后者必須自我有意識地時(shí)常將“理論”在“實(shí)踐”的平臺中加以展開,至少,主觀上具有這樣的自覺擔(dān)當(dāng)。故法律實(shí)踐者的“理論問題”的思考,常需要甚至必須蟄伏在“日常實(shí)踐”上。進(jìn)一步,當(dāng)法律實(shí)踐者在解決具體法律實(shí)踐問題時(shí),“理論思考”,或通過具體法律案件的討論,或通過判決書寫作方式的直接論證,在“具體法律觀點(diǎn)”上留下印記。這便有如在今天中國及西方司法實(shí)踐中,我們常看到的。在此,概括說,一個(gè)重要結(jié)果則是,通過上述“期待”,理論化的“法律知識”被不斷吸入法律實(shí)踐者的意識之中。
第二,從第一點(diǎn)引伸,被吸取的理論化的“法律知識”,勢必需在邏輯上和法律實(shí)踐者主張的“日常實(shí)踐觀點(diǎn)”,形成有效支持關(guān)系。在這里,一個(gè)篩選機(jī)制不能被忽略,即就日常實(shí)踐看,在法律實(shí)踐者意識中留下印記的,總是那些可利用的“法律知識”。眾所周知,理論化的“法律知識”多種多樣,而在思考、討論中,法律實(shí)踐者可推論、總結(jié)甚至想象許多理論化的“法律知識”。但前面一節(jié)提到的理論中的法律知識的“可辯性”,及法律知識本身的對立性,包括法律實(shí)踐者可意識到的實(shí)踐問題的可爭論性,均會(huì)促使法律實(shí)踐者,作出針對某種理論而來的“甄別選擇”。這種“甄別選擇”的具體結(jié)果,會(huì)隨具體法律問題語境的變化而變化,隨微觀權(quán)力關(guān)系、具體需要策略的變化而變化,但“甄別選擇”本身亦會(huì)受“理論”和“日常實(shí)踐觀點(diǎn)”的邏輯關(guān)系的制約。換言之,從論證角度看,法律實(shí)踐者不會(huì)選擇對自己“日常實(shí)踐觀點(diǎn)”沒有邏輯支持的“理論”。
第三,在思考“理論問題”時(shí),法律實(shí)踐者對法學(xué)工作者的“理論觀點(diǎn)”進(jìn)行思考、汲取、借用,是順理成章的。這符合“思考的經(jīng)濟(jì)原則”,亦為法學(xué)工作者的“話語權(quán)威”發(fā)揮作用而導(dǎo)致的一個(gè)附帶結(jié)果。但具有特殊性的,則是法律實(shí)踐者在參照法學(xué)工作者的“理論觀點(diǎn)”時(shí),并不一定僅是模仿,其常會(huì)自覺或不自覺地,將日常實(shí)踐中親歷性的“具體問題”的背景作為依據(jù)。如中國的司法實(shí)踐機(jī)構(gòu),特別是基層的司法機(jī)構(gòu),在接受法學(xué)理論的訓(xùn)導(dǎo)——聆聽法學(xué)家的講學(xué)、閱讀法學(xué)著作等——之際,常會(huì)有意或無意地,在自我法律實(shí)踐的場景中,建立“思考”聯(lián)系,展開對應(yīng)考察,檢試?yán)碚摰目蛇m用性。[1]在地方法院機(jī)關(guān)雜志所發(fā)表的法律實(shí)踐者的作品中,經(jīng)常可看到大量例子。故法律實(shí)踐者對“理論問題”的思考,具有“實(shí)踐反思性”,而非完全順從規(guī)訓(xùn)。深入看,雖然像前面第一節(jié)提到的,有時(shí)可提到“理論指導(dǎo)實(shí)踐”,法律實(shí)踐者會(huì)接受法學(xué)理論的影響,但這以“可成為日常實(shí)踐的邏輯支持的理由”作為前提。
第四,最重要的,同時(shí)也是屬于非常常識的,則是法律實(shí)踐者思考的“理論問題”和法學(xué)工作者思考的“理論問題”,其知識的性質(zhì)為一致。法律實(shí)踐者,不會(huì)因?yàn)樽约旱穆殬I(yè)角色,使自己的“理論思考”有別于法學(xué)工作者。法律實(shí)踐者可能會(huì)具有較明顯的實(shí)踐動(dòng)機(jī),“實(shí)用地思考理論問題”,但進(jìn)行理論思考時(shí),其功能性的角色可暫時(shí)轉(zhuǎn)化為特定的“法學(xué)工作者”。這也是為何我們時(shí)常可看到法律實(shí)踐者寫出學(xué)術(shù)性的理論著述,如論文、專著,并且感覺其為“法學(xué)工作者”的緣由所在。在此,可進(jìn)一步傳遞的信息是:法律實(shí)踐者頭腦中的“理論知識”,不會(huì)因?yàn)槁殬I(yè)角色的一定時(shí)空的差異,而僅屬于法律實(shí)踐者,其為法學(xué)知識者和法律實(shí)踐者所共享。這一信息的深層涵義是:法律實(shí)踐者勢必會(huì)“潛移默化”地將日常實(shí)踐中的一種實(shí)踐觀點(diǎn),一種價(jià)值觀念或利益,帶入自己“理論問題”的思考,進(jìn)一步,帶入自己理論化的“法律知識”之中,因?yàn)?其總會(huì)展開受前述邏輯關(guān)系制約的“甄別選擇”工作;[1]上面四點(diǎn)分析,對中國來說,在一個(gè)制度背景下可能更需注意。這個(gè)制度背景即1990年代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改革上要求各級法院在裁判文書中盡力充分論證裁判理由。見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最高人民法院公報(bào)》1999年第6期,第186—187頁。而法學(xué)知識者“理論思考”的性質(zhì),從另一方面再次被暴露出來。
五、知識形態(tài)的家族類似
上面展開的分析,將法律實(shí)踐者對“理論問題”的思考,和法學(xué)工作者的“理論問題”的思考,加以對照。其目的是說明它們的同質(zhì)性,進(jìn)而說明它們的“知識形態(tài)”的家族類似。但還需提到另外一點(diǎn):法律實(shí)踐者的“理論思考”,不論從現(xiàn)實(shí)角度看,還是從歷史角度看,實(shí)際上是法學(xué)工作者的“理論思考”的邏輯起點(diǎn)。這意味著,某種意義上,可將法學(xué)工作者的“理論思考”視為法律實(shí)踐者的“理論思考”的進(jìn)一步展開。
從現(xiàn)實(shí)角度看,富有爭議的“法律問題”的一個(gè)特點(diǎn),在于“解決過程常是一個(gè)論證的過程”。或可認(rèn)為,一旦出現(xiàn)富有爭議的“法律問題”,則意味著出現(xiàn)某種“論證需求”。當(dāng)然,首先需澄清,沒有人會(huì)否認(rèn)法律作為秩序而存在時(shí),人們之間的關(guān)系有時(shí)十分平靜,每個(gè)人均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循“法律圖標(biāo)”,沒有爭議從而無須“論證”。但更關(guān)鍵的,則是當(dāng)提到富有爭議的“法律問題”出現(xiàn)時(shí),人們實(shí)際上等于提到“依照法律看”,不同觀點(diǎn)、價(jià)值觀念、利益出現(xiàn)沖突,故爭議性的“問題”亦出現(xiàn)了。進(jìn)一步,如果這類“問題”出現(xiàn),并且法律的明確規(guī)定在人們看來不能直接適用,則法律意義上的“理論論證”便無法回避;人們勢必要從“法律理論論證”的角度,闡述自己觀點(diǎn)、價(jià)值觀念、利益是正確的。[2]這是就法律的一般情況而言的。因?yàn)椋袝r(shí),尤其是在某些特別的歷史條件下,人們僅需要權(quán)威性的人物,以解決這類問題,而不需要“法律論證”。
為深入討論,提到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一個(gè)早期法律思想,頗為必要。在他看來,當(dāng)出現(xiàn)富有爭議的“法律問題”時(shí),人們?yōu)檎撟C自己的具體法律主張,需援引大量論證資源,其中,理論化的法律原理,是非常重要的論證資源。[1]參見Ronald Dworkin,Law's 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90。德沃金的思想暗含如下一個(gè)含義:法律論證的過程,實(shí)際上是不斷增加理論化的法律理由的過程。為理解德沃金思想的這個(gè)含義,可回到前面提到的“作為被告人的法官‘玩忽職守罪’”案件的問題。該案審判中,公訴一方和法院一方,在提出具體的法律規(guī)定作為直接依據(jù)時(shí),并且在這些直接依據(jù)“勢均力敵”時(shí)(見前第三節(jié)),均不得不提出理論化的法律理由,以進(jìn)一步論證自己的法律主張。雙方雖然另運(yùn)用經(jīng)驗(yàn)常識、社會(huì)情理等資源,但更著力運(yùn)用的是法律原理。此清晰表明,德沃金思想含義的意思是:越試圖“充分論證”,越依賴?yán)碚摶姆稍淼牟粩嘣?/p>
但德沃金的思路中,更重要的一個(gè)目標(biāo)是:不斷用來論證法律主張的法律原理,可不斷抽象化,而越抽象化,越可成為人們?nèi)粘Kf的“法律理論”的一個(gè)組成部分,甚至是頗為抽象化、一般化的“法理學(xué)”的組成部分。[2]Ronald Dworkin,Law's 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90.這意味著,為利用“法律論證”以證明自己的觀點(diǎn)、價(jià)值觀念、利益是正確的,另需要從若干角度,更重要的,從潛層到深層、從具體到一般,運(yùn)用“法律原理”直至“法律理論”,展開推進(jìn)。就此看,可理解為何德沃金說,“法理學(xué)是司法審判的一般部分”[3]Ronald Dworkin,Law's 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90.;“在法理學(xué)和司法審判或其他法律實(shí)踐之間,并不存在明確的界線”[4]Ronald Dworkin,Law's 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90.德沃金的這些思想,早在1960年代即已初露端倪。參見Ronald 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69。。
現(xiàn)在,用德沃金自己青睞的例子——里格斯訴帕爾瑪(Riggs v. Palmer)案,以說明其更重要的目標(biāo)。該案眾所周知,其他美國學(xué)者[5]比如,卡多佐(Benjamin Cardozo)和泰勒(Rinchard Taylor)的討論。參見本杰明·卡多佐《司法過程的性質(zhì)》,蘇力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3年,第 23—25頁。另見 Richard Taylor,“Law and Morality”.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43(1968),p.626。亦不厭其煩地討論。案件中,一名法官[6]即Justice Gray。堅(jiān)持認(rèn)為,第一,謀殺被繼承人的帕爾瑪(Elmer Palmer)沒有繼承權(quán);第二,雖然當(dāng)時(shí)《遺囑法》條文未提到“謀殺被繼承人者喪失繼承權(quán)”,但《遺囑法》中存在隱含意思;第三,應(yīng)看到法條的明文意思,亦應(yīng)看到法條的隱含意思;第四,應(yīng)注意以往法條和判例中的潛在法律原則,而其中之一,則是“不能因?yàn)檫^錯(cuò)而獲得利益”。[1]可參見Ronald Dworkin,Law's 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17—18,123—124。在這名法官的論證中,十分明顯,不僅“不能因?yàn)檫^錯(cuò)而獲得利益”的一般法律原理被利用,而且,“法律既包含明文意思又包含隱含意思”的法理學(xué)的一般原理,也被利用;就后者而言,其顯然是在表達(dá)一個(gè)法律定義的外延、含義。當(dāng)然,像現(xiàn)在中國學(xué)者普遍接受而德沃金曾著重論述的,還可提到,其中“法律原則是法律的一個(gè)組成部分”的法理學(xué)的一般原理,亦被利用。可看出,在這名法官的論證中,兩個(gè)法律原理,即“隱含法律是法律的組成部分”和“法律原則是法律的組成部分”,是不同角度的,而且,它們相對“不能因?yàn)檫^錯(cuò)而獲得利益”的法律原理,較為深層、抽象、一般;而事實(shí)上,它們正是法理學(xué)理論中的一些重要觀念。
如果進(jìn)一步分析,則可認(rèn)為,德沃金實(shí)質(zhì)上提出了一個(gè)深刻問題:如果法理學(xué)的法律原理,包括法律理論,可成為司法主張的論證資源,那么,為何可認(rèn)為這些法律原理及法律理論,是“描述性”(descriptive)的,進(jìn)一步,認(rèn)為其“中立”“客觀”,或認(rèn)為其是“客觀知識”?
提到謀殺被繼承人案中的法官推理,德沃金意在論證,所有法律原理,包括所有法律理論,均不純粹是“描述性”的,進(jìn)而“中立”“客觀”,或?yàn)椤翱陀^知識”,因?yàn)?其亦內(nèi)在地可被用以論證一個(gè)實(shí)踐的法律主張,即論證一個(gè)關(guān)于“是否應(yīng)當(dāng)”的“實(shí)踐立場”——“能否殺人取財(cái)”;更重要的,其是應(yīng)對對立一方法律論證的手段。而審判謀殺被繼承人案件的另外一名法官[2]即Justice Earl。——對立一方——的法律推理,可十分簡略地概括為:第一,帕爾瑪可繼承遺產(chǎn),因?yàn)椤哆z囑法》僅規(guī)定了遺囑有效的條件,未提到謀殺被繼承人的問題;第二,法律只能是明文規(guī)定;第三,法律原則是條文和判例的抽象結(jié)果,故不是法律的一部分;第四,依法判決,必須是指依據(jù)法律的正式文字。[3]參見Ronald Dworkin,Law's 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18—20,123—124。該名法官的推理中,亦有法律原理及法律理論,如關(guān)于法律的定義——法律是明文規(guī)定。在此,經(jīng)過對比,顯然無法斷定前面一名法官的法律原理及法律理論,是“中立”“客觀”的,屬于“客觀知識”,而后面一名法官不是。而更易為人接受的判斷是:其為“實(shí)踐立場”“實(shí)踐目的”的論證、表達(dá)。
由此深入。
依照德沃金理論的思路,法學(xué)工作者的“法律知識”,以內(nèi)在機(jī)制論,實(shí)際上完全可成為法律實(shí)踐者的“法律知識”的深層“自我”。上述例子中,更抽象的論證的不斷呈示,實(shí)為理論化的“論說”在實(shí)踐化的“論說”平臺中,論證實(shí)踐問題的正誤;換言之,“理論中的法律知識”,要求充當(dāng)“實(shí)踐中的法律知識”的邏輯內(nèi)容,與后者融貫,鞏固其立場選擇。故從現(xiàn)實(shí)看,法學(xué)工作者的“理論思考”,是法律實(shí)踐者的“理論思考”的進(jìn)一步展開。
而從法學(xué)歷史角度看,上面分析同樣適用、成立。在較宏觀的歷史演變中,法學(xué)工作者的“法律知識”,事實(shí)上,總是法律實(shí)踐者的“法律論證”在理論著述中的延續(xù)。
一般看來,法學(xué)工作者習(xí)慣引用實(shí)踐中的具體現(xiàn)實(shí)例子,以寫作闡述。換言之,法學(xué)工作者的“知識討論”,總是無法離開具體現(xiàn)實(shí)例子的支持而展開。但需敏銳覺察,此并非僅因?yàn)榫唧w現(xiàn)實(shí)例子具有說明、提示的作用,可使理論容易被理解,效果較好;相反,主要因?yàn)橹挥性诰唧w現(xiàn)實(shí)例子中,此類“知識討論”才能表明自己準(zhǔn)確的身份意義:為法律職業(yè)提供智識。這里的意思是,實(shí)踐化的法律原理表達(dá),必然與現(xiàn)實(shí)中爭議的具體法律問·題相聯(lián)系,而具體法律問題,自然是在人物、時(shí)間、地點(diǎn)、行動(dòng)等要素構(gòu)成的具體故事中產(chǎn)生的,具體故事的另外表述,便是具體現(xiàn)實(shí)例子;進(jìn)一步,如前所述,實(shí)踐化的法律原理表達(dá)在不斷展開時(shí),便是理論化的法律原理表達(dá)的一般展現(xiàn),由此,法學(xué)工作者的“知識討論”,在邏輯上無法離開法律的具體現(xiàn)實(shí)例子。因此,在頗為一般的法學(xué)歷史圖景中,同樣可認(rèn)定:法學(xué)工作者的理論操作,是現(xiàn)實(shí)中法律實(shí)踐者的“法律說理”在學(xué)術(shù)話語運(yùn)作中的延續(xù)。
作為暫時(shí)結(jié)論,這意味著,從法學(xué)知識起源的角度看,法學(xué)知識的提煉、概括,恰是在具有“地方性”“時(shí)間性”的具體法律實(shí)踐場景中提升完成的。正因?yàn)樵凇暗胤交薄皶r(shí)間化”的充滿對立爭議的實(shí)踐場景中提煉、概況,不由自主、延續(xù)地推論,故其是“一方”的具體支持理由的一個(gè)“法學(xué)”體現(xiàn)。
上面分析,并不否認(rèn)某些情況下人們會(huì)面對沒有爭議的一般法律問題,如公認(rèn)的“民事違約”“刑事詐騙”,因而在此,無須提出什么理論化的“法律論證”。這些情況下,通常看,人們的確共同承認(rèn)“依照法律這是必須給予處罰的”,進(jìn)一步,認(rèn)為只需適用明確的法律規(guī)定即已足夠。但需注意且人們也會(huì)承認(rèn)的,則是其一,這類沒有爭議的一般法律問題,總是“地方化”“歷史化”的,即使特定的一個(gè)較大區(qū)域的,或特定的一段較長時(shí)間的;其二,這類沒有爭議的一般法律問題,一般而言,總是經(jīng)過了漫長磨合——準(zhǔn)確說是長期的溫和爭議——進(jìn)而轉(zhuǎn)化而來,因?yàn)?地域的廣闊變化和歷史的復(fù)雜變遷,總是可提供相反的例子,說明對“沒有爭議”的法律問題的具體個(gè)別的反敘事。[1]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大量比較法和法律史研究,可深入作出說明。
此外,從另一角度看,上面分析,并不否認(rèn)某些情況下某種法學(xué)知識具有一定的普適性,甚至相當(dāng)普適性,可支持許多實(shí)踐中的法律立場。但人們亦不得不承認(rèn),即使一定的普適性,甚至相當(dāng)普適性,其也存在“實(shí)踐立場”的類別差異,即法學(xué)知識總在支持一類“實(shí)踐立場”。作為例子,可注意前面提到的“不能因?yàn)檫^錯(cuò)而獲得利益”。其既可成為法律原理,也可成為法學(xué)知識,而且可認(rèn)為具有一定的普適性,甚至相當(dāng)普適性。但眾所周知,且德沃金也曾細(xì)致分析,一些法律原理或法學(xué)知識,能與“不能因?yàn)檫^錯(cuò)而獲得利益”相互“競爭”,后者并非排他的“絕對普適”;一定條件下,“不能因?yàn)檫^錯(cuò)而獲得利益”,需讓位。[2]參見Ronald 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25—31。在此,所以需讓位,恰緣于后者終究體現(xiàn)了一種實(shí)踐需求。而一種實(shí)踐需求,恰是由一種“實(shí)踐立場”“實(shí)踐目的”所推動(dòng)的;在一種“實(shí)踐立場”“實(shí)踐目的”的背后,恰是一種價(jià)值觀念、利益。故嚴(yán)格說,沒有時(shí)空的普適性并不存在,而且,一定的普適性,甚至相當(dāng)普適性,也總是經(jīng)過漫長磨合——同樣準(zhǔn)確地說是長期的溫和爭議,有時(shí)是激烈爭議——進(jìn)而轉(zhuǎn)化而來。
這里,進(jìn)一步的結(jié)論則是,從法學(xué)知識的整體看,理論中的法律知識是歷史、地方化的,故也是不斷演變的,并非普適真理性的、本質(zhì)的。如果再次不斷回憶侵權(quán)中“過錯(cuò)原則”如何被“無過錯(cuò)原則”修正,“承擔(dān)剝奪他人生命的責(zé)任”如何被“正當(dāng)防衛(wèi)”“依法執(zhí)行死刑”修正,“格守契約承諾”如何被“重大誤解”“顯失公平”修正,加之前面討論的“不能因?yàn)檫^錯(cuò)而獲得利益”如何可被另外的法律原理修正,及前述中作為主要分析對象的“當(dāng)事人證明責(zé)任”如何可被“國家主動(dòng)查證責(zé)任”修正……我們也就可以且不得不去深入理解這一結(jié)論。
六、理論中的法律知識的性質(zhì)
現(xiàn)在,需提出一個(gè)頗有意思的問題:如果通過前面層層遞進(jìn)而又較復(fù)雜的分析,特別是通過在“理論中的法律知識”中設(shè)想——實(shí)際上是考察——法學(xué)工作者如何思考“實(shí)踐問題”,及在“實(shí)踐中的法律知識”中設(shè)想——實(shí)際上亦為考察——法律實(shí)踐者如何思考“理論問題”,且將其中的“邏輯聯(lián)系”“邏輯意義”予以揭示,將其中隱蔽的互通聯(lián)系甚至同一性質(zhì)予以暴露,則可獲得什么洞見?
第一,可發(fā)覺“理論中的法律知識”,就性質(zhì)而言,其實(shí)正是廣義的“實(shí)踐中的法律知識”。換言之,將“理論中的法律知識”視為相對法律實(shí)踐而言的遠(yuǎn)距離的“實(shí)踐中的法律知識”,更為貼切。這是關(guān)于知識定位的一個(gè)洞見。其實(shí),上面一節(jié)分析,已暗示這個(gè)洞見。我們當(dāng)然需承認(rèn),也如前面常提到的,“理論中的法律知識”,總是表現(xiàn)了和法律實(shí)踐的某種“距離”,總是表現(xiàn)了“僅在知識意義上思索法律問題”的某種自我收斂、自我謹(jǐn)慎的譜系;但這種知識,不是僅出于知識生產(chǎn)的智識需要而不斷自我重復(fù),或不是僅出于智慧游戲的愉悅而表達(dá)自我,就像某些哲學(xué)命題的思考,如“宇宙的意義是什么”,“存在可怎樣定義”,“語言為何是我們的存在場所”。就此而言,法律語境中,將“理論中法律知識”和“實(shí)踐中法律知識”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轉(zhuǎn)換為延展關(guān)系,將前者視為后者的就性質(zhì)而言的邏輯擴(kuò)展,更為真實(shí)。
第二,“理論中的法律知識”,其實(shí)不是一個(gè)科學(xué)化、中立化的知識系統(tǒng);相反,其為一種或張揚(yáng)或隱蔽的規(guī)范化(normative)、立場化的知識主張。這意味著,這種知識,要么明確地、要么潛在地宣揚(yáng)“面對法律問題我們應(yīng)當(dāng)如何、需要如何”的規(guī)范命題。它有時(shí)的確表達(dá)“這是什么”,故似乎是表達(dá)事實(shí)命題,但其總在支撐、論證“應(yīng)當(dāng)如何”“需要如何”。即使有時(shí)可看到某些法學(xué)文本提出“這種法律現(xiàn)象就是這么回事,事實(shí)如此”,其中,也依然蘊(yùn)涵著“既然是這么回事,事實(shí)如此,則應(yīng)如何”的規(guī)范企圖。
在這里,可再舉一例。眾所周知,實(shí)證主義法學(xué)和歷史主義法學(xué)均曾提出“法律實(shí)際上是什么”的事實(shí)命題,如“法律是主權(quán)者的命令”、“法律是長期歷史化的民族精神的表達(dá),并不一定是立法者的文字規(guī)定”。我們完全可設(shè)想,當(dāng)出現(xiàn)“法律問題”時(shí),尤其當(dāng)人們之間發(fā)生激烈爭議時(shí),“什么可成為解決法律問題的法律依據(jù)”這一問題,在這樣兩個(gè)事實(shí)命題之間,便會(huì)成為嚴(yán)峻的規(guī)范問題:當(dāng)認(rèn)為“法律是主權(quán)者的命令”時(shí),勢必會(huì)主張依據(jù)主權(quán)者的命令,排斥表達(dá)民族精神的習(xí)慣法,以解決“法律問題”;相反,當(dāng)認(rèn)為“法律是長期歷史化的民族精神的表達(dá),并不一定是立法者的文字規(guī)定”時(shí),勢必會(huì)主張不能僅依據(jù)主權(quán)者的命令,勢必會(huì)主張另外還需考慮表達(dá)民族精神的習(xí)慣法,甚至后者更重要,以解決“法律問題”。故將“理論中的法律知識”視為科學(xué)、中立的知識,實(shí)際上,遮掩了其中人們根本不能忽略的規(guī)范、立場的政治機(jī)制。此為另一個(gè)洞見。
第三,在“理論中的法律知識”里,應(yīng)看到各種知識的“平等性”“競爭性”。當(dāng)一種“理論中的法律知識”成為權(quán)威,或享有“霸權(quán)”時(shí),尤其是宣稱自己是或被他者認(rèn)為是“科學(xué)”“中立”的權(quán)威,進(jìn)而享有“不可置疑”的“霸權(quán)”時(shí),應(yīng)警惕其可能恰在吞噬其他知識存在的權(quán)利。更重要的,則是這種吞噬,完全可能通過“一個(gè)知識權(quán)威壓抑其他未被認(rèn)為是權(quán)威的知識”的方式,消滅實(shí)踐中另外法律主張的需求、愿望、期待。因?yàn)?前面已反復(fù)提到且論證,學(xué)術(shù)知識可成為法律主張的具體支持理由。人們當(dāng)然會(huì)在某個(gè)時(shí)刻、某一場合,達(dá)成一定的共識,從而普遍認(rèn)可一類法律知識,但這類法律知識,并不因此便超越那個(gè)時(shí)刻、那個(gè)場合,而成為沒有時(shí)空限制的普適知識;更值得反思的,恰是就在那個(gè)時(shí)刻、那個(gè)場合,其也在壓抑他者的需求、愿望、期待,因?yàn)?即使某些人成為少數(shù)時(shí),他們也會(huì)堅(jiān)持“少數(shù)人的權(quán)利”以抵抗,這種抵抗,也未必就沒有任何理由[1]參見Ronald 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64—205。。這個(gè)意義上,強(qiáng)調(diào)“理論中的法律知識”的“平等性”“競爭性”,等于在強(qiáng)調(diào)“實(shí)踐中的法律知識”的平等性、競爭性,進(jìn)一步,強(qiáng)調(diào)社會(huì)廣泛意義的主體權(quán)利的平等性和競爭性。這是第三個(gè)洞見。
第四,如果“理論中的法律知識”具有上述性質(zhì)、特點(diǎn),則這種知識的生產(chǎn)者,便應(yīng)意識到法學(xué)的學(xué)術(shù)操作,實(shí)質(zhì)上可認(rèn)為是對法律實(shí)踐的間接、迂回、側(cè)面的參與,其過程,甚至可認(rèn)為是法律實(shí)踐的延展部分;更重要的,則是如果我們特別嚴(yán)肅地思考這里的問題,則其過程可直接認(rèn)為“本身就是法律實(shí)踐”。在此,同樣如前面提到的,將理論和實(shí)踐的關(guān)系,視為“提升”“指導(dǎo)”,直至“鑲嵌”(當(dāng)然是人為“鑲嵌”),都不是十分恰當(dāng)準(zhǔn)確的;相反,認(rèn)為這種關(guān)系是“內(nèi)在”“互含”“不分彼此”,則是更適當(dāng)。從這里出發(fā),法學(xué)學(xué)者也就需要時(shí)刻反思自己的學(xué)術(shù)立場、學(xué)術(shù)產(chǎn)品的真實(shí)意義,甚至需時(shí)刻調(diào)整自己的學(xué)術(shù)立場,包括學(xué)術(shù)目的,當(dāng)然主要是學(xué)術(shù)產(chǎn)品的方向;因?yàn)?其中隱含了實(shí)踐立場、實(shí)踐目的。于是,法學(xué)工作者和法律實(shí)踐者的邊界,也就需要重新“調(diào)整”;法學(xué)學(xué)者的實(shí)踐主體性的自覺,也就需要提到“法學(xué)生產(chǎn)”的議事日程。這是第四個(gè)洞見。
1984年,在耶路撒冷的一次國際法學(xué)學(xué)術(shù)會(huì)議上,西方一些重要法學(xué)家曾討論“理論中的法律知識”和“實(shí)踐中的法律知識”的關(guān)系,而且,主要是就法理學(xué)的一般問題而展開。[2]見Ruth Gavison,“Introduction”,in Ruth Gavison(ed.),Issues in Contemporary Legal Philosophy:The Influence of H.L.A.Hart.Oxford:Clarendon Press,1987,pp.1—5。當(dāng)然,此前,西方學(xué)者已大致且不是很清晰地討論過這個(gè)問題。參見Roger Cotterrell,The Politics of Jurisprudence: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Legal Philosophy.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pp.6—20,223—230。這次會(huì)議中,哈特(H.L.A.Hart)的理論和德沃金的理論成為主要對立兩方。當(dāng)然,另外一位重要學(xué)者——加維森(Ruth Gavison)——作為哈特的重要支持者,也表達(dá)了意見。
哈特認(rèn)為,作為描述性的一般法學(xué)知識,是可以存在的,而且應(yīng)當(dāng)存在。因?yàn)?在設(shè)定法律實(shí)踐的立場、目的時(shí),首先應(yīng)清晰地在一般意義上知道法律的大致特征、表現(xiàn)方式、存在形態(tài)。[3]參見H.L.A.Hart,“Comment”,in Gavison(ed.),Issues in Contemporary Legal Philosophy:The Influence of H.L.A.Hart,pp.37—39。換言之,法學(xué)知識并不必然地需貼上“規(guī)范性”的標(biāo)簽。他說:
一個(gè)事實(shí)是,人們一直需要某種形式的描述性的、一般意義上的法律理論或法理學(xué),其中所表達(dá)的觀念,并非法官在決定“什么是法律”、“法律在具體案件中要求什么”時(shí)所表達(dá)的觀念,而是某種社會(huì)制度的外在觀察者的觀念……[1]H.L.A.Hart,“Comment”,in Gavison(ed.),Issues in Contemporary Legal Philosophy:The Influence of H.L.A.Hart,p.36.
這種對法律實(shí)踐和法律范式的粗略的特征描述(指德沃金的理論描述——本文作者注),不足以回答一些重要問題,那些總是因法律的存在而產(chǎn)生的重要問題,那些不屬于道德論證或政治論證范疇但涉及憲法結(jié)構(gòu)和法律現(xiàn)象關(guān)系的問題。回答這些重要問題,對于理解法律,至關(guān)重要。[2]H.L.A.Hart,“Comment”,in Gavison(ed.),Issues in Contemporary Legal Philosophy:The Influence of H.L.A.Hart,p.37.
德沃金認(rèn)為,法學(xué)知識作為學(xué)術(shù)命題,無論具體的還是抽象的,即使試圖運(yùn)用描述性的方式加以說明、論述,在說明論證之際,其也無法從根本上躲避“規(guī)范性”的問題。[3]見Ronald Dworkin,“Legal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Sense”,in Gavison(ed.),Issues in Contemporary Legal Philosophy:The Influence of H.L.A.Hart,pp.9—20。這里表達(dá)了一個(gè)思想:描述過程,實(shí)質(zhì)上也是表達(dá)“規(guī)范”欲望的過程。他指出:
傳統(tǒng)理論是錯(cuò)誤的……因?yàn)椋鼈儧]有理解法律命題(實(shí)踐者的關(guān)于“什么是法律”的命題——本文作者注)亦在表達(dá)“解釋性”的主張,而且,沒有理解任何有用的針對法律命題真實(shí)條件的說明(即法律理論的說明——本文作者注),注定是規(guī)范性的,而非簡單描述性的。[4]Ronald Dworkin,“Legal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Sense”,in Gavison(ed.),Issues in Contemporary Legal Philosophy:The Influence of H.L.A.Hart,p.13.
在此,德沃金實(shí)際上表達(dá)了前面第七節(jié)提到的法律理論被推出以論證審判的觀念。
加維森認(rèn)同哈特理論,亦類似表達(dá)了法學(xué)知識的描述性的存在。她認(rèn)為,正如大多數(shù)法律學(xué)者承認(rèn)的,作為科學(xué)知識的一類探討,法學(xué)理論或法學(xué)知識,可成為客觀性、觀察性的。[1]參見Ruth Gavison,“Comment”,in Gavison(ed.),Issues in Contemporary Legal Philosophy:The Influence of H.L.A.Hart,pp.21—34。她補(bǔ)充指出:
如果我們試圖提供一個(gè)恰當(dāng)?shù)姆煞治觯瑒t價(jià)值中立的法律理論觀念,既是可能的,也是有用的,甚至不可缺少。[2]Ruth Gavison,“Comment”,in Gavison(ed.),Issues in Contemporary Legal Philosophy:The Influence of H.L.A.Hart,p.27.
可看出,對法學(xué)理論的使命和作用而言,兩方對立觀點(diǎn)的成立與否十分重要。因?yàn)?如果哈特、加維森的理論成立,則以往法學(xué)知識的具有強(qiáng)大傳統(tǒng)的各種努力均應(yīng)獲得認(rèn)可,即使它們的觀點(diǎn)、思路、論據(jù),存在極大差異(就法律的基本定義而言,有的認(rèn)為,“法官所說的就是法律”;有的認(rèn)為,“主權(quán)者的命令就是法律”;有的認(rèn)為,“自然法和符合自然法的實(shí)在法就是法律”……);進(jìn)一步,問題僅在于,如何在辨析、剖解各種努力的“成功之處”和“失敗之處”時(shí),推進(jìn)對法律的客觀認(rèn)識。與此相反,如果德沃金的理論成立,則以往法學(xué)知識的各種努力,均可能付之東流,因?yàn)?它們的基本方向存在錯(cuò)誤,它們均在假定可從一種“客觀”的角度考察法律現(xiàn)象,且假定在考察時(shí),可沒有“價(jià)值”“立場”的干預(yù)。這意味著,以往一切法學(xué)學(xué)術(shù)思考,在根基上均要推倒重來。[3]德沃金本人亦提到這個(gè)意思,參見 Ronald Dworkin,“Legal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Sense”,in Gavison(ed.),Issues in Contemporary Legal Philosophy:The Influence of H.L.A.Hart,p.10。因此,哈特、加維森與德沃金的爭論,是有意義的,而且非常重要,根本不能置若罔聞。[4]1987年,出版了這次會(huì)議的論文集,即Ruth Gavison(ed.),Issues in Contemporary Legal Philosophy: The Influence of H.L.A.Hart.Oxford:Clarendon Press,1987。另外,許多學(xué)者后均加入爭論,主要是批評德沃金的思想。
本文贊同德沃金的基本思路。
但在本文看,其討論亦存在某些盲點(diǎn),或這樣說,其未細(xì)致深入分析其中存在的某些中心問題。第一,其未細(xì)致深入分析,法學(xué)學(xué)術(shù)中的論證理由,在何種意義上,可成為法律實(shí)踐中的“具體法律問題”的“具體”依據(jù)?[1]他在《法律的帝國》(Law's Empire)中討論過“理論爭論”(theoretical disagreement)的問題,認(rèn)為在有爭議的案件中,法官論證背后存在著一般性的“法律理論”。但他沒有明確、清晰地將法學(xué)學(xué)術(shù)中的法律理論聯(lián)系起來加以說明。見Ronald Dworkin,Law's 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5,16—20,90。第二,其未辨析,法律實(shí)踐者的具體法律推論,在何種意義上,可擴(kuò)展為法學(xué)理論的學(xué)術(shù)展現(xiàn)?第三,較具體的法律理論和較抽象的法律理論,當(dāng)“根植”“生發(fā)”于法律實(shí)踐中,或和法律實(shí)踐不分彼此時(shí),究竟如何邏輯地聯(lián)系在一起?第四,其未考察,法學(xué)知識的社會(huì)意義上的“前結(jié)構(gòu)”,究竟怎樣形成?其實(shí),可能恰因?yàn)檫@種“前結(jié)構(gòu)”的存在,故法學(xué)知識的“實(shí)踐參與性質(zhì)”,成為不可避免。第五,其的確忽略了“沒有爭議的法律問題”的問題。
因此,推進(jìn)德沃金的討論,包括推進(jìn)其和對立觀點(diǎn)的爭論空間的理解,并且將所有這些在許多法律理論的話語實(shí)踐中加以反復(fù)澄清,進(jìn)一步揭示問題的更深層次,有其必要性,亦為本文的努力方向。在我看,只有這樣,似乎才能在更有意義的層面上理解這場學(xué)術(shù)爭論及其給法學(xué)理論帶來的重要價(jià)值;當(dāng)然,最主要的,則是只有這樣,才能深入理解“法律知識”的性質(zhì),及這種理解可帶來的其他法學(xué)思考的路徑開拓。
(初審:劉誠)
[1]作者劉星,男,中國政法大學(xué)法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曾任中山大學(xué)法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研究領(lǐng)域?yàn)榉ɡ韺W(xué)、法學(xué)學(xué)說史、西方法律思想史、司法制度等,代表作有《法學(xué)知識如何實(shí)踐》《法律是什么》《西窗法雨》《西方法律思想導(dǎo)論》《中國法律思想導(dǎo)論》《有產(chǎn)階級的法律》《一種歷史實(shí)踐——近現(xiàn)代中西法概念理論比較研究》等,E-mail:xingl@cupl.edu.cn。本文寫作于在中山大學(xué)法學(xué)院工作的最后一年,現(xiàn)作若干修改。其時(shí)與該法學(xué)院同仁就相關(guān)問題多有交流,甚為受教,應(yīng)予感謝,當(dāng)然文責(zé)自負(fù)。在中山大學(xué)法學(xué)院工作的20年,得到前輩、同事、領(lǐng)導(dǎo)和學(xué)生的提攜幫助,至今難忘。愿以此文恩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