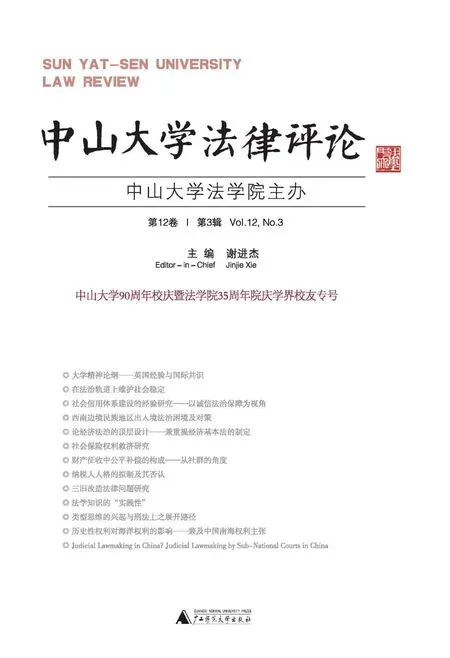大學精神論綱
——英國經驗與國際共識
單文華
大學精神論綱
——英國經驗與國際共識
單文華[1]
自從17歲考上中山大學以來,我就再沒有離開過大學,不是在念書,就是在教書,有時也承擔一些管理工作。我在英國的大學里前后待了16年。這期間,我在劍橋大學這所老牌大學做過訪問學者,讀過博士學位;也在牛津布魯克斯大學這所新派大學任過教職,從講師開始,一直做到教授;還在倫敦、利物浦等“紅磚大學”兼職從事過教學研究工作。現在雖然已經全職回國,但在劍橋仍然保留著一份資深研究員的兼差,因此對英國的大學可以說有一定的經歷和了解。
在我看來,英國的大學精神,就是大學作為一個由學者、學生組成的學術共同體的獨立和自由的精神。[2]毫無疑問,這種精神與中大先師陳寅烙所倡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這種精神,又可分為內外兩個層面:對外,是大學治理的獨立自主,簡稱“大學自治”;在內,是學術探索的無界自由,也即 “學術自由”。
大學自治
大學自治是英國大學的歷史傳統,也是英國大學的基本現實。英國關于大學自治的傳奇故事可謂層出不窮。其中,牛津大學拒絕授予撒切爾夫人名譽博士學位一事堪稱經典。1985年1月30日,牛津大學的議事廳里人聲鼎沸,1000多名教師和學生代表正在激烈地辯論要不要授予他們的校友、當朝首相撒切爾夫人榮譽法學博士學位。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激辯,大學以738票反對、319票贊成的壓倒性多數否決了給予撒切爾名譽博士的提案。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因為自二戰以來,授予擔任英國首相的校友以榮譽博士學位已經成了牛津的慣例,從無例外。但是,在牛津的絕大多數師生看來,這又是一個必然的結果:他們認為,“即使是王國最高長官,也不能期待我們授予她榮譽,而忽略她所推行的政策對我們學人所畢生信奉的價值以及所從事的工作的影響”。究其根源,在于“鐵娘子”政府對教育經費的大幅縮減,使得英國曾經長期領先世界優勢的高等教育陷于嚴重困難的境地。“如果授予撒切爾名譽學位,那將是對公立教育部門每一個人的沉重打擊。”30年過去了,當年決定的對錯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牛津頂住了政治和輿論的巨大壓力,堅持了自己的價值判斷,展示了數百年名校傲世獨立的風范。
所謂大學自治,簡單地說就是大學的事務由大學自己做主,不受政治、經濟等外在因素的不當干擾。正如歐洲大學協會2011年發布的“大學自治排行榜”所揭示的,大學自治具體來說又可細分為組織自治、財務自治、師資自治和學術自治等方面。在所有這些方面,英國大學均高居歐洲教育大國中的最高位置。英國大學的高度自治,于此可見一斑。
英國的大學始于牛津和劍橋。和歐洲大陸的其他中世紀大學一樣,它們一開始就是一個由學者和學生組成的行業性共同體。由于得到教會與王室的庇護,它們不僅擁有高度的自治,而且還享有諸多特權(例如可以免稅、可以罷工),有“國中之國”的地位。19世紀以來,牛津劍橋的教育壟斷被打破,倫敦大學等大學陸續設立,但大學仍長期游離于英國公共事業體系之外,英國政府并沒有對大學進行系統的財政支持。1918年,面對一戰過程中大學的財務困境,英國成立了大學撥款委員會,作為政府為大學提供撥款的咨詢建議機構。1988年《教育改革法》通過以后,英國成立了大學基金委員會以取代原有的大學撥款委員會,增加了社會產業界人士的比重。隨后,英國根據1992年《繼續和高等教育法》組建了新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員會以取代原有的大學基金委員會,但基本延續了大學基金委員會改革的思路,繼續擴大委員會中的產業界代表比例,進一步加強大學與社會產業界的聯系,同時建立更加嚴格的質量監督和評價體制,以財政撥款為媒介,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既便如此,英國政府對于大學的調控以及產業對大學的介入依然遵循法治和間接的原則進行,大學的辦學自主權并沒有受到根本性的影響。正因如此,英國才能繼續以大學的高度自治岸然立世,英國的高等教育也才能繼續保持世界領先的卓越地位。
學術自由
如果說大學自治是大學精神的七級浮屠,那么學術自由就是這座浮屠塔里所供奉的佛骨舍利。大學是學問與知識生產、傳承與養護的場所,而學問、知識得以生產與傳承、養護的前提,就是有一片能夠滋養知識與學問的自由與寬松的土壤。如同在鋼筋混凝土里開不出鮮花一樣,在沒有自由的地方不可能產生真正的、有生命力的學問。
作為培養了世界上最多諾貝爾獎得主的大學,劍橋無疑是世界科學與學術的重鎮。然而,當萊謝克·博里塞維奇校長在談到劍橋科研環境的優點時,并沒有列舉有多少先進的實驗設備,而是指出其提供了充分的學術自由,讓科研人員有根據個人興趣開展研究的時間和空間。劍橋明文列出的核心價值觀第一條就是:“思想與表達的自由。”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曾在劍橋念神學的達爾文,后來卻可以沖破神學觀念和英國基督教環境的束縛,提出與“上帝造人說”完全對立的進化論。如果他的大學當初不曾給予這種自由思想的空間,就難以想象他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就。
在英國做研究很少受到干擾,想研究什么領域,召開哪個主題的學術會議,如果不用申請經費,從來不需要經過任何審批,也從不會有人以會議議題或所發表言語“離經叛道”而橫加干預。剛到劍橋時,我腦子里面更多的是國內幾年研究積累的觀念、知識和經驗,不少帶有比較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用導師們的話來說,就是有點教條。比方說,談到外國投資的征收補償標準,往往就覺得要求充分補償只是資產階級貪得無厭的表現,不存在任何法律乃至道義的正當性。我時不時還會引用國內老先生們所確立的論據來和導師們“據理力爭”,不惜面紅耳赤。導師們不僅沒有生氣,反而覺得我認真得可愛——只是他們會很溫和地指出我需要看到硬幣的另外一面。我在劍橋做的博士論文提出歐盟和中國應該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當時不少人都覺得這個主張有點太超前,因為歐盟當時根本就不具備締結這種條約的法律權能。但是,導師們不但沒有反對,反而特別支持甚至鼓勵我做這個選題。事實證明,他們是對的:10多年以后的今天,歐盟不僅取得了這個法律權能,而且也正在和中國談判這樣一個條約。而這兩方面,正是我的論文首次提出的兩個核心觀點。
事實上,在劍橋,就像在英國其他大學一樣,師生平等對話、唯學是問的故事比比皆是。而我的故事要是和維特根斯坦(和羅素一樣也是我在劍橋學院圣三一學院的院友)的相比只能算是平淡得不能再平淡的了。故事里說,維特根斯坦的劍橋博士論文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戰營里寫就的,叫《邏輯哲學導論》。當時沒有人能夠讀懂他的這部天書,因此出版商找到他的老師羅素。羅素自告奮勇,為這部書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序言,并為這部書的出版費盡心機。書出版了,但維特根斯坦并不領情,還說羅素根本就沒有讀懂他的論文!羅素不以為件,反以為豪,因為他知道天才人物往往有個性,而他作為老師,劍橋作為一所大學,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為這樣的人才提供一片任其馳騁的廣裹天空。
國際共識
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是在英國大學最為彰顯的大學精神,但并不是只“屬于”英國的大學精神。事實上,英國的大學最初效仿的是歐洲的大學,而英國和歐洲的大學又影響了整個世界的大學發展。其結果是,在世界上比較有影響的大學,都遵循大體一致的大學精神。一個最為顯著的表現,就是來自世界上80多個國家的700多所知名大學對于1988年《大學大憲章》(Magna Charta Universitatum)的共同擁戴。其中就包括兩所中國的大學:北京大學和武漢大學。
《大學大憲章》由世界上最早的大學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所首倡,并于1988年在該大學900周年誕辰之際,由來自世界各國的430所大學的校長們所共同簽訂。而該大憲章所確立的四個基本原則中,最根本的兩個原則,正是“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其中,“大學自治”是大憲章所確立的首要原則。它開宗明義:“大學是自治的機構……大學的研究和教學必須從道義上和智識上均獨立于所有的政治權威或者經濟力量。”而關于“學術自由”,大憲章指出:“研究與教學的自由是大學的根本原則;政府與大學必須盡其所能確保對這種自由的尊重。”毫無疑問,這些表述正是大學精神的最好闡釋。
千秋基業
大學之所以需要獨立于政治與經濟之外實行自治并享受學術自由,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在現實的世界里,推動社會的發展演進主要有三種力量:政治、經濟和教育。它們各有其主體與載體。其中,政治的主體主要是政客和官僚,其載體主要是各種權力機關及其所掌握的各種權力資源;經濟主要以商人與企業為主體,并以金錢以及其所能支配的廣泛資源為載體;而教育的主體則主要是受過教育的人群即學者或學生,其主要載體則為以大學為代表的學校以及其所蘊育傳承的知識、思想、學識與學問。
這三支力量之間既相互聯系、互相支持配合,又相對獨立、互相監督制約。其中,一方面,大學與教育亟需政治力量的保護與經濟力量的支持,否則其生產與發展均將難以為繼。古今中外的經驗表明,成功的大學往往得益于政權的呵護和商界的扶持。另一方面,大學與教育又必須保持相對于政治與經濟力量的獨立性。否則它不可能開展其賴以生存的獨立自主的思考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知識創新與文明傳承,也就不可能為另外兩個部門提供必要的人才供給和智力支持。可以說,對于政治與經濟而言,大學與教育的獨立自主和自由生發最符合其最大、最長遠的利益。而在歷史的長河中,往往是,政治和經濟的成就可能倏忽間煙消云散,而大學和教育的成果卻可以歷久彌新,它們可以更深刻、更久遠地定義并滋養著一個民族、一種文明。從這個意義上講,維護大學的獨立自主與學術自由不僅僅是政治、經濟和教育部門共同的事業,而且是它們共同的千秋萬代的基業。
撒切爾曾經斷言:“中國不可能成為超級大國,因為中國只能出口電視機,出口不了創新的理念。”話粗理不粗。中國應該如何重拾大學精神,破解“撒切爾魔咒”,值得政治、經濟和教育部門的遠見卓識和深思慎對。
(初審:謝進杰)
[1]作者單文華,男,1987至1991年間就讀于中山大學法律系,獲法學學士學位;英國劍橋大學圣三一學院法學博士;曾任英國牛津布魯克斯大學終身教授;現任西安交通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法學院院長兼絲綢之路國際法與比較法研究所所長;兼任英國劍橋大學勞特派特國際法中心(LCIL)資深研究員、牛津大學出版社英文期刊《中國比較法學刊》(CJCL)主編、國際比較法科學院(IACL)銜成成員、美國法律科學院(ALI)成員、國家千人計劃特聘專家、長江學者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