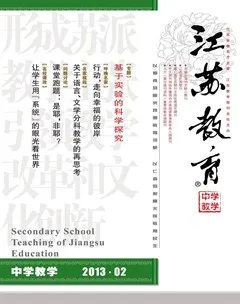大開大合,細處攝神
一直以來,我始終認為,教學,尤其是我們的語文教學,是一種生命的相遇,師生間的、生生間的、師生與作者的,還有與作品中的人的相遇。教學的責任不僅在于授受知識,訓練技能,還在于透過文本走近另一個(有時候是幾個)生命,進而喚醒我們內心的真善美。
語文教育應該基于學生生命的需要和可能,幫助學生領悟作者獨特的對生命的體驗、感悟和理解,而不是接受教師和教參的理解。
《聽聽那冷雨》,在我們的解讀中,它的主旨就是對故鄉的思念。其實,當我們關注了作者寫作本文的年代時,就會有新的發現:1974年臺灣在搞“十大建設”,也就相當于我們現在的城鎮建設。還有作者文中提到的十年前(也就是1964年)臺灣在搞“文化復興”,大陸在搞“四清”,“四清”以后就是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我們不幫助學生了解這樣的背景,學生就不了解當年大陸與臺灣傳統文化被摧殘的情況,也就無法理解作者的糾結。
公開課的教學時間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與學生一起走進文本,走近作者的心靈,尋找一個比較合適的突破點恐怕是最要緊的了。此次授課并不是我第一次執教《聽聽那冷雨》這篇課文,如何上出新意,又不游離文本,一直是我在備課時反復思考的問題。最終,我選擇了一條還原教材,將教材回到作者寫作年代的路徑,將解讀作品主旨作為突破點,在教學的進程中從大處著眼,展現大視野,培養學生的大智慧,同時兼及其余,相機而教。
于是,我在課前讓學生觀看了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中國》,并且上課的時候又給學生發了作者的原文,讓他們對照閱讀。在比較中,在前后的關聯中探尋作者的寫作意圖,進而明確閱讀是要求真的,這真,來自于文本本身的字里行間,而不是我們可以主觀臆測的。
“攻其一點,兼及其余”的教學策略,絕不僅是技術的需要,更是一種教學的策略。從一個一個的點出發,再將一個一個的點交匯,就可以連點成線,連線成面,再將一個個的面組織起來,就是一個個立體的畫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