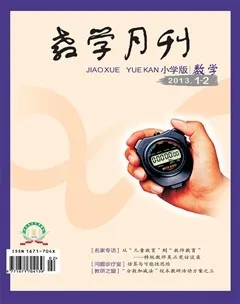估算與可能性思維
本刊2012年第12期中“《課標》估算例題之難”一文詳細分析了利用估算解決實際問題的困難所在。在此基礎上,還需要進一步挖掘估算在數學課程與教學中的育人功能。
一、估算中的不確定因素
估算與精確計算的思考過程不同,其間存在著諸多的不確定因素甚至風險。相對于精確計算來說,這些不確定因素一方面或許是導致其難教、難學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培養學生良好思維品質的契機和素材。
先看這樣一個問題:“一件上衣58元,一條褲子43元,買一套大約需要花多少錢?100元錢夠嗎?”
如果直接精確計算“58+43”的結果為101,立刻就可以得到問題的結論是“100元錢不夠”。如果運用估算,對于“買一套大約需要花多少錢”這一問題,學生通常會運用“數據重塑”[1]將58和43改變為最接近的整十數而后計算,即:
58≈60,43≈40
60+40=100
由此得到“大約需要100元錢”,并且“100元錢夠”的結論。這里出現了直接的精確計算與估算所得到的結論不一致的情況,表明在這個問題情境中,“就近變為整十數”這一習慣的估算策略是不能夠達成問題目標的,也就是說估算策略的選擇與確定是受問題情境和問題目標制約的。同樣的數據在不同的問題中,對其進行數據重塑的方式是不一樣的,這種策略的不確定性導致估算策略選擇與確定具有“不可靠”的特征。
再如:比較51×49與52×48的大小,如果用精確計算的方法,直接計算出51×49的結果為2499,52×48的結果為2496,立刻可以得到“51×49>52×48”的結論,不需要更多的思考。如果用估算的方法,可能采用的方法是將51×49與52×48中的每一個數據都就近變為整十數,結果兩個算式就改變為了同樣的算式50×50,這樣自然就無法比較兩個算式結果的大小。因此,估算策略還會出現“無效”的風險,給解題者造成“無功而返”的感覺。
這種無效的風險還會出現在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中,比如這樣的問題:“禮堂里每排有22個座位,一共有18排。有350名同學來聽課,能坐下嗎?”按照通常習慣的數據重塑進行估算,是將22變為20,18也看成20。這樣“22×18”就近似變成“20×20”,結果為400。但將“22×18”變為“20×20”,并不知道是變大了還是變小了。如果是變小了,那么通過如下的不等式可以得到“350人能坐下”的結論:
22×18>400>350
如果是變大了,仍然不能判定22×18與350的大小關系,當然也就無法得出“能否坐下”的結論。因此將20和18都變為20就是一個無效的估算策略。所以,估算過程中的不確定因素還表現為策略選擇的無效性方面。
用估算解決問題,還會出現不同方法得到不同結論的情況。比如這樣一個問題:“一個籃球49元,買8個籃球400元夠嗎?”
方法1:把49放大看成50,8×50等于400。所以,買8個400元夠。
方法2:把8看成10,49×10等于490。比400大,所以,買8個400元不夠。
方法3:把兩個數都就近看成整十數,當然結論也是不夠。
學生在學習數學的過程中通常都會有“一題多解”的經驗,同樣的問題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解決,不同的方法應當得到同樣的結果。而不同的估算方法可能會得到不同的結論,這就使得估算方法還具有“多元”的特點。
正是估算方法所具有的多元、無效和不可靠的特點,使得估算的過程具有了不確定性的特征。因此解題者在運用估算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自然會出現“拿不準”的感覺,這種拿不準的感覺可能也是許多學生寧愿使用精確計算也不愿意使用估算的原因所在。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拿不準的感覺孕育著一種重要的思維形式,即可能性思維。
二、可能性思維及其作用
所謂可能性思維是相對于確定性的思維形式而言的,指的是針對不確定事物或現象進行比較與判斷的思考過程。在前面運用估算解決問題時,有的估算方法能夠達成問題目標,也有的方法不能夠達成問題目標。這就使得解題者不能夠運用程序化的算法直接解決問題,還需要結合問題情境和問題目標等因素對諸多可能的方法進行列舉、比較和篩選,在此基礎上對方法的選擇作出判斷。如果不采用估算,那么就只需要按照確定的程序計算出結果。相對于估算過程中的可能性思維來說,直接的精確計算過程就是一種確定性的思維形式。
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這種可能性思維也是經常出現的。比如駕車下班回家,有兩條距離相同的路線(路線A,路線B)可供選擇,人們自然的想法是選擇暢通的路線。為達到這一目的,首先需要列舉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
●兩條路線都不堵車;
●兩條路線都堵車;
●路線A堵車,路線B不堵車;
●路線B堵車,路線A不堵車。
接下來就需要形成判斷,究竟哪一種情況會出現?這種思考的困難在于,情況未發生的時候是無法預知哪一種情況一定發生。因此思考的問題就需要改變為“哪一種情況出現的可能性大”。得到這一問題的答案往往需要統計的思維,調動過去已有的經驗進行比較和判斷。如果已有的經驗是前兩種情況出現得多,就會得到“走哪條路線都一樣”的判斷。如果已有的經驗是第三種情況出現得多,就會形成“選擇路線B”的判斷。同樣,如果已有的經驗是第四種情況出現得多,就會“選擇路線A”。需要注意的是,無論選擇了哪一條路線都有可能選錯,因此可能性思維最突出的特征是“可誤”,與前面估算過程的不可靠或無效的特征是吻合的。盡管如此,仍然不能忽略可能性思維的重要作用。
歷史上一些科學研究和發現也能看到可能性思維的作用。比如關于自由落體的理論,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早有論斷:兩個重量不同的物體同時從高處落下,重的要比輕的先落地。意大利科學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發現這一論斷有著不可克服的邏輯矛盾,如果一個100千克的球和一個1千克的球同時從高處落下,按亞里士多德的說法,前者應比后者先落地。如果把這兩個球拴在一起,讓它們同時從高處落下,那么會出現什么情況呢?
●兩個球拴在一起,重量變為101千克,按亞里士多德的理論,它的下落速度應該比剛才兩個球的下落速度要快;
●由于1千克的球比100千克的球下落速度慢,拴在一起后它必然要減慢100千克的球的下落速度,因此拴在一起的兩個球的下落速度比100千克球的下落速度要慢。
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論斷,這兩種可能性都應當發生,而這兩種可能性是相互矛盾的,不可能同時發生,這就說明推理的前提是錯誤的。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考,伽利略推翻了亞里士多德的論斷,建立了新的自由落體理論。在這個事例中,伽利略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論斷,列舉出各種可能性進行比較,發現其中存在的矛盾,進而判斷亞里士多德的論斷是錯誤的,得到“在真空中,輕重不一樣的物體從相同高度同時下落,應該同時落地”這一新的論斷。
這一事例表明可能性思維具有“質疑”的特征,質疑作為一種思維品質幾乎是所有科學研究中所不可或缺的。18世紀瑞士著名數學家歐拉(Leonhard Euler,1707-1783)成功解決了哥尼斯堡“七橋問題”,并在此基礎上建立數學中的圖論,通過分析可以發現其中也有可能性思維的因素。
圖1 哥尼斯堡七橋[2]
歐洲的普瑞格爾河(Pregel River)流過東普魯士(East Prussia)的古城哥尼斯堡(Konigsberg)市中心。河中有兩座島,筑有七座古橋(見圖1),是當地著名的旅游勝地。凡旅游者都有一種愿望,即游覽的景點盡量多,而且不走重復路。人們發現這七座橋不能滿足這一愿望。要想走遍七座橋,就一定有橋重復走;不重復就不能走遍七座橋。這就刺激了人們解決下面問題的欲望:尋找一條行走路線,使得每座橋都走到(不漏),并且每座橋只走一次(不重)。歷經數百年沒有人能夠解決這個問題。而歐拉僅用簡短的篇幅通過證明符合要求的路線不存在解決了問題。[3]
按照人們的意愿,希望找到符合要求的路線,因此問題的目標就鎖定在“尋找路線”,解決問題的思路自然而然地確定為“尋找”,而尋找的前提是“存在”,正是這種確定性的思維模式使得之前的人們沒有成功解決問題。歐拉解決問題的思路與此不同,首先應當是對“存在”這一前提條件產生懷疑,很多人花費很多時間都沒有找到,此時應當有兩種可能的情況:
●路線存在,還沒有找到;
●路線不存在。
在歐拉的思維中一定是相信第二種情況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他就把問題目標改變為“證明走法不存在”,由此帶來解決問題的思路就不是去“尋找路線”,而是證明走法不存在。
20世紀英國哲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和歷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 -1970)關于可能性與必然性的論述,可以恰當地詮釋歐拉解決七橋問題的思維方式:“……任何一個我們具有合理根據而對之抱有某種程度的相信或不相信的命題在理論上都可以排列在以必然的真理和必然的荒謬為兩端的尺度之上。”[4]可能性思維實際上就是介于必然性和不可能之間的一種思維狀態,當支持的證據越來越多時,就偏向了必然性,當否定的證據越來越多時,便偏向了不可能。在七橋問題的思考中,首先是“路線存在”和“路線不存在”兩種可能性的選擇,如果把“路線存在”當成一種確定性,那么就不會有“選擇”的思考了。歐拉的高明之處就在于將自己的思考放在了“存在”和“不存在”之間的尺度上,很多人花費很多時間沒有找到路線作為證據,支持歐拉的選擇偏向了“不存在”。這應當是歐拉成功解決七橋問題的關鍵。
綜上,可以概括出,可能性思維的基本模式,在對諸多可能性列舉的基礎上去尋找證據,通過對這些可能性及其證據的比較,形成對可能性大小的判斷。盡管這樣的判斷可能是不可靠,甚至是可誤的,但在認識事物、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仍然可以起到重要作用。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在數學課程與教學中培養學生的可能性思維。
三、可能性思維的培養
思維的培養不是一日之功,可能性思維的培養應當具有連續性。因此在課程內容中挖掘可能性思維的因素就顯得十分必要。
數學課程中的概念往往強調表述的確定性,其目的是理解的一致性,也就是在每一個人的頭腦中,同一個概念必須是同一個意思。如果對同一個概念出現多元的理解,就會造成推理的混亂。數學中對概念的“定義”,其實就是為了保證這種表述的確定性和理解的一致性。學生對概念的理解僅限于概念的表述方面是不夠的,還應當包括概念的生成階段。這種生成往往具有多元的特征,并不一定是唯一確定的。比如“角”這一概念,從生成的角度看,既可以看做是“從一個端點出發的兩條射線形成的”,也可以看做是“一條射線圍繞端點旋轉而成的”。前者是靜態的理解,后者是動態的理解。再比如長方形這一概念,靜態的理解為“四條線段圍成的封閉圖形,并且四個內角都是直角”。對長方形還可以有“線動成面”的動態理解,也就是把長方形看成“一條線段AB沿著垂直于這條線段的方向平行移動所留下的軌跡”。(見圖2)
正是概念生成的這種多元特征,使得概念的理解蘊含了可能性思維,也就是在多種可能性中進行比較與判斷的思考過程。教學中如果引導學生經歷這樣的思考,無疑對學生可能性思維的培養是有益的。
小學數學課程中的計算教學,通常是以“又對又快”作為評價指標的,因此教學中往往以確定性的計算“程序”為主要教學內容,追求程序化操作的熟練。其實在這種確定性的程序之中也蘊含著類似于估算的可能性思維。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資助研發的小學數學教科書《Think Math》,其中三年級關于豎式計算的內容中設計有選擇百位數字的問題(見圖3)[5]。
圖3中共有9道加法豎式計算問題,題目要求學生“僅寫出百位數字”。9道題目下面有一個“挑戰思考”,要求學生回答:“如果想知道百位數字是多少,你是否需要去看個位數字?并解釋原因。”學生通過對此類問題的思考,自然會形成一種意識,就是加法結果的百位數字不僅與加數的百位數字有關,還與十位數字和個位數字有關,有時有進位的數字,有時沒有進位的數字。因此計算過程中就要有多種可能性的比較與選擇。如果學生經常經歷這樣的思考過程,不僅可能會減少或避免豎式計算常見的錯誤,而且對可能性思維的養成也會有所裨益。
數學課程與教學中倡導“一題多解”是數學教育的傳統,教學中引導并鼓勵學生在解決問題過程中對多種方法進行比較與選擇,應當也是培養可能性思維的有效途徑。比如下面的兩步應用題:“商店里運進大米100千克,運進面粉比大米多50千克。求運進大米和面粉共多少千克?”面對這樣的問題,有教師習慣運用程序化的思考,要想知道大米和面粉共運進多少千克,就必須知道大米和面粉各運進多少千克。由于大米數量是已知的,所以必須先求出面粉的數量,由此得到下面的解法:
100+50=150(千克)
100+150=250(千克)
事實上,解決任何問題的思維方式都不會是唯一確定的,比如上面的問題還可以這樣想:由于面粉比大米多50千克,所以大米和面粉的總量中就包括了大米的2倍和50千克,依據這種思考所得到算式與前面的算式不同:
100×2+50=250(千克)
這種方法同樣也解決了問題,但并不需要求出面粉的數量。有教師認為,這樣的方法只寫出了一個算式,就變成了一步應用題了。其實解決一個問題的思維過程并不是能夠由“步數”進行區分的,解決問題教學的根本目的在于讓學生經歷諸如問題的理解、方法的生成以及不同方法的比較與選擇這樣的思考,并不在乎把解題過程表達成幾步。
可能性思維培養的另外一個渠道是在數學課程與教學中開發更具開放性的資源。所謂開放性的資源指的是對其內容或方法的思考不是唯一確定的,需要針對多種可能性進行列舉、比較與選擇的課程內容。比如人教版教材五年級上冊第68頁就有這樣的問題(見圖4)[6]:
圖4 開放性資源圖例
這一問題不同于一般意義的計算問題,其中所有數據都是未知的,每一個字母都是0 ~9多種可能性中的一個。首先需要思考的問題是“算式中一共出現了4個字母,思考的順序應當是怎樣的”,通常遵循的原則是“從簡單開始”,為此就要在算式中尋找“哪里最簡單”。除此之外,在針對某一個字母“是什么”的思考中,會出現多種可能性,這時就需要將“是什么”的思考改變為“可能是什么”,為了得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就需要思考“不可能是什么”。凡此種種都體現了可能性思維中列舉、比較和篩選的思考過程。這種課程與教學資源的開發并非易事,需要研究人員、教科書編制人員以及廣大教師的共同努力。
綜上可以看出,可能性思維蘊含于數學課程內容的方方面面,概念教學、計算教學以及解決問題中都存在可能性思維培養的契機。因此在日常教學中充分挖掘可能性思維的因素,并將其落實到課堂教學的過程之中,就成為每一位教師的職責。培養學生可能性思維給教師提出的要求是,伴隨著“是什么”的問題同時應當引導學生思考“還可能是什么”;“怎么做”的問題解決了之后,繼續想想“還可以怎么做”。當學生出現多種答案的時候,教師需要“容忍并鼓勵不同,寬恕并理解錯誤”。重要的是讓學生經歷列舉、比較和判斷的過程。
注釋與參考文獻:
[1]郜舒竹. 估算方法知多少[ J ]. 教學月刊,2012(11).
[2]圖中字母A、B、C、D表示陸地,編號1~7表示七座橋.
[3]郜舒竹. 歐拉究竟是怎樣解決七橋問題的[ J ]. 數學通報, 2009(9).
[4] (英)羅素著;張金言譯.人類的知識——其范圍與限度[M].北京:商務印刷館,1983:455.
[5] Education Development Center. Think Math, Student Work Text, Lesson Activity. Harcourt School Publishers.2009.
[6]課程教材研究所,小學數學課程教材研究開發中心. 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數學五年級下冊[M].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8).
(首都師范大學初等教育學院 10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