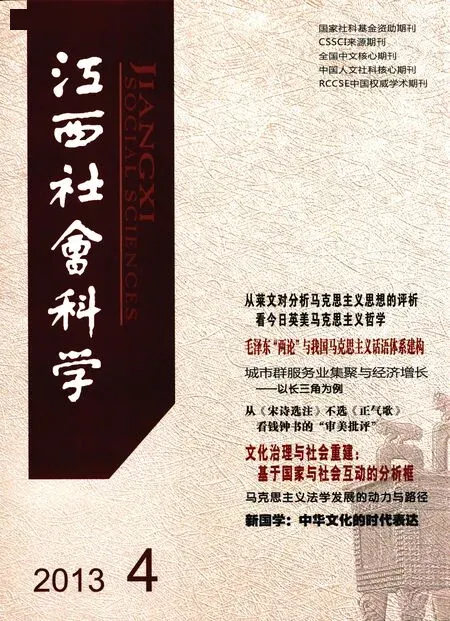城市群服務業集聚與經濟增長——以長三角為例
■谷永芬 洪 娟
產業集聚是城市群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動力,同時城市群又是區域產業集聚發展的重要載體,兩者間的相互協調能夠有效推動區域經濟整體發展。服務業作為后工業社會的主導產業,其集聚效應顯著。我國“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要“科學規劃城市群內各城市功能定位和產業布局”,同時“推動特大城市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可見,研究服務業的集聚效應對于城市群產業規劃和空間組織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長三角地區作為目前我國發展最快、經濟總量規模最大和最具發展潛力的城市群,在城市聚集和產業空間組織方面都對我國其他城市群具有很強的示范性效應,選擇其作為研究對象并對其做定量分析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和前瞻性。
一、文獻回顧
產業的空間集聚是經濟活動最突出的地理特征,與經濟增長是一個相伴而生的過程。20世紀90年代初以Krugman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家開始把主流經濟學家長期忽視的空間因素納入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研究產業在空間的集聚與分散原理,從而為研究區域經濟增長差距提供新的視角。早期的空間經濟模型都是靜態的,一旦經濟達到均衡,經濟增長率為零,除非外生經濟參數發生變化,否則這一均衡結果很難改變。因此,要考察集聚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必須將新經濟地理模型動態化。Englmann&Walz(1995)在 Krugman(1991)創立的“中心—外圍”模型基礎上,首次將新經濟地理學與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融合,解釋了產業集聚與區域經濟增長差異的動態關系。Martin et al和Baldwin et al[1][2][3]創建了勞動力不流動條件下的新經濟地理學動態模型,認為資本存量產生的溢出效應影響新資本的形成成本,從而進一步促進資本積累,最終形成內生經濟增長。Baldwin et al和Fujita et al[4][5]嘗試在區域間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假定條件下,提出了結合內生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地理中心——外圍模型的動態模型,認為地理位置影響經濟增長,集聚對于整體經濟增長有利。
在實證研究方面,大多數經驗研究支持集聚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但同時也存在相當部分研究認為產業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無相關和負相關。如,Ciccone[6]利用歐洲5個國家的Nuts-3級地區628個樣本數據研究了產業集聚(就業密度)對平均勞動生產率的影響,發現制造業與服務業的經濟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具有正面效應。范劍勇[7]借鑒Ciccone提供的模型分別研究了我國地級以上城市非農產業和服務業對生產率的影響,同樣得出了正相關的結論。Rice[8]和Midelfar[9]分別在研究英國和挪威地區間收入差距時發現,即使工資收入對人口密度有正彈性,但勞動生產率與人口密度沒有表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Bode[10]基于德國數據的研究結論也是經濟集聚對勞動生產率幾乎沒有促進作用。Sbergami[11]進一步研究發現,從國家層面看,只在經濟發展的某一水平集聚才能推動GDP增長。陳立泰等[12]采用1995—2007年我國省際面板數據分析得出我國城市服務業與區域經濟增長呈負相關。胡霞和魏作磊[13]研究城市服務業集聚效應認為,服務業發展存在一定的空間規模報酬遞增效應,表明集聚確實能夠促進服務業增長,但過度集聚會帶來負面影響。
根據區域城市群理論,城市群發展的主要動力和競爭優勢來源于產業集聚,新經濟地理學揭示的產業集聚基本規律為:具有前后向聯系的企業為了節約交易成本而集聚,但隨著集聚程度的提高,集聚區的工資和地租等要素價格會上漲,從而導致企業成本增加,當企業增加的成本大于所節約的交易成本時,集聚程度就會下降,即產業集聚程度會隨著交易成本的降低而呈倒U型變化。從這一規律出發,本文檢驗長三角地區城市群內服務業集聚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并以此探討城市群在可持續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服務業集聚的有效空間組織應如何體現在區域政策體系中。
二、長三角城市群服務業集聚程度分析
(一)產業集聚測度指標選擇
衡量產業集聚程度的指標主要有行業集中度、區位熵、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空間基尼系數、EG指數等,其中區位熵指數在測度產業集中度時比較客觀全面,而且計算簡單方便。結合數據獲得的可行性,本文采用此指標進行計算。區位熵指數的計算公式為:

此處,Eij表示第j個地區的第i個產業的產出指標(通常為產值或就業人數)。LQ>1,表明該產業在該地區的專業化水平比較高,在該地區相對集中,高于全國平均水平;LQ<1,表明該產業在該地區的集中度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處于比較劣勢;等于1則處于均勢。區位熵側重描述專業化集聚水平,能夠較形象地反映某個地區的主導產業和產業集聚水平。
(二)服務業空間聚集程度分析
長三角地區是我國經濟最為發達的產業和城市密集區,涵蓋了上海、南京、杭州、寧波、蘇州、無錫、常州、徐州、泰州、連云港、淮安、鹽城、鎮江、南通、揚州、宿遷、溫州、嘉興、湖州、紹興、金華、衢州、舟山、臺州、麗水等25個城市。本文采用區位熵指數測算了長三角地區25個城市(市轄區)2001—2010年服務業的集聚情況,測算結果見表1。
根據測算結果分析:第一,從整體看,長三角城市的區位熵數值大部分大于1,而且在1.5以上,說明長三角地區城市的服務業產業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產業相對聚集且專業化程度較高,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和規模優勢;第二,各城市的區位熵值總體呈下降趨勢,部分地區如杭州、嘉興、紹興等下降幅度較大,說明這種由集聚帶來的地區規模經濟和專業化優勢正在逐步減弱。所以,從區位熵測算結果看,長三角主體城市群服務業的集聚程度已處于集聚規律“倒U型曲線”的右方,鑒于產業集聚與經濟增長的協同關系以及“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推動特大城市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政策背景,“十二五”期間長三角城市群在著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的同時,應該注重分析服務業集聚本身的經濟增長效應,以加強其空間組織效率。
三、長三角城市服務業集聚與地區經濟增長關系分析
(一)模型設定及變量解釋
1.模型設定

表1 長三角地區25個城市服務業聚集程度
產業集聚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可以通過采用影響經濟增長的產業集聚指標來進行。在不考慮區域之間貿易及資本的自由流動的情況下,服務業集聚促進經濟增長的實證模型可設定為:

其中,Yj為區域j的產出水平,Xj為影響區域產出水平的服務業集聚因素(指標),A為區域技術進步。對上式求全微分,兩邊同時除以Yj,并作相應線性處理,可以得到如下計量模型:

其中,αi為服務業集聚因素i對區域的產出彈性。在此計量模型基礎上,本文根據服務業和產業集聚的特點,并借鑒國內外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將長三角地區服務業集聚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基礎模型設定為:

對于嚴格為正的變量,其條件分布常常具有異方差或偏態性,取對數后,即使不能消除這方面的問題,也可以使之有所緩和。在這里我們將變量 pgdp、pd、iq、perh、ui采用對數形式,即相應模型為:


2.變量解釋
模型中lnpgdp為被解釋變量,lq是本文關注的一個解釋變量,lnpd、lniq、pfe、open、lnper和 lnui作為控制變量出現在模型中。各經濟變量解釋說明如下:
lnpgdp代表區域經濟增長率(作為被解釋變量放在模型左邊),pgdp采用各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描述。
lq代表服務業集聚水平,采用根據(1)式計算的區位熵來描述。
lnpd代表生活服務業市場規模,服務業由于生產和消費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不可分性、非物化性、不可儲存性等特點,決定了其產品比工業更依賴于本地市場容量,即服務業市場規模主要取決于本地市場容量。在這里,pd我們采用人口密度來描述。
lniq代表生產性服務業市場規模。與上述同理,iq我們采用區域限額以上工業企業總產值占GDP的比重來描述。
pfe代表政府的干預能力,采用地方財政預算內支出占GDP比重來描述。
open代表區域的開放程度,采用地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占GDP比重來描述。
lnperh代表人力資本水平,perh采用高等學校專任教師數來描述。
lnui代表城市居民的消費能力,ui采用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來描述。
(二)實證分析
本文的樣本選擇在長三角地區16個主體城市基礎上進行了拓展,采用了長三角地區涵蓋的25個市級以上城市 (市轄區)2001—2010年的面板數據來進行實證分析。樣本原始數據主要來源于各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上海統計年鑒》、《浙江統計年鑒》和《江蘇統計年鑒》等。在面板回歸模型選擇上,本文通過對面板數據的檢驗得出應選擇個體固定效應回歸模型。同時,為保證分析結果的科學性,本文對面板數據進行了平穩性 (單位根)和協整檢驗,結果見表2,表明模型中所有變量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可能存在協整關系。對面板變量進行協整檢驗后,從模型回歸殘差序列單位根結果看,殘差序列平穩,說明各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
所采用的250個樣本面板數據的個體固定效應回歸結果見表3。在MODEL[Ⅰ]中,open和lnpd變量未通過檢驗,而且其系數符號為負,與現實經濟意義不符,故將其剔除得到MODEL[Ⅱ],再進行回歸。回歸結果顯示,在MODEL[Ⅱ]中各變量都通過了檢驗,其中,lnui通過5%檢驗,其他都通過了1%檢驗。模型[Ⅱ]計量結果中的修正可決系數為0.901,表明方程回歸擬合效果不錯,可以理解為方程中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對區域經濟增長的解釋程度為90.1%。

表2 各變量單位根檢驗結果

表3 個體固定效應回歸結果
從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看,MODEL[Ⅱ]回歸結果顯示:解釋變量服務業集聚度(區位熵lq)與經濟增長負相關,彈性系數為-0.395,這說明長三角地區城市服務業集聚度(區位熵lq)每提高一個百分點,經濟增長水平相應下降0.395個百分點。從MODEL[Ⅱ]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看,各控制變量(lniq,pfe,lnperh,lnui)的回歸系數都是正數,表明其與區域經濟增長正相關,即各控制變量所代表的經濟變量每提高一個百分點,經濟增長水平將上升相應的百分點。其中,lniq、lnperh和lnui具有較高的彈性系數,說明生產性服務業市場規模、人力資本水平和居民消費水平和對區域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效應。pfe與經濟增長的正效應關系也表明,生產性服務業市場規模、服務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和人力資本建設都有利于區域經濟的增長。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分析
本文的主要結論為:長三角地區城市的服務業集聚程度與區域經濟增長呈現負相關關系,相應的彈性系數為-0.395,負效應影響比較明顯,作為一種“經濟信號”值得關注。同時,研究結果顯示,模型中各控制變量,如生產性服務業市場規模、政府干預程度、人力資本水平和居民消費能力,與經濟增長均呈現正相關,彈性系數分別為0.611、0.0315、0.307、0.127,即這些變量指標的提高,都有利于區域經濟的增長。對于長三角服務業集聚負效應出現的現實原因,本文認為有以下幾方面的解釋:
在衡量服務業集聚程度方面本文采用的是區位熵(lq)指標,該指標主要反映的是服務業集聚的專業化效應,所以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長三角地區城市服務業集聚開始呈現由于單一化特征而帶來的經濟增長負效應,也就是說,服務業集聚結構的過度單一化不利于經濟增長。
高程度集聚由于缺乏相關產業和支撐產業的協同,導致經濟增長負效應。邁克爾·波特在其“鉆石體系”理論中就指出,如果在形成產業集聚的過程中,沒有相關產業和支援產業的配合,產業集聚就會因為缺乏專業化的高級生產要素投入而發生停滯,阻礙經濟增長。所以,產業集聚發展到一定程度,專業化優勢可能會導致某一產業層面上聚集了過多的相似企業 (產業同構和競爭過度),而忽略了相關產業的協同集聚,從而導致集聚增長乏力。
高度集聚帶來的擁塞成本負效應,以及分工不充分帶來的惡性競爭不利于經濟增長。長三角是經濟活動的高密度地區,制造業和服務業水平都比較高,人口密度大,高密度的集聚會帶來交通、物流的擁擠成本。同時由于產業同構、行業結構的單一,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也會產生經濟成本,這些都成為地區經濟增長的阻隔。
(二)政策建議
長三角服務業集聚困境的出現,要求該地區的區域經濟政策應該有所轉變,對服務業集聚引導應從“量”變轉向“質”變,注重對服務業集聚結構和配套設施的調整與優化。
長三角地區在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以服務業集聚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應該把握好服務業規模和水平的適度發展,應注重城市群內基礎設施和交通建設,減少高程度集聚帶來的擁擠成本效應。服務業集聚的規劃應充分考慮城市交通的承載能力,不能一擁而上;同時,要打破行政屬性,注重城市群交通“一體化”建設,應綜合考慮各種運輸方式與地區經濟的配合,重點完善各交通節點與樞紐的通達性。
長三角地區城市服務業集聚的發展應該倡導多樣化,避免由于過度專業化導致的經濟增長負效應。各地區可以通過建立區域利益協調機制,在明確各自的主導產業的同時實行“差異化”定位,如服務產品、規模的差異化,以促進服務產業地區間的合理布局和分工的形成。同時應加大創新服務產品類型的力度,促進服務產業多元化發展。
加強服務業相關產業和支援產業的協同集聚,避免因服務業高程度集聚而缺乏支撐所帶來的負外部性。長三角城市在促進服務業集聚的同時促進配套制造業的協同集聚,這樣不僅有利于各自技術水平的提高,還可以削弱以往制造業集聚引發的地方產業同構、過度競爭和產業萎縮現象,推進區域產業結構的順利升級。[14]
在推動服務業適度集聚的同時,政府應在宏觀層面加強引導,提高居民消費能力、適當擴大服務業市場規模(尤其是生活性服務業市場規模)、加強合理干預程度和人力資本建設。
[1]Martin.P,G.Ottaviano.Growth and Agglomeration.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Volume42,Issue4,2001.
[2]Baldwin,R.E.,P.Martin and Ottaviano.Global Income Divergence, Trade and Industrialization:The Geography of Growth Take-Offs.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6,2001.
[3]Baldwin,Richard et al.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4]Fujita M.,and J.F.Thisse.Does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Foster Economic Growth?And Who Gains and Who Loses.The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Vol.54(2),2003.
[5]Berliant and Fujita.The dynamics of knowle dgediver sity and economic growth.http://mpra.ub.uni-muenchen.de/21009/1/berliantfujitaiiiv44.pdf,2010.
[6]Ciccone A.Agglomeration Effects in Europe.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46(2),2002.
[7]范劍勇.產業集聚與地區間的勞動生產率[J].經濟研究,2006,(11).
[8]Rice P.&A.J.Venables.Spatial determinants of productivity:Analysis for the regons of Great Britain.CEP Discussion paper,0642,2004.
[9]Midelfar,K,H.Does agglomeration explain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ies,mimeo.Norweg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CEPR,2004.
[10]Bode,E.Productivity effects of agglomeration externalities, Third Spatial Econometrics Workshop, Strasbourg, cournot2.u-strasbg.fr,2004.
[11]Sbergami F.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Some Puzzles[EB/OL].HEI Working Paper,No.02/2002.
[12]陳立泰,張祖妞.服務業集聚與區域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0,(10).
[13]胡霞,魏作磊.中國城市服務業集聚效應分析[J].財貿經濟,2009,(8).
[14]王奇.推進生產性服務業高端化發展的對策[J].經濟縱橫,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