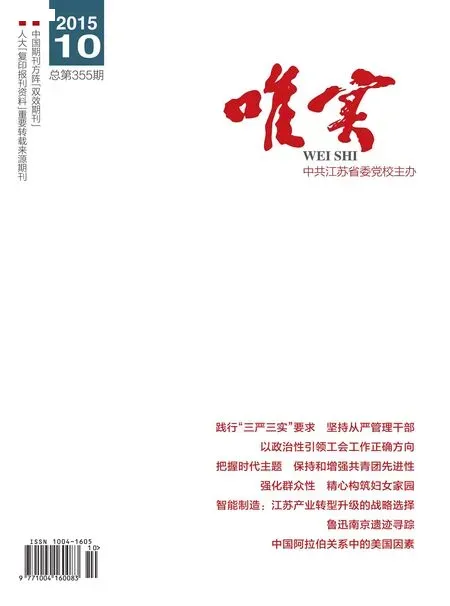絕、怪、奇泰州文化“名片”鄭板橋
鄒祥鳳
(作者系中共泰州市委黨校常務副校長)

鄭板橋,名燮,字克柔,號理庵,又號板橋,清揚州府興化縣人。生于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1693年11月22日),歷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曾任七品縣令,兼擅詩、詞、曲、文、聯、印、書、畫,為“揚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卒于乾隆三十年(1766年),享年73歲。板橋一生坎坷,歷經磨難,嘗盡人間酸甜苦辣,然則板橋以其入仕、辭官、賣畫的傳奇經歷,書法、詩文、繪畫的獨特風格,狂怪不羈、標新立異的思想品德,剛正不阿、胸襟坦然的文人形象,以及思想奇、風格怪、藝術絕而獨步古今,享譽四海!
一、板橋之絕
清代張維屏《松軒隨筆》評:“板橋大令有三絕,曰畫曰詩曰書。三絕之中有三真,曰真氣曰真意曰真趣。”
鄭板橋擅畫蘭、竹、石、松、菊、梅,而尤以水墨蘭竹石成就最高,取法于明代徐渭、清代石濤等,而自成家法。他畫的蘭竹石,以草書豎長撇法運筆,多不亂,少不疏,體貌疏朗,筆力勁峭,自稱“四時不謝之蘭,百節長青之竹,萬古不敗之石,千秋不變之人”,借以寄托其堅韌倔強的品性。他常常把竹、蘭、石生動地組合在一幅畫面上給予盡情發揮,在筆墨之外給人們留下許許多多回味無窮的感受。板橋的作品題材幾乎全是蘭、竹、石。專家分析說:以板橋之才氣,畫何物不成?只有蘭竹石最能表達其志向。蘭,有君子之德,清身脫俗;竹,高潔(節)之氣,親民之聲;石,堅強屹立,不媚俗承歡,本性固然。由此可窺見板橋錚錚鐵骨,清潔不屈之品質。
板橋的詩多見諸于題畫。“八怪”時期,藝術創新求新求變,別出心裁的題畫以及文人書畫相互題跋,是一種時尚,其中佼佼者,又首推板橋。板橋的題畫詩長于寫意,耐人尋味。廣為流傳的《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以竹喻人在惡劣的環境中堅挺頑強,獨立不移的崇高人格與堅勁精神;“葉自短,花自長。蓄其力,揚其芳。花在室,香滿堂。”“身在千山頂上頭,突巖深縫妙香稠。非無腳下浮云鬧,來不相知去不留。”靈石千年永恒,翠竹四時不凋,是一曲生命的頌歌。“四十年來畫竹枝,日間揮寫夜間思。冗繁削盡留清瘦,畫到生時是熟時。”“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把創作的艱辛、追求的執著,最終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生動、形象地表達了出來。
板橋以書畫聞名于世,書畫比較,書名又大于畫名。板橋書法以漢八分雜入楷、行、草,綜合草隸篆楷四體,再加入蘭竹筆意,獨創工楷隸書法,寫來大小不一,歪斜不整,自稱“六分半書”。他以黃山谷筆致增強作畫的氣勢,以“亂石鋪街、浪里插篙”形容其書法的變化與立論的依據。板橋的字怒不同人,追求作破格書。破格,即破王羲之之格,破唐宋傳統之格,破董其昌、趙孟頫之格,破書壇諸圣賢之格。板橋的字隸入行楷、亂石鋪街、醉漢夜歸、震雷驚電,自辟蹊徑,別成一家,有創新突破,有情致韻味,為世人所稱道、所推崇、所寶貴。
二、板橋之怪
板橋之怪體現為拒絕桎梏、張揚個性、不守成規、富于創造,其以畫怪、文怪、性情怪、行為怪出名,窺其潤例、辭官、率性之舉,可見面貌。
板橋《潤格》,寫字畫畫,斤斤計較于酬金,自是俗不可耐。但板橋毫不隱諱,而且明定出一則可笑的怪潤例:“大幅六兩,中幅四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若送現銀,則中心喜悅,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恐賴賑。年老神疲,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板橋公開潤格,便是公開認可藝術也是商品,這是把藝術品推向市場的一種驚世駭俗之舉,也是板橋走出表里未必一致,心口未必一致,徹底把生存需要宣示于人的一種心理突破。“畫竹多于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春風過耳邊。”明明是俗不可耐的事,但出諸板橋,轉覺其俗得分外可愛,這是用藝術的形式重申《潤格》內容,同時也是他直率坦誠性格的真實表露,面對無知卻又想以字畫獲取商業利潤的市儈和附庸風雅的達官顯貴來說,自然也不排除這是一張閉門謝客、拒絕騷擾的免戰牌。板橋是中國歷史上進士明碼標價、公開銷售字畫第一人,亦是中國歷史上文人從商、融入市場經濟第一人。

板橋任濰縣知縣,遇饑荒,修筑城池,迫富豪平價售糧,被密告,以賑災不當被懲,乃辭官歸去,并畫竹別濰縣紳士民:“烏紗擲去不為官,囊橐蕭蕭兩袖寒;寫取一枝清瘦竹,秋風江上作漁竿。”又為惜別僚屬,畫菊詩:“進又無能退又難,宦途跼蹐不堪看;吾家頗有東籬菊,歸去秋風耐歲寒。”一般為官者都會了解,為政得罪巨室,就難有好的下場。而板橋一反積習,獨行其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最后,不惜扔掉熱烘烘的烏紗,而寧可回到冷颼颼的秋江上去釣魚,必須曠達的心胸,才能自然流露出這般的瀟灑。“畫竹插天蓋地來,翻風覆雨筆頭載;我今不肯從人法,寫出龍須鳳尾來。”既寫畫竹的氣勢,又喻人與竹的“擇善固執”及不從俗流、不為俗物的個性;其詩文去陳舊套語,白話代替古典,是板橋志節的寫照,也是其“三絕詩書畫,一官歸去來”生平的概括和體現。
板橋的“怪”,頗有點濟公活佛的味道,“怪”中總含幾分真誠,幾分幽默,幾分酸辣,頗有罵名。每當看到貪官奸民被游街示眾時,板橋便畫一幅蘭竹石,掛在犯人身上作為圍屏,以此吸引觀眾,借以警世醒民。辭官歸來,無官一身輕,再回到揚州賣字畫,身價已與前大不相同,求之者多。但板橋最厭惡那些賣弄斯文的暴發戶,縱出高價,也不加理會。高興時馬上動筆,不高興時,不允還要罵人。這種怪脾氣,自難為世俗所理解。一次為朋友作畫時,板橋特地題字以作坦率的自嘲:“終日作字作畫,不得休息,便要罵人。三日不動筆,又想一幅紙來,以舒其沉悶之氣,此亦吾曹之賤相也。索我畫,偏不畫,不索我畫,偏要畫,極是不可解處。然解人于此,但笑而聽之。”其坦誠率真、特立獨行躍然紙上。
三、板橋之奇
徐悲鴻題板橋《蘭竹石軸》云:“板橋先生為中國近三百年來最卓越人物之一,其思想奇,文奇,書畫尤奇。觀其詩文及書畫,不但想見高致,而其寓仁慈于奇妙,尤為古今天才之難得者。”板橋的民本思想超凡脫俗,人生態度則處處閃爍著思想的光輝。
板橋的民本思想,表現在關注農村生活,關心農民疾苦,憎惡貪官盤剝,謳歌親情友情。《逃荒行》描繪了山東農民逃荒流落的悲慘經歷;《悍吏》、《還家行》充滿了濃濃的人道主義精神;《滿江紅·田家四時苦歌》描繪了一幅幅生動逼真的農家苦樂圖:既有“霜歲未儲終歲食,縣符已索逃租戶,更爪牙常例急于官”的罪惡與苦難,也有“桄桔響,村歌作,聽喧填社鼓,漫山動郭”的熱烈與歡樂;既有“耘苗汗滴禾根土,更養蠶忙殺采桑娘”的辛勞,也有原上摘瓜、池邊濯足,“晚風前個個說荒唐”的愜意。其中最為人所稱道的還是那首《衙齋竹畫軸》:“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其詩文書畫中,總是不時地透露著這種清新的內容和別致的格調。板橋的畫“三不賣”:“達官貴人不賣,夠了生活不賣,老子不喜歡不賣。”但是,鹽商官吏們弄不到的作品,許多清貧學子和農夫、小販、工匠、士兵等下層小人物卻很容易“求”到。其行如其言:“凡吾畫蘭、畫竹、畫石,用以慰天下之勞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板橋的超凡脫俗,表現在豁達大度、詼諧幽默,表現在蔑視功名利祿、淡泊榮華富貴。板橋作官時,其弟因蓋房與鄰居爭地,彼此互不退讓,以致各向前修圍墻,阻斷道路。弟弟修書希望幫忙打贏官司。板橋回信:“千里捎書只為墻,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鄰居知悉非常感動,遂各自退讓三尺,而成了“六尺巷”。板橋辭官回家,“一肩明月,兩袖清風”,惟攜黃狗一條、蘭花一盆。一夜,天冷,月黑,風大,雨密,板橋輾轉不眠,適有小偷光顧。他欲呼喊捉賊,但恐無力對付,便吟:“細雨蒙蒙夜沉沉,梁上君子進我門。”小偷聞聲暗驚,繼又聞:“腹內詩書存千卷,床頭金銀無半文。”小偷轉身出門,仍聞:“出門休驚黃尾犬。”小偷正欲逾墻而出,又聞:“越墻莫損蘭花盆。”小偷看墻頭果有蘭花一盆,乃細心避開,足方著地,屋里又傳出:“天寒不及披衣送,趁著月黑趕豪門。”“老書生,白屋中,說黃虞,道古風;許多后輩高科中。門前仆從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龍。一朝勢落成春夢。倒不如蓬門僻巷,教幾個小小蒙童。”板橋道情道出了板橋真性情。
板橋的人生態度,表現為大智若愚、寵辱不驚。“聰明難,糊涂難,由聰明轉入糊涂更難。放一著,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后來福報也。”板橋本是個聰明絕頂、通今博古的一代文豪,卻偏偏寫什么“難得糊涂”,并煞有介事地再加上個注:“聰明難,糊涂難,由聰明而入糊涂更難”。“難得糊涂”,既是有鑒于官場中的糊涂,他難得那種糊涂,只有及早抽身;又有點看透世態,為免多惹煩惱,不妨糊涂一點。“滿者損之機,虧者盈之漸,損于己則亦于彼。外得心情之平,內得我心之安。既平且安,福即于是矣。”“難得糊涂”、“吃虧是福”,平淡、簡約、精煉有味的名言,其睿智、思辨、哲理充溢于字里行間,亦以其頓悟、啟迪、教化深刻流芳百世。
康乾盛世時之板橋,其思想、風格、藝術的“奇”才睿智、“怪”言懿行、“絕”古鑠今,一直為人所研究、敬仰、贊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