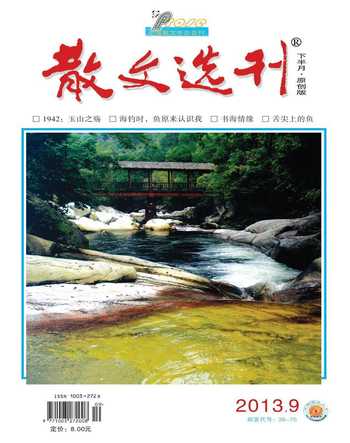海之殤
李淑菲
一
夏季,我經常隨著老公孩子到海濱浴場,我是“旱鴨子”不敢下水,水到齊胸處便會倒吸氣。我屢次想學游泳,就是戰勝不了那份莫名其妙的恐懼,但我又喜歡到海邊,在這特定的時刻,人,在不經意間打破了固有的防線,彼此之間多了一份欣賞與善意的目光。而我呢,不會游泳,只好在金色的沙灘上撿零星散落的七彩貝殼,踩著柔柔的沙灘,每踩上一步就留下一個孤獨的腳印。
當我獨自面對大海的浩渺,在沙灘上空蕩蕩地承受潮起潮落的僵硬風景,寂寥空落襲上心頭。微微蕩漾的藍色海面,像一塊柔柔的綢緞,飄逸、雋秀而舒適。
覆蓋在這塊湛藍的帆布底下的海就像一首歌、一篇散文、一首詩、一部長篇小說,寫滿不同的人可以解讀的內涵。
二
漁村林頭與東山的大嵼村隔海相望,往來僅靠小木船渡人,古來如此。
后來架起了跨海橋,是座連心橋。我站在施工了一半的橋板上,晃晃蕩蕩的鐵索抖動著,腳底有些發癢,透過木板間的縫隙,可見腳底下蕩漾的波濤,人在碧波之上,間隔著距離,卻又有著絕對的安全和美感。我站在“橋”上,聽海濤、沐海風,凝望著海面,海潮一浪漫過一浪,漲潮了,海浪轉側著,伸著腰和腳,抹著眼睛,一刻比一刻興奮,有時又一浪高過一浪,激昂澎湃像千軍萬馬急馳而來,聲音像戰鼓聲、銅鑼聲、嗩吶聲等各種聲音在一起爭鳴。
就在橋下,大概十年前發生了一起海難。這起海難像海水撞擊著礁石發出轟然聲響,真是千萬次安然無恙卻經不起一次的意外。那一年,一只小船載著村里的十幾個人,天氣預報已經發出警報,他們懷著僥幸心理出海了。剛出海不久,突然風浪滔天,似有一只巨大的手掌,輕而易舉地把海面上的一切揪翻了,船兒就像一只翻轉的魚兒出沒在風波里,就在片刻間,船翻了,人沒了,漁民在海水中奮力掙扎,巨浪像侵略者一樣絕情地把人一會兒頂到波浪頂尖,一會兒又把人重重按到深深的海水里……掙扎、呼救、殊死搏斗……人與自然的爭斗最后以人的血淋淋的悲劇而告終。
烏云久久不散,當地人對這片海域有著莫名的恐慌。大概十年之后,林頭與大嵼的海面上架起了鐵鎖鏈,緩釋當地人心中的隱痛。
海風輕輕吹,我一直站在橋上,這里除了海浪的翻卷聲,顯得真安靜啊,沒有人來打擾,更少有人像我這樣在橋上一站就是老半天。
獨自一人在海邊,心的波濤便與海的波濤同節拍,泛起淡淡的落寞。
三
小時候曾經聽媽媽說“沉東京,浮南澳”,說的是地理的變遷,雖然沒有確切的記載,但很多關于大海的民間話語卻是一張龐大的灰色的網,令我戰栗。
我曾經隨同村里的人去“討海”,凌晨四點多出發,走夜路似在夢中,急急忙忙走了幾里崎嶇小道到了海邊,等海水“退潮”,大家急忙卷起褲腿“下海”了,其實是到灘涂上撿來不及隨潮流的小魚小蝦,反正到了回家時,我除了腳底被貝殼殘片刮破隱隱作痛,背簍里僅有幾顆小貝殼和小魚蝦,夠不著喂貓吃一餐,就這么一次下海,夠折騰又無所獲。自此,對海邊的漁民敬意頓生。那是怎樣的人生哪?
一次鬧臺風后,村里來了一位說話含混不清“咬舌尾”的大姐姐,挑著一擔大黃魚,一塊錢三斤,可是幾十斤魚在幾十戶人家的村子里竟然賣不完。那時是生產隊集體生產時代,口糧定額,好多人家甚至缺糧,哪來的錢買魚?我見那個大姐姐瑟瑟發抖,嘴唇發黑,原來他家已經米缸底朝天,他餓著肚子就出門賣魚了。我望著原生態的大黃魚睜著大眼睛,似乎還會說人話。等那位姐姐走后,鄰里在竊竊私語,大概說那位姐姐是村里的準媳婦,她哥哥長得粗壯如牛,生性粗魯,但是,他家“成分”好,窮苦出身,經介紹“等對”,找到村里成分高出身“富裕”的大媽家,她兒子身材壯實臉盤周正,女兒也是村里一枝花,就這樣,這兩家的婚事成了村里第一個“敢吃西紅柿”的新聞“姑換嫂”……
當天塹變通途的時候,一切,變了。
跨海大橋在空中跨過,橋下的海浪碧波已經干涸了,海灘上再模糊了往日貧窮的尷尬痕跡。近海岸的海域,一間、兩間,無數間海上小屋在飄蕩著,一個個用泡沫制成的圓圓的浮球在風浪中起伏,像大海的眼睛,上邊沾滿珠圓的海水,是不是大海的淚水呢?泡沫浮球牽扯的是“網箱”,網箱里養殖的是珍貴的海魚,那些瀕臨絕跡的,人所喜歡的美味佳魚粉墨登場,在餐桌上散發誘人的香味,現代運輸的高速,速凍保鮮手段的前所未有,終于使餐桌有了大魚大肉。
當地人很時尚的一味菜肴:“苦瓜花蛤湯”,清淡而味美。可是,市場出現一種個兒大肉豐的花蛤,價格更高,后來有漁民自暴玄機:喂養“避孕藥”催生而速長,還有“超大”黃鱔魚也是,并非魚販所說“野生”的……還有一些魚翅、魚膠干貝之類的海制品,也經過“藝術”處理而膽寒。
原來尋常人家不可能見到的名貴海魚,現在可以在市場上隨意買到,倒是一些海鮮成為稀罕之物,有的瀕臨絕種,連小時候見得最多的大黃魚,也少見了。
責任編輯: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