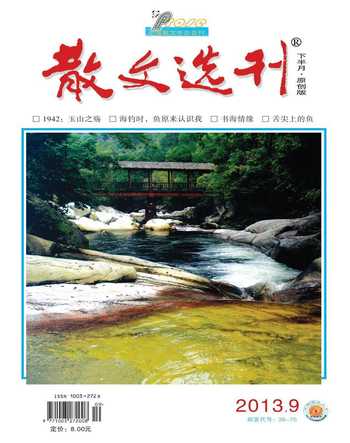母親的村莊
李文凱
故鄉寧靜的夜,被含露的蛙鼓敲醒。母親牽動清晨的云朵,穿行一路鳥語花香,開始新的一天勞作……
她的這些蹤影,起伏的群山、蜿蜒的溪流、層疊的田土,在四季輪回中見證。母親認為,川東丘陵是一片神奇的天地,五谷雜糧養育了生靈,希望的田野捧起了村莊。因此,她始終默默地守望在那里。
母親之所以摯愛腳下的土地,是因為與這里的村莊有著締結難解的緣分。她上世紀30年代出生于居無定所的佃戶人家,共和國一場改天換地的壯舉,讓包括母親在內的鄉親們當家做主,分得了房產和田地。父親為了守住來之不易的平安生活,他參加了征糧剿匪斗爭,接著派駐母親的村莊指導農業生產,與母親成家立業后,又調往全縣各地管理農事。誰知,上世紀60年代初發生的災荒,使所有的村莊陷入極度困境,父親第一批申請還鄉。母親不愿意去父親那百里之遙的起鳳村,父親說起鳳村能夠聽到鳳凰鳴叫、看見龍鳳呈祥,沒有上過學的母親懷揣著好奇,跟著父親跋山涉水來到村里,發現受了誆騙,一直埋怨父親。母親隨著家庭擔子的加重而面對現實,認定父親所扎根的地方才是她真正的村莊。
村莊聚落構成了遼闊疆土上的鄉梓面貌,人們依賴山水,肩挑背磨,靠天吃飯。母親跟村莊一樣瘦,父親病故后她更瘦了,她時刻把名聲守成一座堅固的牌坊,把炊煙送上天空,把兒女送進學堂,把日子當做衣服,縫了又補,補了又縫,活得像一首土得掉渣的歌謠。
飽經滄桑的村莊,終于在劃時代的變革中被詩意地瓦解,盼來綠柳舒眼,春風浩蕩。不愁吃穿的母親,扛著鋤頭,走向山坡,走進菜園。她深深懂得手中的鋤頭,能刨出生計,能開劈出一家人的未來;她用力鏟埋雜草,碎散泥團,播下種子,用汗水去澆灌禾苗,去茁壯兒女的夢想。
母親偶爾進一趟城,我們每次都勸她定居城里,她一直沉默著,不答應。有一次,她說:“那些田土出產的糧果蔬菜,養活了農民,也養活了城市的人,放棄村莊就是忘本。”母親的這些說法,好似有一種憂患意識。難怪,她每次在城里住不上兩天,就會念叨起來:“檸檬樹要施肥,修村公路要幫忙,幺嬸滿百歲要趕酒,張家媳婦快生娃娃要去照看……”母親的唇齒間一旦跑出類似語言,就是發出要離開的信號。我仿佛從母親樸素真誠的言行中,看到她時刻在惦記著村里的鄉親們。
我雖然身居城市,但割舍不了與村莊的血緣,餐桌上的飯菜,總是讓我想起村莊,想起母親。我經常憑一串號碼與母親傳遞親情,她說現在村里人能夠領養老金,看病拿藥報銷,娃娃讀書免費……大家知道的這些事情,她每次都要津津樂道一番。每當聽到母親被幸福替代的心情,回首村莊的幾度枯瘦豐盈,她的話語總是揪扯著我的靈魂。
母親皈依田園,和農作物朝夕相處,以自信的荷鋤姿勢,鐫刻人類文明的蒼茫的圖騰。
責任編輯:黃艷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