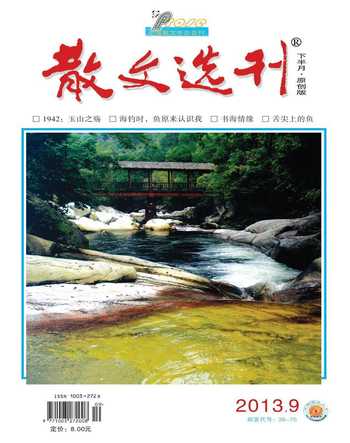割葦記
趙力
1975年秋天,在我們下鄉再教育的第二年,決定蓋房解決自己的住宿問題。知青們在大隊的糧倉里住了一年多,隨著人數的增加,已經住不下了。我們十幾個小伙子,自帶行李,開上拖拉機來到莎車縣東方紅水庫邊,在水管站簡易土床上擺下行李后,引吭一曲《沙家浜》,走向蘆蕩。
“蘆蕩”一詞,在我的想象中,應是葳蕤繁茂、蓬蓬勃勃、隨風起伏沙沙響之狀,可這水庫下游無際無涯的灘地上,哪曾出現這般景象?縱目望去,似乎有一片海市蜃樓般的綠濤翻涌,在召喚著你的銀鐮,在召喚著你急切下手的欲望,可當你一走近,仍是那叢叢低矮的葦子在呆站著。
“葦灘”很大。兩尺來高的葦子東一撮,西一撮;那連成一片的因互相搶占養分的緣故,就更矮了。我們十幾個人,向四面八方散開,各自占地一大片。每人幾乎都是一樣的動作,割倒幾叢,跨一兩步,等手中的已經握滿,就放成一堆,隨手抽出堆中最長最壯的,系一個結,把成堆的緊緊一扎,就成捆了。
年輕人誰也不吝嗇汗水,就連擦汗,也很少抬頭;偶爾抬頭看到別人的捆比自己的多,又暗暗地加力了。就是手被葦葉割破,也不吭一聲。半天下來,每人都擁有了一座“小山”,一座墨綠色的山。歇息時,小組長從軍用挎包里掏出金燦燦的包谷馕,扔你一個扔我一個,馕香鋪了一地,那是我們的美味佳肴啊。在余暉里,一個個著紅背心的腰身起起伏伏,像綠野里一蓬蓬跳動的火焰,逼向天邊。
月亮升起來了。割葦的第一夜,由我和K君值班,看護“葦山”,這是我們主動提出來的。有一個明確目的,就是趁著割葦的新鮮勁,作一首名叫《戰蘆蕩》的詩。這題目是白天小憩時兩人一起定的。
太陽落山之前,十幾個人把各自的葦捆搬運集中,由我和K君壘成一個方形的“葦城”。“城墻”約兩米高,墨綠色的“墻”,給人一種清雅,一種暖意,更給人一種蔥蘢蓊郁的詩情。我們從水管站的土房里搬來鋪蓋,喜滋滋地躺在蘆葦床上,吮吸著葦子清芬的氣息,吮吸著泥土溫馨的氣息,疲倦的身子溢出一股青春的豪光,蘸著月色,鋪展稿紙,作起詩來。你吟出一句“滔滔碧海一臂挽”,我對出一句“簇簇浪花一鐮撈”,一聲低,一聲高,空寂荒涼的“葦灘”里,兩人的聲音蒼茫而又渺小——
風卷蘆蕩掀波濤,知青腳步似鼓敲。一路風塵未打掉,蘸著汗水磨鐮刀。
滔滔碧海一臂挽,簇簇浪花一鐮撈。借得手中千層繭,堆起蘆葦百丈高。
多像當年新四軍,青紗帳里逞英豪。引吭一曲《沙家浜》,激起胸中萬丈濤。
嚓嚓鐮聲抒豪情,蘆葦點頭拍手笑。捆捆蘆葦化紙片,頻傳張張紅喜報。
月兒升高,拙作寫成。最后兩句有意“偷換”了最終目的,我們割葦不是用來造紙,而是用來蓋屋。
在那荒誕無稽的歲月,我們不也是一根根風霜中的葦子嗎?我們割著葦子,時間的利刃同時也割著我們;葦子感覺到疼痛紛紛倒下,而我們絲毫沒有一絲痛感,流血的心都像花兒一樣笑著開放,還美滋滋地寫出了“抒豪情”的“紅喜報”。當年那個月夜,我們躺在捆著的葦稈上,可又是誰把我們的身心捆著?!
1976年秋,又一批知識青年下鄉,房子不夠住了。
公社革委會決定由我帶隊,再一次開赴葦灘。有人提出換一個地方,我不肯。我對他們說,在頭年割去葦子的地方,今年的葦子必定長得更加茂盛茁壯。有人不信。
到了葦灘,安營扎寨,只見連片的青葦隨風起伏,把綠色的旗幟一直展向天邊。我用刀把量葦子的身高,果然比去年高許多,知青們揮動的銀鐮也覺得比去年鋒利。
我進城工作以后,經常乘車路過那片葦灘,再也未見過一個割葦人。那每一棵蘆葦,都朝我射來憂郁的目光,似乎在責怪我:為什么不來割刈我?那葦子們高高低低,不繁茂且不茁壯,身心也似乎過早地褪色,秋風一過,葦葉紛紛揚揚,嘆息著飄向戈壁深處。
每一個靜夜,我都能聽到鋒利的巨鐮,在收割著我生命的青葦,“嚓嚓嚓嚓”,清脆、有力,音色是那樣絕美,那樣凄迷。
責任編輯:子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