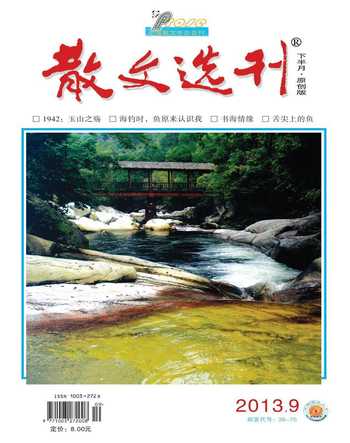遠逝的石榴花
陳曉頻
那時候,天蒙蒙亮,我就離開家,去很遠的學校讀書。走到山谷的入口,總會看見鄰村的丹丹站在石榴樹下等我。
山谷并不長,半個小時就可以穿過。山路兩邊雜草叢生,隨風起伏。早醒的鳥兒一聲驚叫,從草叢中一飛沖天,嚇得丹丹雙手緊緊拽住我的衣角。那時候我上初中,還是個懵懂無知的少年,經常嘲笑她膽小如鼠。
傍晚,我們在校門口等待對方,因為我倆的村莊都很小,而且地處偏僻,找不到其他的同伴。一路上,她就像我的影子,緊隨在我身后,對我說些天南海北的事。她的爸媽帶著弟弟在深圳打工,每半月給她寫一封長長的書信。回家的路上,她愛將信里的內容講給我聽,聽著她繪聲繪色的講述,我的心不覺飛向了外面的世界。
山谷的入口處,曾經筑起一道兩米高的大堤,攔住從山上流下來的雨水,形成一座小型水庫。大堤兩端各種有一棵石榴樹,石榴果實每年發育不充分,因而不能食用。但是一到五月,火紅的石榴花開滿枝頭,熱鬧出無限風情。有一年大堤崩潰,水庫和一棵石榴樹從此消失,另一棵石榴樹卻幸存下來。清晨,我和丹丹在石榴樹下見面;傍晚,我倆在石榴樹下分手。喜愛石榴花的丹丹常說,那石榴樹是山谷最美麗的風景。
五一勞動節還沒到,樹上就喧鬧起來。丹丹站在樹下,小心翼翼地問我:“美嗎?”我信口答道:“一派繁華!”丹丹又說:“再看看!”我圍繞石榴樹走一周,說:“絢爛之極!”丹丹鳳眼一低,柔聲說:“你只看花,就不看別的?”我這才注意到丹丹穿著火紅的裙子,玉樹臨風般站在石榴樹前,笑吟吟地看著少年不經事的我。她的背后,艷麗的石榴樹在初夏的清風中婆娑。那一刻,我心迷意亂,神情恍惚,恨不能立即逃走。我說:“走吧!”丹丹跟在我身后,扯扯我的衣角,說:“今天是你15歲生日,我特意穿了一件新裙子,從深圳寄回來的——”我的心怦怦亂跳,不敢回頭看她。
我爬上學校的單杠給秋千系繩子,不慎摔下來跌傷了左腳。我住進了市人民醫院,丹丹只好跟鄰居朱屠夫一道穿過山谷,他每天清晨挑著豬肉去外村叫賣。至于傍晚,丹丹就只能壯著膽子獨自穿過山谷了。一個多月后,也就是中考前四天,我從醫院回到家里,才知道發生了巨大的變故。丹丹的爸爸突然從深圳趕回,接走了即將參加中考的女兒。她的奶奶突然喝下滿瓶農藥,痛苦地離開了人世。這是為什么呢?我心里一片茫然,只聽見丹丹細碎的腳步聲。
我孤獨地走進山谷,看見丹丹的爸爸揮舞著柴刀,瘋了似的亂砍,茅草和樹木紛紛倒在他的腳下。我走出山谷,還能聽見他歇斯底里的咆哮聲在山谷里回蕩。有幾回放學回家,見他累倒在路旁,撕扯自己的凌亂的頭發,一綹又一綹,在風中頹唐地飄落。
山路兩旁的柴草砍倒了一大片,丹丹爸爸的頭發也差不多掉光了。曬枯的柴草全部挑走了,丹丹家門口堆起五個大柴垛,全都高過屋檐。中考成績揭曉了,我考上了理想中的學校;而丹丹,那個成績與我難分上下的丹丹,卻沒有參加考試。我坐在村前的一棵古老樟樹上,傻傻地想:“丹丹去了深圳,很遠很遠的南方城市……”
丹丹的爸爸做起了養狗專業戶,他每天到各村買狗回家飼養,準備到冬天賣給城里的火鍋店。一天黃昏,他牽著一只黃狗從我家門前走過。我看見他一雙眼睛躲在睫毛后,透出陰森的殺氣;胡須亂蓬蓬的,就像被他砍伐后留下的柴草樁。他的形象太可怕了,我不敢上前打招呼,默默地看著他離去。等到他的背影消失在夜幕中,我悔恨交加:為什么沒壯膽問問丹丹的情況呢?哪怕只得到一個地址也好啊!
晚上,我和哥哥睡在竹席上,說了很多關于丹丹的事。哥哥突然爬起來,盯著我看了很久,驚訝地說:“你長大啦!弟弟!胡子長出來了!”
天氣一天比一天熱,就是不見一滴雨落下來。我騎坐在村口的樟樹杈上,不住地思念丹丹。對面就是她的村莊,群狗狂躁的叫聲傳進我的耳朵里,我的心情跟著煩躁起來。我無所事事,百無聊賴地等待新學期的開始。
后來的一天,我又坐在樟樹杈上,哥哥跑過來對我說:“知道嗎?朱屠夫被狗咬了,正在醫院搶救。聽說像狗一樣叫,悲慘得很哩!”我從樹上滑下來,想探聽個究竟。哥哥告訴我,丹丹的爸爸好幾天不喂狗,一群狗饑腸轆轆,餓得嗷嗷叫。不知它們怎么逃了出來,沖到隔壁朱屠夫的肉案,瘋狂地撕咬。朱屠夫慌了神,隨手拿起板凳去驅趕,被咬得渾身是傷。在鎮衛生院治療了一天,第二天送進市人民醫院,醫生攤開雙手,嘆口氣——狂犬病無藥可治,他們無能為力。
突如其來的事故,在附近村莊掀起巨大的波瀾,大家都在談論、嘆息。人們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竊竊私語,神秘兮兮的,似乎在談論什么秘密。我越發好奇,整天纏著大人打聽,但是沒有人向我透露只言片語。
朱屠夫死了,他的四個兒子怒氣沖沖地從廣東趕回,向丹丹的爸爸索要一大筆錢。丹丹的爸爸拿出多年的積蓄,又賣掉了一切有人購買的家產,還向親朋好友借了一些錢,終于平息了朱屠夫一家人的怒火。
后來,丹丹家大火沖天。睡熟的村民被驚醒,衣衫不整地跑出來救火。人們驚恐萬狀,不知丹丹的爸爸是生是死。他卻從村頭慢悠悠地走出來,手里握著一瓶啤酒,破開喉嚨喊:“別救了——別救啦——除了幾堆柴草,什么東西也沒有!”天亮的時候,丹丹的爸爸走了,說是去深圳和妻兒團聚。想到他無家可歸,從此浪跡天涯,大家都嘆息不已。臨行前,他十分熱情地和四鄰告別,令人驚訝不已。丹丹的爸爸遠走他鄉,卻沒能帶走我對丹丹的思念。
朱屠夫葬在山谷里,使我感到莫可名狀的恐懼。一天早晨,我去鎮里購物,走到石榴樹下,想象朱屠夫狗一樣地慘叫,不禁毛骨悚然。猶豫良久,我決定繞道而行。我暗自慶幸:初中總算畢業了,清晨必須通過山谷的日子結束啦!
可是丹丹,你在哪里呢?
許多年過去了,我都沒有見到丹丹,也沒有收到她的來信。只是聽到村里人說,丹丹的爸爸到達深圳的第二天,夫妻倆就辭了職;第四天,一家人就搬走了。他們究竟去了哪里呢?我附近村子里的人跑遍了廣東的城市,至今都沒有見到他們一家人的影子。村里人都說,也許那一家人根本就不在廣東。
我少年心事里的丹丹,15歲的丹丹,就是那朵最最美麗的石榴花啊!
責任編輯:黃艷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