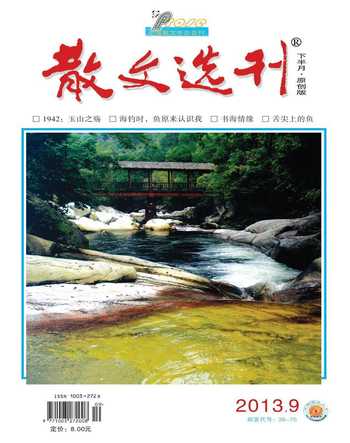豐盛的午餐
洪建生
小時候,我們跟著父親,租住在生產(chǎn)隊的一戶農(nóng)民家里。
父親苦出身,喜愛和熟悉農(nóng)活,很快就和農(nóng)民朋友打成一片,不久便被“三結(jié)合”,重新回到公社上班。也就在這一年,我隨父親到公社所在地的一所學(xué)校讀小學(xué)三年級。那時我們?nèi)伊谌耍瑑H靠父親一人的工資維持生活,有些窘迫。但生產(chǎn)隊給了一塊菜地,我們在父親的帶領(lǐng)下,生產(chǎn)出一些菜蔬和五谷雜糧,補貼家用,填補了一些空缺。這樣,我下午放學(xué)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到菜地干活。有時是獨自一人,有時隨父親。隨父親時,總要做得很晚,直到暮色四起時,才被母親一遍遍地喊著吃晚飯。
父親工作的公社,坐落在解放前一大戶人家的祠堂里。祠堂里面深邃幽靜,高比現(xiàn)在的三四層樓房,白墻黑瓦,從前至后有三進,穿過兩道天井。祠堂有許多根兩人才能合抱的圓形木柱、四方石柱,它們都聳立在鼓一般形狀的石墩上,柱和柱之間是規(guī)格不一的冬瓜梁連接,形成了現(xiàn)在已經(jīng)難以見到的房屋結(jié)構(gòu)。里面的墻體都是用上好的木板隔斷,木板下端和地面四周是長條和整齊劃一的青石板排列和鋪就。地面的材料,據(jù)老年人說是用糯米熬成的汁與石灰砂石攪拌而成的,堅實而又平滑,呈淺灰色,上面還分布著淺淺的網(wǎng)狀線條。房間分立兩旁,臨天井的方向一律開了窗戶采光。夏天里,常常見有五彩的蝴蝶和蜻蜓從大大的門庭里款款地飛進來,然后又從高高的天井悄無聲息地舞出去。
記憶中,公社的干部人數(shù)很少,能數(shù)得過來也只是十個人出頭一點。農(nóng)忙的季節(jié),干部們推了自行車,戴了草帽,走村串戶包生產(chǎn)隊去了。父親雖然是秘書,也是要經(jīng)常到生產(chǎn)隊去的。所以我和父親一起吃午飯的次數(shù)是很少的。白天里公社靜悄悄的。中午放了學(xué),我到父親房間里,拉開抽屜,數(shù)出飯菜票,到食堂買四兩飯,一份菜,青菜或者豆腐,偶爾也能買幾塊紅燒肉,是很好的了。比在家里的伙食要好一些,而且不用與兄妹們分享。父親因為工作的需要,占了兩間房,一間是臥室,一間做辦公用。臥室很小,里面差不多被床、桌子、凳子、箱子、洗臉盆架子塞滿了,外面辦公間卻是空曠得很,靠天井雕花的木窗下,擺了三張三屜桌,兩張相對一張橫頭,聚在了一起。父親的辦公桌上多出一塊玻璃臺板,上面壓了介紹信證明之類,顏色已經(jīng)泛黃了。有一面墻,靠墻立著兩張多抽屜木櫥子。木櫥的一端有一根木條上了鎖,開其中的任何一個抽屜,都要先開了壓在上面的木條。開木條上面鎖的鑰匙是父親長年掛在褲腰帶上。有一回,父親把鑰匙放在了桌面了,我因為好奇,順手抓在手里玩。父親看見了,從我手里拿過鑰匙,對我說,公家的東西不要亂動。但我感興趣的是立在我父親辦公桌座椅的背后的一只木架,那上面架著的,是那個年代常見的三種報紙:《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參考消息》。
我把飯菜端到父親辦公的桌上,并不急著吃。而是先從報架上然取下一份報紙,通常是三份報紙都要翻一下的,但主要是《人民日報》。這好像是吃飯之前先要進行的一道儀式。雖然以現(xiàn)在的眼光看,那時報紙的內(nèi)容有些空泛,曲高和寡,版面設(shè)計難以出新,但讓我在中午的時間里,了解到比我的同學(xué)多很多的國內(nèi)外大事。由于中午有充裕的時間,一個人又獨占一間辦公室,中間并無人來打擾,便一邊咀嚼,一邊細(xì)細(xì)地讀可口的文章,以至于炊事員阿姨總是跑到窗子底下,催要碗筷拿到廚房去洗。每天讀報,我注意看的是周總理同外國賓客的合影照。周總理居中,將右手端于右側(cè)胸腹之間,臉龐清瘦、表情凝重。后來知道,這是周總理最困難的時期,所以到現(xiàn)在想起來,也是久久地?fù)]之不去。此外就是散文、詩歌、雜文,我差不多是每篇都要讀一下的。我在這一時段里,對《人民日報》的鐘情,成全和培養(yǎng)了我對閱讀的愛好。以至于有一次校長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對全校考試情況進行點評時,舉了幾個學(xué)習(xí)用功的同學(xué)為例子,號召全校同學(xué)學(xué)習(xí),我也在其中。對我的介紹,則注重說我在吃飯時間不忘記讀報,意思是我的學(xué)習(xí)精神可嘉。但我要心存感激的是,因為父親工作的關(guān)系,使我的每頓午餐都變得豐盛起來,而別的同學(xué),是沒有這樣待遇的。
此后參加工作,我的辦公桌上一度也常年擺放著《人民日報》。只是由于工作忙碌,不能像在父親的辦公室時從容地讀看《人民日報》。但是只要有空,或者出差,或者去參加一個會議,我都會把隨身攜帶的《人民日報》悄悄打開,悄悄地閱讀。
因為它是我平生閱讀的第一份報紙,就好比是初戀。
責(zé)任編輯: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