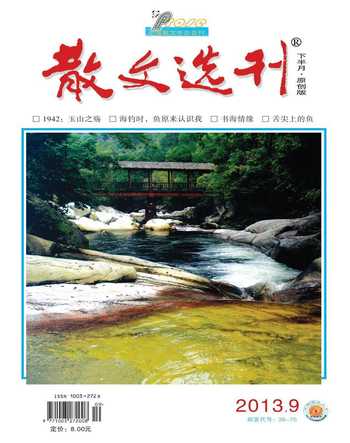丁香結(jié)
張曉帆
那一年,我在省城的一家醫(yī)院工作。那是一所大型國有企業(yè)的內(nèi)部醫(yī)院,與著名的北方大學(xué)僅一墻之隔。北方大學(xué)以校園里遍植紫丁香而成為這個(gè)城市一道著名的風(fēng)景。在省城工作的幾年,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gè)城市的五月天,因?yàn)椋钦嵌∠慊ê氯锏臅r(shí)節(jié)。
我在內(nèi)科病房工作,經(jīng)管著七八個(gè)病人。其中住在301家化病房的陳子源,是臥病多年的高位截癱病人,因?yàn)殡p下肢已完全萎縮,只能以輪椅代步,所以大家稱他為“轱轆”。轱轆患有多種慢性疾病,腦中風(fēng)后遺癥已失語。廠里請(qǐng)了一個(gè)60歲左右的男保姆照顧他。從我接手經(jīng)治開始,護(hù)士長就告訴我,這個(gè)患者是個(gè)有淵源的人,他是個(gè)很不幸的人,他的家屬特不是人——妻子特?zé)o情、兒女特不孝。
隨著治療的深入,我漸漸從偶爾來看望他的同事和同學(xué)口中了解了他的一些事兒,原來他是上世紀(jì)50年代北方大學(xué)畢業(yè)的高才生,曾是這個(gè)大型國企的高級(jí)工程師,項(xiàng)目帶頭人。他是十幾年前,在一次事故中工傷造成高位截癱的,他享受這個(gè)醫(yī)院最高級(jí)別的治療和護(hù)理(不包括飲食起居),這是廠長和醫(yī)院院長特批的。同時(shí)我也真正感到,護(hù)士長說得真是沒錯(cuò),他的妻子和一雙兒女都是特狠心的人。兒女在迪拜做生意,聽說幾年都沒有來看過他。他的妻子每周來看他一次,但我從沒見她給他帶過任何吃食,也沒見過她給過他什么溫情。她只是來以他的名義,開走他應(yīng)得的那份高檔藥品和營養(yǎng)品。我知道,他的神志是清醒的,僅僅是無法用語言表達(dá)而已。他的眼神幽怨而茫然。有時(shí)候他會(huì)嗷嗷嗷地叫幾聲,也許是以此來宣泄心中的無奈吧。那個(gè)男保姆是個(gè)鄉(xiāng)下鰥夫,根本就不會(huì)服侍人,加上轱轆家人對(duì)他的不聞不問,所以他就愈發(fā)偷起懶來,該擦洗的時(shí)候不給他擦洗,該翻身的時(shí)候不給他翻身,以致到我經(jīng)治時(shí)他已生了嚴(yán)重的褥瘡,而且并發(fā)感染。我心里真的很是同情他的遭遇,偶然,我也會(huì)指使他的男保姆為他做些必要的事兒。但他的病還是日益沉重了。
大約四月初的一天,不知為何,男保姆竟然卷起鋪蓋卷辭職了,而且連工錢也沒有結(jié),只打了個(gè)電話給轱轆的妻子,就坐車回了老家。他妻子這才慌了神,急三火四地趕來。沒頭沒腦地說了些抱怨廠里和保姆的話,護(hù)士長走過來說:“你抱怨什么都沒有用,要馬上找一個(gè)保姆來這才是最要緊的,在沒找到保姆之前,你家要每天派一個(gè)人守著他,照顧他。”他的妻子極為不滿,面露慍色。勉強(qiáng)守了一夜,連早餐都沒喂給他吃,就打車走了。
沒想到,到中午的時(shí)候,新保姆就來了。是個(gè)看上去50歲左右的很有氣質(zhì)很漂亮的婦女,聽說是自己找到醫(yī)院來毛遂自薦的。她帶來一束芬芳四溢的百合花,放在轱轆的床頭柜上,然后又是給他洗臉又是給他擦背和按摩手腳,最后又給他喂了滿滿一保溫桶瘦肉稀飯。她的動(dòng)作十分的輕柔體貼,在做事的同時(shí),還喃喃地同他低語著什么。這個(gè)人是誰呢?她氣質(zhì)不凡,看上去就像一個(gè)高級(jí)知識(shí)分子,她為什么要來給轱轆當(dāng)保姆呢?我們百思不得其解。大膽的小護(hù)士去問,她也只是笑笑說:“我只是個(gè)保姆,來照顧他的,我姓林,你們就叫我林阿姨好了。”有到門口冰品店買冷飲的護(hù)士看到過,她兩天前曾約轱轆的男保姆在那里談了什么,她看到她給了男保姆一大沓人民幣……
新保姆林阿姨是個(gè)極勤快和愛清潔人。她每天一大早就出去買好做早餐的原料,順便買一束鮮花,放在轱轆的床頭柜上,有時(shí)是百合,有時(shí)是康乃馨等等,然后就躲到廚房里忙忙碌碌起來。她煮的早餐精美而富有營養(yǎng),豬肝三鮮面、菠菜肉絲面、雞絲粥……然后就給轱轆圍上一條洗得干干凈凈的白毛巾,用小湯匙,一匙一匙地喂給他吃,每喂一口,都要用嘴巴吹一下,還要用紙巾擦一下他的嘴角。嘴巴里說著:“哎,真乖,來,再來一口,哦,好,有進(jìn)步……”我們看了,都很動(dòng)容。這個(gè)謎一樣的女人,她到底是誰呢?她和轱轆之間到底是什么關(guān)系呢?在他的關(guān)照下,轱轆的身上總是干干凈凈的,她還請(qǐng)樓下美發(fā)店里的師傅給他理了發(fā),刮了胡子,轱轆的精神好了很多,有時(shí)甚至露出了笑容。
她很關(guān)注他的病情,經(jīng)常來我這里詢問治療情況。我不得不告訴她雖然我們盡最大努力治療,但他的病還是日益沉重了,各器官都出現(xiàn)衰竭的情況。她聽了我的介紹后,心情非常憂郁,更加關(guān)照他了。她甚至給他唱歌,唱的好像都是上世紀(jì)50年代流行的歌曲。而轱轆的妻子在林阿姨來后不到十天就去了迪拜,她只是給我和護(hù)士長打了個(gè)電話,臨走時(shí)都沒來看望自己丈夫一眼。
大概是林阿姨服侍轱轆20多天后的一個(gè)下午,一對(duì)衣著考究的青年男女打問著找到轱轆的病房,那時(shí),她正在給他清理大便。那青年女子一見就哭了,說:“媽,你這樣到底是為什么?圖什么啊?媽……”她沒做聲,輕柔地給他清理好,蓋上被子,然后說:“丫頭,我們到外面談。”經(jīng)過護(hù)士站時(shí),她還請(qǐng)求護(hù)士照顧下301的陳子源。好事的小楊護(hù)士,尾隨著他們來到樓下的冷飲店,假裝買飲料。據(jù)她回來說,那對(duì)青年男女,留下了一大筆錢,說:“媽媽,你太偉大了!”他們是哭著開車走的。她還得意地說,她在冷飲店老板那里知道了她的一切:那對(duì)青年男女是她的女兒和女婿,而轱轆是她大學(xué)時(shí)代的同學(xué)。
第二天下午,有一個(gè)女人打我的電話,自稱姓楊,說是301病人陳子源的親屬,約我晚上八點(diǎn)到醫(yī)院附近的咖啡廳見面。晚上,我提前十分鐘來到咖啡廳,剛到門口就見一男一女兩個(gè)人迎上前來,哦,原來是他們——轱轆的保姆林阿姨的女兒女婿。入座后,他們倆熱情地為我點(diǎn)了一杯藍(lán)山咖啡和許多小食品。寒暄了幾句后,楊小姐就說:“張醫(yī)生,我約你來,是為了陳子源陳叔叔的病情,您應(yīng)該知道了吧,陳叔叔那個(gè)保姆就是我的母親,她是南方一家國企的高級(jí)工程師,剛退休。我想,現(xiàn)在我有必要給您講講他們兩人的故事。我媽媽和陳叔叔是北方大學(xué)的同班同學(xué),相戀了幾年,也是蒼天有眼,畢業(yè)時(shí)恰好同留在這座北方的重工業(yè)基地,雖然不在同一個(gè)單位,但是能在同一個(gè)城市就已經(jīng)是萬幸了。工作兩年后,兩人申請(qǐng)結(jié)婚,可陳叔叔單位的組織上沒批準(zhǔn),陳叔叔家也極力反對(duì),因?yàn)槲彝夤页煞植缓茫夥徘笆琴Y本家。而陳叔叔是黨員。他們抗?fàn)幜藥啄辏l料,到了60年代,政治運(yùn)動(dòng)越來越嚴(yán)峻,最終他們還是勞燕分飛了。后來我母親就調(diào)回了南方老家工作,嫁給了同樣是工程師的我父親。我的父親于五年前病故了,偶然她在同學(xué)口中知道了陳叔叔的現(xiàn)狀,百感交集,就來了。她給了陳叔叔的保姆一筆錢,讓他辭了工,她就毛遂自薦當(dāng)了陳叔叔的保姆……起初,我和我愛人一百個(gè)不理解,她這樣又是何苦呢?可是,昨天我母親在醫(yī)院樓下冰品店里說的一席話,感動(dòng)了我,我頓悟了。母親說:‘我不是唯心主義者,但我寧愿相信佛家說的因緣,一個(gè)緣字定終生,今世的因緣,不是在為前生償還什么。但今生的相遇相知,都是前世未了的緣,不到生命的最后時(shí)刻,誰都不應(yīng)該輕言放棄。不能相濡以沫,不能親手為自己所愛的人穿上嫁衣,能伴他走到生命的盡頭,為他親手穿上壽衣,也是愛的最高境界……張醫(yī)生,他們的這種情意可以說已經(jīng)滲透進(jìn)了靈魂深處,甚至超越了靈魂,所以我和我愛人頓悟,我們決定支持我母親所做的一切,請(qǐng)您盡最大的努力,延長陳叔叔的生命,讓我的母親有更長的時(shí)間來了卻她的心愿,這樣她會(huì)好受些……”那晚,我流淚了,我們都流淚了。
五月中旬的一天,轱轆突然出現(xiàn)呼吸衰竭癥狀,搶救了好久,才緩過來。但,一系列的器官衰竭癥狀都加重了。他的神志時(shí)而清醒,時(shí)而糊涂。這次他怕是挺不過去了。護(hù)士長打了電話給廠里,廠里已通知了她的妻子兒女馬上回來。林阿姨萬分難過,她按北方的風(fēng)俗,先給他穿好了考究的壽衣(北方風(fēng)俗,壽衣要在還沒咽氣前穿好,才算是真的穿上了),但她依然不甘心他就這樣匆匆離去,她撫摸著他的頭哽咽著說:“你好起來吧,一定要好起來,我還要推著你去我們母校北方大學(xué)看丁香花呢,五月了,北方大學(xué)的丁香花就要開了。從前,我們最喜歡在丁香花叢中散步,當(dāng)年你最喜歡給我背誦戴望舒的《雨巷》,你說我就是那個(gè)有著丁香一樣的顏色,丁香一樣芬芳的結(jié)著愁怨的南方姑娘,因?yàn)橛辛四悖也畔穸∠慊ㄒ粯泳`放了,后來我們被迫分手了,我寫了一首詩給你,你還記得其中的那幾句嗎?獨(dú)自彳亍在五月的丁香叢中/我沒有了丁香一樣的顏色/和丁香一樣的芬芳/我只有如丁香一樣千頭萬緒/千頭萬緒的心……”轱轆的神志突然間清醒了,眼角溢出了兩滴淚水,他抓著她的手,嘴里反復(fù)“啊啊啊,啊啊啊”地說著什么。林阿姨站起來,對(duì)我們說:“醫(yī)生、護(hù)士,麻煩你們照顧一下子源,我出去一下,很快就回來,你們知道嗎?他說的是‘丁香花,丁香花啊……”她流著淚走了。
一刻鐘后,她懷里抱著一大束含苞欲放的丁香花,急匆匆地出現(xiàn)在樓梯口。樓道里靜悄悄的。遠(yuǎn)遠(yuǎn)地,她看見,301病房里推出一輛治療車,車上睡著的人從頭到腳都蓋著雪白的床單。她的身體猛然顫抖了一下,愣了片刻后,她就像突然清醒了似的,幾步走上前去,護(hù)士們立即停下車來,她沒有號(hào)啕,只是無聲地抽泣著,她把花放到自己的唇邊吻了一下,然后輕輕送到他蒼白的唇邊,再輕輕地放在他的枕邊,用雙手輕輕地?fù)崦艘幌滤n白的臉龐,最后輕輕地給他蓋上白被單。她嘴里喃喃著“啊啊,北方大學(xué)的丁香花就要開了,北方大學(xué)的丁香花就要開了……”
責(zé)任編輯:黃艷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