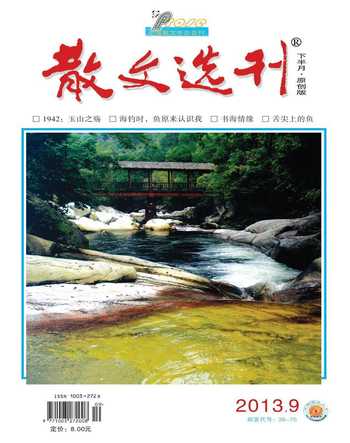母親
唐興順
一
母親作為一個農民,一個勞動婦女,身體一直很好,快60來歲的時候還和父親在老家種地。母親天生的皮膚白嫩,年齡大了的時候,也沒有出現過老人斑,也不發胖,走路兩手前后微微擺動,腳尖向外,悠閑而從容。說話時,開始聲小,說著說著就聲高起來,同時漲紅了臉。母親吃飯從不揀食,條件好時和條件不好時都一樣。小時候每天晚飯都是一羅鍋稀湯,外加的主食是半箅子餾紅薯。主食先讓給我們吃,母親蹲在灶臺旁喝稀湯,一碗一碗地喝,從不讓浪費掉。這個形象長期印在我的腦海里。條件好了以后,一家人吃飯,飯桌上她喜歡的不喜歡的,都不讓浪費,總是把一些剩下來的盡量吃掉。母親到老年時是真正的性情淡泊。我有一次站在遠處看她和只有幾歲的孫女孫子玩紙牌,小孩們只是稍稍識牌,什么都還不懂,相互之間極其認真。母親隨著他們出牌,很認真地玩,那表情叫孩子們歡喜的不得了。母親懂得大道理不多,卻非常重視兒女們取得的榮譽。我們在社會上有了什么好事,總是先給母親報告,她不一定能聽得懂事實,卻會跟著孩子們高興,說出來的話也總是很有精神性、文化性。她天生有一種文化藝術的細胞,只不過沒有在世俗社會中開花結果,這些偉大的情性終身蘊涵在她自我的生命之中。
早年在村上都知道我母親有兩件本領,一是會剪紙花。過年的時候,母親盤腿坐在炕上,把紅紙綠紙剪成各種花樣,牛、兔、雞、牡丹花、石榴花等多種,我總是爬在窗臺上先把自家的窗戶貼得花花綠綠,也有許多鄰居拿著紙來讓母親剪,除了窗花,平時還為村里人剪枕頭花,鞋花等。母親的另一個本領是會針挑“羊毛疔”,給人消除疼痛。經常有害脊梁疼的人到我家來,進門常說的一句話是:脊背上像扣了個大磨盤,也有說像壓了個鐵鍋蓋的。母親就說那是羊毛疔吧!然后讓這個人趴到炕上,母親把他的衣服撩起來,用縫衣裳的針在他的后背上扎。從母親的眼神上看像在找什么東西一樣,一手按著,一手拿針,突然定神用力,連挑幾下。母親就會說:“啊呀,真是羊毛疔啊,這不都成白絲兒了。”然后舉起手,讓大家看挑在針尖上的那帶著黑紫血色的白細絲。這個人直起腰來連喊:“松了,好了。”母親的這些本領我當時并不重視,以為誰都會,只不過是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幫助罷了,大了以后才知道這是一種特殊的才能。
母親的才情還體現在做衣服上。在那貧困的年代,人們衣服的季節性都模糊了,往往脫了單衣就是棉衣,全沒有從薄到厚從厚到薄的中間過渡。有一年天已經很冷了,我還穿著單衣,母親竟然用一晚上時間就給我翻新了一件棉襖。她把父親的一條破單褲和她自己的一條破單褲拆洗干凈,分別取可用的部分,改制棉襖,以前襟為分界線,一邊是黑皂色,一邊是天藍色。第二天我穿在身上往學校去,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上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我第一次到縣城參加紅小兵培訓班,母親拿自己親手織的粗布,用槐籽把它染成藍色,給我縫制了平生第一件“套裝”。布衫上有四個帶蓋兒的口袋,褲子兩邊有兩個斜插的口袋,是當時最時髦的衣服呢。我個子矮,衣服自然也很小,但穿在身上,感覺十分的新奇和鮮亮,人也像一下子大了很多。集訓時上早操,領導讓我負責喊隊,我單獨跑在隊伍外側,高喊著“一二三四”的口令穿行于縣城的街道上,威風八面。回到村上后,母親正在村西地里干活,我穿著這套新衣服跑著喊著去找母親。地里有很多人,老遠就看見母親站起來向我擺手。我的身影在母親的視線里一定是一幅絕妙的風景。
母親心靈手巧,但沒有心機,不會想著法子對付人。可是又很情緒化,脾氣一旦發作起來就如熊熊燃燒的烈火。有一次,一戶人家的雞被人打死了,懷疑是我們干的,找上門來叫罵。事實上我們那一天都沒有出門,完全是無理取鬧。母親忍受不了,也不和他辯解,以牙還牙,比那個人罵得更兇,一直把對方攆回了家,還漲紅著臉,站在他家門口,叫嚷了很長時間。母親的確很勇敢,特別是當我們這些孩子受到傷害時表現得更為充分。有一回,母親正在曬棚上干活,聽人喊叫說我三弟跌進紅薯窖里了。母親來不及從梯子走,本能地拽著墻根的柿樹枝就從房上下來了,直接跳入紅薯窖,這個窖子20多米深,底下有七八米的水,實際上就是個水井,好在窖筒比較窄,母親下去后用四肢撐在石壁上,從水里撈出了三弟。一到地面上,母親就癱軟在地。在我的意識里,弟兄三個,母親對我這個老大的感情是更濃厚些。從小到大,家里最好的資源和條件總是先讓我享用,總認為我優秀,特別的給予珍惜。我剛參加工作,在外面稍有發展時,回到老家,一些少年時的伙伴來聊天,母親隔一會兒就到屋門口望望,見我總是不停地給人家說話,一聲高一聲低的。客人走后,她就對我說:你不要總給他們說,話多了會泄氣的。有一年夏天我赤著脊梁推著獨輪車去野外鏟草皮,集綠肥。回來后中暑休克了,父母用稈草(谷子稈)烘火,讓人抬著我在火上熏。我醒來了,母親卻癱瘓在一旁沒了氣。母親從來不要求我,她認為我做的什么都對,徹徹底底,無邊無涯地相信我,還寬容我性格上的缺陷,知道是毛病,也不忍心說,假裝沒看見,不知道。想起這些,都讓我感到,我對母親的感情如果有半點假,如果有半點虛偽,那就不是人了。
但是,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沒有正視母親年齡的變化,其中肯定有主觀回避的因素,模模糊糊,蒙蒙沌沌里,總覺得母親還是那個母親。實際上,母親已經老了,她的體力,她的眼神發生了很大變化。只不過,我們習以為常,她自己又不有意表現年齡,直到她70歲那一年,突然腰疼得厲害,早晨下床得扶著墻,走著還行,要停住坐下就十分困難。晚上睡覺需要人抱到床上。雖然醫生說不是大不了的問題,但卻讓我很上心,讓我面對面的,真切無疑地感到,母親正在老去。我的母親沒有任何特殊性,她和天下所有人一樣,最終都要離開這個世界。平日里只顧在紅塵中奔波,爭地位,爭名利,爭尊嚴,把全部感情都投入到了那無邊的不確切的虛空之中,老母親被忽略在一邊。這一次我召集全家人商量決定,再忙也要帶著母親遠游一次。一輛專用面包車,載著父母和我們弟兄三個,妯娌三個,及其下一代孫子孫女,共十二個人,走出了太行山,真是一次難得的行動啊。在路上都擔心母親下車后怎么走路。在北京故宮,輪流攙著她過金水橋,過午門,看太極殿。到了最后邊的御花園時,有一泓池塘,邊上是荷花、垂柳,水里游動著成群的各種顏色的魚,游人們向里邊扔食物,魚們就竄奔翻騰成一團。母親一見這個便甩開攙扶的人,昂首大步直行過去。到跟前后一手扶著欄桿,一手指著池中,驚喜的招呼我們趕快來看。我們大家都圍攏了過去,和母親一起喜樂。后來又去了山西,游了晉祠,還麻煩一位朋友在一個豪華酒店設宴,招待了我們全家。堂皇的擺設,精致的碗碟勺筷,各色各樣的美味佳肴,特別是朋友敬酒時對全家的溢美之詞,這樣烘托出來的一種氣氛,讓母親真正的高興起來了。她還喝了三小杯茅臺酒,滿面紅光,神清氣爽。母親太缺少這樣社會化的場合了。這次外出不僅使母親的腰腿之疾完全好了,而且還對她的精神產生了深遠影響。我再一次去看她時,推開門,廳里卻沒人,進到臥室,才看到母親,但并不能說話,她正立在那里練氣功。只見她微合著雙眼,兩手掌伸開在胸前左右擺動。事畢,母親告訴我,從外邊回來后,她一閉眼腦子里就是外邊的風景,像一張一張的圖畫。還說,過去身體不好時,晚上躺在炕上,看天花板上全是蛇蟲在滾動。從外邊回來,這些都沒有了,眼前、心里都是清清利利的。她說,現在練氣功,就使用這些畫面,一次一個風景,像掀看掛歷上的畫兒一樣,感覺身體松散通順。我后來想,母親這樣一種說法,應該是有些夸張,其中肯定包含了鼓勵我們子女的意思。但有一點是真實的,那就是母親后來的生活方式確實變化了,再也不整天待在家里了,學會了散步,有時還打的和父親一起到寺廟里去游逛。她本來就愛花草,現在更用心了。普通的指甲草花,用壇壇罐罐栽著,擺了半院子。上一年的花種落在墻根石縫里,第二年春天長上來,母親像看小孩一樣護著它,以致讓它長得很大,主干差不多有搟面杖粗,分條細枝密匝繁茂,一蓬紅花搖曳,如掛著滿身的鈴鐺。母親還養了一株枸杞,本來是小小獨苗,竟成了一架藤狀植物,像紫荊和葡萄一樣遮著半個窗戶。尖葉、碎花、紅籽,婆娑而文靜。我每次去看望母親,總是和她站在院中,看半天說半天枸杞的事。可惜,現在枸杞還在南窗下,母親已是逝去人。
二
我現在經常想,生活在世間的人,熙熙而來,攘攘而往,生動活潑,密密麻麻。但上帝是忙而不亂的,他對每一個人從開始到最后都有明確細致的安排。像我母親,本來已經好好的了,根本顯不出一點要離去的跡象。可是,有一天,她耳朵下邊的脖子上突然疼起來,用眼看,拿手摸,都好好的,就是疼。母親說是從里向外的疼,一頂一頂的疼。讓醫生看,診斷是淋巴結核,就是民間俗稱的“老鼠瘡”。不好治療,很多人為此喪命。父親和一個鄉村中醫是多年朋友,這個朋友配著處方給母親治,內服外敷并用。可是有的西醫又說,應該做手術,把里邊東西挖掉。怎么辦?我和父親坐在院中竹子下,把兩個弟弟找來商量。做手術,首先得在脖子上開刀,問題會不會解決,先喪了老人的元氣。麻醉、手術用藥的過程,血液,心臟等環節會不會節外生枝。我一想這些就恐懼起來,低下頭默不作聲。很大一會兒,才問父親中醫治療的效果。父親說,用他的辦法好像是穩住了,沒有以前疼了。可不敢說下一步會怎么樣。最后決定只要沒有新發作就不動刀,藥物治療。停了幾天,母親脖子上的瘡從下邊露出了頭兒,露到了皮膚外,看著那里發炎化膿,一家人又害怕起來,后悔該早做手術。父親的那個朋友卻說:你們害怕,我卻高興呢,用藥的預期效果出現了,說明處方對路。就這樣,我母親躲過了這一劫,用如此輕松的辦法解決這么繁難的病癥,事后連那個醫生都有些后怕,說他已把治療全過程作了記錄,要作為成功醫案研究探討。這一年春節,全家人都很高興,我們照例在城西的豐盈酒樓訂了一桌年三十中午的聚餐宴。父母、弟兄三家,特別是在外工作、上學的孫女、孫子們都回來了。每年這都是一次重要活動。父母坐于上位,聽大家說收獲,敘見聞,接受兩代人輪番地敬酒和祝福。父親不飲酒,母親總是能喝一點,每逢此時,我就能看到她由衷高興的神情,雙頰微紅,兩眼時而睜開,時而瞇著,嘴里說著感嘆幸福生活的話語。母親白里透紅的臉上洋溢出的笑容讓我終生難忘。
年三十早晨電話鈴響,一接是父親,說母親起床后到陽臺上取東西,跌倒了,摔著胳膊了。真是難以形容我當時的心情,什么也別說,趕快把母親送到了醫院,春節全家的所有安排和秩序被改變。母親的胳膊在胳肘關節以上被折斷,X光照片上顯示出破碎了的骨頭茬子,像折折的一段樹木。馬上開始體檢,輸液消炎,準備年后做手術,還是逃脫不掉開刀這一劫!除夕夜,起五更,初一、初二、初三,一家人輪流在醫院度過。從接到父親電話到整個過年,我心里壓上了從未有過的重擔,我預感到年三十的這件事是一個不吉之兆,我的母親可能有了真正的麻煩。但仍然需要笑臉迎人用最大努力幫助母親去和冥冥之中的命運抗爭。我們用了當地最好的醫生,手術使用的鋼板也是最好的。沒出正月十五,母親的胳膊就好了。母親住院期間,特別是術后療養的日子里,子女們的很多朋友來醫院探望,有的捧著鮮花,有的提著營養品,有的從家里提來精心烹制的飯食。花紅柳綠的男女,各種甜蜜慰問的聲音,一連幾日包圍著母親。她斜身坐在潔白的床鋪上,不停地和大家說話,應酬各方面的話題,享受著特別的尊榮。由于營養和久居室內的原因,使她顯得比住院前更加豐腴飽滿,神采照人。以后差不多一年都很順利。八月十五全家人還進行了歡樂聚餐。可是到第二年初春的時候,兇神第三次找上門來。母親被查出患了癌癥。這個繁稠難看,人人都望而生畏的漢字阻擋不住地出現在了我們面前。從不相信,非理智的排斥到幻想、僥幸過后的無奈和接受,一家人在恐懼和折騰中度過了最初的幾天時間,又經過咨詢、檢查、比較,我們弟兄三個帶著母親來到了城市西南角的專科醫院。床位很緊張,通過朋友讓醫院抓緊收拾騰出了一間寬大房子作病房。
我們三個陪著母親站在院子里等人去辦手續。母親已經瘦了很多,她今天上身穿了一件天藍色的布衫,腳上是平底方口布鞋,站在初春斑斑的樹蔭下,我們三個孩子像小時候在老家村外的野地里一樣,依偎在她的身邊,非常無奈,非常無助,非常可憐。母親啊,我們怎么能夠留住你。我知道這種病,再怎么治,也是兇多吉少。三個人互相回避著眼神,都朝這望望,朝那望望,止不住的心酸,擦不干的淚水。母親反倒比較坦然,對于病情,我們也沒有專門回避她,也沒有正面認真給她說,知道我的母親是聰明人,不用細說她全部會明白。此時她反而一個一個叫著安慰我們。雖然也皺著眉頭,但整個身體和精神都在堅強地挺著。手續拿來后我們正準備上樓進住,三弟前幾天委托的另一個朋友打來了電話,說人民醫院在外地進修的那個名醫回來了,母親可以到那里去醫治。這是我們求之不得的。當即就掉頭到東關的人民醫院來了。也沒有給這邊告辭,也沒有退房子,踩著兩頭碼,心想過兩天哪里合適就住哪里。人民醫院的這個醫生姓宋,是科室主任,一見我母親就笑哈哈地拉家常,在醫辦室影像機前看了一下X光照片,拍著母親肩膀說:大娘,沒事!按我的辦法,讓你一個療程就見效,三個月保證能吃一碗餃子。很長時間來我們都第一次出現了笑容。心里知道是安慰病人和家屬,但這話響亮叮當的,肯定也不是胡亂說的。這種治方,主要是口服一種從國外進口的新藥,再加上每天一次輕度電療。用藥后,出現一些過敏癥狀,母親痛苦地扭曲著臉,但她能夠忍受,還不時主動和我們說話。
七月二十二日這天天空出現了日食。我攙著母親走出病房,在樓西頭的過橋上望天空。地上昏暗著,太陽只還有月牙兒樣的一個弧形的金邊。我給母親講所知不多的天文知識。她仰頭望著,應答著我的話。我心里知道,天上發生的這種大事件,我此生沒有機會再和母親共同經歷了。宋醫生治療的很用心,不斷地翻閱書籍資料,不斷和外地專家聯系。母親有了很大好轉。三弟媳從事醫務工作,出院時主動要求把母親接到了自己家。三弟和我住著隔壁。每天都能見到母親。眼看著母親慢慢又好起來了,又和父親一起出去散步了。有一次我從外面回來,在小區門口看見她們兩人一前一后從遠處走來。母親又邁開了她那從容松散的步伐。為母親祈禱,讓她盡量延長快樂的時光。這年秋天,我出嫁了一個姑娘。喜事期間,家院里支了大鍋,每天喜氣盈門,人群熙熙攘攘。人多的時候,母親在三弟家門口坐著向這邊望,人少了時就笑盈盈地走過來,指著一摞一摞的碗,一筐一筐的筷子,高興地和家里人說笑話。過年除夕晚飯,母親在三弟家還真是吃了十來個餃子,并且也沒有不舒服。去醫院復查,也未發現新變化,似乎奇跡真在出現,希望像一輪太陽朦朧地出現在我意識的地平線上。
可是最終這太陽沒有升起來,它被無情地淹沒在了意識模糊的遠方。春天到來時,母親舊疾復發,這一次什么藥也不見效,惡化得很快,眼看著母親的臉和身體一圈一圈瘦下來。開始我們還拿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話安慰她,后來干脆就很少跟她說這類話了。經常獨坐默語、面面相覷,我們都意識到母親最嚴重的情況即將發生。當時我自己剛學會駕車,就拉上母親和父親,還有妻子,從市區出發,往老家走,往母親娘家的山坡上走,有時開車走大路,從窗口向外望,有時下車穿插一段小路,讓母親在她小時候玩耍的地方,并且經常講給我們聽的地方,任意游走。正值初春槐花盛開的時候,母親在一片林子邊停下來,讓我們把一棵樹彎下來,她很認真地采摘槐花,又說起小時候和她父親,和她的姐妹們苦熬艱苦歲月的情景。一棵樹采完了,又采另一棵樹,放在路邊好幾堆,她也不要求往車上拉,母親清楚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到兒時玩的地方來了,心里是什么滋味?可她一直高興地和我們說笑。拿著成榾柮的槐花擺來擺去。又走了一段,見村邊野坡上架了一個土秋千,用藤條拴著一塊木板系在兩棵樹之間。我們把母親攙上去,扶著她前后游動了好大會兒,她雙手拽著兩邊的藤條,兩腳離地,瞇著眼,讓我們擺她。下來后說小時候在某某地塊和某某某就是蕩的這種秋千。我家院里靠南墻長了一棵杏樹,正在開花,那一段日子,母親在三弟家吃罷藥后,有時候就走過來,坐在樹下的板凳上,長時間地坐著,二弟以此為背景給她拍了幾張照片。我知道這差不多都是母親的最后經歷。再后來母親就無力出門了,連下床也很困難,白天黑夜斜靠在床上,母親說她不怕死,但她何嘗不想活下去呢?三弟媳從醫院給她取回來的各種藥,無論多苦,多難咽,她都要一點一點喝下去。連流食也吃不進去了,可她還艱難的吃,咽進肚里一會兒又難受,又得吐。母親這時候的痛苦模樣像往我們心里戳錐子。我經常避開她,去我家沙發上大哭一場。人心如一個洞,再不能忍受的事也得一點一點塞進去。再不適應的事也得一點一點適應,一點一點把非常變成正常。我們在社會上已經行走了這么多年,為很多人解決過這樣那樣的困難,幫助不少人脫離過困境。可是面對自己的母親,我們卻一點辦法也沒有。
三
最后得回老家了。母親實際是不想回去的。她知道回去意味著什么,盡管在痛苦難忍的時候,她不止一次地叫喚不想活了,還說你們再給我治療,多活多受罪,就是忤逆不孝。可真要回老家時,她又留戀與難舍。但不回去怎么辦呢?父親和我商議,哭了一臉又一臉,最終我決定讓母親回去。父親給母親一說,母親再見到我們時就變了口氣,說咱回去,趁早回去。我駕車拉著母親,一家人一塊回到了老家,把已經弱不禁風的母親攙下車,走了一段胡同,進入家門。盡管不是原來的房子,母親還是在進屋前停下腳步,扭頭把整個院子看了一遍。新房是二弟和弟妹用了很大精力建起來的,就還在原來的老宅基上。這一小片土地,曾經是我們從小到大一家人的依托所在,是父母帶領我們從苦難中爬出來的地方,這地方回蕩著我們多少次的喊娘聲。如今我們全家又一起回來了,可我們是來干什么的?是來為娘送終的。
母親住進新屋,躺在新床上,南邊是寬大的玻璃窗。母親說,好時光都讓我過了,臨去了,又住上了嶄新房子。要是早幾年日子苦時就沒了,怎還能過這么多年好時光。讓我們別難過,說她沒遺憾。村上的鄰居,早年一起下地勞動的老姐妹來看她,她精神又煥發起來。和前幾天有了很大不同,和親人們說話也多起來。有一天晚上,我坐在窗外院子里,聽母親在屋里給三個兒媳婦講我父親,聲音很大,語速也快,講父親年輕時候的事,講父親的個性,講他們結婚時候的事。逗得三個媳婦笑出聲來。我獨自心傷,知母親是在說最后的話。她已經把自己的生命擺開來,拉開了陣勢,要獨自面對正在到來的事。這期間母親又讓人攙著到大門口走了一次。盡管已經瘦得不成樣子,母親還是讓人給她系上一條紅腰帶,自己舉手攏攏頭發,在門外的十字口上艱難地走了幾步,向四周向天空望了望。然后回來,躺下。我的母親真是一個偉大的人,她有敏感多情的心靈,她有清醒堅定的生命意識。同時在不得不向命運低頭時,她也要表現自己的個性,哪怕是面對人生的最后一難。
這以后母親就被病痛完全吞沒了。看著她難受的樣子,有時候真是想讓她早點咽氣。她已經沒力氣說話了,我們站在床邊,她用眼望著我們,后來連這樣的眼神也沒有了,眼睜著,但似乎已經不是她的眼睛。有一次我俯在她耳邊,給她講李叔同臨終所題的“悲欣交集”四個字,用我的話解釋說,此生命解脫,彼生命到來,彼岸是一片桃花等等。想讓母親生命結束的時候,在絕望黑暗的前方閃耀一點光明,哪怕是飄忽模糊的,作為她在人世上的兒子,我盡力做。看不到母親有明確的反應,也可能她已經離開自己,正在向那一片桃花走去。
2010年6月29日早晨,新一輪太陽升起來的時候,母親走了。她臉上沒有了一點痛苦的印痕,安詳如睡。在去殯儀館的車上,我和二弟坐在母親的頭兩邊。我哭了一路。想幾天前從市里回來,母親還坐著、說話,現在她就平躺下了。火化后,我們看到母親的骨灰,出奇的潔白,一顆一顆像玉石子般晶瑩,母親一生善良,心地淳樸,從不做害人的事,這莫非真是應證嗎?
我把骨灰用紅布包上摟在懷里往家走,悲痛中產生出一種神圣的情感:小時候,母親抱我。現在,我抱著母親。
四
母親去世前后發生過一些奇怪的事情,使我對生命和靈魂的認識更加迷茫。
去世前頭一天下午,大家都在院里說話,突然聽到屋內母親躺的木床咔嚓咔嚓響了兩聲,聲音很大,都還沒有回過神來,母親的干女兒從屋里跑出來,說在屋內也聽到了響聲。幾個人共同回屋去看,母親仍昏迷著,一切都沒有變化。吃罷晚飯的時候,在院里又聽到屋內有像垛了一架東西突然癱倒的那一種響聲,似乎發生在樓梯下。去看,什么東西也沒有。我并沒有特別恐懼,也沒有說什么,但內心深處是非常震驚的,事后想想,這難道就是母親靈魂出竅的時刻?就是這靈魂擺脫束縛,出屋離世的響動?還有出殯那一天,按照風俗抬著棺木舉著靈幡進行街祭,小侄子雙手端著母親的牌位走在隊伍中,突然從天空落下一滴鳥屎,不偏不倚,正好落在母親牌位底座的正中間,你說稀罕不稀罕,青天白日,漠漠高空,難道就這樣湊巧,千分之零的概率里成就了百分之百的神奇,叫人很愿意想成是神鳥“天糞”(諧音“天封”吉祥意)。再就是母親下葬后的第三天,親人們按照風俗去村西的墳上做“復三”。走到離墳還有50多米的地方停下來等人,一切都好好的,無風無雨,突然看到母親墳上有一個花圈騰空飄起來,像風刮著人舉著一樣在空中平移了一大段,落在墳西邊的石岸根。不是親眼所見,真是難以置信。人究竟有沒有靈魂呢?靈魂與肉體的關系又是怎樣呢?也許有多種可能性,比方說肉體寂滅后靈魂游離出來,或獨立存在,或與其他靈魂相混合,或者又找到了新的附著物。也可能都不是,肉體滅跡,一切無存,正所謂“人死如燈滅,好似湯潑雪”,無跡無痕無由來。但是,按照“物質不滅”的科學思想,哪怕是一粒塵埃,哪怕是一粒塵埃也不是,生命無論以何種形式,總不會跑出這個自然空間吧。
茫茫宇宙,無邊河漢,生命與生命之間應該是同光和塵,靠了某種機緣,總會實現千絲萬縷的聯系。
責任編輯:黃艷秋
美術插圖:段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