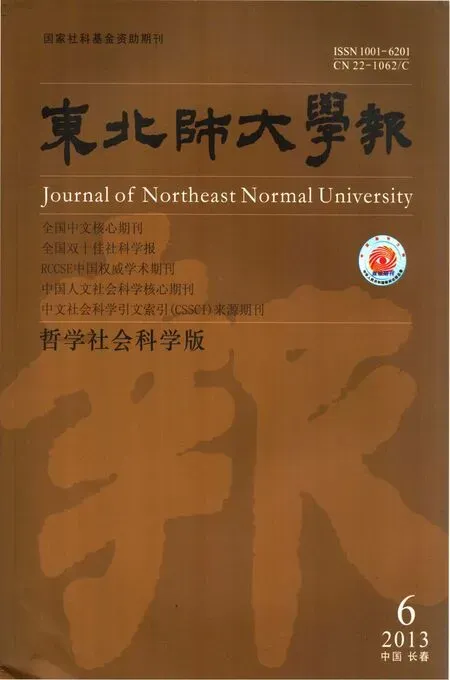讀者反應理論與圣經(jīng)批評
梁 工
(河南大學 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河南 開封 475001)
20世紀60年代末期,西方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發(fā)生重大轉折,結構主義標榜的統(tǒng)一性、整體性和秩序性遭遇嚴重質疑,作為后現(xiàn)代文化思潮在文學理論中的反映,后結構主義應運而生。后現(xiàn)代文化主張意識形態(tài)的多元性,宣稱不存在涵蓋絕對真理的宗教信仰或世界觀,亦不存在“全然客觀”的解釋;由于任何理解活動都寓有特定的價值觀,那種據(jù)信能賦予所有個體講述以意義的“宏大敘事”(meta-narrative)須予以根本否定。后結構主義在研究實踐中可分為讀者反應批評和解構主義批評,前者主張意義來自文本與讀者之間的互動;后者進而提出,在讀者各不相同的認知體驗以外,某種整齊劃一的意義根本無從獲得。這兩種理論都被引入圣經(jīng)批評,成為解讀圣經(jīng)文本的新途徑。本文僅在較為寬泛的意義上考察歷代圣經(jīng)學者如何表達對“讀者”或“受眾”的關注。概覽之,讀者反應理論在圣經(jīng)研究界遭遇到不同的對待,有人大體認同,局部接受;也有人態(tài)度抵觸,予以排斥。
一、關于“受眾批評”
由于圣經(jīng)文本帶有鮮明的勸說性質,其中的律例典章、先知預言和智慧語錄均誨人棄惡揚善,其作者大都預設了某些來自讀者的反應。對于這類關切,讀者反應理論顯得別有一番重要性。甚至在讀者接受問題成為文學理論的焦點以前,圣經(jīng)研究者就已論及日后讀者反應理論所矚目的問題,只是尚未形成系統(tǒng)的理論和方法論——他們業(yè)已完成的工作可納入“受眾批評”(Audience Criticism)的范疇中。
圣經(jīng)各卷書是寫給誰看的?這個提問通常為研究者所思考。典范的“圣經(jīng)導論”都會探討某部先知書、福音書或使徒書信的預期接受者,其間的潛在假設是,那部書帶有某種對話性質,是作者與其受眾溝通交流的結果。既然如此,要想恰切地理解它,就應當對受眾的身份、處境、視點及其關注的話題有所了解。所以很自然,多種形式的受眾批評為近代以來的圣經(jīng)研究者所踐行。
柏亞德在《受眾批評與歷史上的耶穌》[1]中將“受眾批評”一詞首次用于圣經(jīng)研究,該詞取自一般文學理論,與后來的“讀者反應批評”多有相通之處。反觀一百多年的圣經(jīng)文學研究,學者們曾運用諸多方法——從形式批評到社會學分析——獲取涉及受眾的信息,例如不少人討論過《哥林多前、后書》的受眾,深入考察了哥林多信徒中存在的問題:拉幫結黨,分成“保羅派”、“亞波羅派”、“磯法派”、“基督派”;男女信徒淫亂,有人甚至與繼母同居;婚姻不穩(wěn)定,丈夫隨意休妻、妻子輕易改嫁;以及圣餐禮混亂、濫拜偶像等。研究者常用的技巧包括:從直接、間接的歷史資料中取材,借鑒社會學調查和修辭學、文章學分析的成果,以及所謂“逆向閱讀法”——即從保羅的爭辯和批駁中推導出其對手的觀點。20世紀下半葉,一批帶有社會學性質的專著推動了圣經(jīng)受眾剖析,代表作可舉出H.C.基的《新時代的社群:〈馬可福音〉研究》、布朗的《可愛的門徒社群》、J.H.艾略特的《無家者之家:〈彼得前書〉的社會學詮釋》等。
但“受眾批評”與“讀者反應批評”卻存在明顯差異:前者所矚目的是文本的原初讀者或第一批接受者,后者所探討的則是后世乃至當今的接受者——他們被關注的并非其身份和處境如何,而是在閱讀過程中的那個“特定時刻”,他們與文本發(fā)生互動的具體情狀和后果。
二、“合理范圍內”的讀者釋經(jīng)
克萊因承認,無論怎樣尋求經(jīng)文作者或編者的本義,以及原初讀者最可能理解的意思,后人閱讀圣經(jīng)時都難以得出全然一致的結論。這是由錯綜復雜的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作者或經(jīng)文的意圖并非清楚到可以排除任何其他選擇,將那些選擇判斷為非正統(tǒng),或者次于圣經(jīng)的觀念”(換言之,是說那些選擇均未出現(xiàn)嚴重問題,甚至達到宣揚異端的地步)[2]。當這種情況發(fā)生時,即釋經(jīng)者缺乏足夠的理由去維護某種見解或者特定見解時,就應當允許有人對經(jīng)文做出不同解釋,發(fā)表不同看法,而不能指責他們的看法為異端或謬誤。也就是說,在某種“合理范圍內”,即在正宗信仰的基礎上,應當認可不同讀者群體自由釋經(jīng)的合理有效性。
例如,基督教各派都以洗禮為入教的基本禮儀,然而,應當如何運作施洗或受洗?圣經(jīng)本身并未做出清楚界定。一些教派依據(jù)《使徒行傳》8:38-39等處經(jīng)文主張浸禮,并在湖中、河中或池中為信徒施浸禮。另一些教派則想象當年耶穌和約翰均站在及膝的約旦河水中,約翰用壺取水澆在耶穌頭上——那些教派乃據(jù)此奉行澆水式,或者灑水式洗禮。由此進而衍生出另一個問題:除了信徒必須接受洗禮,嬰兒是否也應當受洗?對此,兩種不同的見解長時期爭執(zhí)不休,“二者均想努力忠于圣經(jīng)教訓”,但他們“對圣經(jīng)經(jīng)文的含義竟然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3]。正是借助于這種超越了經(jīng)文本身的閱讀理解,一些釋經(jīng)者析出與其教派路線相吻合的意義,將之附加于圣經(jīng)。至于“合理范圍內”,是說那種闡釋必須在基本教義限定的范疇內進行,否則就會成為“異端邪說”,遭到口誅筆伐。
三、運用文學技巧分析的讀者反應批評
上述“受眾批評”大體上屬于圣經(jīng)歷史考據(jù)學,意在獲得與經(jīng)文最初接受者及其周邊環(huán)境相關的資料,以利于當代讀者更全面地理解圣經(jīng)文本。然而由于這類資料極其匱乏,“受眾”的本真面貌難以窺見,一些學者便轉而從文學技巧角度展開讀者反應批評,用以揭示圣經(jīng)的敘事、論說和抒情藝術在讀者接受過程中所發(fā)揮的作用。此類著述可舉出克洛桑的《崩塌的懸崖:耶穌比喻中的悖論和多價》(1980)、福勒的《五餅二魚:〈馬可福音〉中提供食物故事的功能》(1981)、庫普柏的《第四福音書剖析》(1983)、杜·普萊希斯的《明晰與含渾:同觀福音書中發(fā)送者、比喻與接受者之間的文本交流關系研究》(1985)、斯坦利的《初吻的印痕:對第四福音書中隱含讀者的修辭考察》(1985),以及麥克耐特的概論性著作《圣經(jīng)與讀者》(1985)。
在這批著作中,圣經(jīng)文本被視為一個文學實體,以多種文學手段寫成,其中一些為當代讀者接受理論家所津津樂道,例如對“空白”(blanks)概念的運用。讀者接受理論認為,文本對意義的表達兼具確定性和不確定性兩種特征。就確定性而論,為了傳輸確切的含義,文本往往會訴諸于多種語言學手段或技巧,如變換不同的人稱代詞,運用不同的時態(tài)、語態(tài)和語氣(諸如陳述、呼求、祈使、命令、抒情、論斷、指責、稱頌等);又如采取靈活多樣的修辭策略。《加拉太書》3:28稱“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你們在基督耶穌里都成為一了”,便是以世俗生活中司空見慣的主仆關系、男女關系為例,喻指信徒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完全相等,不存在高低貴賤之分。彼得遜的研究表明,在《腓利門書》的象征系統(tǒng)中,人際間的親屬關系被保羅成功地用來證明“基督徒之間親如一家”的神學原理。
然而,文本中固然存在多種將讀者導向確定性理解的符號線索,在讀者接受理論看來,不確定性依然是文學文本的基本特征。伴隨著種種由于被揭示而已知和明確的東西,文本中總有尚未被揭示以致未知和含混的東西,正是這種已知與未知、明確與含混的辯證關系,設定了閱讀過程的運動狀態(tài)。“空白”是導致“不確定性”的重要原因之一,特指由于文本中未作交待,讀者不易覺察到的“情節(jié)中斷”環(huán)節(jié)。在伊瑟爾看來,讀者與文本的交流就發(fā)生于這類“空白”處,它們是讀者必須“以揣度去填補”的地方,能把讀者“牽涉到事件中,以便提供未言部分的意義”。鑒于未言部分是在讀者想象中存活的,它們能被“放大”,“比原先擁有更多的含義,甚至連瑣碎小事也深刻得驚人”[4]。
奧爾巴赫在其《模仿論:西方文學所描繪的現(xiàn)實》中則論及“亞伯拉罕燔祭獻子”(《創(chuàng)世記》22:1-14)的敘事空白。他發(fā)現(xiàn),作者對那篇故事的講述過于簡約,以致給讀者留下許多疑團,例如開篇時上帝在什么地方呼喚亞伯拉罕,亞伯拉罕又在哪里?在情節(jié)演變過程中,作者省略了諸多細節(jié),涉及時間、地點、背景、環(huán)境、亞伯拉罕的姿態(tài)和心理活動等。亞伯拉罕攜子前往目的地的三天路程宛如一段真空:他們途經(jīng)何處、在哪里投宿,父子二人說了什么、做了什么,讀者均一無所知。全篇敘事顯得干巴而簡短,缺乏對人物和景物的描繪,就連形容詞也難以看到。父子二人相貌如何?性格及脾氣怎樣?兩個仆人各叫什么名字,對亞伯拉罕父子是否忠心?作者均無可奉告。空白的大量存在營造出一種緊張氣氛,使讀者因重重懸念而集中起注意力,時刻不忘亞伯拉罕所受的考驗,傾心于體驗事態(tài)的沉重和亞伯拉罕的忠誠。一連串空白有待于讀者去闡釋、去解讀,以便發(fā)掘文本的無盡內涵,這種敘述技巧提供了多樣性理解的可能性,使接受者得以在戲劇性解讀的過程中獲得極大滿足。
四、“游移視點”理論在觀察圣經(jīng)敘事過程中的功能
此外,作者如何運用“游移視點”(wondering viewpoint)強化敘事效果,也為讀者反應批評家所關注。“游移視點”指讀者的注意中心在閱讀過程中不斷變化轉移的現(xiàn)象。伊瑟爾指出,讀者閱讀和領會文學文本不僅區(qū)別于人們認識外部世界,也區(qū)別于人們閱讀科學文本。就前者而論,主體總是處于客體之外,不斷以客體為中心來展開認識活動;就后者而論,主體雖然處于科學文本之中,卻從未與其表現(xiàn)的東西融合為一。與此相反,讀者閱讀文學文本時不但必須介入那種文本的情境之中,還必須持續(xù)體驗時刻變化著的情境。伊瑟爾用“游移視點”表示文本意義在讀者想象中獲得生命力的過程:讀者的視點游移于文本各部分之間,使那些部分建立起明確的聯(lián)系;在閱讀的每個特定時刻,被讀者視點凝聚之處會形成一個主題,該主題成為下一時刻將要形成的另一個主題的背景;如此周而復始,使讀者的注意力總能處于一種游移過程中,最終形成一個富于生命力的審美對象。
有研究者考察圣經(jīng)敘事時指出,視點不僅指向文本中那個象征性世界的敘事中心,還是讀者觀察文本所述世界的“實時向導”;當讀者以游移視點觀看情節(jié)變遷的動向時,很可能為某種藝術技巧所制約[5]。
五、圣經(jīng)歷史批評家對激進讀者反應理論的質疑
在激進的讀者反應理論家看來,文本自身無關緊要,意義乃基于讀者與文本從本體論上的結合,最終取決于讀者的“創(chuàng)造”;就連作者的動機也滲入讀者的知覺之中,一如費希所論:“讀者經(jīng)驗的形態(tài)、形式的單位,以及原意的結構乃是同一回事,它們同時納入眼簾,不存在所謂優(yōu)先順序或獨立性問題。”[6]這種極力抬高讀者功能的理論為定位于歷史的圣經(jīng)批評家所質疑。由于對語言及圣經(jīng)文本的性質秉持不同見解,圣經(jīng)歷史研究者欲克服這種抵觸感并不容易。
傳統(tǒng)的語言觀和生命觀是相互支撐的,二者都采納了啟蒙時代以來流行的理論模式,其間主體與客體、人類與自然分別隸屬于不同種類,主體及人類在各自的二元組合中皆居于主導位置。語言被視為效命于人類的工具,作為主體的人類則借助于語言與其所言說的對象建立起聯(lián)系,使其正在論述的真理生效。然而在激進的讀者反應理論家那里,主客二分法卻遭到消解,主體與客體混為一談。這也許是對某種早期語言觀念的復歸,那時人類與自然尚未分離,而由某種共享的力量整合起來,語言甚至能對自然施加影響。當然,在讀者反應理論家看來,語言的影響僅僅作用于讀者本身而非自然。
福勒嘗試對讀者反應理論的時空性質加以探討。他對語言交流的“時間模式”(temporal model)和“空間模式”(spatial model)加以區(qū)分,稱前者發(fā)生于時間流程中,被言說的語詞采取了口耳相傳形式;后者則以特定空間為條件,書面語詞通過寫作和閱讀被人感知。在他那里,讀者反應理論向早期語言觀念復歸,意味著那派學者“贊同閱讀的時間模式而非空間模式,與口耳相傳的語言形態(tài)情投意合。”[7]圣經(jīng)如同其他古代經(jīng)典,雖然是以書面文字傳之于后世的,卻也經(jīng)歷過口耳相傳的早期孕育階段,那個階段的重要性并不亞于后來的編纂成書。
六、關注讀者接受的“效應史進路”
在20世紀下半葉的圣經(jīng)文學批評領域,矚目于讀者接受的方法論還包括“效應史進路”(History-of-Effects Approach),其特色在于以宏觀歷史視野將圣經(jīng)文本傳世以后的重要闡釋成果及其對讀者的影響效應進行綜合評估,既引導當今讀者認清自己的闡釋角度、習慣和盲點,又開闊其視野,使之注意到文本的多重含義。比如,瑞士學者陸茲(Ulrich Luz)原期待寫一部歐洲天主教徒和基督徒都能認同的《〈馬太福音〉注釋》,卻發(fā)現(xiàn)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兩派信徒均擁有持守了多年的神學傳統(tǒng)和釋經(jīng)方法,不可能接受對方的見解。歐洲歷史上多次由于圣經(jīng)詮釋而引發(fā)沖突,已造成慘不忍睹的百年宗教戰(zhàn)爭,以及排斥猶太人的種族歧視和大屠殺。考慮到這一事實,陸茲除了深入分析《馬太福音》的歷史內容和文學構思外,還精心梳理兩千年來歷代讀者對那卷書的理解和接受,兼而指出他們的洞見和謬誤,客觀評價那些闡釋對教會產(chǎn)生的影響,及其發(fā)生過的正面和負面效應[8]。然而,這種“效應史進路”固然關注以往圣經(jīng)闡釋對歷史上讀者發(fā)生過的效應,卻并不甚注意當今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與文本之間的互動,與讀者反應理論的側重點還是有所不同。
[1]Baird,J.A.Audience Criticism and the Historical Jesus[M].Philadelphia:Fortress Press,1969.
[2]克萊因,等.基道圣經(jīng)手冊[M].尹妙珍,等,譯.香港:基道出版社,2004.
[3]Crossan,J.D.Cliffs of Fall:Paradox and Polyvalence in the Parables of Jesu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4]Sternberg,Meir.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5:193-213.
[5]Fish,S.E.“Interpreting the Variorum”,In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177.
[6]Fowler,R.W.Who Is the “Reader”in Reader Response Criticism?[J]Semeia,1985(21):20.
[7]葉約翰.耶穌比喻的詮釋:當代研究方法與效應史進路[J].圣經(jīng)文學研究,2011(5):275.
[8]Luz,Ulrich.Matthew1-7:A Commentary [M].Trans.James Crouch.Minneapolis:Fortress Press,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