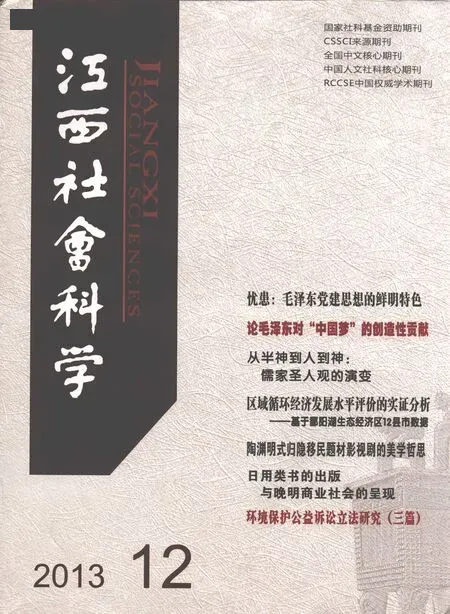多元敘事模式下的莫言長篇小說研究
張 麗
多元敘事模式下的莫言長篇小說研究
張 麗
敘事模式是一個比較靈活的概念,學界至今沒有明確的界定。但可以確定的是,敘述者、敘述視角、敘事技巧是敘事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小說中,不同的組合組成了不同的敘事模式。在中國當代文學中,莫言的小說以它的敘事性被許多人解讀。莫言長篇小說在敘述者層面形成了客觀型、主情型、體驗型的交流體系;在敘述視角層面,形成了多維時空下的話語狂歡體系;在這種交流體系與話語體系中,凸顯了作家獨特的述史與敘事相結合的精神空間。
敘事模式;莫言;話語狂歡;精神空間
張 麗,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博士生,江西省社會科學院中國敘事學中心助理研究員。(北京 100872)
中國傳統的小說模式比較講究故事的開端、發展、高潮和結局,注重故事的講述和懸念的設置。近代中國的小說模式在原來的基礎上進行了改變,作家們在注重故事情節塑造的同時,也融入了抒情環節和對人物心理的刻畫,從而使比較單調的文學創作表現出多元的趨勢。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獨特的生活經歷,都有他自己的價值尺度,在文化多元的21世紀,莫言既借鑒了西方小說的敘事方式和表現手法,也融合了中國本土文化的多種文學現象所具備的敘事方式,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敘事策略。他將中國古老的敘事藝術(中國神話、民間傳說)與現代的現實主義結合在一起、將虛幻與現實結合起來,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幻覺現實主義”風格。他的小說始終以自己的故鄉——山東高密東北鄉為大背景,敘述那里的人和事,展現那里人們的成長過程,同時通過內心獨白、多視角敘述、意象、象征、想象等手法抒寫對故鄉愛恨交加的情感。
在展開具體的論述前,先對“敘事模式”這一概念進行簡要的探討和界定。“敘事模式”是一個比較靈活的概念,敘事學界沒有明確的界定,但不少研究者根據自己的研究情況對它進行了界定。在借鑒中西方學者對敘事模式界定的基礎上,筆者認為:敘事模式是指作者通過敘述者敘述故事的方式。這其中包括了敘述者和敘述故事的方式兩大要素,而要了解這兩大要素,必須先厘清敘述視角、敘述人稱、敘述聲音這三個問題。即選擇什么角度來觀察和感知故事世界(敘述者);以什么身份來敘述故事(敘述視角);表述故事的方式(敘事技巧)。因此,敘述者、敘述視角、敘事技巧也構成了敘事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的組合組成了不同的敘事模式。本文所關注的敘事模式,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1)敘述者在敘述過程中形成的客觀型、主情型、體驗型的交流體系;(2)敘述視角在不斷選擇和切換過程中形成的多維時空下的話語狂歡體系;(3)莫言小說獨特的述史與敘事相結合的多元組合的精神空間。這三種敘事模式在莫言的長篇小說中,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并存、相互聯系的。筆者在細讀莫言長篇小說的基礎上,對莫言長篇小說中的敘事模式進行了綜合的歸類與闡述,并進一步考察莫言長篇小說中這種多元敘事模式的意義和作用。
一、多環節的敘事交流體系
巴赫金在對小說雜語的討論中,曾經列舉了小說引進雜語的幾種主要方式,而現代敘事理論則對小說敘事交流環節作了更加細致的系統化研究,發展出一整套術語,詳細討論了小說交流過程中牽涉的多個環節。這個交流的過程不僅發生在文本內部,發生在文本外部的交流也同樣精彩。在這個交流過程中,從故事層面來講,敘事被看做是一個多極化的交流的工具:在文本內從隱含作者、通過敘述者到受述者、到隱含讀者,而文本之外則是從真實作者到真實讀者。莫言長篇小說中,從敘述層面來講比較有特色的是敘述者的多環節交流,在同一部小說中敘述者有不同的類型,即客觀型敘述者、主情型敘述者、體驗型敘述者,通過不同敘述者的眼光來敘述故事,觀察故事情節的變化過程,從而完成敘事功能,增強故事的可讀性。
(一)客觀型敘述者——通過內聚焦方式來觀照客觀社會
客觀型敘述者是凌駕于故事之外的敘述者,他以客觀、冷靜的語調來敘述所發生的事情,增強了故事的可信度。如,《透明的紅蘿卜》中的黑孩,帶有非常神秘的色彩,他是一個孩子,經常被后媽虐待,他是故事之中的一個小角色,但又游離在故事中的大人世界之外,用一個兒童的眼光,敘述著周圍大人的事情,敘述著自己的種種感受,用兒童的眼光觀照著現實世界。①與黑孩相似的還有《酒國》中的少年金剛鉆、余一尺等,他們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是心智很不成熟的孩子,沒有具備把握世界的能力,因此,在整個敘述故事的過程中,他們只是以旁觀者的身份介入故事中,他們的敘述大多停留在簡單的感官直覺上,但這種比較直白的敘述也增強了故事的真實性。
(二)主情型敘述者——細述人物的情緒與心理
主情型敘述者是一個雙重性的敘述主體,他的任務是細述人物的情緒與心理。敘述者可以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也可以是次要人物,小說中的人物既包括實實在在的“人的形象”也包括“物的形象”。敘述者用平等的眼光對待故事中的人與物,使得他們之間能夠自由平等地對話,同時用物的眼光抒發感情,發表見解,從而打通了物與人之間的界限,讓物用人的思維方式、人的眼光來表達情感,從而塑造了許多令人難以忘懷的物的形象。在《檀香刑》中,敘述者孫眉娘的敘述,始終在主觀愿望與客觀現實之間徘徊,孫眉娘比較復雜的心理描述,使得人物的感情比較細膩。孫眉娘的敘述,主要是靠心里的感受來結構全文,來展示某種深刻的人生哲理,使作品產生一種荒誕美。
(三)體驗型敘述者——換位言說,代替人物敘述者講述他們的故事
莫言長篇小說中的敘述者比較突出的是對體驗型敘述者的設定,敘述者在敘述故事的過程中,自己也在隨著故事時間的發展,慢慢長大,有了一定的社會閱歷,因此在充當敘述者的過程中,也會出現換位思考的現象。故事中的他們在逐漸成熟的過程中,對事情的看法有了更深的了解,比如,《豐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他是上官魯氏的寶貝兒子,上面有八個姐姐,但他是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對大人的世界始終有一種陌生感和排斥感。在他的敘述中,他在講述著母親與姐姐們的故事,他既代替了姐姐們敘述她們自己的故事,也在敘述著自己的故事以及自己對一些事物的看法,他的敘述使作家的主觀愿望得到了酣暢淋漓的發揮。另外,在《檀香刑》中,敘述者“我”代表了很多人物,故事中出現的所有人物,都以敘述者“我”來敘述他們各自的故事。由于這些人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具有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因此敘述者在敘述的時候也會受到限制,但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敘述者通過自己對生活的體驗,在主觀敘述語調與客觀敘述語調中能夠自由地轉換,這種轉換的技巧是別的小說中所不具備的。
總之,在莫言長篇小說中,同一部作品的敘述者在客觀型、主情型、體驗型之間展開敘述并不斷轉換。有時敘述者會以旁觀者的態度游離于故事之外,敘述故事;有時敘述者以文本中人物的形式出現,他參與事件的發展;有時敘述者又以隱含作者的聲音來評論故事中的人物,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這種多環節的敘述者在倫理、認知和解讀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但偏差構成了張力。在故事層面雜亂紛繁的線索情節中,在大量插敘和倒敘中,敘述者的敘述顯得無序而雜亂,讀者卻可以從其中任何一個敘事點切入并加以閱讀,這種布局方式,給了讀者很大的閱讀自由,為讀者從不同層面切入文本留下了廣闊的空間。
二、敘述視角的轉換與女性生存的悲劇
判斷故事講得好與壞的標準,最主要的還是看如何處理敘述者和故事之間的關系,也就是敘述視角的問題。敘述視角是指敘述者或人物與敘事文本的時間相對應的位置或狀態,即敘述者從什么角度來觀察故事。美國學者華萊士·馬丁曾經認為:“敘事作品中,由于敘述視角的存在,使得文本中的沖突、懸念激發了讀者的興趣,而這些敘述視角是讀者根據自己對故事情節的把握程度,逐步發現的。”[1](P57)一部小說的敘述視角不同,所產生的敘事效果也不同。華萊士·馬丁甚至認為:“在很多情況中,如果敘述視角被隨意改變,整個故事就會變得面目全非。”[1](P59)因此正確把握敘述視角就顯得非常重要。莫言小說在敘述視角方面一個最為重要的表現就是敘述視角靈活多變。即敘述者人稱一致,但同一人稱所代表的人物會不斷發生變化;同一故事情節中,敘述人稱不斷變化,因此敘述視角也在隨著不斷變化。在莫言的長篇小說中,這種轉換很多,可以說,莫言運用這種敘述視角轉換的方法,一方面在挑戰自己,另一方面也在挑戰讀者。因為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稍不留神就分不清文章中的你、我、他指的是誰了。
20世紀以來,西方批評界十分關注不同作品之間“人物有限視角”與傳統全知模式的差異。但在很多作品內部出現了兩種“限知”模式的交換出現,敘述視角在全知敘述者與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之間轉換,這樣使故事主題出現了多種形式。莫言長篇小說中的敘述視角打破了傳統有限視角的局限,通過敘述視角的多角度轉化,來形成文本中多維度的時空模式。這種角度的變化主要體現著敘述者、人物以及讀者等層面,通過這些變化進一步展現小說的深層內涵,特別是小說中涉及的女性問題。總體來講,莫言長篇小說中敘述視角的轉換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敘述視角的選擇與切換
莫言小說中的敘述視角不斷地在作者敘述、人物敘述、旁觀者敘述、讀者疑惑、解惑等模式中交替運用,它顛覆了以往的敘事常規,進一步加強了作品的反諷效果和人物命運的不確定性,增強了作品的感染力。
從最早的 《透明的紅蘿卜》中客觀、冷靜的敘述方式,到 《球狀閃電》、《紅蝗》、《豐乳肥臀》、《生死疲勞》、《檀香刑》、《四十一炮》中眼花繚亂的敘述視角和緊湊的敘述節奏,再到近期的《蛙》中,敘述者的視角重新回到了平緩、冷靜的狀態,表現了作者對敘述節奏的合理把握,在這樣的節奏中,作者、創作主體與敘述者形成一種動態關系。如《豐乳肥臀》中,當敘述視角轉移到敘述鄉土中國歷史時,讀者可以感受到一種歷史的滄桑與悲壯感;同時,當敘述視角轉向母親與姐姐們的生活時,讀者又可以在荒誕的情節中感受著戲謔與狂歡。
(二)在時間和空間中自由穿梭
對敘述視角進行選擇后,讀者可以隨著敘述視角的轉換而在莫言的虛構世界中自由穿梭。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穿梭中,作者進行了性別的虛構,即在異性視角下對女性的生活體驗進行敘述,由男性來代替女性敘說她們的故事,這種獨特視角的轉換使得小說在情感上表現得至真至情,以男性的角度來看待那時代的女性,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表現了特定時代女性生存的悲劇。《檀香刑》中的鳳頭部孫眉娘浪語、趙甲狂言、小甲傻話、錢丁恨聲和豹尾部趙甲道白、孫眉娘訴說、孫丙說戲、小甲放歌、知縣絕唱都運用了多種敘述視角,形成眾聲喧嘩的多元化敘事效果。孫眉娘的敘述夾雜著諺語、俗語、俚語、歇后語、順口溜、粗話,體現出一個放浪、大膽的民間女子的敘事角度和思想特征。《紅高粱》通過戴鳳蓮和余占鰲的故事,以時空錯亂的順序,借用意識流的表現方法,敘述了昔日發生在山東某鄉村的一曲生命的頌歌。
(三)多維時空中的話語狂歡
柏格森把時間分為空間時間和心理時間,認為人們所公認的時間觀念即空間時間,不過是各個時刻一次延伸表示寬度的數量概念,而心理時間則是各個時刻的相互滲透,表示強度的質量概念。這個理論在20世紀20年代影響了大批作家,從而產生了意識流小說。曹文軒在《小說門》中認為:“小說往往喜歡異境——特別的空間。這種空間的一大標志就是它的孤立。它遠離人類社會,并且似乎在它之外就不存在其他空間。宇宙突然縮小,縮小到只剩下這一點空間。”[2](P203)莫言小說深受意識流影響,在他的小說中也擺脫了傳統的故事情節和時間觀念。運用意識流的創作方法,主要表現在三方面:(1)運用時空交錯的形式,實現對物理時間的超越;(2)使敘述擺脫情節,打破邏輯;(3)揭示人物隱秘的內心世界。
在《四十一炮》中最能體現莫言民間化創作努力的,就是他模仿古代說書人的口吻,創造了一種自由言說的文本。小說的結構也很特別,它并不是一個具有內在嚴密邏輯關系的文本,而是由多個故事嵌合在一起,連接它們的就是羅小通不停地講述。這些故事發生的時間各不相同,羅小通也并不是每個故事的主人公或親歷者。但他就是用說書人的口吻,以全知視角,以足夠的信心和想象力來講述每一個故事。《檀香刑》中鳳頭部:“孫眉娘浪語”、“趙甲狂言”、“小甲傻話”、“錢丁恨聲”四章,如同在舞臺上生、旦、凈、末、丑各色人物分別登臺亮相,用符合人物聲口的語言,交代故事、人物關系、表達自己的感情和看法。且在每章正文前都有一節貓腔唱詞作引子,使讀者在享受這些話語狂歡所帶來的快感的同時,在作者塑造的各種空間中穿梭。
三、述史與敘事:多元組合的精神空間
莫言曾說:“歷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堆傳奇的故事,越是久遠的歷史,距離真相越遠,距離文學愈近。人對現實不滿時便懷念歷史,人對自己不滿時便崇拜祖先……我們的祖先跟我們差不多,那昔日的榮耀和輝煌大多是我們的理想。”[3](P78)在莫言的筆下,在他遠離那份至今難以確定的歷史真實的背后,莫言心中對歷史有一種新的構想,在他的理念中,歷史雖然已經遠去,但人性深處保留的那份最真實的狀態還沒有消失,因此,莫言帶著自己對歷史和未來的想象,對歷史進行重新虛構,通過歷史的變遷來找尋人類普遍意識中的那份美與純潔,他將歷史與當下、現實、理想融為一體來傳達自己的情感與思想。在這種傳達的過程中,主要通過象征的模式和多種創作模式中的雙層結構來實現著述史與敘事的結合。
(一)象征模式體現著作家的精神寄托
象征是一種具有特殊意義的符號,它由 “外在的表現方式”和“內在的意義”兩部分構成。在莫言小說的象征模式中,“紅高粱”是高密東北鄉的象征,它既象征了堅韌不屈的民族精神,也象征了斗志昂揚的個體精神。“豐乳肥臀”象征了母愛的偉大和生殖力的強大。上官魯氏有著所有母親身上的寬容、慈愛、默默奉獻精神。當她的兒女,無論是懦弱無能的、堅強能干的、蠻不講理的、忍辱負重的、神迷鬼道的,以任何一種方法出走,在任何環境下回歸,她都毫不猶豫地接受他們,默默地承擔起維持他們生存的重擔。《檀香型》中的“貓腔”是一種具有象征意義的民間表演形式。它發源于民間,平時是老百姓用來自娛自樂的藝術形式,它與民間有著血肉相連的關系。它唱腔上的悲涼和旋律上的婉轉均表現了當時民間生活的艱難辛苦。作為“貓腔”的傳人,孫丙不僅將它發揚光大,直到生命的最后,他更是和 “貓腔”合二為一。孫丙領導的民間力量雖然以悲劇而結束,但他們的反抗卻喚醒了正在徘徊的民眾。因此,“貓腔”象征著一種自發的、深藏的、堅忍不拔的民族力量;同時,“貓腔”作為一種流傳的民間藝術,表現了當時民眾豁達、樂觀的心態。
(二)多種創作形式體現的雙層結構
莫言借用民間和傳統文學形式,甚至戲劇、戲曲表達作者深層的創作心理。《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勞》三部長篇中,莫言從民間文化和傳統習俗中汲取營養,借鑒說唱藝術、戲劇戲曲、古典小說那里的敘事方式和表現手法。因此,三部小說既有相同之處,又由于莫言向民間或傳統借鑒的角度和側重點不同,導致它們形式上各有特色。
他的小說出現了現實和心理的雙層敘事結構。作家在敘述單一的線索之外,還有一條心理線索,兩個敘事層面平行展開,成為一種獨特的模式。《檀香刑》的故事情節很簡單,其著力表現女主人復雜的心理過程,因此在小說中就會出現兩個層面:一個是現實情節層面,敘述者用很平靜的話語講述著故事;另一個就是人物的心理層面,看似簡單的孫眉娘,內心卻充滿了無聲的抗爭,在現實的壓抑下暗潮涌動,最后終于爆發。兩個層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現實層面女主人公是溫柔賢惠、孝順公公的好兒媳,在心理層面卻對公公的所作所為厭惡至極。現實層面的孫眉娘是一個賢妻,在心理層面她卻為追求愛情奮不顧身。《檀香刑》中比較突出的是敘述者兼主人公的非理性、無序的心理敘述。這種心理敘述的特點是:以主人公意識情緒本身的內在結構取代情節的因果結構,從而真實地再現人物的心理真實。
總之,莫言長篇小說最顯著的一個特點就是情感、情緒的介入。小說的敘述方式出現了向內轉的傾向。在外部結構上是敘述現實的故事;在內部結構上,則是打破了小說中的以故事的物理時間為標準的表現方式,而以心理時間為樞紐,人物形象塑造也以情緒、情感為主。
四、多重視角中敘事模式的意義考察
(一)在現實、想象、虛構的結合中實現作家的人文情懷
沃爾夫岡·伊瑟爾在《虛構與想象——文學人類學疆界》中提到:“(文學虛構是)對現實世界進行侵犯的有意識的行為模式,于是,虛構就成了越界的行為。雖然如此,它對被越界部分卻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惕。結果,虛構同時撕裂分散和加倍拓展了這個供它參照的世界。”[4](P165)并認為現實、想象、虛構是三元合一的關系。虛構世界在表達作家認識時更加自由,更加有多義性。
莫言通過對他所熟悉的鄉土記憶的虛構,尋找一種內心深處的現實,在對現實的思考中,融入想象的成分,進一步達到虛構世界的升華,這樣使作者的創作與內心深處的追求達成一種融合。同時,作家又有著對民間與歷史的思考。在莫言那里,民間既是一種寫作個性,又是一種創作資源,既包含著作家對地域文化的傳承,又以獨特的書寫歷史的新視角和立場,揭示一種普遍的人性思想。
莫言構筑了帶有強烈地域色彩的“高密東北鄉”,并把“高密東北鄉”帶進他所創造的文學世界中,這個世界映射出作家對歷史、對民族的一種想象與塑造,既勾勒出獨特的地域形態特征,也表現出了獨特的生命狀態與生命意識,形成作家對經驗世界的一種特殊的表達。
(二)主題的多重闡釋
一般的小說中,讀者通過閱讀小說的因果聯系和人物行動的因果關系可以推斷出作者所反映的現實世界的規律性,在這些情節中,時間的因果關系和人物的性格比較容易把握,有明確的主題。在莫言的長篇小說中,即使小說中有比較清晰的情節和人物,結構卻是破碎的,這就導致了小說的多重主題,而且這些主題具有很大的包容性。這對于讀者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挑戰。主題的多重闡釋是莫言長篇小說吸引讀者的地方,多重的敘事主題使小說逐漸擺脫了情節模式單一的現實主題,對多重主題的探索也可以使讀者更加體會到作家比較復雜的創作歷程。《生死疲勞》是一個變形記的故事,卡夫卡的形而上的變形記,在這里被改變為一種歷史的變形記,一個階級的變形記,人在歷史中的變形記。從這個意義上看,莫言把卡夫卡中國本土化了,并超越了卡夫卡。《檀香刑》中的主要人物包括孫眉娘、趙甲、趙小甲、孫丙,作者在敘述他們的故事的時候,幾乎每一個人物都用了很重的筆墨,因此,讀者很難分清哪個是主人公。但當把他們的故事組合起來的時候,讀者會發現潛藏在他們故事結構下面存在著一個豐富的歷史世界:這里既有官方的統治和外交,又有民間的男女私情;既有邊緣的刑獄文化,又有義和團綠林文化;既有各種正常人對歷史的理解,又有智障者對歷史的感受。
綜上所述,莫言小說中的多元敘事模式不僅體現在文本中的敘事技巧層面,更體現在作家的小說創作理念之中,這種敘事模式是敘事技巧和意義內涵的雙重建構。莫言的小說超越了民族、性別的界限,用一種開放的姿態反對一切阻礙自由寫作的權威,他在文本中尋找著真實的敘事方式,并不斷突破、跨越將文本敘事推向更遠的方向。
注釋:
①本文所選莫言作品均出自《莫言文集》,作家出版社,1994年版,2012年版。
[1](美)華萊士·馬丁.當代敘事學[M].伍曉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2]曹文軒.小說門[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3]高曉春.有理想就有疼痛:中國當代文化名人訪談錄[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
[4](德)沃爾夫岡·伊瑟爾.虛構與想象——文學人類學疆界[M].陳家定,汪正龍,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責任編輯:彭民權】
I206.7
A
1004-518X(2013)12-0111-05
江西省社會科學院2013年青年課題“莫言長篇小說的敘事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