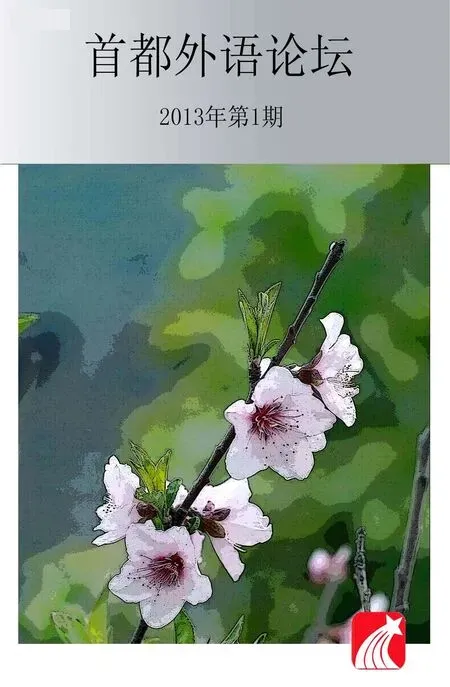“目的論”——翻譯理論的新視角
首都師范大學 王維中
人類社會的進步,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現代化通訊技術以及交通工具的廣泛應用,為人類各個語言集團之間的頻繁交流提供無限的契機,也為翻譯實踐活動以及基于此的翻譯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廣闊前景。信息載體由紙質向電子過度,不僅改變了各個語言集團了解外來文化的方法和手段,也更新了翻譯功能,從而改變了人們對翻譯的認知理念,對翻譯實踐提出了新的要求。翻譯家們不再沉湎于追求譯文忠于或者對等于原文,把譯作與原作的關系視為翻譯的生命線,而是更多地采納了解市場運作的翻譯委托人的建議,了解譯文讀者的要求和愿望,在考慮源語文化和譯語文化、原作讀者和譯作讀者、原作的創作目的和譯作的翻譯目的等諸多因素的前提下,進行翻譯實踐活動,從而達到其目的。翻譯理論家們也拓寬了他們的視野,為指導實踐的翻譯理論制定了新的衡量標準,他們不再把譯作與原作的關系視為評判譯作質量的唯一標準,而是以全新的理念,從更高的立足點出發,致力于探索翻譯是否符合譯作讀者的要求,是否達到其最終目的。在這種注重跨文化要素的翻譯背景條件下,一種全新的翻譯理論誕生了。這就是由德國翻譯理論家卡塔林娜·賴斯(Katharina Reiss)及漢斯J· 費爾梅爾(Hans J.Vermeer)提出的“目的論”(skopostheory)。“目的論”堅持翻譯之根本是其目的,認為達到目的要比采取何種翻譯方法更重要,強調必須把翻譯的中心從原文轉移到譯文讀者上,要求翻譯必須以譯文讀者定向,譯者首先要對譯文讀者負責,為此,“目的論”的倡導者甚至提出“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目的論”以其全新的翻譯理念,打破了翻譯理論界長期以來由“等值論”、“相似論”、“信達(雅)說”等一系列以原文為中心的翻譯理論一統天下的局面。為翻譯理論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全新的視野,把翻譯理論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是翻譯理論發展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
一 何謂“目的論”
“目的論” (skopostheory)是德國“功能派”成員賴斯和費爾梅爾于20世紀70年代創立的翻譯理論。“skopos”一詞,源自希臘語,意為“目的”,故這一理論被稱為“目的論”。
賴斯和費爾梅爾于1984年在他們共同出版的專著《普通翻譯理論基礎》①Katharina Rei?/Hans J.Vermeer,“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n Translationstheorie”Max Niemeyer Verlag,Tübingen,1994.中,首次系統地對“目的論”這一翻譯理論作了科學的論述。此后,費爾梅爾在他題為《翻譯作為文化轉移》②/HansJ.Vermeer,“übersetzen als kultureller Transfer”übersezungswissenschaft,Eine Neuorientirung Mary Snell-Hornby (Hrsg)Franke,Tübingen,1986,P.30.的論文以及在其他的諸多學術論文中,對“目的論”作了進一步的論證和補充,功能派的其他成員,如諾爾特(Christiane Nord)也對這一理論作了多方面的補充,使這一理論不斷趨于完善。賴斯和費爾梅爾的“目的論”與曼塔利(Justa Holz Mantari)的“行為論”(actiontheory)以及諾爾特的“功能論”(Funktiontheory)構成了20世紀80年代德國功能派翻譯理論的核心。
賴斯和費爾梅爾的“目的論”基于曼塔利的“行為論”。根據曼塔利的理論,任何人類行為都有其目的,人們通過達到行為的目的來改變現實。曼塔利提出任何人類行為均以目的定向(目的決定行為)。賴斯和費爾梅爾把曼塔利“目的決定行為”的理論引入至翻譯中,堅持原作的創作和譯作的翻譯均為有目的之人類行為,提出“翻譯是其目的的功能”③Katharina Rei?/Hans J.Vermeer,“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n Translationstheorie”,P.105.,翻譯過程取決于翻譯目的,達到翻譯既定目的要比用何種方式進行翻譯更重要。①Katharina Rei?/HansJ.Vermeer,“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n Translationstheorie”,P.100.賴斯和費爾梅爾將“目的決定行為”這一規則定義為“目的準則”,視之為翻譯理論的最高準則。②Katharina Rei?/HansJ.Vermeer,“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n Translationstheorie”,P.101.
根據賴斯和費爾梅爾的理論,作者的創作行為屬于原始行為,譯者的翻譯行為屬于二手行為,換言之,翻譯是原文所提供的信息的再提供。翻譯屬于在目的語的文化和語言中提供關于在原語文化和語言中所給信息的信息。③Katharina Rei?/HansJ.Vermeer,“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n Translationstheorie”,P.105.根據“目的論”,譯者僅將原作視為翻譯的信息來源。就創作和翻譯的行為、目的、要求以及作者和譯者能享受的權利、應履行的義務和承擔的責任而言,創作和翻譯都是獨立的,平等的,并非一方依附于另一方。無論是創作還是翻譯,作者和譯者都根據各自的讀者群對即將創作或即將翻譯的作品的期待確立各自目的,并為達到既定的目的而努力。根據“目的論”,任何作品,乃至作品的各個組成部分都具有不同的目的,創作行為與翻譯行為的目的都不止一個(目的多于1),這些目的分別按主次等級依序排列。每個目的都必須有意義,確定一個目的應有充分理由。④Katharina Rei?/Hans J.Vermeer,“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n Translationstheorie”,PP.103.翻譯目的可與創作目的一致,但也可偏離創作目的:某國一位總統候選人發表了一篇競選演講,該演講者的創作目的非常明確:要獲得國民更多的選票。一位譯者將它譯成了中文,但譯者的目的絕非要讓譯文讀者去為該候選人投票,而是有他自己的翻譯目的。這就意味著,原文的創作和譯文的翻譯可以有不同的目的。對此,賴斯和費爾梅爾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論證:
第一、相對于創作行為,翻譯行為原則上是另一種創作行為,它可以為其它的目的服務。
第二、翻譯被定義為信息提供的特殊形式。只有當信息發送者預計到信息的接收者對所發送的信息感興趣時,他才會將信息發送給對方(信息的新穎性)。而正因為所發送的信息具有這種新穎性,所以它完全有可能擁有另一個目的。賴斯和費爾梅爾進一步強調,翻譯保留原作的目的,是文化專項的規則,而不是普通翻譯理論的基本要求。⑤Katharina Rei?/Hans J.Vermeer,“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n Translationstheorie”,PP.103.
這里涉及到兩個關鍵問題:其一,當創作目的與翻譯目的不同時,是否允許譯文偏離原文,對此,賴斯和費爾梅爾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們的理論是:作者創作要對作品讀者負責,作者為了使其作品滿足讀者的要求,可以采取各種創作手法;相應地,譯者翻譯也須對譯作讀者負責。譯者為了使其譯作符合讀者要求,也可以采取各種翻譯手段。由于原作讀者和譯作讀者屬于不同的文化群體,這兩個群體對于原作文化的理解有巨大的差異,要使譯作讀者能夠理解原作所提供的信息,就必須允許譯文偏離原文。其二,譯文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偏離原文?對此,費爾梅爾提出,譯文可以在不改變原作基本功能的前提下,對原作進行細微的修改。為此,費爾梅爾援引伊原克曼(Eykman)的理論:在不改變文章功能的前提下,一些圖片可以被另一些圖片替代或者一些表達被另一些表達替代,伊原克曼稱之為“細微的修改”。①Katharina Rei?/Hans J.Vermeer,“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n Translationstheorie”,PP.98.費爾梅爾認為,對于翻譯,這種細微的修改在必要的條件下是允許的。
根據費爾梅爾的觀點,翻譯的目的是否能夠達到也取決于翻譯的行為情景,并非每一個目的都能在每一個行為情景中達到,如果一個行為情景發生了變化,則一個目的就不合適了。因為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活動,它需要克服語言文化的障礙。在翻譯的過程中,原著的創作情景對于譯著讀者而言發生了變化,由此可能產生下列三種情況之一種:
(1)翻譯的目的不變,而翻譯的另一個或數個要素發生變化,比如作用,效果等,
(2)原作不適合翻譯,
(3)譯作的目的發生了變化。
賴斯和費爾梅爾提出,從確定翻譯目的到它的實施從方法上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1)確定翻譯目的
在確定翻譯目的之前首先要了解未來的譯作讀者,譯者根據讀者的要求和愿望確定目的。
(2) 評估并更改原作
依既定目的在譯前評估原作各部分,以確定在譯前或譯間或譯后據既定目的更改原作。改寫可在譯前或譯后由專業人員完成,亦可由掌握原語文化之譯員在翻譯期間完成。
(3) 達到翻譯目的
在考慮譯作讀者群要求之前提下進行翻譯。②Katharina Rei?/Hans J.Vermeer,“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n Translationstheorie”,PP.102.
根據賴斯和費爾梅爾的理論,翻譯提供信息,屬于信息的再提供,它具有描述性質,但不具有明顯的可逆性。①Katharina Rei?/Hans J.Vermeer,“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n Translationstheorie”,P.105.換言之,譯著不可能被隨意回譯至原著。
諾爾特通過“文本結構說”從另一個角度論證了賴斯和費爾梅的理論。諾爾特認為,每一文本都有一個由相互關聯的要素組成的特定結構。如果其中的一個要素發生了變化,則其他要素在該結構中也會自然而然地發生相應的變化。翻譯的目的是要克服語言文化障礙,使交流成為可能,因此,即使原作與譯作所擁有的各個要素,包括原作讀者與譯作讀者在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等方面完全相等,至少有兩個要素發生了變化:文化與語言。②Christiane Nord,“Textanalyse und übersetzen”,Julius Groos Verlag Heidelberg,1995,P.27.諾爾特強調,受文化的制約,譯作讀者所掌握的知識、他們的生活習慣以及“閱讀文章的經歷”都與原作讀者不同,而且,原作讀者熟悉原作所使用的術語,因為作者在創作過程中考慮到了其讀者的文化背景,而這些術語對于處于另一種文化背景中的譯作讀者而言往往是陌生的③Christiane Nord,“Textanalyse und übersetzen”,P.29.。諾爾特認為不存在譯作與原作相似的“常規”,譯作與原作不相似這種“非常規”現象就是翻譯中的常規現象。④Christiane Nord,“Textanalyse und übersetzen”,P.27.
二 “目的論”與傳統翻譯理論之間的關系
“目的論”是一種較為年輕的翻譯理論。它與包括“等值論”在內的傳統翻譯理論既有對立性又有兼容性。它的對立性存在于:“目的論”崇尚翻譯以譯文讀者為中心,翻譯要充分考慮譯文讀者的愿望與要求;而傳統翻譯理論則強調翻譯要以原文為中心,譯文要與原文“等值”、要“忠實反映原文”;它們的兼容性存在于:從“目的論”的視角分析傳統翻譯理論的“等值”或“忠實”,不難看出,它們都是為翻譯目的服務的,換言之,受傳統翻譯理論指導的翻譯實踐,其目的要求譯文與原文“等值”、要求譯文“忠于原文”。這里涉及到翻譯的兩大策略:異化翻譯(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和同化翻譯(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這是由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創造的、用來描寫翻譯策略的兩個術語。異化是指根據既定的語法規則按字面意思將和源語文化緊密相連的短語或句子譯成目標語。異化翻譯能夠很好地保留和傳遞原文的文化內涵,使譯文突破目的語常規,保留原作的異國情調。同化翻譯是指在必要的時候,對原作的語言形式或內容進行適當的更改,以適應目的語的語言文化環境。這兩種翻譯策略基于兩種不同的翻譯理念:一種是用譯語再現源語文化,譯者通過翻譯這座橋梁把譯作讀者引向原作作者創造的源語文化氛圍中去,讓讀者能夠在原作作者創造的文化氛圍中理解、探索、研究、領略原作作者的思想、情操和風采;另一種是通過更改原作,為譯文讀者創造一個他們熟悉的文化氛圍,以便他們能夠更容易地理解譯作。這兩種翻譯策略的應用取決于翻譯的對象和翻譯的目的。這里,我們引入英國翻譯理論家紐馬克(Peter Newmark)的文本分類理論,對翻譯的基本對象作一分析。紐馬克根據文本的種類和特征,將各種文本分為三種類型, “表達型文本”、 “信息型文本”和“呼喚型文本”。紐馬克根據翻譯目的,把嚴肅的文學作品,包括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抒情詩、戲劇等和權威性著作,如:法律文獻,權威人士的學術著作等以及一些名人自傳、信函等列入“表達型文本”的范疇。 “表達型文本”特點是作者的地位對譯文讀者而言是至高無上的,譯文讀者非常在意他讀的譯文是否是原湯原味。而且,這些讀者往往掌握了一定的源語文化,或者對源語文化有較大的興趣,有的甚至是譯語語言集團中源語文化的傳播者。他們不讀原作,僅僅是因為憑借他們所掌握的源語知識尚無能力閱讀原作,但是他們也許有可能與原作讀者坐在一起討論原作,一旦他們發現他們閱讀的譯作與原作有距離時,他們就會有被譯者欺騙了的感覺,所以,對于這類文本的翻譯,譯者往往采用異化翻譯策略,他要把譯文讀者帶進原作作者創造的環境中去。
紐馬克的“信息型文本”主要是指有關自然科學、科技、工商經濟類的文書等。對于這類文本,信息的“正確性”是關鍵。譯文讀者往往把譯文理解為正確傳遞了原文所表達的信息,我們可以說,沒有一位光碟機使用說明書的譯文讀者在按照說明書的操作程序成功打開光碟機后,一邊欣賞音樂,一邊去研究譯文是否與原文“等值”,更不會再去關注原文作者是誰。因此,對于這些“信息型文本”。譯者完全可以采用同化的翻譯策略,按照“目的論”的要求,把譯文讀者的愿望和要求放在首位,為他們創造一個符合他們習慣的閱讀環境,能夠用最簡單的方式掌握文本的內容。如果說對于“信息性文本”,譯者可以采用同化的翻譯策略,則對于“呼喚型文本”更應如此,因為根據紐馬克的理論,翻譯呼喚型文本時應遵循“讀者第一”的原則,把讀者及其反應作為核心,所以更要注重譯文的可讀性,要求做到通俗易懂。
由此可見,我們可以根據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采取的策略,將翻譯分成兩大類:使用異化策略的翻譯和使用同化策略的翻譯,前者受包括“等值論”在內的傳統翻譯理論的制約,后者則受“目的論”的影響。值得注意是,隨著社會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隨著包括互聯網、多媒體技術在內的高科技在我們生活中的廣泛應用,以及信息載體由紙質向電子的過渡,人類的交流方式以及獲取信息的方式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這種變化也導致翻譯文本種類之間的比例的變化,即:“描述型文本”在翻譯總量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小,而“信息型文本”和“呼喚型文本”在翻譯總量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其原因在于:(1) “描述型文本”的分流。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其一,描述型文本的主體,包括長篇小說在內的經典文學作品本身隨著影視技術的發展得到分流;相應地,以紙質媒介存在的文學作品的讀者也得到了分流;其二,人們更愿意通過視聽技術來欣賞文學藝術,這就使得以紙質媒介存在的文學作品的市場萎縮了,而這一點也是名作家們從事其他職業的主要原因之一;(2) “信息型文本”規模急速膨脹,使得它在翻譯中占有的份額劇增。對此,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切身體會:幾小時之前還只是在一個語言集團之間傳播的信息,幾小時之后就幾乎世界各地家喻戶曉了,它一方面擴大了信息量的基數,另一方面也擴大了“信息型文本”在翻譯中占有的份額; (3)許多曇花一現的名人、名著不斷涌現,促使人們重新定義“描述型文本”中的名人、名著的概念。許多一夜成名,甚至被炒作紅極一時的名人名著,往往還未等到他們的譯著廣為流傳就已經銷聲匿跡了。這種曇花一現的“名著”翻譯不僅動搖了譯者用傳統的翻譯理論指導翻譯實踐的信念,也打擊了讀者追隨、崇拜名人的心理; (4)由于翻譯人力資源的擴大,一部作品往往有多個版本的譯作,這也使得譯文讀者對譯作的依賴性有所減弱。讀者有機會通過不同版本譯本的分析、比較,研究譯文的可靠性,從而影響“表達型文本”翻譯的權威性。這些因素一方面阻礙了以原文為中心的傳統翻譯理論的發展,影響它們對翻譯實踐的正確指導,另一方面又促進了強調以譯文讀者為中心的“目的論”發展,這不僅是因為信息型翻譯的比重在全部翻譯中的比重越來越大,而且還因為閱讀同化翻譯作品要比閱讀異化翻譯作品更容易。
三 結束語
“目的論”屬于相對年輕的翻譯理論,它打破了“忠實”、“等值”等以原文為中心傳統翻譯理論近一個世紀來一統天下的局面,為翻譯理論的發展開辟了新的視野,對于我們的翻譯實踐具有切實的指導意義。盡管使用異化策略翻譯的作品在全部翻譯中的比重會越來越小,但只要有它的市場存在,這種翻譯方法就不會消失。換言之, “目的論”將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與“等值論”等傳統理論并存,它們將會互為補充,相輔相成。從這個意義上說,對“目的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Eggers,H.“Deutsche Sprache Jahrhundert”,München,1973.
[2]Eykman,Chr.“?Ph?nomenologie der Interpretation”,Bern-München,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