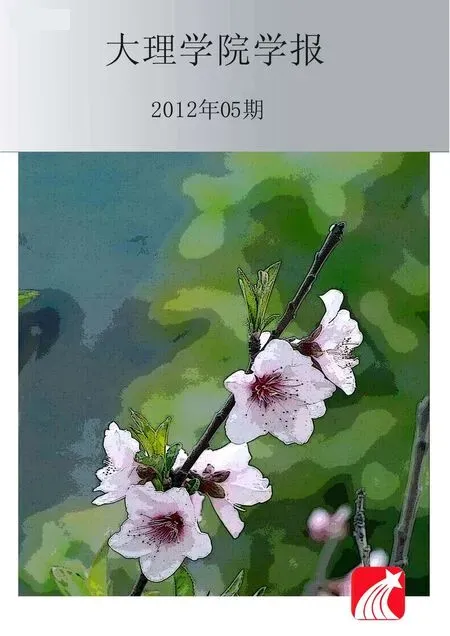唐代和明代小說中的娼妓形象演變
何蕾
(蚌埠學院文學與教育系,安徽蚌埠 233040)
唐代和明代小說中的娼妓形象演變
何蕾
(蚌埠學院文學與教育系,安徽蚌埠 233040)
明代擬話本中的娼妓形象對唐代傳奇中的娼妓形象既有繼承又有發展,有相似處也有不同處。以《霍小玉傳》《李娃傳》與《賣油郎獨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為考察對象,可以看出唐代和明代小說娼妓形象的演變反映了時代的變遷以及作者創作理念上的差異。這些差異表明,中唐傳奇作者的浪漫主義情愫逐漸讓位于晚明商品經濟社會的現實主義思考。
小說;娼妓;演變;時代
唐傳奇是中國小說史上的一座高峰,記載著一批流傳至今的愛情故事。更難得的是,伴隨城市經濟的發展,娼妓形象也開始出現在唐傳奇中,成為唐傳奇著力表現的對象。明代擬話本是中國小說史上又一座高峰,為滿足市民階層的娛樂需求,娼妓形象大量出現,也更加豐滿傳神。唐明小說中娼妓形象有相似處也有不同處。本文試以唐傳奇《李娃傳》與《霍小玉傳》和明擬話本《賣油郎獨占花魁》與《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為考察對象,探尋唐明小說娼妓形象的演變軌跡和社會變遷。
唐傳奇名篇《李娃傳》與《霍小玉傳》向讀者展示了中唐名妓的兩種人生,擁有愛情的李娃嫁入名門,與夫偕老;失去愛情的霍小玉纏綿病榻,憂憤而終。明擬話本名篇《賣油郎獨占花魁》與《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的兩位名妓莘瑤琴與杜十娘,一位與底層小商人相知相愛,躍身泥污,相夫教子;一位懷著被欺騙與被拋棄的憤怒,投身大江,以死自潔。從故事最終結局看,唐明小說中的娼妓形象似有重疊之嫌,李娃與莘瑤琴,霍小玉與杜十娘,前者幸福終老,以一個美好的結局撫慰讀者,后者香消玉殞,以一個悲慘的收尾刺痛讀者。然而,細致對比之下,唐明小說中的娼妓形象并不完全相同,明擬話本對唐傳奇中的娼妓形象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她們之間的差異恰恰反映出唐明兩朝社會環境的差異和作者觀念的變化,也間接反映出特定時代環境下娼妓的生存狀態以及社會對娼妓的認知程度。
一、汧國夫人和商人之婦的象征意義
在唐明小說中,著力塑造娼妓形象,以大團圓收尾的愛情短篇,以《李娃傳》與《賣油郎獨占花魁》最為典型。兩篇小說有著相似的故事框架,男女主角的情愛均發端于邂逅之際。在《李娃傳》中,男主角滎陽鄭生“嘗游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于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遂。闔一扉,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1〕164。而在《賣油郎獨占花魁》中,賣油郎秦重于偶然的機會一睹花魁莘瑤琴美貌后,“準準的呆了半晌,身子都酥麻了”〔2〕29。兩個故事的結局美好而相似,李娃與鄭生琴瑟和鳴,夫科場高中,仕途暢達,婦相夫教子,夫貴妻榮。秦重迎娶莘瑤琴后,夫婦和諧,家業興旺,傳為美談。從故事的發端與結局來看,《賣油郎獨占花魁》的情節設定相對于《李娃傳》來說,似乎沒有明顯突破,然而從故事結局的人物身份設定來看,悲歡離合的才子佳人浪漫故事幻想已逐漸演變為柴米油鹽的市井細民樸素情感敘事。唐明社會環境的變遷從中亦可見一斑。
毫無疑問,李娃與莘瑤琴的初始身份是相同的,不管是唐朝還是明朝,在法律意義上,娼妓都屬于賤民階層。然而,兩位名妓的最終身份卻迥然相異,前者被封為汧國夫人,不僅擺脫娼妓的身份,更上升到上層社會,后者嫁給小商人,融入到平民階層中去。這兩位娼妓的最終身份,凸顯了小說作者迥異的觀念。
(一)汧國夫人——門閥社會知識分子的浪漫理想
李娃是古典短篇小說娼妓形象中最光輝燦爛的一個,也是人生最為圓滿的一個。然而,結合唐代社會背景和道德律法來看,一個慣熟風月的娼妓,為大家族滎陽鄭氏認可,并被朝廷封為一品夫人,于律于禮,絕無可能。唐代婚姻重門閥之風甚嚴,士人娶妻必娶有門第者,婢女、娼妓等一切律法上的“賤類”,即便從良,也不堪正室之任,只能為妾。至中唐此風猶有余烈。敢于挑戰既有等級秩序,必會遭到家族的反對和社會輿論的譴責。例如杜佑晚年將妾李氏“扶正”為妻,接受“密國夫人”的封號,導致“時論非之”〔3〕。
娼妓從良后嫁人生子,結局圓滿者數見不鮮,然而被世家大族聘娶為正妻,并且封為國夫人的例子不見載于唐史書。《唐律疏議》卷十四《戶婚律》,總第92條規定:“諸雜戶不得與良人為婚,違者,杖一百。”疏議部分云:“其工、樂、雜戶、官戶,依令‘當色為婚’,若異色相娶者,律無罪名,并當‘違令’”〔4〕。按律,李娃嫁人應當嫁“當色”人,也即和她同一階層的人。滎陽鄭氏是唐代七大姓之一(參見《唐語林校證》卷五:“高宗朝,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崔,隴西、趙郡李等七姓,恃有族望,恥與諸姓為婚”〔5〕),身為家長的滎陽公鄭某如何能夠主動接受曾經的名娼為兒媳,并且“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1〕171,一絲不茍地遵照禮儀,明媒正娶李娃進門?無疑,對這個問題較為合理的解釋是:李娃最后的圓滿結局承載著中唐知識分子的浪漫理想。而非“以自我主體意識和卓然獨立的行為構筑自己的歸宿,改變了女性的附庸身份”〔6〕。
文中以李娃之口傳達了作者對現實困境的清醒認識。鄭生得官后,“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愿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1〕170-171。可見當時的社會風習仍舊崇尚門當戶對,門閥世族對于娼妓仍舊持有拒斥的態度。以鄭生的家世而言,配偶應當是“鼎族”名媛,絕非娼妓之屬。
作者雖以李娃之口表達出對于社會習俗的清醒意識,卻以另一種方式將這種認識轉化為對現實困境的超越。鄭生對李娃以死相脅,只求李娃不離開自己,鄭父恭謹備禮迎娶李娃為兒媳,李鄭正式婚配之后家道興旺。這種在現實生活中難以見到的大團圓結局,正是作者思想觀念中對現實社會婚配崇尚門第之風的撥正與對現實困境的超越。小說結尾以“倡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逾也”〔1〕171之語,熱烈贊頌李娃,正說明李娃形象的可貴與社會現實的殘酷。娼妓有情者難得,情義兼備者更難得,能嫁入世家大族并被封為國夫人的則更為罕見。作者白行簡視李娃的人生為奇聞異事,為其設定美好的結局,正是以一種虛構的方式實現對跨階層婚姻現實困境的超越,表達的只是中唐知識分子的浪漫理想而已。
(二)商人之婦——市民社會作家現實思考
同樣是被禮聘入門,李娃汧國夫人與莘瑤琴商人之婦的身份反差體現了時代環境的變化和小說作者的觀念變化。從汧國夫人到商人之婦,可以看出中唐傳奇作者的浪漫理想正演變為明代通俗文學作者的現實思考。
與唐代相比,明代社會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商人階層崛起,商人子孫可以讀書作文、著書立說,也可以考試、做官,躋身于文人知識分子之列,比如晚明著名思想家李贄,就是商人的后代〔7〕。官僚知識分子也開始理解商人,以一種新的眼光看待商品經濟,王守仁便是其中之一〔8〕。而植根于現實生活的通俗文學作者,以深刻而現實的眼光,將市民階層納入文學作品表現的范疇,塑造了一系列鮮明生動的市民階層人物形象。同時,對于娼妓形象的摹寫也在發生著變化。相對于唐傳奇中的娼妓形象,明代小說中的娼妓形象更具現實意義。與李娃的浪漫傳奇相比,莘瑤琴的形象顯然更為真實。
下面,通過考察莘瑤琴對秦重的態度變化,來輔證明代小說中娼妓形象的現實意義和真實性。莘瑤琴對秦重的感情發展歷經三個階段,由排斥到一定程度的接受,再由接受到傾心相許。初次交往,莘瑤琴不肯對秦重投以青眼。身為花魁的莘瑤琴,尋常所接之客非富即貴,一個走街串巷的賣油小商人,哪里會放在眼中?深怕與之交往掉了身價。鴇母設計讓秦重與之見面的晚上,莘瑤琴說道:“娘,這個人我認得他的,不是有名稱的子弟。接了他,被人笑話”〔2〕35。可見,莘瑤琴雖身為娼妓,眼光甚是清高,不肯委身于一個無“名稱”的小商人。然而在酒醉嘔吐,被秦重無微不至地照顧一夜后,莘瑤琴心中的冰塊開始融化,不由想到:“難得這好人,又忠厚,又老實,又且知情識趣,隱惡揚善,千百中難遇此一人。可惜是市井之輩,若是衣冠弟子,情愿委身事之”〔2〕37。此時,莘瑤琴已經接受秦重的人品,但礙于秦重市井小民的身份,不肯與之進一步交往。一年之后,兩人重逢之際,正值莘瑤琴落難。秦重救了被惡少凌辱的莘瑤琴,這雪中送炭的舉動,令莘瑤琴徹底拋棄對秦重“市井之輩”的看法,轉而對其傾心相許,誓要嫁其為妻,情酣意濃之時對秦重說道:“看來看去,只有你是個志誠君子。況聞你尚未娶親,若不嫌我煙花賤質,情愿舉案齊眉,白頭侍奉。你若不允之時,我就將三尺白羅,死于君前,表白我一片誠心,也強如昨日死于村郎之手,沒名沒目,惹人笑話”〔2〕41。
秦重既非世家公子又非文人學士,色藝雙絕的花魁娘子莘瑤琴選擇他這個走街串巷的賣油郎,看中的是其“忠厚”“老實”“志誠”“知情識趣”“隱惡揚善”的品性。家族名望、權勢財富未必能給人帶來幸福、平安的生活,對于這一點,久歷風月的莘瑤琴自然熟知在心。于她而言,最切實、最穩妥的人生莫過于脫離煙花道路,和一位愛慕自己、心疼自己的老實男人過一輩子平凡的生活。而嫁給王孫公子的未來遠遠沒有嫁給勤勞致富的平民更有保障。因此,莘瑤琴選擇秦重,既是秦重志誠付出的結果,也是莘瑤琴對現實生活清醒認識的結果。作為社會底層的娼妓,縱使錦衣玉食,笑傲歡場,終是賤類,與豪門權貴之間有著天然的鴻溝。莘瑤琴的觀點極富現實性與平民性,無疑隱含著小說作者的想法。沒有了唐傳奇作者超越現實的浪漫情愫與理想,明代擬話本作者筆下的人物和故事更為真實,更加富有人文氣息。
二、自憐與自尊——霍小玉與杜十娘形象折射出時代的影響
唐明小說作者通過一系列娼妓形象的塑造,自覺或不自覺地順應了社會思想的變遷。霍小玉與杜十娘分別是唐傳奇和明代擬話本中最令人痛惜的悲情女主角,兩人有著相似的命運軌跡,卻折射出不同的時代環境影響和社會思想變遷。
(一)從自憐到自尊蘊含著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
霍小玉與杜十娘在生命凋零前均對薄情郎、負心漢進行了痛訴,聲聲血淚,令人動容。而正是這臨終誓詞,凸顯了霍小玉與杜十娘形象的差異。
霍小玉臨終前以酒酹地,痛斥李益的薄情:“我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弦管,從此永休。征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后,必為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1〕116。臨終前的霍小玉,清醒地道出身為女性的悲哀,指出正是李益導致她的生命陷入黑暗,但感情太深,愛恨交雜,復仇的利劍投向無辜者,而非李益。杜十娘投水前,血淚交迸,痛切陳詞:“妾櫝中有玉,恨郎眼內無珠,命之不辰,風塵困瘁,甫得脫離,又遭棄捐。今眾人各有耳目,共作證明,妾不負郎君,郎君自負妾耳”〔9〕330。
霍小玉的怨憤中埋藏著深深的自憐,“我為女子,薄命如斯”一語道出身為女性的悲哀與無助,而杜十娘“妾櫝中有玉”一語表現出的卻是強烈的自尊。同是痛斥薄情郎,霍小玉用“君是丈夫,負心若此”表達對李益的怨情,杜十娘用“恨郎眼內無珠”一語來痛斥李甲的淺薄與無情。同為情人所棄,霍小玉內心深藏著自憐與自卑,而杜十娘爆發出的卻是自尊與決絕。
霍小玉的不獨立和杜十娘的剛強根源于作者為其設定的不同出身。王府的生活和父親的寵愛,仿佛是溫室的大棚,隔斷了霍小玉認識殘酷現實的道路。霍小玉名為娼妓,實則是不諳世事的少女,純潔而多情。她雖然意識到自己一朝踏入歡場再難翻身,與世家子弟李益有著身份上的鴻溝,因此垂淚自憐,但是仍舊對李益抱有幻想,將自己一生的幸福押在李益的良知上。當李益食言負約之后,她仍舊無法自拔,全然不顧慈母在堂需要供養的事實,變賣首飾來打聽李益的消息。
反觀杜十娘,與鴇母斗智,設計贖身,積蓄錢財,這些行動處處體現出一個慣于風月、熟諳人心世事的名妓的成熟。與曾經錦衣玉食的王府小姐霍小玉不同,杜十娘幼年被賣入妓院,開始賣笑生涯,多年的風月生活戕害了她的身心,也使她感知到人情冷暖,賣笑的同時也在考慮為自己安排脫離歡場的道路。在遇到李甲之前,她從不曾向人敞開心扉,遇到有情人后,才一步步設計脫離風月場,渴望過上正常人的生活。
(二)社會思想變遷對霍小玉和杜十娘的形象塑造具有決定作用
霍小玉的天真、純潔和父系高貴的血統,反映了中唐小說作者對于門閥社會愛恨交雜的矛盾態度,而杜十娘的多智、剛強與決絕形象的背后隱約透露出晚明社會崇尚個性的時代特征。
霍小玉母為婢父為王,這種卑微與高貴血統的混合,本身就是門閥社會的產物。然而,在以父系血緣為宗親社會唯一紐帶的唐代,如霍小玉這種身份的女子,從王女降而為娼女的可能性有多大?皇室后代的世系、族譜均有專人掌管,《唐六典》卷十六“宗正寺”條云:“宗正卿之職,掌皇九族、六親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紀親疏之列,并領崇玄署,少卿為之貳”〔10〕。霍小玉為霍王小女,又受其寵愛,霍王沒有理由不將其名納入家譜,和嫡出的子女排在一起。綜觀唐史,沒有皇室宗親之女淪為娼女的任何相關記載。而小說中的小玉,卻在父親死后,由王府千金淪為風塵女子,這樣一種悲劇而又與現實不符的形象恰恰體現了崇尚門第之風對作者的影響,并非“表明了唐代士人對婦女權益的重視”〔11〕。婚配重門第的習俗早已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接受,小說作者自然不能遺世而獨立。作者為霍小玉安上高貴的父系出身,為其天真、美麗、純情的形象籠罩上一層高貴、迷人的色彩,使其超越現實娼妓的層次,也增強了故事的悲劇色彩。作者在潛意識中認同門閥社會的婚配標準的同時,又意識到此種習俗對愛情和人性的戕害,然而卻對此無能為力,處在一種既接受又抗拒的矛盾狀態中。因此,為霍小玉安排了一個高貴的父系血統,卻又讓其在門閥的勢利環境下凋零。
而《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的作者生活于明代晚期〔12〕,商品經濟迅速萌芽發展,金錢成了維系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重要工具,婚配唯門第是從的習俗已經失去了當初的影響力。處于社會底層的杜十娘,擅長在風月場逢場作戲,深知金錢的力量,因此,對進入李甲家庭的前途充滿信心。她相信自己積蓄的金銀財寶能夠打開李甲的家門。在投江前的一刻,她說道:“前出都之際,假托中姊妹相贈,箱中韞藏百寶,不下萬金。將潤色郎君之裝,歸見父母,或憐妾有心,收佐中饋,得終委托,生死無憾”〔9〕330。而李甲拋棄杜十娘的直接原因恰恰也是金錢。一千兩白銀,就使李甲由山盟海誓的情郎變為將情人當作商品出賣的惡徒。在李甲的眼中,金錢顯然比美人和感情更重要!在商品經濟蓬勃發展的初期,娼妓對于金錢的力量深信不疑,可算社會常態,而李甲,作為官宦子弟與讀書人,卻也膺服金錢的魅力,將熱戀自己的情人當作商品出售,這不能不令人思考,在晚明社會的商品經濟大潮中金錢的力量強大到了何等程度,因此,可以說李甲拋棄杜十娘的直接導火索是金錢的誘惑。反觀李益,拋棄霍小玉的直接原因卻是門閥社會的壓力。霍小玉和杜十娘的悲劇人生折射出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在前者生活的時代里,門閥孑遺仍舊左右著人們的生活,成為橫亙在有情人之間的鴻溝;而在后者的時代,金錢卻成為情人之間的羈絆,可以讓讀書人俯首稱臣,置良心與情感不顧,做出卑污可恥的行為。
綜上,從中唐傳奇《李娃傳》《霍小玉傳》到明代擬話本《賣油郎獨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可以看出小說作者從浪漫的想象轉向現實的思考,從著力表現門閥制度對男女結合的阻礙轉向揭露商品經濟初期金錢對于感情的戕害。唐明小說作者通過一系列娼妓形象的塑造,向讀者展示了一條清晰的時代環境發展與社會思想變遷的痕跡,中唐傳奇作者的浪漫主義情愫逐漸讓位于晚明擬話本作者對商品經濟社會的現實主義思考。
〔1〕程遙,千里.唐代傳奇譯注〔M〕.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
〔2〕〔明〕馮夢龍.醒世恒言〔M〕.北京:中華書局,2009.
〔3〕〔五代后晉〕劉煦.舊唐書·杜佑傳:卷一四七〔M〕.北京:中華書局,1975:3983.
〔4〕〔唐〕長孫無忌.唐律疏議〔M〕.劉俊文,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270-271.
〔5〕〔宋〕王讜.唐語林校證〔M〕.周勛初,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44.
〔6〕吳毓鳴.武則天的政治顛覆與唐傳奇的女權伸張〔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7):107.
〔7〕張建業.李贄評傳〔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18-21.
〔8〕趙靖.中國經濟思想通史:第四卷〔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70.
〔9〕〔明〕馮夢龍.警世通言〔M〕.北京:中華書局,2009.
〔10〕〔唐〕李林甫.唐六典〔M〕.陳仲夫,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2:465.
〔11〕李炳海.女權的強化與婦女形象的重塑:唐傳奇女性品格芻議〔J〕.學術交流,1996(3):110-114.
〔12〕程毅中.明代的擬話本小說〔J〕.明清小說研究,2002(2):7.
(責任編輯 黨紅梅)
Evolvement of the Images of Prostitutes in the Novels of Tang and Ming Dynasties
HE Lei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Education,Bengbu College,Bengbu,Anhui 233040,China)
Prostitute images in the vernacular novels of Ming Dynasty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Tang legends.This paper takes Biography of HUO Xiaoyu,Biography of LI Wa and The Businessmen Selling Oil Married a Courtesan,DU Shiniang Angrily Discarded the Box Filled with Treasure into Water as study objects,and points out the evolvement of the prostitute images and the differences of authors'creating concepts.These differences indicate that the romantic feelings of the Tang romance author have given way to the realistic thinking of the commodity economy society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novel;prostitute;evolvement;times
I207.41
A
1672-2345(2012)05-0017-05
2012-03-09
2012-03-14
何蕾,講師,博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