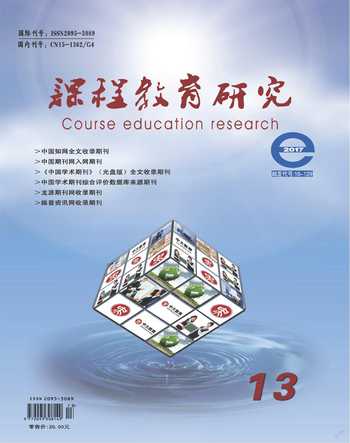中小學(xué)教育信息化發(fā)展現(xiàn)狀及對(duì)策研究
【摘要】教育信息化作為推進(jìn)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質(zhì)量的重要手段,正受到越來越多國(guó)家和地區(qū)的重視。本文通過概述我國(guó)中小學(xué)校教育信息化發(fā)展現(xiàn)狀,分析了發(fā)展教育信息化存在的問題,最后提出相關(guān)建議。
【關(guān)鍵詞】教育信息化 現(xiàn)狀 瓶頸 對(duì)策
【中圖分類號(hào)】G633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2095-3089(2017)13-0044-01
一、我國(guó)中小學(xué)校教育信息化發(fā)展現(xiàn)狀
1.高度重視,營(yíng)造良好的外部環(huán)境。《國(guó)家中長(zhǎng)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提出:“加快教育信息化進(jìn)程”。教育部印發(fā)《教育信息化十年發(fā)展規(guī)劃(2011—2020年)》,為我國(guó)中小學(xué)校教育信息化發(fā)展做出科學(xué)規(guī)劃。各級(jí)政府高度重視,通過加強(qiáng)引導(dǎo)、政策傾斜等措施,努力營(yíng)造外部環(huán)境,為中小學(xué)校教育信息化發(fā)展培育了“沃土”。
2.經(jīng)費(fèi)投入持續(xù)增加,軟硬件條件明顯改善。近年來,隨著各方面投入的逐年增加,我國(guó)中小學(xué)信息化教育進(jìn)入了加速發(fā)展的“快車道”,為推動(dòng)教育教學(xué)改革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主要表現(xiàn)為:一是我國(guó)教育信息基礎(chǔ)設(shè)施體系初步建成,并處于不斷完善中;二是教育信息化專業(yè)人才隊(duì)伍不斷發(fā)展壯大;三是數(shù)字化教育資源不斷豐富,但是教育信息資源缺乏共享性;四是信息技術(shù)與教育教學(xué)不斷融合。
3.開展地方試點(diǎn),不斷摸索前進(jìn)方向。近年來,全國(guó)各地紛紛結(jié)合自身實(shí)際,重視信息化的功能定位,從規(guī)劃建設(shè)、人才培養(yǎng)等方面著手,開展信息化教育試點(diǎn)。通過試點(diǎn)進(jìn)行探索,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浪費(fèi),同時(shí)不斷總結(jié)經(jīng)驗(yàn),相互交流好的做法,教育信息化總體呈現(xiàn)出“欣欣向榮”之勢(shì)。
二、困難與瓶頸
信息化教育是一項(xiàng)系統(tǒng)工程,實(shí)施起來相當(dāng)復(fù)雜,目前還找不到非常成熟成功的區(qū)域樣本供參照。我國(guó)中小學(xué)在推進(jìn)教育信息化過程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難與阻力,與“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展趨勢(shì)和全面實(shí)現(xiàn)教育現(xiàn)代化的要求仍有不小的差距,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五個(gè)方面:一是教育系統(tǒng)上下、家長(zhǎng)和社會(huì)各界對(duì)信息化教育的認(rèn)識(shí)還不夠清晰和統(tǒng)一;二是城鄉(xiāng)教師的信息技術(shù)素養(yǎng)很不均衡,駕馭先進(jìn)信息技術(shù)的能力有待提升;三是信息技術(shù)與課堂教學(xué)的融合還不夠緊密,信息化教育應(yīng)用的廣度和深度不夠,信息技術(shù)與教育教學(xué)“兩張皮”的現(xiàn)象仍舊存在;四是發(fā)展信息化教育的投入機(jī)制還不夠完善,城鄉(xiāng)之間、校際之間的推進(jìn)力度還不夠均衡;五是持續(xù)推進(jìn)信息化教育的創(chuàng)新力度還不夠,考評(píng)激勵(lì)機(jī)制有待進(jìn)一步完善。
三、對(duì)策與建議
要突破制約信息化教育發(fā)展的困難與瓶頸,建議從以下幾個(gè)方面著手,努力建設(shè)“人人皆學(xué)、處處能學(xué)、時(shí)時(shí)可學(xué)”的學(xué)習(xí)型社會(huì)。
1.要進(jìn)一步提高認(rèn)知水平。一是加大宣傳力度。采取多種宣傳形式,介紹教育信息化的相關(guān)內(nèi)容,使社會(huì)各界充分了解教育信息化的優(yōu)越性,揭開其“神秘面紗”。二是用成績(jī)?yōu)樽约骸按浴薄S酶鷮?shí)的舉措加大教育信息化推進(jìn)力度,用更實(shí)在的成效改變師生家長(zhǎng)和社會(huì)各界對(duì)發(fā)展信息化教育的疑慮。
2.要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培訓(xùn)培養(yǎng)。一是建立和完善各級(jí)各類教師教育技術(shù)能力標(biāo)準(zhǔn),持續(xù)開展各級(jí)各類教育信息化專業(yè)人員能力培訓(xùn);二是明確教育信息化專業(yè)人員崗位職責(zé),制定相應(yīng)的評(píng)聘辦法,重視信息技術(shù)專業(yè)人才梯隊(duì)建設(shè);三是優(yōu)化本科生和研究生培養(yǎng)計(jì)劃和課程體系,鼓勵(lì)高校信息化相關(guān)學(xué)科畢業(yè)生到基層單位或?qū)W校從事教育信息化工作。
3.要進(jìn)一步重視應(yīng)用融合。利用信息技術(shù)創(chuàng)新教學(xué),將云計(jì)算、大數(shù)據(jù)、物聯(lián)網(wǎng)等新技術(shù)與教育緊密結(jié)合起來,突破教育難點(diǎn),提升核心素養(yǎng)。同時(shí),建議有關(guān)部門加強(qiáng)教育信息化標(biāo)準(zhǔn)規(guī)范制定和應(yīng)用推廣,確保數(shù)字教育資源、軟硬件資源、教育管理信息資源等各方面內(nèi)容的標(biāo)準(zhǔn)化和規(guī)范化。
4.要進(jìn)一步建立健全經(jīng)費(fèi)投入保障機(jī)制。建議政府部門轉(zhuǎn)變職能,堅(jiān)持創(chuàng)新、協(xié)調(diào)、開放、共享的發(fā)展理念,建立健全經(jīng)費(fèi)投入保障機(jī)制,切實(shí)保障信息化教育的發(fā)展需求。一是“廣開源”,建議按照“政府主導(dǎo)、分級(jí)投入、多方籌措、均衡發(fā)展”的原則,鼓勵(lì)多方參與投入建設(shè),不斷拓寬經(jīng)費(fèi)來源渠道;二是“調(diào)結(jié)構(gòu)”,優(yōu)化經(jīng)費(fèi)支出結(jié)構(gòu),加大對(duì)教育信息化的投入力度,尤其要加強(qiáng)對(duì)農(nóng)村地區(qū)、貧困地區(qū)教育信息化的經(jīng)費(fèi)支持。
5.要進(jìn)一步探索激勵(lì)機(jī)制。建議認(rèn)真總結(jié)教育信息化發(fā)展過程中的經(jīng)驗(yàn)以及教訓(xùn),促進(jìn)教育服務(wù)供給方式、教育教學(xué)和管理模式的變革。同時(shí)研究探索教育信息化相關(guān)從業(yè)人員激勵(lì)機(jī)制。
參考文獻(xiàn):
[1]郭濤,王亮.我國(guó)農(nóng)村中小學(xué)教育信息化現(xiàn)狀和對(duì)策[J].繼續(xù)教育研究,2012,(2):106-108.
[2]焦建利,賈義敏,任改梅.教育信息化宏觀政策與戰(zhàn)略研究[J].遠(yuǎn)程教育雜志,2014,(01):25-32.
[3]張文波.中小學(xué)教育信息化發(fā)展新階段問題的現(xiàn)狀及對(duì)策研究[J].中國(guó)電化教育,2014,(328):39-43.
作者簡(jiǎn)介:
沈榆峰(1987.11-),男,漢族,四川大竹人,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