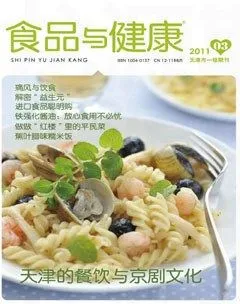天津的餐飲與京劇文化
中餐與京劇同為國粹,亦是姐妹藝術。
我們還是由一個字說起——爨。
“爨”是《新華字典》中筆劃最多的字之一。在漢字造字中的“六書”中,它就占了三法:象形、指事、會意。它的頭上是一個象形的“甑”,甑是用于蒸食的古器,兩邊以“臼持之”。中部的“冖”是個灶口,下部表示“推林納火”,整個字形象地推演了中國發明蒸食文化的過程,所以“爨”的第一種意思便是“炊也”,即做飯。“爨室”即是廚房。老朽是研究食文化的,自號“爨翁”,即為此也。爨還有第二個意思,是戲曲名稱。《輟耕錄》說:“宋徽宗時,爨國人來朝,見其衣裝、巾裹、舉動皆可笑,使優人效之以為戲焉。”后世遂將“爨弄”來指代戲曲。由此可見戲曲與飲食關系密切之一斑。
日本學者奧野信太郎把京劇和烹調稱為中華文化“最大的兩座高峰”,余覺得毫不為過。老朽在為友人題箑時,曾寫到“舞者的(定)格,京劇的(亮)相,津菜的扒,中醫的望(聞問切),妙處全在飛白。白受彩,甘受和,表現了有限中的無限。所以,中國書畫以不畫處為畫,有畫處以息為形,無畫處將息化氣。所以,大畫無形,大樂無聲,大味必淡,不說是真禪。其妙在和也。”
中餐與京劇都是中華文化的優秀代表,也就是年輕一代說的“很有中國味”。什么是味呢?就是隱在中餐與京劇后面的不可見文化的整合。凡是帶有“中國味”的文化門類,諸如中餐、京劇、中國書畫、中醫藥等,經過這種不可見文化的整合制約后,無不例外地被打上了“中國印”,而展現出濃濃的傳統之味,成為中華民族的凝聚力,而得以世代傳承。其中重要的一種文化全息基因碼即為“和”。
《淮南子》記載了“廚祖”易牙“桓公甘易牙之和”的故事。“甘”作動詞,表示欣賞;“和”就是烹調或菜肴的代稱。“和”的本意屬于音樂的范疇,其古體字形是“龢”或“咊”,“龢”字左邊是多管樂器的形象,表示多音階共奏;變體為口字旁,表示一唱一和。您看,烹調的五味調和與京劇的聽戲聽味,都講究和諧,具有同樣的藝術屬性。幽默小品大家林語堂先生斷言,“西餐把菠菜和燒鵝分別做熟,一起放在盤中,是不懂得調和。”中餐與西餐在飲食史上有著粒食、肉食的根本差異,這是古之生產方式決定的,使中西餐飲與戲曲背后的文化哲學支持大相徑庭。
道明了中餐與京劇的文化血緣之后,再談天津這方生長繁育中餐與京劇文化的熱土。
高成鳶先生考察發現,京劇與中餐這兩座高峰竟然是同時崛起的。京劇的形成,公認以徽班進京為標志(1790年),而中國烹飪的成熟,飲食文化研究界公認以大美食家袁枚的《隨園食單》的問世為標志(1792年)。差不多成熟于同一時期。
天津在中國是一個晚近發展起來的城市,如果從元代的直沽寨算起至多也不過六百多年的歷史。但是天津的文化發展,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歷史因素,這便是余在多篇文章中提到的“四個九”機緣,即“九河下稍、九五之門、九方雜居、九國租界”。
“津菜”進入社會,為較大消費階層所接受,并初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文化體系,應該是清代中葉以后的事情。道光詩人崔旭的詩句,“翠釜鳴姜海味稠,咄嗟可辦列珍饈。烹調最說天津好,邀客且登通慶樓。”把當時天津的高級餐飲業的地位說得很是清楚。
當時的天津有不少巨賈,特別是鹽商有錢沒處花,便附庸風雅,蓋起上好的園林,一來接駕,哄得皇帝老兒高興,討些好處。二來可以招引大批文人墨客來就食,以示雅好。這些人不用掏腰包,便可白吃白住,焉有不樂之理?以至“江東才子,投屐爭來,鄴下詞人,停車不去。”鐵嘴銅牙的紀曉嵐評曰:“文人往來于斯,不過尋園林之樂,作歌舞之歡,以詩酒為佳興云耳。”然而,正是有了文人的介入,天津餐飲才不僅服務于達官貴人和巨商富賈,“以飫老饕”的雞鴨魚肉。二是開始上了書本,上升為文化,上了更高層次,以至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借鑒了不少的天津餐飲文化素材。
清末民初,專門為帝后服務的宮廷廚師和戲劇演員流落到民間。天津毗鄰京都,又有九國租界,是外國資本的灘頭,失意的軍閥政客腰纏竊國萬金紛紛來做寓公。他們無所事事,天天酒食征逐。僅末代皇帝在津開支每月就在銀元萬元以上。失去宮廷依托的高級廚師和演員紛紛被市場所接納,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激烈的商業競爭,促進了烹飪和戲劇在京津兩地的迅速發展。
天津與“首善之區”的北京相比,比北京更開明而“摩登”。“吃盡穿絕天津衛”,使得王公貴族以及后來的軍閥政客,沒有了僭越的顧慮,食遍中西華洋。出了菜館進戲院,成為幾代人最時尚的生活方式。
余幼年生活在天津的南市榮業大街,在上個世紀的三四十年代,是個飯館與戲院扎堆的地方。記得當年居所附近的飯館有:天一坊、十錦齋、天源樓、天和樓、五芳齋、同福樓、松竹樓、晉春樓、泰豐樓、義和成新記、聚合成、蓬萊春祥記、聚慶成、登瀛樓飯莊、燕春樓羊肉館、燕坊樓、恩華元飯莊、會賓樓、永元德羊肉館、增興德等。戲院有慶云、群英、升平、聚華、大舞臺等。那時家里來了客人,一般是打電話叫飯莊送飯,不用多大功夫,飯莊伙計便提著提盒送到,上桌時飯菜還是熱的。飯后,就可以就近定個包廂請客人聽戲。余是個戲迷,特別愛聽戲,每到下午四點左右,戲園子便“門戶開放”,于是,幾乎每天都可以騎在家人的脖子上,站在后排,白看“戳腿戲”。餐飲業和戲院的繁榮,使天津成為上個世紀二十到四十年代的京劇和烹飪中心。
烹飪與京劇融入天津市民的生活成為了一道特殊的社會風景。京劇唱的地道與否,那叫“味”,是要借助飲食語言來表達。俗語說,“馬連良的腔,山東館的湯”,形容都是精品。還有人拿京劇的“唱念做打”跟菜肴的“色香味形”相提并論。四十年代時,著名老旦李多奎的《釣金龜》唱段,轟動了京津滬沈,一時街頭巷尾,時常有人學唱。當時的聽眾把其中“叫張義”等三段唱譽為“紅三段”,意思是唱完之后必有叫好聲。同業又把這三段唱稱作“三做鯉魚”。這京劇名段怎么又和美食聯系起來了呢?原來,“鯉魚三吃”是名魯菜,天津又有不少魯菜館,所以得名。一段“叫張義我的兒聽娘教訓”稱為“紅燒魚頭”,“有幾個賢孝子聽娘來論”稱為“醬汁中段”,“這幾輩賢孝子休得來論”稱為“清燉魚尾”。好吃又叫座,可見藝術相通矣。
天津是京劇名角和京劇嗜愛者們集中的大都市。她地處南北通衢要沖,凡是由北京到各地入京演出的演員,都愿意先到天津演出,意為經過天津觀眾的認可,再到各地演出才有把握。一是因為天津觀眾懂戲,擅于細致鑒別優劣。二是天津的票房林立,很多的票友文化水平和藝術造詣都很高。“老鄉親”孫菊仙、李宗義都是天津籍票友下海。李東園先生有全套戲箱戲服,經常“傍”金少山、侯喜瑞、荀慧生等名角演出。戲迷群的出現給天津營造了一個良好的藝術氛圍。
1935年渤海大樓建成,1936年中國大戲院建成,遂使勸業場地區成為天津乃至華北最繁華的商業區。中國大戲院是當時華北地區規模最大、設備最新的戲院,開業時許多名角來這里連臺演出,場場客滿,盛況空前。由于這樣的戲曲氛圍,幾乎所有著名的京劇演員,如梅、程、尚、荀四大名旦,楊、譚、馬、奚四大名生,以及楊小樓、郝壽辰、高慶奎、李少春、李萬春、葉盛章等,在排出新編劇目以后,多愿意先到天津演出,以博取天津觀眾的鑒賞和認定。
這些名角到了天津,自然離不開天津的美食,因為這些藝術家出于職業修養、養生需要,大都鐘情于美食。
梅蘭芳先生到天津演出喜歡吃蘇閩菜館的“周家魚”。荀慧生先生愛吃名廚周大文的“核桃饹”。馬連良先生在天津有“疙瘩樓”,喜吃南市永元德的涮羊肉。譚富英先生喜吃黃家花園“又一村”的“扒肘子”。奚嘯伯先生到天津演出,余看的次數最多,他喜歡吃東馬路“中立園”的“蝦仁 面筋”。楊寶森先生好的一口,是天增里飯館的“吃白斬雞,就白蘭地下酒”。他們戲臺上是角兒,臺下是美食家,場合不同,“多味齋”里演繹多味人生矣。
在天津餐飲史上,曾經有多位精通百藝的大廚。周大文是其中之一。周曾任過要職,卸職后開餐館并下海主廚。天津玉華臺飯莊是經營淮揚菜的老字號,其名稱便是由創始人馬玉林的“玉”字和周華章(大文)的“華”字而得名。他酷愛烹調藝術,虛心向老前輩請教,逐步自成一家,成為與穆祥珍、陳士和齊名的津門三大廚。他的廚藝吸引了許多當時的名人前來品嘗,如郭沫若、荀慧生等,就連各國駐華使節也常來光顧。周大文不但精通廚藝,還酷愛京劇,常常粉墨登場“傍”名角演戲。有記載的就有和南鐵生、樂元可、高聯慶,還有小說家張恨水等同臺演出過。
還要特別提出的是余之師友耿福林先生,耿老是中國烹飪大師,長期在利順德主廚,廚藝高超,多次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做餐飲服務。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許多劇團的團長入住利順德,耿老得以結交了不少名角“大腕”,如馬連良、譚富英、裘盛戎、趙燕俠、張君秋、厲慧良、鮮靈霞(評劇)、銀達子(河北梆子)等,他(她)們對耿老的廚藝交口稱贊,結下了京劇與烹調藝術之緣。
京劇與烹調藝術的互通,還產生了不少“京劇菜”,比如,京劇有《貴妃醉酒》,上海有以紅葡萄酒烹制的“貴妃雞”。天津有以10只鵪鶉為料烹制的“十老安劉”、以肥腸和青椒為料烹制的“乾坤圈”、以元魚和雞為料烹制的“霸王別姬”、以雞胸肉和口蘑、冬筍、青豆為料烹制的“打金枝”、以牛舌和鴨舌為料烹制的“舌戰群儒”、以雞胸肉、蝦仁、海參為料烹制的“古城會”、以大王魚、小筍雞為料烹制的“龍鳳呈祥”,美食后面有故事,好吃又有文化品味。
余自幼既好美食又愛聽戲,后來因研究食文化又結識了不少烹飪界與戲劇界的朋友,但自認為還是此兩圈外的“棒槌”。好在,學習京劇京胡的小孫女拜在了名師門下,而且近日登上了中央電視臺演出,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圓了老朽的追尋藝術之夢,幸矣!
中國的京劇已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養育了中華民族的中餐文化經過新飲食觀念的整合,也必將發揚光大。
(下期預告:中國食文化四大貢獻之一——大豆及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