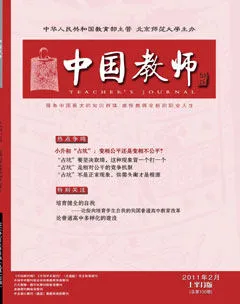課程的本體論價值和工具論價值之關系研究
近年來,關于學生“高分低能”“思維發展受阻”等方面的報道不斷見諸媒體,引發了學術界關于關注課程本體論價值的呼聲日益高漲。這種轉變對改變以往工具論價值一統天下的局面無疑有著重要意義。但這類主張更多的是一些口號式的觀點,并未闡述如何在把握課程的本體論價值和工具論價值之間找到一個恰當的平衡點,也沒有考慮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新課改以來,受所謂“新課程理念”的影響,學者和一線教師對課程“本體論價值”的關注已經遠遠超過了對“工具論價值”的關注,他們認為,課程應該注重的是培養學生的道德品質,融入生命教育理念,促進學生的心理健康發展,并發展學生的創造性思維,等等,這些內容屬于“本體論價值”的范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以實用性為主的“工具論價值”,例如掌握各種知識和技能,則應居于次要地位,甚至不在課程的關注范圍之內。這類主張中體現出兩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一是本體論價值和工具論價值的實現被認為是兩個相互獨立和封閉的不同領域,二是本體論價值重于工具論價值,需要“優先發展”。對這兩種不同于以往教學觀念的傾向,我們需要認真進行分析。
一、本體論價值與工具論價值是否相互獨立?
關于課程的本體論價值和工具論價值之間的關系,可以追溯到“形式教育”和“實質教育”之爭。在夸美紐斯以后,由于啟蒙思想開始傳播,自然主義教育思想就開始形成潮流,自然主義教育思想有兩大特點:一是主張教授實用學科,二是認為感覺是一切認識的來源,這是“實質教育”的主張。但是由于自然主義理論本身的固有缺陷,它無法回答“如何通過感覺經驗實現認識的完成”這一問題,因此“形式”依然具有生命力,而教育就需要對這些“形式”的東西進行加工,促進悟性能力、思維能力、理解能力的發展,而非積累實用性的學科知識,這是“形式教育”的主張。教育思想發展到赫爾巴特之后,開始出現試圖將形式教育和實質教育相融合的嘗試。赫爾巴特一方面擁護古典主義學校及其課程,因而被列入形式教育派[1];另一方面又反對官能心理學,主張重視課程和教材,分科教育由他開始確立并逐漸成為主流,這又體現了實質教育論的思想。在赫爾巴特之后,蘇聯教育學,杜威、克伯屈等人的新教育運動試圖克服形式教育論和實質教育論各自的片面性,但都未能在實質上取得突破,尤其是杜威對分科教學的批判雖然深刻,但可操作性不強,因而分科教學在各個國家一直被普遍接受并廣泛運用至今。
當前我國仍然采用的是分科教育的體系。由于分科教學沿襲的是“實質教育論”的路子,因而任何一個學科的存在,其初衷都在于追求該學科的“實質性”價值,即學科知識的傳授和積累。因此離開工具性而談本體論,本身就不符合分科教學的最基本理念。
例如,學生的思維發展固然重要,但“思維教學與內容教學能否統一”這一疑問之所以出現[2],前提就在于學生的思維和“工具性的東西”——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教學內容是對立的。有學者借用杜威的觀點,在對現有教學進行批判的時候,將問題根源歸結于傳統教學“混淆了思維過程的邏輯和思維結果的邏輯”[2],并由此推斷傳統教學成為學生思維的屠宰場。但這一批判忽視了杜威對思維過程和思維結果之間必然關系的認識:“實在令人吃驚,兩個對立的教育派別都忽視了思維的實際過程和思維的結果之間的內在的、必然的聯系”[3]。杜威所說的思維結果,其實就是指的教學內容,即“工具論價值”所追求的、實用性的知識和技能,而“真正的思維必然以認識到新的價值而告終”[3]。因此,在杜威看來,所謂發展思維,說到底,最核心的意義在于認識到新的價值,即我們今天所說的知識的豐富、觀念的完善,等等,這些當然都屬于工具論價值的范疇。拋棄“工具性”的東西而空談思維,思維將陷入“無思維對象”的境地。
又例如,道德品質當然也很重要,但道德品質能不依賴于知識、技能、本事、文化意識等“工具的”“實用的”東西就能養成嗎?赫爾巴特早就回答了這個問題。他把道德看得無比重要,認為,“教育的目的是道德”[4],但他并不因為道德的重要而撇開教學的工具論價值而孤立地談道德的養成。恰恰相反,他說:“不存在‘無教學的教育’這個概念,正如反過來,我不承認有任何‘無教育的教學’一樣”[4];“最初的智力活動安排得越少,對德行的培養也就越少,特別是考慮不到德行培養可能具有的多樣性。愚蠢的人是不可能有德行的”[4]。可見,所謂道德養成的“本體論意義”,必須建立在智力活動、認知獲取等“工具論意義”的基礎之上。沒有“工具論價值”,道德這一“本體論價值”也就失去了根基。
二、本體論價值與工具論價值孰輕孰重?
當前部分專家學者和一線教師對本體論價值反復強調和對“工具理性”的批判,容易讓人以為本體論價值是更“高”的、更“重要”的課程價值,因而淡化甚至否定課程的工具論價值。有不少學者提出,教學論要由認識論向價值論轉向,因此,以認識形成或者技能獲取為目的的“工具論價值”應讓位于美德形成、興趣培養、課堂愉悅感養成等“本體論價值”。但是,這種說法是很有疑問的。打個比方,如果我們說,“熱愛教學的品質及教學過程帶來的愉悅感是教師教學過程中高于其教學質量的更重要的價值”,因而主張教學的質量指標從對學生綜合水平的考量轉移到對教師教學過程的愉悅感的測查方面。大家會覺得這是在說笑話,因為這種觀點將降低教師工作的質量,導致學生的學習質量下滑。那么,將本體論價值凌駕于工具論價值之上,又會是什么局面?試想,如果數學教師將大部分的時間用于培養學生的道德素質和生活觀念,而非培養計算、證明等技能,我們不禁要問,這堂課還叫數學課么?如果英語教師將主要精力用于促進學生的心理健康發展,而非著眼于聽、說、讀、寫等語言能力,我們不禁要問,這堂課還叫英語課么?如果地理教師將課堂重心放在發展學生的創造性思維、邏輯思維、抽象思維,而非地理知識與分析能力,我們不禁要問,這堂課還叫地理課么?……上述課程更像是人生觀課程、思維拓展課程,但無論如何不能再叫學科課程了。學科本身的特點被所謂的“本體論價值”給消解掉了。固然,工人勞動的愉悅感很重要,但工人勞動的最重要目的是工具論性質的——建筑物本身的質量;學生的思維能力也很重要,但如果將其重要性放在學科特色本身之上,那學科課程本身區別于各種思維拓展訓練課之處又在何處?
三、如何正確把握本體論價值和工具論價值的關系?
將課程本體論價值和工具論價值相割裂的觀點,其實是認為課程可以獨立地追求本體論價值和工具論價值,二者互不干擾,以至于現有研究中出現了種種脫離課程最基礎的內容而追求道德品質、情感體驗、思維發展、生命理念等價值的觀念。這類主張將情感、思維作為教學內容,學科知識作為副產品而不是直接的教學內容,這就顛倒了教學內容和價值的順序,造成教師像講解知識要點一樣“把情感、態度、價值觀直接‘教’給學生”的局面[5],不但達不到教育目的,也非新課程改革的初衷所在。有學者指出:“‘情感’是知識的自然衍生物……在教學中,它只能并且應該作為知識學習的副產品,如果把‘情感’也作為教學直接追求的一個目標,造成的結果就只能是‘強扭的瓜不甜’”[6]。這種觀點才是對教學的工具論價值和本體論價值關系的準確把握,對課程本體論價值的發掘,決不能拋棄工具論價值單獨得以實現。
認為課程的本體論價值的意義重于工具論意義的觀念,和當前教育界對“知識”的批判一脈相承。有學者認為,目前我國教育陷入了機械主義和工具理性的禁錮之中,教學的目的僅在于讓學生獲得所謂的正確知識,只要學生獲取了知識,就自然而然地能夠應用知識;傳授知識作為教學的中心工作,就能最大限度地實現教學的工具論價值;這樣的教學當中缺少人文關懷,過程變得僵化,失去了生命力。要改變教學當中的這些問題,必須對教學中的“知識至上”觀念進行徹底批判,將本體論價值作為教學的最重要價值追求。但是,如果教學不重視知識,那么我們教學到底教的是什么?例如:數學課堂的教學內容只能是計算、證明、推理等數學知識和技能;英語課堂的教學內容只能是單詞、語法、段篇章等知識,聽、說、讀、寫等技能,以及某些英語國家的文化和風俗;地理課堂的教學內容只能是地理知識和利用地理知識分析地理問題的能力,但這些東西都是“工具論”價值層面的,“實用”的內容,即便有時候涉及道德、思維方式、心理品質等內容,也是作為工具論價值的載體形式而存在的,很難想象,當情感、思維、德行成為課程直接的追求對象的時候,學科課程還具有學科特色嗎?離開了工具性的東西,教學內容還能是什么呢?
當前的教學之所以被批判為知識中心主義,到底是知識本身的錯,還是教學環節出了問題?有學者提出,造成學生被壓抑、被規訓的其實不是通常意義上講的知識,而是被考試的壓力“異化”了的知識,知識本身是人類經驗的提煉和結晶,是有積極意義的,但當知識被異化為考試的工具,只對學生的考試負責的時候,知識便不再有益于學生的發展,反而成為限制學生的外在力量[6]。這位學者指出了當前教學問題的根本所在——思維、德行、品質,種種對學生有益的東西,都“讓位于”考試的需要。因此,課程的工具論意義被放大、強化到不可思議的地步,本體論價值則不被提及。因而,提倡重視課程的本體論價值,避免工具論價值機械化,這些觀點對教學工作的改進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如果認為本體論價值可以獨立于工具論價值之外,或者將本體論價值置于工具論價值之上,就顯得矯枉過正,將教學領向另一個極端,同樣不利于教學活動的開展。
參考文獻:
[1]岡察洛夫.教育學原理(初譯稿)[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173-174.
[2]呂星宇.有效對話:為思維而教[J].教育學報,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