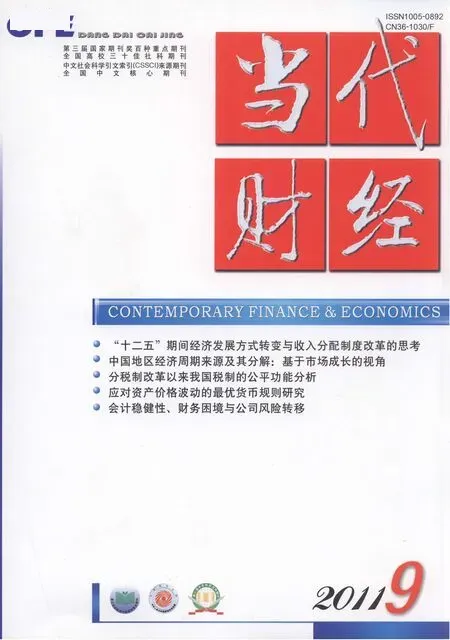環境規制競爭對經濟增長效率的影響:基于省級面板數據分析
王文普
(1.山東大學 經濟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2.南通大學 商學院,江蘇 南通 226019)
一、引言
經濟市場化改革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但大規模和快速的工業化與城市化使污染和環境破壞加劇,資源環境約束矛盾更為突出,環境與經濟的不協調問題更為嚴重。盡管我國的污染排放強度有所降低,但從絕對數來看,污染物排放量仍處于高位運行。環境污染不僅損害人們的健康,影響資源的使用效率,甚至影響到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近年來,對于我國污染排放量居高不下的形成機理的研究上,主要以轉軌過程中體制缺陷所引起的環境規制競爭行為扭曲來解釋。這類研究關注到我國分權改革的負激勵。中國經濟的成功轉型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經濟領域的分權改革。[1]一些學者認為,分權改革為地方政府圍繞經濟增長展開競爭提供了動力,因為地方經濟增長直接關系到本地的財政收入與就業,也影響到官員的業績評定。[2]在環境保護方面,有些學者則提出,經濟分權改革扭曲了地方政府的環境規制行為,省際間競相降低環境標準的競爭是引起我國環境污染水平處于高位的一個重要原因。特別在經濟相對落后地區,為了爭奪外部資源,地方政府有可能會降低環境標準、容忍污染企業以作為“招商引資”的一個重要手段。對于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業來說,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業的遵規成本,實質上將企業的遵規成本外部化。高污染行業生產中的環境污染成本被嚴重外部化,導致了這些行業過度的產能投資,進一步加劇環境污染。這種競相實施較松環境規制的現象,就是所謂扭曲的環境規制競爭行為或環境規制競爭。①
從現有的經驗研究來看,有關直接檢驗環境規制競爭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不多。少數經驗研究的結果也是模糊的。Potoski(2001)比較了美國“清潔空氣法”頒布前后空氣污染狀況,結果發現,各州間沒有出現明顯的環境規制競爭現象,甚至有些州制定的環境標準高于國家標準。[3]與Postoski(2001)的相反,國內的一些學者研究發現了環境規制競爭的證據。楊海生等(2008)利用空間計量模型檢驗了我國省際間環境規制競爭,結果顯示,各省之間為了爭奪流動性要素和強化本轄區資源而展開了相互攀比式的環境規制競爭:鄰近省區加強環境監管,本轄區也實施比較嚴格的環境監管;周邊省區環境規制減弱,本轄區環境監管也較弱。[4]崔亞飛和劉小川(2010)從稅收競爭的角度檢驗了省際稅收競爭與環境污染的關系。他們發現,地方政府為了維護已有的稅收收入和擴寬稅基,爭取經濟考核和政治競爭優勢,對那些產值大、利稅高、污染排放大的工業企業的二氧化硫排放采取了松的環境監管與防治策略。[5]
環境規制競爭的關鍵在于靜態地看待環境規制與經濟增長關系,認為環境規制不可避免地給企業帶來額外負擔,從而損害了經濟增長效率。本文關注的是環境規制競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性質與方向,試圖通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來檢驗以下幾個問題:首先,環境規制競爭會不會妨礙經濟增長效率;如果有,這種影響有多大?其次,這種影響是否是由環境規制競爭引起的。最后,運用數據包絡方法將全要素生產率分解為前沿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估計環境規制競爭對全要素生產率及其構成的具體影響。
二、環境規制競爭與勞動生產率的省際比較
生產率是反映經濟增長效率的一個常用指標。為了直觀地描述省際間環境競爭對經濟增長效率的影響,我們比較中國31個省的勞動生產率變化。我們使用每工人產出(GDP/W)來近似地測度省級水平的勞動生產率。圖1描繪了1992年和2008年各省的勞動生產率相對于全國勞動生產率②的比值。從圖1可以看出,1992年31個省份中有13個省的勞動生產率高于全國勞動生產率,其中,東部所占比例近77%。到2008年有17個省的勞動生產率高于全國勞動生產率,比1992年提高了近31個百分點,其中,東部各省的勞動生產率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而低于全國平均勞動生產率的省份都在中西部地區。從縱向比較來看,1992-2008年間,勞動生產率增長最快的省份是上海,其次是江蘇。在考察期內,25個省份的勞動生產率均出現上升,北京、海南、貴州、寧夏、新疆和云南有所下降。

圖1 省級GDP/W(全國=1)
為了比較省際間的環境規制競爭,需要測度環境規制強度。文獻中常見的衡量方法有兩種:投入型和產出型。前者與環保努力有關,如環境R&D支出、污染減排與控制支出等,后者反映環境規制的結果。Quiroga等(2007)認為產出型環境規制強度指標優于投入型指標,因為產出型指標不僅考慮了環境規制的嚴厲程度,也考慮了環境規制的執行、各種補貼或抵消某些嚴厲規制效應的環境政策。[6]所以,我們選取單位產出污染物排放量(SO2和工業COD)來表示環境規制強度。這隱含地假設單位排放量越小,則表明環境規制越嚴厲。選擇SO2和工業COD這兩種污染物,主要是基于以下考慮:酸雨是我國的一個重要的環境問題,而SO2是形成酸雨一個主要污染物;隨著我國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水的使用量不斷上升,水污染也是一個重要的環境問題;它們也是我國環境污染控制中最重要的兩個指標,并且有比較完整的統計數據。所以,選取單位產出SO2和工業COD排放量可能會比較好地反映各省的環境規制強度,也可以較好地反映各省之間的環境規制競爭狀況。
圖2和圖3表明了單位產出的SO2和工業COD的排放量。圖2顯示,總體上看,1992-2008年間,單位產出SO2排放量出現下降的有12個省市,其中東部有北京、江蘇、遼寧、山東和天津5個省市,占41.7%;中部有安徽、黑龍江、吉林和山西4省,占33.3%;西部有內蒙古、四川和陜西,占25%。橫向比較看,1990年中有13個省的SO2/GDP高于全國水平,其中東部占15.4%,中部占30.8%,西部占53.8%。到2008年仍有13個省的SO2/GDP高于全國水平,并均出現在中西部地區,其中,中部占15.4%,比1992年下降了近15個百分點;西部占84.6%,比1992年增加了近51個百分點。這表明東部各省和中部部分省的SO2排放強度均出現了下降,而西部的SO2排放強度出現明顯的上升。這也似乎表明,東中部的環境規制強度有明顯的提高,特別是東部各省。

圖2 各省SO2/GDP(全國=1)
由圖3可知,1990年單位產出的工業COD排放超過全國水平的地區有14個,其中東部占21.4%,西部占21.4%,中部占57.2%。到2008年工業COD排放強度超過全國水平的地區有12個,均出現在中西部,其中西部占66.7%,比1992年提高了45.3%;中部占33.3%,比1992年減少了23.9%。1992-2008年間,有22個地區的工業COD/GDP出現了下降,其中西部僅為云南、貴州和西藏等3個省區,東中部各省的工業COD排放強度均出現下降。這說明,東中部各省對工業COD的規制強度有明顯的加強,而西部大部分省區對工業COD的規制強度出現明顯的下降。

圖3 各省COD/GDP(全國=11)
總之,考察期內,SO2排放強度和工業COD排放強度從東部到中部再到西部呈階梯式遞減趨勢,這意味著東中部各省的環境規制強度在逐漸增強,而西部各省的環境規制強度有不斷下降的態勢。這些似乎都說明環境規制競爭不僅表現在省際間,而且也呈現出在區域間的特征。
圖4描繪了1992-2008年的單位污染排放強度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散點圖和簡單擬合關系。縱軸為勞動生產率的對數,橫軸分別表示單位產出SO2和工業COD排放量的對數,實線表示單位產出排放強度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擬合關系。從散點圖和擬合關系看,單位污染物的排放強度與勞動生產率之間存在負向關系,表明較高的污染排放強度,則有較低的勞動生產率。這也意味著環境規制競爭并不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即環境規制競爭并不一定會改善經濟增長效率。

圖4 單位污染排放強度與勞動生產率的擬合關系
三、經濟增長效率的測度與分析
生產率分析是研究經濟增長效率的一個重要手段。上述使用勞動生產率來近似表示各省的生產率水平,以初步分析省際間環境競爭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然而,勞動生產率指標比較單一,不能全面地度量各省的經濟增長狀況。目前對生產率的研究已經由對勞動生產率、資本生產率等的單純測算發展到對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測算。全要素生產率更能從整體上反映一個經濟體的生產率狀況,尤其對TFP增長率的分解能更好地度量要素效率的改善和技術進步程度。[7]我們將使用數據包絡方法來測算各省的全要素生產率并對其進行分解。
1.生產率的測算方法
由于中國各省的生產率差異明顯,不宜設定同一的生產函數形式,運用非參數的數據包絡分析法來測算Malmquist指標比較合適。Malmquist指數不僅反映生產率的變化,而且反映生產率變化的原因,因為生產率變化被分解為兩部分:追趕效應(效率變化)和最佳實踐前沿面的移動(技術變化)。本文運用Fare等(1994)[8]建議的規模報酬不變的產出型Malmquist指數來測算省級水平的全要素生產率(TFP)。




Malmquist生產率指數是估計兩個時期的一個“決策單位”的生產率變化,屬比較靜態分析;與其他計量方面相比,該方法不需要事先設定具體生產函數形式和行為目標。
2.生產率的測算結果分析
在計算各省的Malmquist指數時,我們選取各省GDP作為產出,各省年中就業人員和固定資產存量作為投入變量。資本存量的計算是一個復雜的過程。目前,常用的資本存量度量方法是永續盤存法和資本租賃價格法。近年來,一些學者對中國各省的資本存量進行了測算,然而測算結果不盡相同,無法獲得公認的結果。結合已有數據,我們用全社會固定資產形成額表示當年的投資變量,使用永續盤存法計算各地的資本存量Kit=Iit+(1-δ)Kit-1,其中Iit為當年的固定資產投資,δ為固定資產折舊率,取δ=5%。初始資本存量的計算采用穩態法。參照Hulten和Isaksson(2007)[11]的做法,假設各省經濟處于穩態時的資本產出比。穩態時的資本產出比k=i(g+δ),其中k=K/Y為資本產出比,i=I/Y為投資產出比,g為穩態GDP(真實值)增長。這里選取考察期內的投資產出比和GDP增長率的年平均值作為穩態值,從而計算出各省的初始資本產出比,然后計算作為各省的初始資本存量(1992年)。各省GDP和固定資產投資按1995年價格計算。固定資產投資使用各省的固定資產價格指數進行平減。
近年來,因教育程度的提高、工資和社保成本增加,產業部門對非熟練勞動力需求下降、對技術工人需求上升。這些變化預示著非熟練勞動力在經濟中的重要性下降,人力資本的重要性上升。[12]為了考慮這種影響和作為比較,我們再將人力資本作為另一種投入,重新計算Malmquist生產率。人力資本的計算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替代。這是用“教育成就”作為衡量人力資本水平的指標。[13]令popil、poppr、popju、popse和popcol分別表示文盲半文盲、小學、初中、高中、大專及以上受教育人數占總人數的比重,則平均受教育年限③為

計算結果顯示,1992年各地平均受教育年限為5.23年,標準離差為0.96;2008年平均為7.07年,標準離差為1.001。1992-2008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長率為1.95%。
表1報告了不含人力資本和包含人力資本的各省Malmquist生產率及其分解的年平均值。表1顯示,引入人力資本因素后,效率變化受到的影響甚微,而技術變化所受的影響比較大。31個省區中有19個Malmquist生產率值有所下降,有12個省區的Malmquist生產率值有所增加。Malmquist指數值下降主要是由于人力資本因素降低了技術變化值。盡管人力資本也有助于改善效率,但這種影響并不明顯,例如廣東,引入人力資本變量后,效率值略有增加(從1.043升至1.044),技術變化值由1.125下降到1.062。Malmquist指數值上升得益于人力資本促進了技術進步,例如,在包含人力資本因素時,遼寧的效率值沒有變化,而技術變化從1.212升至1.223,提高了近1個百分點。
這里,我們以包含人力資本因素Malmquist生產率為例進行詳細說明。從效率變化平均值來看,共有17個省區效率變化大于1,其中,東部有6個、占35.3%,中部有7個、占41.2%,西部有4個、占23.5%;效率值最高為江蘇、吉林和江西,但多數省份的效率變化值較小,說明效率高的省與效率低的省之間的效率差距逐漸縮小。從技術變化值來看,技術變化平均值均大于1,表明在考察期內各省的技術進步有所提升;然而,技術變化值在省際間有較大的變化,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省際間的技術進步存在較大的差距。表1中最后一行表明,1992-2008年間,Malmquist生產率年均增長了18.1%,技術進步提高了15.4%,而效率改進增加了2.4%。
對TFP增長進行分解后,可以清楚地看出,31個省區中,技術變化高于效率變化的省區有26個,占比為83.9%。也就是說,各省的生產率增長的大部分是通過技術進步(由最佳實踐決策單元組成的生產前沿面的移動),而不是通過效率改善,表明各省生產率的提高主要來自于技術進步。下面的計量分析將使用包含人力資本因素的TFP測算結果。
四、環境規制競爭對經濟增長效率影響的經驗估計
1.模型設定
要估計環境規制競爭對生產率的影響,參照Barla和Perelman(2005)[14]的分析框架,將模型設定為:

其中,PIit表示第i省在t年的Malmquist生產率增長率(TFP)、效率變化率(EC)和技術變化率(TC),lnSO2和lnCOD分別表示單位產出SO2或工業COD排放量的對數,以反映環境規制競爭對生產率的影響,取滯后1期是避免污染物排放強度與誤差項的同期相關性。時間效應(ηt)用年度虛擬變量來表示,以捕捉共同的技術效應,μi表示各省的固定效應,eit為隨機誤差項。
控制變量Xit。根據生產率研究文獻,技術效率是影響生產率的主要因素,取滯后一期的技術效率水平來捕捉技術追趕過程的動態效應,以反映技術模仿和技術擴散是生產率增長的一個重要源泉。由于前一期技術效率值較低的省區可能從技術效率值較高的省獲益,因而預期其對生產率和效率有負向影響。
R&D活動是影響生產率的另一個潛在來源。在考察期各省的R&D支出數據存在較多的缺失,我們選取科技經費內部支出占當期GDP的比重(ST/GDP)it來表示R&D活動對生產率的影響。R&D支出不僅能夠產生新的知識和信息,也能增強企業的吸收能力,進而促進知識和技術的擴散。因而預期R&D支出將有助于改善生產率,然而當期的R&D支出最初可能會對生產率有抑制作用。
外資活動是中國經濟增長效率的又一個可能途徑。中國是目前世界上最主要的FDI接受國之一。一些研究發現,外資企業的生產率高于國內企業,進而對國內企業提高生產率產生了示范效應。[12]外
資活動影響生產率主要通過兩種途徑:一個是外資通過技術溢出效應而提高生產率,另一個是外資的大量流入可能會削弱內資企業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有些學者認為,在中國,外資企業對內資部門的溢出效應主要體現在人員流動上,用外資部門就業人員數占就業人員比例來反映外資活動的影響。[15]我們選取各省的實際利用外投資占當期GDP的比重(FDI/GDP)it來捕獲外資活動的影響。

表1 平均Malmquist生產率及其分解
新技術總是體現在購置的新設備中,新增投資也可能提高生產率。我們用投資占資本存量之比[Δ(I/K)it]的變化來捕捉這種效應。然而,投資也可能對新的環境規制做出反應,這個變量還可以捕捉到環境規制之外的某些效應。
工業增長不僅是各省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發動機,而且工業也傾向于污染密集型。[16]為了反映工業結構的作用,使用工業增加值占當期GDP的比重(Ind)來表示。Inpop表示人口密度的對數,人口密度為各省年中人口數除以其土地面積,以控制規模效應。
本分析所使用的環境數據來自《中國環境年鑒》,其余來自《新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科技統計年鑒》。數據的真實值以1995年價格計算。表2報告了主要變量描述統計量。

表2 主要變量的描述統計量
2.結果分析
我們估計的樣本區間為1992-2008年中國31個省級的面板數據。估計面板數據時,首先需要確定使用的估計方法。使用Hausman設定檢驗來確定使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其次,Malmquist生產率指數是跨期指數,上期的生產率變化影響當期的生產率變化,這將可能產生跨期跨截面的序列相關問題。動態模型通過包含滯后的因變量以消除序列相關。如果因變量和自變量都是一階非平穩的,那么,靜態回歸可以解釋為因變量和自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根據這種解釋,如果模型是對數據產生過程的正確表述,那么殘差應是平穩的。因而,殘差平穩性檢驗也是一個重要的模型設定檢驗。我們使用Maddala和Wu(1999)[17]建議的Fisher面板單位檢驗以檢驗殘差的平穩性,進而確定我們所使用的回歸模型設定是否合適。最后,截面依存性檢驗。面板數據很可能表現出顯著的截面依存性,這種依存性可能產生于共同沖擊、不可觀測的因素(這些因素最終為誤差項的組成部分)、以及空間依存性等因素。如果誤差項在截面間存在相關,那么將使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模型的推斷功效大大降低。因而,對回歸殘差進行Pesaran的CD檢驗。最后,作為比較目的和驗證初步分析,我們也估計了環境規制競爭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
表3報告了包含人力資本的生產率及其分解的估計結果和有關檢驗。在勞動生產率的估計中,滯后一期的SO2和COD排放強度的系數均為負,這驗證了初步擬合結果,即勞動生產率與SO2排放強度和COD的強度之間存在負相關,表明減少SO2和COD的排放強度對勞動生產率有正向作用,盡管統計上不顯著。這意味著競相降低環境標準的競爭會對勞動生產率產生抑制效應。然而,殘差的單位根檢驗表明,殘差序列存在單位根,說明該估計的結果有可能是不可靠的。

表3 估計結果
接下來,重點討論Malmquist生產率的估計結果。在TFP估計中,滯后一期的SO2變量系數為負,說明提高環境規制強度將有助于TFP的增長,然而這種影響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意味著競相降低環境標準的競爭并非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良策”。降低SO2排放強度對TFP的影響是兩部分疊加的結果:一方面,降低SO2排放強度促進了技術進步,這支持Porter假說,即污染減排將會促進技術進步。另一方面,降低SO2排放強度也改善了效率。當SO2排放強度每降低1個百分點,那么效率和技術進步將分別提高0.021個百分點和0.016個百分點,進而生產率將增加0.03個百分點。這些結果表明,提高SO2的環境規制強度不僅能促進生產率增長,而且也改善了效率并促進了技術進步。然而,這些影響在通常顯著水平上均不顯著,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我國對SO2的控制是以脫硫改造為重點的投資項目。這雖有助于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但是這些項目建成后或運行效率低下或無法正常運行,達不到預期的脫硫效果。二是對SO2排放收費標準偏低。我國在擴大SO2排放收費范圍和提高收費標準。然而,與SO2治理成本相比,收費標準嚴重偏低,從而激勵企業主動采用新技術設備和進行技術改造的動力不強。三是環境監管能力薄弱,還往往遭遇地方保護的阻力。在配合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我國實施了“上大壓小”的策略,淘汰關閉一批技術落后、污染嚴重、資源浪費的企業。“九五”期間,我國關閉了8.4萬家小企業。“十一五”期間,全國關停小火電機組超過7000萬千瓦。但由于各地把經濟發展作為“優先”戰略,特別是中西部地區。加之,在環境執法中常常遭遇地方保護的干擾,使得該項政策難以落實到位。這一現象與觀察到的事實基本相符:在考察期內,SO2排放強度下降出現在東部各省和中部部分省區,而西部各省的SO2排放強度均有明顯上升。
與降低SO2排放強度的效果相反,工業COD強度每降低1%,效率變化率和技術變化率將分別會減少0.011個百分點和0.042個百分點,生產率增長率降低0.051百分點。工業COD的減排對效率和技術進步的影響統計上不顯著,但是二者疊加作用的結果對生產率增長率有顯著的不利影響,盡管顯著水平比較低,僅為10%。然而,考察期內工業COD的排放強度在絕大部分省中均出現下降。據此,我們認為,提高工業COD排放強度對生產率及其構成的不利影響,不是由于省際間競相降低環境標準的結果,而是在于:一是我國的工業廢水污染治理主要集中于末端治理而不是過程防治。二是與SO2收費標準一樣,工業廢水收費標準也低于治理成本,使得企業寧愿受罰,而不愿意對生產設備和工藝技術的更新改造。三是“退二進三”策略意在促使企業搬遷時實行產業升級或技術改造,然而因“違法排放”處罰成本比較低,使得部分污染嚴重的企業不過是進行污染遷移。
與預期的一樣,滯后一期的TE對效率增長的系數顯著為負,這驗證了追趕效應的存在。離最佳生產前沿面越遠的省份在下一時期將有較大的技術效率改進。滯后一期的TE對TFP和技術進步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R&D活動對改善效率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對技術進步有不顯著的正向作用。二者綜合作用的結果對生產率的影響統計上不顯著。這可能與科技活動支出的作用存在較長的滯后效應有關。此外,從科技經費支出構成來看,勞動費支出的比重過大,使得科技經費被“人頭費”所擠占,實際用于科研生產活動的部分并不多。
新增投資將提高生產率的增長率。新增投資每提高1%,生產率增長將增加2.15%。新增投資不僅有利于推動技術進步,而且也顯著地改善了效率。新增投資不僅直接地改善了效率,而且能夠通過學習效應增強推動技術創新,進而提高了生產率。
外資活動對生產率增長和技術進步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盡管外資活動對效率變化有不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與多數FDI的研究結論相同,外商投資企業通過人員培訓與流動、示范效應等途徑對本土企業產生積極的影響,也可能通過企業間競爭,促使本土企業改善內部管理。
工業結構對效率變化有不利影響,而對技術變化和生產率變化有正向作用,這些影響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表明工業結構變化也是生產率增長和技術進步的一個推動因素。規模因素對生產率增長和技術變化有顯著的負影響,而對效率變化有不顯著負的影響。
此外,Brusch-Pagan的隨機效應未能拒絕固定效應方差為零的零假設,殘差的CD檢驗表明,殘差不存在截面依存性;單位根檢驗也顯示,拒絕了殘差是非平穩的零假設。這些檢驗結果表明,上述估計可能是合理的。
3.敏感性分析

估計中包含high·lnSO2it-1和high·lnCODit-1兩個交叉項,以捕捉高污染組對環境規制行為的影響。表4給出了穩健性檢驗結果。殘差的CD檢驗統計量均未能拒絕了截面獨立的零假設,Maddala-Wu(1999)[17]的單位根檢驗則拒絕了殘差是非平穩的零假設,這進一步表明模型的設定是恰當的。與表3的結果相比,主要變量的符號和顯著性均未出現顯著的改變,說明基本回歸結果可能是比較可靠的。

表4 穩健性檢驗結果
下面主要討論環境變量。表4顯示,對于低污染組來說,SO2排放強度每降低一個百分點,效率變化和技術變化將分別提高0.024和0.031個百分點,而生產率增長將增加0.054個百分點,這時TFP中SO2變量系數統計上顯著,但是顯著水平比較小;對高污染組而言,SO2排放強度每減少1%,效率變化增加0.017個百分點,技術變化和生產率增長將分別提高0.069%和0.084%。這表明,提高SO2的規制強度對高污染組的效率改善稍有不利的影響,然而更有利于促進高污染組的技術進步和生產率的提高。這意味著,提高環境規制強度不僅不會抑制本地經濟增長,反而會促進經濟增長效率。
由于交叉項系數為負,與低污染組相比,提高工業COD的規制強度將促進高污染組的生產率增長以及效率的改善和技術進步。如果高污染地區的工業COD的排放強度每減少1%,相對于低污染地區而言,高污染地區的效率變化和技術進步將增加0.012個百分點和0.01個百分點,從而生產率增加0.03個百分點。可見,即使在高污染地區,加強對工業COD的減排也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效率的提高。然而,這些影響在統計上均不顯著。正如上面分析,工業COD減排總體上對生產率及其構成的不利影響,其原因不是嚴格的環境規制所引起的,而是在于當前的工業廢水治理策略上。
五、主要結論
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的經濟市場化改革推進了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其中環境污染就是比較突出的問題之一。本文以SO2和工業COD為例,運用1992-2008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并通過數據包絡方法測算了各省的經濟增長效率,研究發現,在考察期內,Malmquist生產率年平均增長了18.1%,其中,技術進步和效率變化分別提高了15.4%和2.4%;31個省區中有26個省的技術變化高于效率的變化,表明多數省的生產率的提高主要來自于技術進步的貢獻。省際間的比較結果表明,SO2和工業COD的排放強度從東部到中部再到西部呈現階梯式遞減趨勢,說明東中部各省的環境規制強度在逐漸增強,而西部各省的環境規制強度有不斷下降的態勢。同時也表明環境規制強度差異不僅表現在省際間,而且也呈現出區域特征。
我們還檢驗了環境規制競爭對生產率及其構成的具體影響。估計結果表明,SO2減排競爭不僅有助于改善效率,而且促進技術進步和生產率的增長。與SO2的減排效應相反,工業COD減排競爭對效率、技術進步和生產率的增長都存在負作用,這種負影響不是由于省際間競相降低環境標準的結果,而是治污策略上的“誤配”造成的。此外,我們也發現,在高污染地區,提高對SO2和工業COD的減排強度也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效率的提高。但是這些影響統計上均不顯著。這些結果意味著,省際間環境規制競爭不僅不會促進本地經濟增長,反而會阻礙本地經濟的良性發展。
本文的結論對于我國環境污染治理具有較強的現實含義。第一,省際間環境規制競爭并非是發展本地經濟的“良策”。利用較低的環境標準來取得經濟發展等目的往往“南轅北轍”。第二,加大SO2治理力度,提高SO2的治理效率。特別要以脫硫項目建設為主線,改變脫硫設施運行效率低下的狀況。脫硫設施的高效運行不僅有利于提高資源的使用率,增加企業收益,同時也降低SO2排放。第三,調整工業廢水治理策略,加快由末端治理向過程控制轉變。第四,提高排污收費標準,促進污染企業從被動治理向主動治理轉變。最后,加大環境執法監督和處罰力度,提高污染者的違法成本,使環境治理政策得以有效實施。
注 釋:
①環境規制競爭行為的扭曲是指為了發展經濟等目的而降低環境標準、實行松的環境監管等的行為。本文稱之環境規制競爭或環境競爭。為行文方便,我們交替使用這些術語。
②以全國平均水平作為基準,取全國GDP/W=1。
③受教育年數,取文盲半文盲為1年,小學為5年、初中為8年、高中及中等教育為11年、大專及其以上取15年。
④高污染組有19個省,包括重慶、甘肅、廣西、貴州、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吉林、江西、遼寧、內蒙古、寧夏、四川、山東、陜西、山西、新疆和云南,低污染組包括安徽、北京、福建、廣東、黑龍江、海南、江蘇、青海、上海、天津、西藏和浙江等12個省。
[1]王永欽,等.中國的大國發展道路:論分權式改革的得失[J].經濟研究,2007,(1).
[2]陸 銘,等.收益遞增、發展戰略與區域經濟的分割[J].經濟研究,2004,(1).
[3]Potoski M. Clean Air Federalism:Do States Race to the Bottom?[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1,61(3):335-342.
[4]楊海生,陳少凌,周永章.地方政府競爭與環境政策:來自中國省份數據的證據[J].南方經濟,2008,(6).
[5]崔亞飛,劉小川.中國省級稅收競爭與環境污染:基于1998-2006年面板數據的分析[J].財經研究,2010,(4).
[6]Quiroga M.&T.Sterner&M.Persson.Have Countries with Lax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Polluting Industries?[R].RFF DP07-08,2007.
[7]宮俊濤,孫林巖,李 剛.中國制造業省際全要素生產率變動分析:基于非參數Malmquist指數方法[J].數量經濟技術經驗研究,2008,(4).
[8]Fare R.,S.Grosskopf,M.Norris&Z.Zhang.Productivity Growth,Technical Progress,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84(1):66-83.
[9]DiewertE.W.&D.Lawrence.Measuring New Zealand’s Productivity[R].Treasury Working paper,1999.
[10]OECD.Measuring Productivity:Measurement of Aggregate and Industry-level productivity[R].OECD Manual,2001.
[11]Hulten,C.R.&A.Isaksson.Why Development Levels Differ:The Sources of Differential Economic Growth in a Panel of High and Low Income Countries[R].NBER WP No.13469,2007.
[12]王小魯,樊 綱,劉 鵬.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換和增長可持續性[J].經濟研究,2009,(1).
[13]Barro R.J.&J.W.Lee.International Data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Updates and Implications[J].Oxford Economic Papers,2001,(53):541-563.
[14]Barla P.&S.Perelman.Sulphur Emission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J].Annals of Public&Cooperative Economics,2005,76(2):275-300.
[15]曹容寧.中國工業經濟發展中的外資與內資:一個計量檢驗的實證分析[J].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07,(3).
[16]呂 政.我國工業化進程中面臨的主要矛盾[J].當代財經,2005,(12).
[17]Maddala,G.S.&Wu Shaowen.A Comparative Study of Unit Root Tests With Panel Data and A New Simple Test[J].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9,61:631-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