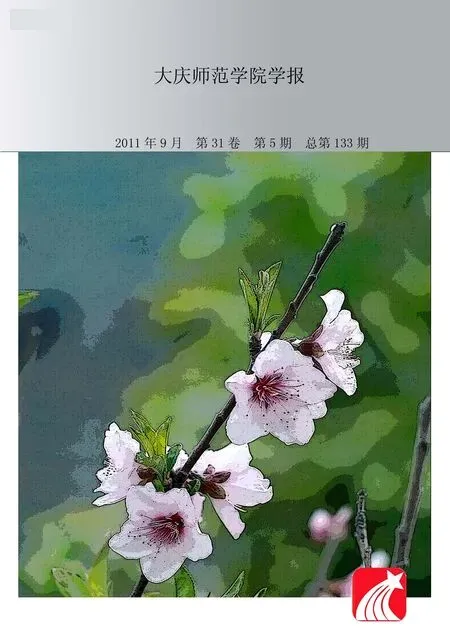晉令的內容及其在律令法體系中的作用
馬韶青
(北京中醫藥大學 人文學院,北京 100029)
一、晉令[注]本文所研究的晉令指作為令典的《泰始令》。沈家本認為,晉還存在單行的令,"'籍田令'是適用于當時的權宜法令,不便歸入晉令四十篇,因此別以籍田名篇"(沈家本:《歷代刑法考o律令三》,中華書局,第897頁)。但目前"籍田令"僅在此有記載,沒有其他的史料據以佐證,因此,暫時不考慮此篇。的制定背景
東漢末期,三國鼎立,社會處于動亂之中。司馬氏在豪家大族的支持下建立西晉,實現了國家短暫的統一。為了保證統治者和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迫切需要適用于全國范圍的法律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但由于漢魏時期的法律分散、龐雜,不具有系統性和完整性,因此,重新制定簡約而又完備的法律就顯得尤為必要,泰始律令應運而生。
漢魏時期法律龐雜而繁密。《晉書·刑法志》記載,漢代有律六十篇,又有令甲、令乙、令丙三百余篇,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注]《魏書·刑罰志》作九百六十卷。,加上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數十萬言,因此,“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余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注]《晉書·刑法志》。。問題不僅在于數量龐大,更在于內容駁雜混亂。曹魏時大加整理,取消了繁雜的傍章、科令,將其條文吸收于律令之中;同時根據新的情況和統治的需要,將律、令內容按性質歸類,該分的分,該合的合,必要時另立新篇章。經過此番整理,最后制定了魏新律十八篇,魏令一百八十篇。然而,曹魏改革法律的重點僅在于整理、歸類,旨在解決內容之重復與混亂,至于條文數目、懲罰輕重,似乎變動有限,和漢代律、令沒有明顯的出入,無法解決法律如何以簡馭繁的問題。因此,“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依此邏輯,立法要做到包羅無遺,只能“多其篇目”。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制定出來的《魏新律》難免落入“科網本密”的窠臼。[1]針對魏律“科網本密”的問題,晉的法律制定者們“蠲其苛穢,存其清約”,“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號,正其體號,改舊律為《刑名》、《法例》,辨《囚律》為《告劾》、《系訊》、《斷獄》,分《盜律》為《請賕》、《詐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為《衛宮》、《違制》,撰《周官》為《諸侯律》,合二十篇”,[注]《三國志·魏志·明帝紀》。并制定令四十篇。“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注]《三國志·魏志·明帝紀》。泰始四年,新的律典、令典頒行天下。
二、晉令的內容
晉《泰始令》共四十篇[2]目錄,主要包括行政、教育、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內容,規定了國家的政治制度、選舉制度、教育制度和戶籍制度,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而非一時的“權宜之計”。
(一)行政方面的法律規范
首先,晉令規定了國家的政治制度——九品中正制度。《貢士令》詳細規定了九品中正制度,規定了任用官吏和士人獲得品級的標準與方式。九品官人法,是魏晉時代選拔、任用官吏的主要形式。九品官人法給每個官員職位都規定了任職的品級資格。沒有資品,就沒有入仕的資格。獲得資品,必須符合六個條件,即“一曰忠恪跡躬、二曰孝經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為己”。另外,“察舉制”也是獲得資品的一種途徑,秀才、孝廉、賢良方正等科目察舉而被推薦于中央的士人,他們的人才優劣評判和資品的授予,并不是由中正作出,而是經過考試,由主持察舉的國家機關決定。[2]37-50
其次,晉令規定了國家的選舉制度。《選吏令》則在“九品中正”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了選舉官吏的機關、選舉官吏的限制性規定以及官吏考核和擢第的條件等內容。在行政機關內部,司徒長吏主持九品的評定,而吏部尚書則主持官吏的選拔,“外官,州刺史、郡太守、縣令,均由吏部選用”。同時,《選吏令》還規定了一系列官吏選拔的禁止性規定,例如,春夏農忙的時候不得對郡縣各官吏進行變動、選舉官吏不得任用鄉親、姻親之間擔任相互監督的職位、有罪的人不能夠當選等等。[2]263-272
《貢士令》和《選吏令》構成晉令的核心內容。此二令的穩定性與長期性顯而易見。正如張鵬一所說的,“貢士、選吏二法,是晉之政治中堅,此為重要。外則州郡孝秀,人才首選;內則吏部尚書、丞郎,萬流具贍。江左孤懸,得以半壁撐持者,顧、賀、王、謝、陶、郗、紀、周、桓諸人,皆由此選。此讀晉令者,應為留意。即謂晉祚百余年,維系于貢士、選吏諸令也,非過也”。[2] 4-5
另外,晉令規定了一系列相關的行政法律規范,例如,《官品令》、《吏員令》、《俸廩令》、《服制令》等。這些法律規定是國家政治制度的補充規定和實施細則,有助于保證國家政治制度在實踐中的具體運用。
(二)教育方面的法律規范
晉令規定了國家的教育制度。《學令》規定了學校的設置、學生的培養、課程的教授、教師的選拔等內容,是貫以一朝的穩定性法律規范。晉代設置學校的目的在于使“先王之道不廢”和“恢復仁義禮讓之風”,袁瓌在提倡興國學的原因中指出,“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風音,盈于京室,味道之賢,是則是詠,豈不盛哉?”。[注]《晉書·袁瓌傳》。學校有太學、國學、辟雍,“太學、國學以講學,辟雍行禮”,以漢五經、《三字經》、《春秋》、《尚書》為學生學習的主要課程,并以是否通曉儒家經典以及通曉的程度作為考核學生的標準。選拔教師的標準是“深博道奧、通洽古今、行為世表者”,教師的職責包括三個方面,“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弘儒學”,“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質疑”。
(三)經濟方面的法律規范
首先,晉令規定了國家的戶籍制度。西晉以一定的戶籍為單位組織人民,《戶令》規定了戶籍的種類、戶籍的登記制度、戶籍的管理機構等內容。西晉時期,按照身份地位的不同可分為正式戶口和非正式戶口,正式戶口用黃紙登記,非正式戶口用白紙登記。正式戶口包括民戶、七戶、營戶、雜戶、冶戶、雜胡戶。衣食客、佃客、奴婢附于本戶,不單獨登記戶口,稱為“支戶”。晉時全國有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戶,分別隸屬于河南、滎陽、弘農、上洛等十二個州郡。登記戶口時,登記人員要寫明本人的基本情況,例如,需要寫明本人的出生年月日、姓別、爵位等,另外,還得注明所隸屬的州郡縣里的名稱。[2] 7-21其次,晉令規定了國家的占田、課田制度。《佃令》規定了每戶占田的數量、官員占田的標準和軍隊的屯田制度。例如,“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官吏則根據官品等級確定占田、課田的數量。[2] 139-146再次,晉令規定了國家的賦稅制度。《戶調令》規定了每戶輸調之數量、所輸絹布的尺寸、以及輸調數量及種類的地區差異等。例如,“丁男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所輸之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匹。六十尺為一端”[2]134-138。《佃令》則規定了每戶占田輸租的數量。例如,“凡民丁課田五十畝,收租四斛,絹二匹,綿三斤”[2] 134-146。最后,還包括一些生產管理、市場交易方面的法律規定,例如,《鹽鐵令》、《倉庫令》、《酤酒令》、《關市令》等。
(四)軍事方面的法律規范
晉令還包括軍事方面的法律規范。從第三十一篇《軍戰令》到第三十八篇《軍法令》,規定了西晉初期水戰與陸戰各自的組織、管理原則,規定了違反軍令的處罰方法,例如,“誤舉烽燧,罰金一斤八兩,故不舉者,棄市”[2]292-307。這些關于軍事方面的法律規范,大多是適用于當時戰爭狀態下的權宜之計,在國家太平以后,法律只保留一些基本的制度,其余的則予以廢除。
三、晉令在律令法體系中的作用
晉令實現了律令界限的基本區分,完成了令的法典化,在中國古代律令法體系形成中發揮著承上啟下的關鍵性作用。
(一)晉令實現了律令界限的基本區分
在中國古代律令法體系中,律令內容有著明確的區分:律指刑事性法典,令指制度性法典,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晉泰始令的頒布,實現了律令界限的基本區分。
漢代律令內容混雜,律中包括令的規定,例如,漢代的戶律、金布律、秩律中有大量的制度性規定;而令中也包含律的內容,如《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入令,罰金四兩”,《令乙》“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注]《漢書·張釋之傳》如淳注引。因此,漢代律令界限并不十分明確,中田薰認為,“漢的令典不象律典是原先就有編排順序的法典,而是將前代皇帝的詔令,根據皇帝死后的事情輕重分為甲乙丙諸篇的詔令集”[3]。曹魏頒布魏新律的同時,頒布了三篇令,雖然律令單獨編纂,似乎內容上有一定的區分,但魏令并沒有實現法典化,堀敏一先生認為,“在說明變革漢朝舊的法律并制定魏律諸篇的《序略》的記錄中,載有魏設置郵驛令、變事令之事。郵驛令、變事令是屬于州郡令以下的哪一個令呢,還是單行令呢,語焉不詳[注]中田薰在其《關于支那律令法系的發達補考》中認為是單行令。。因此,魏令是否具備魏律那樣作為單一法典的性質,值得懷疑”[4]。晉泰始律令的頒布,律令各自具有了相對獨立的內容,律為刑事性法規,令為制度性法規。同時,晉令的篇目結構及編撰體例也有了很大的改變,即令的編排與修訂以體系化為主要特征。晉令的制定者在出臺律令時,就明確地以“律多少篇”、“令多少篇”的形式加以確定,即“全體律或令是作為不可分的單一法典(律典、令典)來編纂施行的,凡是稱為律或令的法規,全是同時制定同時廢止的。……其數目,在律典令典編纂之際就已經被‘總計幾篇幾百幾十條’地精確清點好了”。[注]滋賀先生在考證曹魏新律十八篇篇目時認為:“以唐律令為典型的的律令體系,在法典編技術上有兩個特征:一、以刑罰、非刑罰為標尺對法典進行分類和編纂。二、全體律或令是作為不可分的單一法典(律典、令典)來編纂施行的。具體地說就是:甲、一個時代只分別存在唯一的律典和令典。也沒有不包含于律典令典的以‘律’或‘令’稱呼的法規。從而,凡是稱為律或令的法規,全是同時制定同時廢止的。其數目,在律典令典編纂之際就已經被‘總計幾篇幾百幾十條’地精確清點好了。乙、律典令典制定以后,雖有被廢止的,但沒有對其加以部分變更的。如果有修正的必要,就采取編纂新律典令典、廢止原律典令典的形式。”(滋賀秀三《西漢文帝的刑法改革和曹魏新律十八篇篇目考》選自《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8卷,注釋三六,中華書局1992年7月出版,第98頁)因此,令在西晉時期成為法典,完成了律令界限的基本區分。
需要強調的是,晉令只是實現了律令界限的基本區分,還沒有實現律令界限的完全區分。原因在于晉令還包含歲刑、罰金刑、肉刑和死刑等有關律的內容。[注]關于歲刑的規定,如“凡民不得私煮鹽,犯者四歲刑,主吏二歲刑”(《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五條引晉令)。關于罰金刑的規定,如“凡民皆不問私釀酒酤,其有婚姻及疾病,聽之。有犯罰釀藥酒,皆(罰)金八兩”(《北堂書鈔》一八六引晉書)。關于肉刑和死刑的規定主要體現在有關軍事方面的令文中(張鵬一著《軍戰令第三十一》,三秦出版社1989年元月出版第189-300頁)。令文里出現罰則的規定,說明晉代刑法中的犯罪構成事實并未與刑罰相分離,張建國在論述“晉令包含罰則”時指出,“以烽燧的規定為例,據魏律序,漢代原在興律,魏新律將其劃歸到新增的驚事律中,性質是刑律。晉把它們移至令中,附有罰則,無論怎么看,也說明晉令至少在其初期制定時確切無疑的有罰則存在”[5]。因此,魏晉時期只是律令界限區分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實現了律令界限的基本區分,為隋唐時期律令界限的明確區分奠定了基礎。
(二)晉令促成了律令法體系的初步形成
中國古代的律令法體系,萌芽于戰國,發展于秦漢,初步形成于魏晉,確立于隋唐,宋、明、清時期進一步完善。晉令在這一體系形成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晉令的法典化,使律令界限有了基本的區分,令成為與律同等重要的國家基本法,二者居于法律體系的核心地位,律令法體系隨著晉《泰始令》的頒布而初步形成。滋賀秀三先生認為,“可以作出如下判斷:具備前述第二個特征的法典始于魏律,承魏之緒,并配備以‘令’,從而創造了律令體系雛形的,則是晉律”[6]。
晉以后的南北各朝均頒布令典,其內容和體例基本沿襲晉令。到了隋代,令典的構成有了較大的變化,保留的晉令舊篇目有《戶令》、《學令》、《官品令》、《祠令》、《宮衛令》、《關市令》、《獄官令》、《喪葬令》、《雜令》等九篇,其他或予以刪除,或變更名稱,或數篇和為一篇,增加新篇,形成三十篇《開皇令》。唐代立法者則在隋開皇令的基礎上結合晉泰始令的內容進一步完善令典[注]唐《開元令》中增加了隋開皇令中缺乏的營繕、醫疾兩篇令。醫疾令的內容與晉、梁各令篇目中的醫藥疾病相當。形成了簡約而又完備的《開元令》[注]開元二十五年唐令包括30卷,33篇,其篇目為:官品、三師三公臺省職員、寺監職員、衛府職員、東宮王府職員、州縣鎮戍岳瀆關津職員、內外命婦職員、祠、戶、學、選舉、封爵、祿、考課、宮衛、軍防、衣服、儀制、鹵簿、樂、公式、田、賦役、倉庫、廄牧、關市、捕亡、醫疾、假寧、獄官、營繕、喪葬、雜(池田溫《律令法》,載楊一凡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一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第141頁。盡管唐代多次修訂令典,但至開元二十五年令以后,則變動不大,因此,這里只列舉開元二十五年令的篇目)。,“可以說唐令至少在篇目這一點上,是前代諸令的集大成者”。[7]唐令典篇目簡明,內容詳備,與唐律共同成為中華法系完備的代表。戴建國在考察唐《開元二十五年令》之《田令》篇時認為,“(唐代)律與令的關系十分清楚,律用國家超強制力來保證令的貫徹執行。……唐令是關于國家體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規,因而也是唐代整個法律體系的主干”[8]。唐律令的頒布,標志著中國古代律令法體系的正式確立。可見,晉令在律令法體系形成過程中起著承上啟下的關鍵性作用。
[參考文獻]
[1]劉篤才.論魏晉時期的立法改革[J].遼寧大學學報:哲社版,2001(6):8-9.
[2]張鵬一.晉令輯存[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
[3]中田薰.關于支那律令法系的發達[M]//中田薫.法制史論集:第四卷.東京:巖波書店,1951:76.
[4]堀敏一.晉泰始律令的形成[J].中國史研究動態,1990(4):19.
[5]張建國.魏晉律令法典比較研究[J].中外法學,1995(1):30.
[6]滋賀秀三.西漢文帝的刑法改革和曹魏新律十八篇篇目考[M]// 劉俊文.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8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98.
[7]仁井田陞.唐令拾遺[M].栗勁,譯.長春:長春出版社,1989:810.
[8]戴建國.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J].歷史研究,2000(2):4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