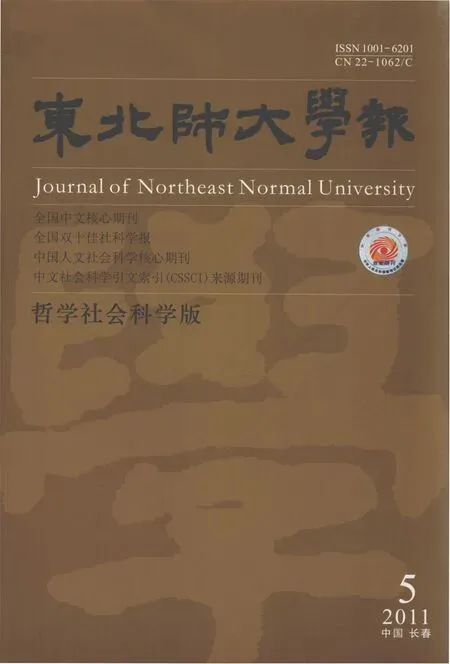簡論基督教世界視角下的第一次十字軍武裝
——從安條克之戰談起
王向鵬,徐家玲
(東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吉林 長春130024)
簡論基督教世界視角下的第一次十字軍武裝
——從安條克之戰談起
王向鵬,徐家玲
(東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吉林 長春130024)
安條克之戰是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關鍵戰役,基督教史家們對這場戰役的記載反映了十字軍的規模、構成、武器以及其軍事的理念。十字軍的構成體現了中世紀封建西歐的社會結構和秩序。十字軍的武器裝備和軍事理念凸顯了11世紀基督教世界封建軍事的發展趨勢和前進方向。
十字軍;安條克;武裝;基督教世界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是由教皇烏爾班二世發起的,以奪回“主的圣墓”為名的“十字對新月”的戰爭。安條克之戰是這場歷時三年的漫長遠征的關鍵之役。在這場歷時8個月的艱苦戰役中,十字軍先后挫敗大馬士革、阿勒頗的強援,攻克安條克城,最終擊敗了摩蘇爾總督率領的突厥聯軍。安條克的勝利是決定性的,重挫近東諸強的十字軍至此踏上了通往耶路撒冷的坦途,圣城的陷落已不可避免[1]114。當世的基督教史家們對這場戰役做了詳細而生動的記述,使得我們能夠從基督教世界的視角,去窺探十字軍武裝的全貌——它的規模、構成、武器及其軍事理念。
一、十字軍的規模和構成
首先,無論這支十字軍被冠以了何樣的名義、被賦予了怎樣的形態,它仍舊是一支典型的11世紀基督教的封建軍隊。在12世紀末以前,甚少能看到“crucesignatus”,即所謂“十字軍”的稱謂出現在拉丁文獻中。他們更多的是被稱作“legions”、“exercitus”,或“manus”——這些是對封建軍隊的普遍稱呼。十字印記更多的是一種形式,軍事封建才是其本質。
這支十字軍無疑是龐大的。在阿爾伯特的筆下,兵臨安條克城的武裝人員有30萬[2]198,安娜也提到了80 000名全副武裝的步兵[3]342。夸張的數字從側面展現了十字軍異乎尋常的人數。保守估算,包括非武裝朝圣者在內,十字軍離開尼西亞的時候有5萬人,其中7 000人是騎士或領主[4]142。按照每名騎士會攜帶2-3名全副武裝的扈從或軍士參戰的傳統估算,十字軍武裝力量的主體是貴族騎士以及他們的扈從。組織如此龐大規模的貴族武裝的可能性,只能到11世紀基督教的西歐封建社會才能尋找得到。
領地分散、財源匱乏、附庸關系的微妙,特別是封建制度本身的限制,以及教會所做出的諸如“上帝和平”的種種努力,使得封建領主難以組織和維系龐大的軍事力量。基督教世界對秩序的要求使封建戰爭變得有限。然而,社會的穩固、秩序的重建,特別是依照功能劃分階級的三元模式——教士祈禱、武士征戰、農民勞作——凸顯了封建貴族的軍事化[5]258。騎士崛起并逐漸融入了上層社會,英勇善戰成為貴族不可缺少的美德。一定意義上,在封建的基督教世界中,專事戰爭的武士集團以階層的形式出現了。11世紀興起的“武功歌”,歌頌的幾乎全部是貴族騎士在戰場上的豐功偉績。貴族們在將戰爭當成了自己的理想和事業的同時,也壟斷了發動戰爭的權利和資源。因此,盡管有種種阻礙——需要慎重的考慮和權衡、要冒大的風險、可能會付出沉重的代價,從11世紀起,封建權貴們逐漸組織起大規模、長時間的軍事征伐,諸如威廉征服、十字軍、巴巴羅薩征伐意大利、布汶戰役等等,“隨著封建制度穩固并交接,大規模的軍事活動變得愈發普遍”[6]15。
這支兵臨安條克城的十字軍策源地眾多,遍布西歐大部,是完全依照著封建體系組織起來的。十字軍的領導者是貴族。十字軍沒有大一統的軍事領袖,軍事事務實行貴族集體領導。安條克之戰中,從圍城布陣、攻打城門、部署崗哨,到軍事征伐,修建堡壘,奇襲阿勒頗的援軍,商討應對突厥聯軍的策略,夜襲安條克,乃至同突厥人媾和,一切重大的軍事決定和戰略部署,都是通過貴族會議的商榷實現的。貴族會議做出的決定具有強制力、權威性,不受任何個體的挑戰,“無論高低貴賤,都不得做違背命令的任何事情”[2]216。
貴族會議中,并非所有貴族都擁有同等的權力和地位。四個集團的領袖——日耳曼的戈德弗里、諾曼的博希蒙德、佛蘭德斯的羅伯特、南部法蘭西的雷蒙德——掌握著話語權和決策權,組成了核心領導集體。重大的軍事行動基本都由上述四人具體組織和實施,他們充足的財力,崇高的個人威望,雄厚的軍事實力,關鍵時刻所體現出的決斷能力和領導才能,是其統領整個貴族階層的基礎和保證。總而言之,盡管在集團內部存在著權力的劃分和制衡,貴族以階級的形式占據著十字軍的領導層,他們是指揮者,決定著戰爭的形勢和走向。
十字軍的主體是貴族的騎士附庸和扈從軍士。他們依照著封建的依附關系,圍繞著各自權貴們的核心軍事武裝組織集結,依照地域和民族形成了四個大的軍事集團,通過貴族會議組成了協同配合的作戰體系。在這種軍事體系中,最基本的軍事單位是個體封建家族。圣波勒伯爵休帶領兒子和幾個臣屬對突厥伏擊的反制[2]212-214,是以家族武裝為基本軍事單位的典型的小規模武裝沖突,也是封建時代最為常見的戰斗形式。
十字軍中除了戰士,還有大量的非武裝朝圣者,以教士和平民為主,他們的職責和功能基本是非軍事、輔助性的。隨軍教士主要負責禱告和圣禮。教士的布道是戰前動員、鼓舞士氣的重要環節和手段。宗教儀式對十字軍是不可或缺的:在決戰的前夜,十字軍全軍通宵祈禱,做懺悔,分領餅和酒,以信仰來強化戰斗的信念和決心[2]320。教士用顯圣、訓誡、彌撒在精神層面引導著這支軍隊。安條克城內“圣矛”的發現是這種精神導向的最直接、最富戲劇性的表現[7]171。
此外,軍隊中還有龐大的平民群體(uulgi)。他們的主要工作是搜集糧秣,運輸輜重,修筑塔樓堡壘,從事各種戰爭之外的體力勞作,一般不會走上戰場。在基督教史家們的記載中,他們更多的是戰爭的犧牲品和受害者,唯有在遭遇突襲,慘遭屠戮的時候才能夠與戰斗聯系起來。只是在安條克城破,關乎十字軍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平民大眾才被明確地描述為戰斗的參與者。即使如此,阿爾伯特對他們的評價也是刻薄的:“incautos Christianos inertis uulgi”——“魯莽遲鈍的基督教眾”[2]282。
11世紀出現的依照功能劃分社會階級的三元模式,映射在了十字軍的結構和組織。一定意義上說,十字軍是中世紀封建西歐的縮影和寫照:貴族騎士負責征戰,教士主持圣禮禱告,平民大眾專心勞作。封建秩序在十字軍中得以彰顯。
二、十字軍的武器裝備及其軍事理念
整體來看,十字軍是重裝的封建武裝。權貴、騎士還有他們的扈從軍士都是全副武裝的。十字軍的重裝上陣主要表現在了防御力量的強化上。鎖子甲(lorica)是最主要的防具,也是11-13世紀最為普遍和常見的盔甲式樣。鎖子甲以大量用鉚釘固定的鐵環緊密連接而成,靠著環的尺寸大小的變化均衡全身的負重,重約14公斤[8]19。雖然這時的鎖子甲缺少對手腕、小腿的保護,但是它常連帶保護頭部的貼頭帽,保護面部的護面在平時會被垂掛在胸前[9]23。由于是鐵環相連而成,鎖子甲不像中世紀后期的板甲那么笨重,一體式的設計便于行動,韌性和抗擊打能力則明顯強于之前的皮甲和鱗甲,因而被當時的武士們普遍采用。當世的文獻中所提到的盔甲,基本都是鎖子甲。此外,還有兩件必不可少的護具——頭盔和盾牌。頭盔(galea)多采用錐形樣式,鐵制或銅制,因制作工藝的不同,產生了一體式和分段式兩種結構樣式。錐形盔被戴于鎖子貼頭帽上,一般有護鼻,間或有保護后腦的延伸。相比頭盔,盾牌(scutum)隨著形式的變化而具有更大的防護效力。11世紀的歐洲普遍采用了新式的鳶盾,其頂部為圓形,通體呈倒三角形,可以對騎兵從肩部到腿部的整個身體左側形成有效的保護。鳶盾為木制,中央有飾扣,邊沿包鐵,表面呈少許彎曲狀,以擴大覆蓋面。依照阿爾伯特的記載,盾牌會被繪上諸如金色、綠色、紅色等明亮的顏色[2]198,這符合中世紀人們對鮮亮顏色的喜好[5]335。身著鎖子甲,頭戴錐形盔,手持鳶盾,是一名11世紀武士的典型形象,也是十字軍騎步兵的標準配置。依照修士羅伯特的記載,十字軍以劣勢兵力迎戰阿勒頗的數萬馳援的時候,依仗的就是盔甲、盾牌和頭盔所組成的全面防護[10]130。鐵制防具的普遍應用有效提高了戰斗個體的防御能力。同時,大型的鳶盾也增強了步兵陣列的傳統防御模式——盾墻的防御效果。步兵首先排列起緊湊的陣線,然后將寬大的鳶盾豎立在身前左側,形成對左側同伴的右側身體的保護,依次緊密相疊的盾牌就組成了一面高大的盾墻。以龐大的鳶盾組成的盾墻,是步兵陣列最為堅固的防御壁壘。哈羅德面對威廉的騎兵沖鋒,就曾憑借這樣的盾墻做出過頑強的抵抗。十字軍在爭奪鐵橋的時候也使用了同樣的盾墻戰術,成效顯著[2]192。
在進攻端,基督教世界最主要的武器是矛(hasta)和劍(gladius),所有的十字軍武士手中都可能持有這兩種兵器。需要注意的是,在11世紀,除了長度,步兵使用的矛和騎士的長矛尚沒有特別顯著的區別。在中世紀,盡管戰爭受到技術上的限制,防御總是優于進攻,但是隨著防御裝備的改進,特別是鐵制防具的普遍引入,進攻武器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首先是武器的形質改變了。中世紀早期乃至10世紀,這兩種武器的刃口都較寬,矛頭呈扁平狀,劍普遍為寬刃,劍身呈直線平行狀,尖端呈半圓形,較鈍。這種形質,強調的是武器的劈砍能力。隨著鎖子甲的出現以及煉鐵甚至煉鋼技術的發展,武器的外形和質量發生了明顯的改變。矛的矛頭更短、更厚、基座更為堅固,還加上了凸緣或翼,以防戳刺過深無法拔出[11]130。劍的尖端呈錐形,劍刃向尖端變窄;劍柄結構簡單,多為十字形護手;劍身長度不一,一般為76—83厘米,有貫穿劍身的血槽或突脊,有銘刻,較輕便,單手使用,“布永的戈德弗里之劍”只有約1.5公斤重[6]22。這些變化主要是為了提高武器的穿透性,突出戳刺能力,以突破鎖子甲和盾牌組成的堅固防御。冶鐵和煉鋼技術的發展,為武器的進化奠定了基礎。早在8世紀,斯堪的納維亞就已發展出了冶煉純質鋼的技術,使得劍刃變得更輕、更加堅韌、更加鋒利[8]27。安條克之戰期間,戈德弗里在一次沖突中將穿著護甲的突厥武士一劍劈成兩半,在這次為基督教史家們津津樂道的“壯舉”中,劍刃所表現出的鋒利程度可見一斑[10]133。
相應的,武器的使用方式也有所改變。劍的重量減輕,韌度加強,劍刃變窄,尖端銳化,護手簡化為十字形,都是為了便于突擊戳刺使用,從而增加了劈砍之外的新動作,豐富了這種近身武器的攻擊手段。矛的使用方式在騎兵中變化得更為顯著。騎兵在作戰中,已經不再將矛作為投擲武器使用,這對于擁有大型鳶盾的對手來說已不再奏效。騎兵主要將長矛應用于沖鋒,突擊穿刺是這種武器最有效、最受人敬畏的殺傷手段。在記述坦克雷德于安條克城外同突厥騎兵交鋒的場景時,拉爾夫做出了近乎崇敬的贊嘆:“坦克雷德拿起了他的矛,就像通常那樣,刺穿了帶頭的那個人……他的進攻將頭盔變成了頭巾,盾牌變成了披風,鎖子甲變成了襯衫……。”[12]78長矛的持有方式有多種,或是較為傳統的舉過頭頂,過肩持有,或是依住身體,夾在右臂腋下平持,即長矛平持。長矛平持是一種先進的、騎兵沖鋒時所使用的持矛姿勢,早在11世紀中期的貝葉掛毯中就已出現,于12世紀中期普及,可能被十字軍所采用。但在阿爾伯特的記述中,并沒有類似平持長矛的細節,貴族們沖鋒的時候,經常是“揮舞著長矛,以盾牌擋住胸膛”,“uibrata hasta”這種說法,顯然描述的還是老式的持矛方式[2]226。
此外,對手的變化也會導致武器戰場價值的變化。十字軍來到近東戰場,在到達耶路撒冷之前面對的主要是塞爾柱突厥人的武裝勢力。弓騎兵是突厥軍隊的支柱,其馬匹血統優良、耐力持久、平衡性強、機動靈活。突厥騎手善騎射,可以在各種地勢環境下精準射擊,阿爾伯特承認,突厥人的箭術高于十字軍,極具耐力[2]192。突厥弓騎兵攜帶多個箭袋,火力覆蓋范圍可達365米[13]120。弓騎兵的箭矢齊射對于十字軍來說是可畏的,經常被形象地稱為箭雨(grandine sagittarum)[2]222。雖然弓騎兵的遠程射擊對身著鎖子甲的騎兵無法造成致命傷害,卻能有效地殺傷馬匹,十字軍騎兵力量因而減損嚴重,到最終決戰的時候,只剩下200匹適于戰斗的馬匹[2]332。圍繞著弓騎兵,突厥人形成了獨特的戰術體系:晝伏夜出,避免接戰,利用數量優勢對劣勢敵人進行突襲,以弓騎兵的機動靈活,從側翼包抄、箭矢挑釁、佯裝撤退、破壞十字軍的隊形和秩序,誘敵深入、伺機設伏。這對于習慣正面對決、短兵相接的十字軍武士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挑戰。
于是,為了遏制對手弓騎兵的遠程打擊和機動力,十字軍遠程武器的威力和價值凸顯了出來。首先是弓,即“arcus”。與東方穆斯林普遍使用的復合弓不同,十字軍用的是單弓,由一整塊木料制成,多以紫杉、榆樹和白蠟樹做原料。11世紀的弓,與著名的英格蘭“長弓”并無區別,只是長度略短一些,約為1.5米,15世紀時增加到了1.8米[14]75。弓木呈圓形,中心部位是“D”形斷面,向兩端逐漸變細;兩端有搭住弓弦的鉤,有時為角質;彈性較好的邊材會被用在弓木的外側,韌性更好的心材則被用于內側,從而增加了弓的張力[14]71。弓的射程取決于弓本身的長度和使用者的開弓力量,基本射程約有365米[6]26,有效的殺傷范圍為90米[8]33。弩(“baleari arcu”)是更加致命的遠程武器。弩是利用扳機原理擊發的一種機械弓,由短弓、弩臂、弩機構成。弩使用的是方鏃箭,短而粗,錐形頭,雖然射程為200米,不過有效射程約為100米,與弓相比,射速更高、威力更大,能夠穿透7厘米厚的木材[6]26。
弓和弩在東方戰場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有著相當高的戰場價值。它們的射程和威力迫使突厥弓騎兵不敢輕易進犯,從而有效地維持了十字軍的陣形,保護了寶貴的騎兵陣線。弩的威力尤其巨大,它簡單易學,提前上弦后可隨時擊發,因而受到廣泛青睞,很快被后世的東西方步兵陣列普遍配備。在安條克的最終決戰中,十字軍充分利用了這兩種遠程武器的威力:他們將所有的弓箭手和弩手放到了全軍陣列的最前方,以遏制突厥弓騎兵的遠程打擊。在弓和弩的掩護下,十字軍騎步兵得以搶先從橋門突圍而出,奪取了戰略的主動[2]324-326。弓和弩的遠程壓制和威懾作用在安條克被正名。
然而,武器的戰斗功效和戰場價值并不等同于它的社會地位。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對武器的態度和看法,更多的是取決于它們持有者的身份和地位,而非它們本身的價值。于是,封建社會依照著它們的主人,對武器做出了迥異的評價。最高尚的武器是貴族的劍。劍為中世紀武士普遍持有,特別受到騎士和貴族們的喜愛。劍象征著榮譽,代表著光榮,不僅出現在騎士受封、國王加冕的儀式中,也經常出現在印有國王和權貴身姿的印章及錢幣上,具有極大的象征意義。中世紀普遍流傳,劍會被主人的勇氣、力量及榮譽所同化,帶給其新的所有者同樣的殊榮,被高度尊崇,世代傳承[8]24-25。
最卑劣的武器是農民的弓和弩。在戰爭中,只有出身卑微的人才會持著它們走上戰場。它們受到了基督教社會普遍而持久的鄙視。弩從11世紀末開始被教會明令禁止使用——在繪畫中常常被描繪為惡魔使用的武器[9]113。這種態度和評判標準顯然蔓延到了文獻記述中。在十字軍的文獻中,甚少有對基督教弓手的描述。在這些基督教史家們的筆下,所有的十字軍勇士都是用長矛寶劍立下的赫赫戰功,只有異教徒敵人才會在灌木叢中、山頂上,城墻內暗箭傷人。這種功能和地位的矛盾,鮮明地表現在了安娜對弩的評價上:它威力驚人,可以射穿城墻,卻是惡魔的機械[3]316-317。尊貴的人被卑賤的人殺死,恥辱和憤怒感被轉嫁到了下層使用的武器——弓和弩的身上。武器被賦予了階級性,成為社會的寫照,反映了封建社會的等級和秩序。
對武器的態度和價值的判斷,逐漸衍生出了上層武士們的戰斗精神——騎士精神,這種精神主導了整個基督教社會的戰斗理念:長矛寶劍短兵相接,以血肉相搏。這種軍事理想是近身的白刃戰[5]341。這種理念是根深蒂固的,它源于精神,植根于階級,很難被改變。由封建權貴統帥,騎士附庸、扈從軍士主戰的第一次十字軍自然具備了同樣的戰爭風格。盡管面對新的戰場環境,新的敵人,十字軍被迫做出了戰術上的改變,如組成更為緊密的陣形,更加強調組織和紀律,強化騎步兵之間的配合,重視相互之間的掩護和協作,甚至也有意識地采取了伏擊戰術,但是這種變化是適度的,無法也沒有改變其根本的戰爭風格:戰斗總是要歸結于近距離的搏殺,騎士的集團沖鋒永遠是最后決勝的殺手锏。盡管十字軍在東方戰場上,為了適應截然不同的戰爭環境,被迫做出了激烈的改變,其歐洲封建軍隊的戰爭風格也只是被調整,而非被變革[6]232。
十字軍的武器裝備——無論進攻或防御——基本是鐵制的,這也是同時代的封建武裝的普遍特征,客觀上反映了11世紀基督教歐洲的采礦、冶煉,以及鍛造加工技術的進步。但是,為了獲得這些愈發沉重的金屬裝備,人們所要付出的經濟代價同樣巨大。礦石的采集和冶煉手段仍然簡單原始,煉鋼是非常困難的。盡管出現了諸如斯堪的納維亞和萊茵蘭這樣的龐大的武器制造中心,但是裝備制造主要是由個體作坊來完成,其質量和樣式完全取決于工匠個人的技藝和經驗。武器裝備的制造難度大、成本高、效率低下,花費驚人。一件鎖子甲就價值60只羊或6頭牛[6]32。在10世紀中期,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生產的最好的劍刃,僅制作時間就要一個月,工藝程序極其復雜,其價值相當于120頭牛[8]26。
新式武器裝備不僅需要付出高昂的經濟代價,還需要長時間的訓練才能夠被熟練掌握。騎士比武于11世紀出現,是歐洲武士們演練陣形、磨煉技藝的場所,最初混亂廝殺的模式凸顯了這種競技運動的實戰目的。貴族們會帶著自己的騎士扈從,常年在外參加騎士比武,以強化他們的作戰技能[13]87。安條克之戰期間,在迎接法蒂瑪特使的時候,十字軍為了壯大聲威就做了類似于騎士比武的展示[10]136。對于11世紀的封建武裝來說,專業的軍事技能和實戰經驗都是必需的。
裝備所需的高昂花費,使用技巧和訓練時間上的苛刻要求,客觀上將農民排除在了戰場之外。這種變化體現在了文獻的著者們的態度——農民武裝被稱作烏合之眾,貴族的軍隊才是勢不可擋的。“全民皆兵”的軍事理念被淘汰了,貴族軍事化,唯有重裝上陣的武士才是戰場的主導者,戰爭成為他們壟斷的特權。這種結果同社會結構的變化,不同階層的社會功能的轉變是相吻合、呼應的。在隨后的幾個世紀里,戰爭日趨專業化、職業化,新的武裝力量——專事戰爭的職業雇傭兵、制式化的市民武裝相繼崛起,中世紀基督教西歐的封建軍事和武裝正在向著新的階段和方向發展。從基督教世界的視角剖析第一次十字軍的武裝,反映了中世紀西歐封建社會的技術、等級、秩序以及前進的方向。
[1]Jim Bradbury.TheMedievalSiege[M].Woodbridge:Boydell Press,1992.
[2]Albert of Aachen,edd.and trans.Susan B.Edgington.HistoriaIerosolimitana,HistoryoftheJourneytoJerusalem[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3]Anna Comnena,edd.and trans.E R A Sewter.TheAlexiadofAnnaComnena[M].London:Penguin,1969.
[4]John France.VictoryintheEast:amilitaryhistoryoftheFirstCrusade[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5]Jacques Le Goff,trans.Julia Barrow.MedievalCivilization:400-1500[M].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1988.
[6]John France.WesternwarfareintheageoftheCrusades,1000-1300[M].London:UCL Press,1999.
[7]Matthew of Edessa,trans.A E Dostourian.ArmeniaandtheCrusades:TenthtoTwelfthCenturies:theChronicleofMatthewof Edessa[M].NewYork: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3.
[8]David Edge and John Miles Paddock.ArmsandArmoroftheMedievalKnight:AnIllustratedHistoryofWeaponryinthe MiddleAges[M].New York:Crescent,1988.
[9]David Nicolle.ArmsandArmouroftheCrusadingEra,1050-1350:WesternEuropeandtheCrusaderStates[M].London:Greenhill Books,1999.
[10]Robert The Monk,trans.Carol Sweetenham.RobertTheMonk'sHistoryofTheFirstCrusade:HistoriaIherosolimitana[M].Aldershot:Ashgate,2005:130.
[11]Kelly DeVries and Robert D Smith.MedievalWeapons:AnIllustratedHistoryofTheirImpact(WeaponsandWarfare)[M].Santa Barbara:ABC-CLIO,2007.
[12]Ralph of Caen.The Gesta Tancredi of Ralph of Caen:a history of the Normans on the First Crusade[M].Aldershot:Ashgate,2005.
[13]AnnHyland.The Medieval Warhorse from Byzantium to the Crusades[M].Conshohocken:CombinedPublishing,1996.
[14]JimBradbury.The Medieval Archer[M].Woodbridge:BoydellPress,1985.
On the Army of the First Crus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ristian World——See through the Battle of Antioch
WANG Xiang-peng,XU Jia-l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The battle of Antioch is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the First Crusade.This battle is recorded in detail by Christian authors whose accounts reflect the size,the structure,the weapons,and the military ideas of the army of the First Crusade.The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of this army show the structure and order of Western European society in middle ages.The military ideas project the developmental trend and direction of the feudal military of Christendom in 11th century.
Crusade;Antioch;army;Christendom
K561.3
A
1001-6201(2011)05-0074-05
2011-03-20
王向鵬(1983-),男,河北石家莊人,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徐家玲(1949-),女,吉林長春人,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
[責任編輯:趙 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