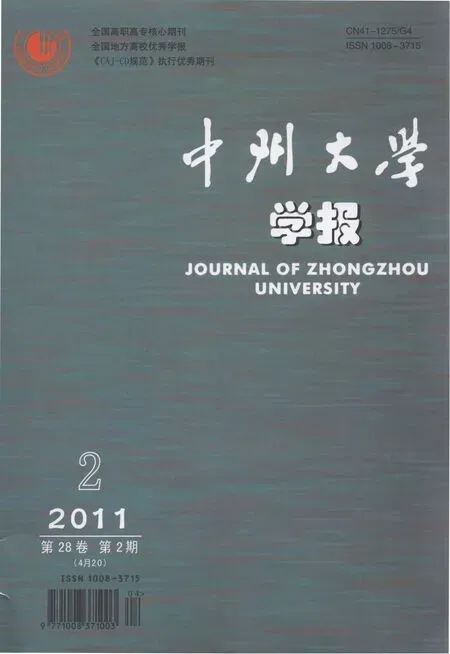欲望敘事·偽欲望敘事·敘事倫理——從電視劇《蝸居》說起
伍茂國
(河南大學(xué)文藝學(xué)研究中心,河南開封475000)
作為一部社會劇,《蝸居》在2009年的熱播和熱議應(yīng)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為電視劇所講述的故事幾乎囊括了當(dāng)下中國社會最為敏感的話題:房子、小三、腐敗等等。受眾輕輕松松就能找到情感或情緒共鳴的因素。但稍微細(xì)心一點,看似散點透視的題材之下涌動著的仍舊是焦點透視的格局,即聚焦于同一個問題的兩面,那就是“房事”:高房價之下買不起房子的房事以及初涉世事的女大學(xué)生與人情練達的貪官之間的那一點“房事”。一般大眾的興奮點集中在前一個房事:一日三變的房價讓小老百姓們委實憋著一口怨氣、怒氣、窩心氣,一旦從公共媒介中看見自己的典型生活,那種反觀自身的命運所得到的強烈刺激,是其他雖然轟轟烈烈的歷史題材電視劇或好萊塢大片般的連續(xù)劇所無法企及的,這一點與20世紀(jì)80年代曾經(jīng)萬人空巷的《渴望》異曲同工。而第二個“房事”以曖昧的敘事調(diào)子挑逗著所謂80后哥哥妹妹們那潮起潮落的代際幽怨,引發(fā)無數(shù)控訴或同情。正因如此,《蝸居》被許多普通受眾,也被不少職業(yè)評論家稱為近年來難得的針砭現(xiàn)實的電視劇代表作,是“刺進現(xiàn)實的一根刺”,[1]標(biāo)志著“現(xiàn)實主義的復(fù)興”。[2]但也有些評論家不以為然,甚至視之為故意暴露社會陰暗面,有礙和諧社會建設(shè)大局。更有意味的是,北京電視臺還迫于房地產(chǎn)商的壓力而停播了該劇。其實,無論那種觀點都是《蝸居》操作成功的體現(xiàn)。電視劇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日常消遣藝術(shù),而在消遣之外能激起一點點有意義的討論來,那當(dāng)然是電視本身所孕育的社會意義的佐證。確實,從《蝸居》之中,我們看到了高房價和腐敗所帶來的巨大的社會危機,尤其是其中的倫理危機。房子不僅讓海萍夫婦失去了本來的純潔,也使渴望人生美好遠(yuǎn)景的海藻陷入傳統(tǒng)語境無法接受的人倫大忌。但在筆者看來,這種“正確的審題”無法透視《蝸居》真正可怕的危機:那就是欲望敘事的能指狂歡與對偽欲望的倫理首肯,這才是當(dāng)代電視敘事倫理的“紅色警戒”。
一、現(xiàn)實講述及其背后的欲望
《蝸居》極盡能事敘述現(xiàn)實并且呈現(xiàn)其背后的欲望。《蝸居》有兩條敘事線索。一條是姐姐海萍。海萍與蘇淳夫婦畢業(yè)于江城的名牌大學(xué),卻蝸居在10平方米的石庫門房子。攢夠首付,變身房奴是他們最大的夢想;另一條是妹妹海藻。海藻和男友小貝與人合租一套三居室。他們也是只等攢夠首付就談婚論嫁。這兩條線索緊扣“房事”現(xiàn)實,并且經(jīng)由敘事把這一現(xiàn)實所生發(fā)的空前焦慮展示得淋漓盡致。正是基于這種焦慮,才勾連起另一個令人側(cè)目的現(xiàn)實主題:官場腐敗。具體到電視敘事中則是宋思明與海藻的情欲糾葛,這構(gòu)成“房事”的另一層含義。
盡管敘事框架在一定的程度上能讓成熟的(或職業(yè)的)受眾自覺到電視劇的虛構(gòu)性質(zhì),因而可以避免直接的現(xiàn)實對比。但同樣無法回避的是,由于《蝸居》題材選擇有意對時代敏感話題強烈觸電,尤其是抓住了相當(dāng)多的“真實細(xì)節(jié)”,因而仿佛構(gòu)成了對當(dāng)下現(xiàn)實的復(fù)敘事,這就造成絕大多數(shù)的受眾無法區(qū)分虛構(gòu)世界的復(fù)敘事與現(xiàn)實理性世界的原生敘事,所以面對虛構(gòu)世界中底層人們的“艱難世事”和貪官與奸商狼狽為奸的種種鏡像時,《蝸居》的虛構(gòu)元素自行瓦解,并且暴曬在現(xiàn)實的廣場上,原本深藏不露的“人類的欲望邏輯與喬裝打扮的社會邏輯”[3]直接撞擊觀眾的眼球,這種撞擊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致不費吹灰之力就激起了觀眾對于電視敘事邏輯所生成欲望的敏感反應(yīng):物欲、情欲和支配欲。
《蝸居》為房子而活著的海萍們(白領(lǐng)),其人生理想無非就是打拼、賺錢、住別墅、成為人上人,而伴隨著房價的一步步高漲,欲望也如暴雨般傾瀉而下。從整個電視敘事看,與其說,海萍們是為了滿足“居者有其所”的基本欲望,毋寧說,房子無形中已經(jīng)成為對金錢、對物質(zhì)瘋狂追逐的表征。在當(dāng)代中國的現(xiàn)實土壤里,受眾清晰地看到了批判現(xiàn)實主義經(jīng)典作家巴爾扎克所描述的19世紀(jì)巴黎物欲橫流的景觀復(fù)制:金錢成為人們的上帝,“……運轉(zhuǎn)社會的樞紐是金錢,或勿寧說是缺乏金錢,渴望金錢。”[4]看看被“房事”左右著的海萍們,那曾經(jīng)神圣而純潔的愛情變成了什么:“男人若真愛一個女人,別盡玩兒虛的,你愛這個女人,第一個要給的,既不是你的心,也不是你的肉體,一是拍上一摞票子,讓女人不必?fù)?dān)心未來;二是奉上一幢房子,至少在擁有不了男人的時候,心失落了,身體還有著落。”而宋思明一句似乎玩深沉的話:“通往精神的路很多,物質(zhì)是其中的一種”,則一覽無余地告訴人們,就連精神也從價值蛻變?yōu)槌恋榈榈氖褂脙r值,可以說物欲已經(jīng)無孔不入。
情欲是《蝸居》著力渲染的另一欲望。原本以“房奴”和“反腐”等現(xiàn)實話題為切入點的電視劇,在開篇不久就嚴(yán)重跑偏,重心變?yōu)楹T鍨檫_目的甘心做二奶的故事。其中,巫山云雨的鏡頭和諸如“我是來×你的”之類的“色情”臺詞層見疊出,讓整個敘事浸潤在情欲中不可超拔。所以在許多受眾眼里,所謂“蝸居”,實為“蝸在居室里”干的“那點事兒”。
與物欲及情欲糾纏不清的則是第三種欲望:支配欲。支配既表現(xiàn)為對物的支配,也表現(xiàn)對情的支配。《蝸居》中所有為房子而活著的人們說到底無非想在大都市江城擁有、支配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從常理說,這一要求并不過分,但當(dāng)擁有房子的欲望變身為“據(jù)為己有”的偏執(zhí)心理時,作為物的房子實際上已經(jīng)失去了居住功能,而抽象為空洞的“支配”對象。電視劇放肆渲染的宋思明與海藻的所謂“情欲”,也不過是居于強勢地位的宋實現(xiàn)、滿足自己對于作為“他者”的海藻的占有、支配欲望。因此,無論物欲、情欲抑或支配欲根本上是一體的,都是變革時代釋放的欲望總體的變形金剛。所以,《蝸居》已從表面的現(xiàn)實主義轉(zhuǎn)換為充滿吊詭的欲望敘事。
二、從欲望敘事到偽欲望敘事
欲望是什么?迄今人言人殊。但五花八門的看法中,認(rèn)為欲望是匱乏的滿足則是最大眾化同時也是最古老的觀點(有據(jù)可查的歷史在西方最遠(yuǎn)可以上溯到柏拉圖)。以這種觀點看來,欲望是一種主體匱乏和被動存在的實體,一旦匱乏填滿,欲望便得以滿足。從哲學(xué)探究看,這一普泛性的欲望觀在黑格爾手里得以認(rèn)真思考。黑格爾認(rèn)為對立著的自我意識和生命都是欲望,只不過前者是差別性統(tǒng)一,而后者則是統(tǒng)一本身。“當(dāng)下欲望的對象即是生命”而“生命乃是自身發(fā)展著的、消解其發(fā)展過程的、并且在這種運動中簡單地保持著自身的整體。”同樣“自我意識就是欲望”,[5]“但是在自我意識的這種滿足里,它經(jīng)驗到它的對象的獨立性。欲望和由欲望的滿足而達到的自己本身的確信是以對象的存在為條件的,因為對自己確信是通過揚棄對方才達到的;為了揚棄對方,必須有對方存在。”“自我意識只有在一個別的自我意識里才獲得它的滿足。”[5]顯然,黑格爾已經(jīng)悄悄地切除了欲望的實體性尾巴,指認(rèn)了欲望的他者化。
拉康正是在黑格爾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欲望空無說。他把欲望(desire)與需要(need)和需求(demand)加以區(qū)分。需要即我們通常理解的匱乏,屬于具體的、可滿足的生物性欲求。而要求表征著“從具象的需要到非具象的欲望的一個中間環(huán)節(jié)。”[6]即離開了原初的需要的想象化,是一種整體的文化欲求。如果說,需要自然性地表征人與物的關(guān)系,指向?qū)ο螅敲匆蟆熬褪怯谜Z言這個騙人的東西表達出來的需要。”[6]它不再直接指向?qū)ο螅瑥亩蔀橐环N主體間關(guān)系,主體間即意味著他者,而象征性語言構(gòu)成文化的大寫他者。欲望在整體的要求和個體需要的縫隙中成長,換言之,欲望總是尋求需要和要求無法達成的整體性。但欲望的這種努力在拉康看來也是勞而無功,無法臻至最后滿足,因為在他的哲學(xué)語境中,從弗洛伊德主義出發(fā)的、作為人的本真性存在依據(jù)的欲望(愿望)不再具有合法性,人的欲望總是虛假的,真實的需要和要求經(jīng)過層層異化,欲望變?yōu)橐环N無意識的“偽我要”。按照拉康的觀點,“個人主體的欲望從鏡像異化以后不再是主體本己的東西,特別是在進入象征域之后,在能指鏈的座架之下,我的欲望永遠(yuǎn)是他者的欲望之欲望。”[6]歸根結(jié)底,欲望總是虛假和變動不居的。
從拉康對欲望的別具一格的哲學(xué)分析可以看出,電視劇《蝸居》欲望敘事正試圖把現(xiàn)實的需要經(jīng)由要求轉(zhuǎn)化為非具象的欲望,欲望成為欲望的能指鏈,從而追索人類欲望空無化的本體境界。
《蝸居》通過敘事表征欲望空無最明顯但又不太好理解的當(dāng)然是海萍們的“房事”,也就是對房子的需要。按照一般社會看法,在中國這樣安土重遷的文化語境中,擁有自己的房子幾乎是所有老百姓最大的需要,而這種需要經(jīng)過媒體的不斷放大,驟然凸顯,并衍化為當(dāng)代政治、經(jīng)濟、文化和倫理的焦點。所以,否認(rèn)海萍們的“房事”欲望的真實性,視之為空無,顯然是故意的“找抽”行為。但是,只要我們真正反省敘事背后的欲望邏輯,這種看似鐵板釘釘?shù)恼鎸嵭赃€是會露出可疑的尾巴。
海萍對房子需要的迫切性來自孩子。有一天女兒冉冉(六六的同名小說中是一個男孩,叫歡歡)從海萍的錢包中偷取硬幣到門外騎電動馬,當(dāng)問及孩子如何處罰時,冉冉歪頭想了想,回答說:“媽媽抱抱吧!”此時海萍愣住了,呆住了,怔住了,心如刀絞。海萍要處罰她,她選擇抱抱。孩子已經(jīng)懂事了。他知道誰是她的親人,她只跟那些與她日夜在一起生活的人交流情感。而媽媽,什么是媽媽?媽媽就是電話那頭的“喂”,媽媽就是每年來兩個星期的女人,媽媽就是一個象征,一個符號。“我為什么要一個孩子?我要她,難道就為了有一天,她想起我的時候,甚至想不起來模樣嗎?難道就為了有一天給她一套房子嗎?難道就為了別離嗎?”這樣拷問過后,海萍驀地決定:“回去就買房子!馬上買!我要和我的孩子生活在一起!”所以,這種欲望有著真真切切的現(xiàn)實基礎(chǔ)。難怪一提起《蝸居》,人們首先想到的是房子的事,而且一致認(rèn)為電視劇一針見血地觸痛了扭曲變形的房市的神經(jīng)。但海萍對房子的欲望沒有那么真實和簡單。房子遠(yuǎn)不是隔離海萍與孩子的罪魁禍?zhǔn)住K吞K淳完全可以租住一間大房子以解決暫時困難,為什么一定要買了房子才能擔(dān)負(fù)一個媽媽的責(zé)任呢?所以我在想,電視敘事雖然為海萍找到了一個似乎很符合觀眾心理的理由——母愛,但母愛對于房子只是微不足道的由頭,因為房子的壓力是自己找的。正如海萍和蘇淳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意識到的,他們可以回到家鄉(xiāng),回到有房子的地方。但海萍覺得自己家鄉(xiāng)太小,什么都沒有,沒有高高的電視塔,沒有麥當(dāng)勞,沒有伊勢丹,什么都沒有。所以關(guān)鍵的不在房子,關(guān)鍵在房子所表征的現(xiàn)代性欲望,即城市這個“近似于語言的一項最可寶貴的集體發(fā)明”,[7]在現(xiàn)代性視域中,像語言一樣成為以“磁體-容器”為隱喻的大寫他者。城市“先具備磁體功能,爾后才具備容器功能:這些地點能把一些非居住者吸引到這來進行情感交流和尋求精神刺激……是城市固有活力的一個證據(jù),這同鄉(xiāng)村那種較為固定的、內(nèi)向的和敵視外來者的村莊形式完全相反。”[7]城市不僅像容器一樣裝載海萍們這樣的人群和她們所需要的器物,而且更重要的是像磁體一樣充盈著海萍們欲望著的欲望。基于這樣的分析,筆者認(rèn)為,當(dāng)看新房的時候,海萍的手機里出現(xiàn)“江蘇移動歡迎您”的短信,姐妹倆所發(fā)出的無奈的笑,因此具有了盡管虛假然而逼真的形而上意義:一種對于欲望空無的無奈。
《蝸居》欲望空無的另一吊詭的敘事可以用一個問題提出,即宋思明何以要以海藻為欲望對象。對此電視劇中有幾處交代。原因一,作為官場潛規(guī)則,沒有小三會被看作另類,無法融入官場。對于深諳官場三昧的宋思明來說,這無疑是其與海藻生發(fā)“房事”的重要動機。然而從另一角度看,這一動機并非充分理由,它最多只能說明宋思明的欲望對象的不確定性,他可以選擇海藻,也可以選擇其他女孩,何況海藻還是那么普通的一個女孩呢?因此第二個原因應(yīng)運而生。宋思明第一次占有海藻之后,發(fā)現(xiàn)海藻還是處女,按照世俗理解(也可以稱為人類學(xué)依據(jù)吧),宋思明的處女情結(jié)使得海藻成為他的欲望對象。但電視敘事在接下去不遠(yuǎn)的地方卻含蓄地點破那一點點讓宋思明心旌神搖的處女之血不過是海藻月經(jīng)提前的結(jié)果。所以,這第二個原因?qū)嶋H上敘事用十分世故的噱頭把欲望對象的本質(zhì)懸擱了。但電視劇又不經(jīng)意地交代了第三個似乎更有力的理由:海藻酷似宋思明大學(xué)時代的夢中情人白逸純(六六的同名小說中叫程惠)。這個理由很容易迷惑人,電視劇的一處旁白也似乎刻意強調(diào)這一看似美好實則媚俗的理由:
宋思明心里充溢著一種熟悉的,曾經(jīng)有過的沖動,像毛頭小伙兒一樣熱血沸騰。這些日子,從見到海藻的第一天起,他的眼前總是那個普通的小姑娘。她是那么的普通,談不上姿色,清湯掛面的頭發(fā),不施粉黛。可不知道為什么,是哪里,是哪一種神態(tài),竟如此打動宋思明的心。也許就是那種無時無刻,都可以鉆進自己的童話世界夢游的神情,還有那簡單像句號一樣的眼睛,宋思明可以看見那雙善良的明眸后,有一天會有晶瑩剔透、溫潤濕熱的淚水流出,只為他流。
然而這真是宋思明欲望著海藻的原因嗎?或者說,由此可以確認(rèn)海藻真的成為宋思明的實質(zhì)的欲望對象嗎?答案是否定的。我們繼續(xù)分析。
宋思明出身農(nóng)家,靠著弟弟讓出來的讀書機會考上了大學(xué),與父親為大學(xué)教授且聰明漂亮的白逸純相比,顯然名不當(dāng)戶不對,所以應(yīng)當(dāng)可以假設(shè)即便宋喜歡白逸純也不敢表白,最多只能使其成為夢中情人。敘事過程中,白逸純雖然作為實體的欲望不在場,但卻永遠(yuǎn)成了宋思明的欲望著的欲望。電視劇有一個情節(jié)安排,我以為很詭秘,那就是讓白逸純紅顏薄命,這一安排隱喻著宋思明對白逸純的欲望的空無性,同時也無意識地斷絕了宋思明在具備了支配欲望能力之后對白的欲望實現(xiàn)。這進一步提示我們,根本上宋思明對海藻的占有、支配并非愛情使然,而是對不能實現(xiàn)的欲望替換。有人可能會說,宋思明對海藻懷著的孩子不是充滿著關(guān)心、愛護嗎?難道這還不是愛情的體現(xiàn)嗎?然而事實表明,這不過是編劇和導(dǎo)演明著誤導(dǎo)或忽悠觀眾,在潛意識里海藻的孩子也是欲望的替換,這種替換就像海藻對白逸純的替換一樣永遠(yuǎn)不可能成功,孩子最終流產(chǎn)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本來,如果沿著這樣的欲望敘事邏輯,《蝸居》在敘事藝術(shù)上可以突破一般社會劇的局限,臻至更加深刻的藝術(shù)境界。但令人遺憾的是,拉康意義上欲望空無的本體化并未真正成為敘事者的價值偏愛,正如分析所揭示的,它最多只是顯現(xiàn)了欲望敘事的某些癥候,敘事者真正專注的仍然是客體小a的欲望剩余——筆者稱之為“偽欲望”。
客體小a是拉康欲望理論極為重要的一個概念,即小寫的他者,指主體的對象。如果說大寫他者A是象征性語言,那么小寫他者a則是非言語的,是一種不能稱為欲望的零碎的東西。欲望沒有這種東西不行,因為客體小a是主體欲望走向本體的過渡。沒有小a欲望無從談起,但反過來,欲望的最終結(jié)果要以拋棄小a為代價。“這個時刻是主體意識完全覺醒的時刻,也是主體以死亡為代價建構(gòu)自身的時刻。”[8]然而《蝸居》偽欲望敘事展示的卻沒有到達主體意識覺醒時刻,也沒有主體悲劇性的死亡意識,反而沉醉于客體小a位置的欲望剩余之中不可自拔。
這種偽欲望敘事在某種程度上像花邊新聞或社會新聞一樣固然能夠迅速吸引受眾的眼球,獲得較高的收視率,但危機也隨之而來。著名藝術(shù)評論家賈磊磊教授從社會批評的角度斷言這樣的偽欲望敘事“吸毒式的快感麻痹了人的進取精神”,“動搖了公民對社會公平與正義的理想信念”,“摧毀了人們奮斗進取的精神支柱”,是“電視劇誤導(dǎo)觀眾的致命毒藥”。[9]但在我看來,更為嚴(yán)重的還在于《蝸居》將敘事倫理追求的現(xiàn)代性語境的欲望敘事閹割為基于妻子玉帛滿足的偽欲望敘事,也就是將本體降格為實體,將欲望降低為客體小a,降低為零碎欲望。這實際上暴露了當(dāng)下審美文化的敘事倫理六神無主,而其表征的現(xiàn)實人心秩序或精神生態(tài)也是亂象叢生,亟待療救。
三、結(jié)語
按照馬克思的基本看法,欲望并非洪水猛獸,“人作為對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個受動的存在物;因為它感到自已是受動的,所以是一個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熱情是人強烈追求自己的對象的本質(zhì)力量。”[10](這里的“激情、熱情”有的直接譯為“情欲”)也就是說,欲望本身也是人的本質(zhì)力量的確證,不過,“吃、喝、性行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機能。但是,如果使這些機能脫離了人的其他活動,并使它們成為最后和唯一的終極目的,那么,在這種抽象中,它們就是動物的機能。”[10]當(dāng)代許多打著欲望敘事旗幟的敘事文本,其中的欲望正是脫離了人的其他活動的欲望,因而從欲望敘事變成了偽欲望敘事。而這種偽欲望敘事迄今為止不僅未能得到有效反思,反而遍地開花,蔚為壯觀。我們的敘事藝術(shù)正遭遇著空前的敘事倫理危機。
雖然敘事倫理是一種虛構(gòu)倫理,與現(xiàn)實理性倫理不可同日而語,但是,經(jīng)由敘述者的價值偏愛而構(gòu)建的虛構(gòu)倫理會在與受眾的互動中對現(xiàn)實倫理產(chǎn)生不可回避的影響。盧卡契論及歌德奠定了把藝術(shù)陶冶功能推廣為一般藝術(shù)的哲學(xué)基礎(chǔ)時,曾很恰當(dāng)?shù)亟忉屨f:“如果人與自然對象及其組合的視覺關(guān)系是一種道德關(guān)系——我們重新考慮我們對社會與自然界物質(zhì)交換的反映的有關(guān)論述——那么在它的藝術(shù)映象所喚起的效果中,會產(chǎn)生具有道德特征的震撼作用。”[11]確實,“故事之蛇可以吞掉自己的尾巴,但對故事的模仿并未就此終止。”[12]由于敘事引導(dǎo),受眾對以《蝸居》為代表的虛構(gòu)世界欲望人物的倫理同情正以無法逆料的方式和速度泛濫開來,為當(dāng)下本已“賤賤”(《蝸居》有一句經(jīng)典臺詞:“我賤賤地賤賤地愛上你”)的現(xiàn)實欲望更加雞零狗碎化提供了不應(yīng)有的美學(xué)支持。
[1]肖復(fù)興.《蝸居》是指向現(xiàn)實問題的一根刺[J].學(xué)習(xí)時報,2009-12-07(9).
[2]張宏.從《蝸居》看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的當(dāng)代意義[J].經(jīng)濟管理文摘,2009(24).
[3]李勇.電視敘事的特征[J].當(dāng)代電視,2003(12).
[4][丹麥]勃蘭兌斯.19世紀(jì)文學(xué)主流:第五分冊[M].李宗杰,譯.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203.
[5][德]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上卷[M].賀麟,王玖興,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79:120-121.
[6]張一兵.偽“我要”:他者欲望的欲望:拉康哲學(xué)解讀[J].學(xué)習(xí)與探索,2005(3).
[7][美]劉易斯·芒福德.城市發(fā)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M].倪文彥,宋俊嶺,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1989:41-46.
[8]劉玲.拉康欲望理論闡釋[J].學(xué)術(shù)論壇,2008(5).
[9]賈磊磊.問題作品的消極快感與當(dāng)代中國現(xiàn)實社會的心理裂變[J].藝術(shù)百家,2010(2).
[10][德]馬克思.1844年經(jīng)濟學(xué)哲學(xué)手稿[M].劉丕坤,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6-51.
[11][匈]喬治·盧卡契.審美特性:第二卷[M].徐恒醇,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1:287.
[12][愛爾蘭]理查德·卡尼.故事離真實有多遠(yuǎn)[M].王廣州,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7: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