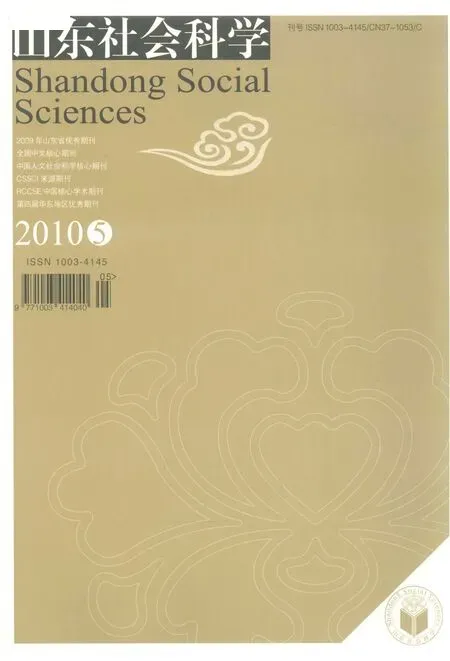新版《魯迅全集》注釋的一點(diǎn)瑕疵
亓鳳珍
新版《魯迅全集》注釋的一點(diǎn)瑕疵
亓鳳珍
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 2005年版《魯迅全集》第三卷《華蓋集》的《青年必讀書》一文后,有如下注釋:“1925年 1月間,《京報(bào)副刊》刊出啟示,征求‘青年愛讀書’和‘青年必讀書’各十部的書目。本文是作者應(yīng)約對(duì)后一項(xiàng)所作的答復(fù)。文章發(fā)表后,曾引起一些人的詰責(zé)和攻擊。后來作者又寫了《聊答“……”》、《報(bào)〈奇哉所謂〉……》等文(收入《集外集拾遺》),可參看。作者在 1933年寫的《答兼士》(收入《準(zhǔn)風(fēng)月談》)中談及本文的寫作背景及主旨,亦可參看。”
問題出在注釋的最后一句,乍一看,好像《答兼士》是專門寫給沈兼士的一篇文章。但翻閱《魯迅全集》第五卷的《準(zhǔn)風(fēng)月談》,并沒有什么《答兼士》,倒是有一篇《答“兼示”》,署名豐之余。在《答“兼示”》中,魯迅先生回顧了寫作《青年必讀書》的背景,說那時(shí)候,“正是許多人大叫要作白話文,也非讀古書不可之際,所以那幾句是針對(duì)他們而發(fā)的,猶言即使恰如他們所說,也不過不能作文,而去讀古書,卻比不能作文之害還大。”顯然,他在《青年必讀書》書中所說的“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guó)書,多看外國(guó)書”,主要是對(duì)“非讀古書不可”的觀點(diǎn)所發(fā)的。“非讀”二字還告訴我們,他為什么只答復(fù)“青年必讀書”而不答復(fù)“青年愛讀書”,因?yàn)椤皭圩x”是個(gè)人的興趣、愛好,而不是“必讀”,不是“非讀不可”。
這篇文章之所以題名《答“兼示”》,是因?yàn)樗怯脕砘伛g施蟄存的《致黎烈文先生書——兼示豐之余先生》的。其中“兼示”意思很明確,就是如魯迅先生在《答“兼示”》一文開首所說:“前幾天寫了一篇《撲空》之后,對(duì)于什么‘《莊子》與《文選》’之類,本也不想再說了。
- 山東社會(huì)科學(xué)的其它文章
- 基于價(jià)值網(wǎng)的汽車制造業(yè)供應(yīng)鏈協(xié)同管理研究*
- 農(nóng)民工養(yǎng)老保險(xiǎn)收支與我國(guó)養(yǎng)老金缺口精算分析*
- 不對(duì)稱的平衡性:聯(lián)姻宗族之間的階序性關(guān)系*
——以華北鄉(xiāng)村為例 - 梁漱溟鄉(xiāng)村建設(shè)運(yùn)動(dòng)對(duì)社會(huì)主義新農(nóng)村建設(shè)的幾點(diǎn)啟示*
- 省級(jí)社會(huì)養(yǎng)老保險(xiǎn)基金風(fēng)險(xiǎn)管理機(jī)制研究*
——以山東省為例 - 基于地理集中度的中國(guó)版權(quán)貿(mào)易不均衡分析*